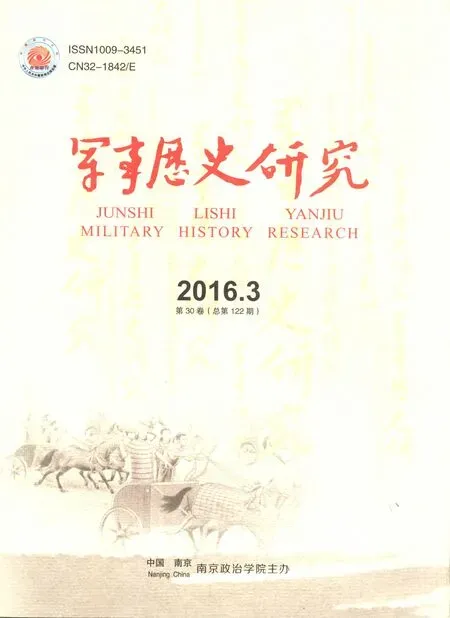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的若干结构性因素
2016-10-14田玄
田 玄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热点研讨: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理论思考与史实追索·
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的若干结构性因素
田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共党史军史上一个最为危难而又最为辉煌的阶段和节点。中共中央和红军能够转危为安,并胜利到达陕北,其原因十分复杂。但马列主义政党强意识形态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红军官兵的坚定信仰、中共及红军严密的组织形态、创新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略、高度灵活的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是中共及红军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结构性因素。长征制胜之道是中共及红军极为珍贵的政治历史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代,对于已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建设,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结构性因素
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制胜之道是海内外史学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形成丰富成果。然而,对于中共特有的强意识形态政党*20世纪世界政党形态一般分为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政见认同形态等。在苏俄革命主义强意识形态影响下,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起就是一个强意识形态的革命政党。而中国国民党就总体而言,只能是一个政见认同形态的政党,其结构性差异表现在政治动员及其整合能力的巨大反差上。及其严密的组织形态、统一战线政略和新型战略战术等内在结构性因素*现代政治科学认为,结构是事物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稳定的组织形式。结构与事物不可分割。一定的结构,可以使组成事物的各个要素发挥它们单独不能发挥的作用;不同的结构,可以使相同的要素形成不同的事物。西方当代政治学者对于共产党强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结构特质及其动员和整合能力,与非意识形态政党和组织形态结构特质及其动员和整合能力间的极大差异取肯定态度。其代表人物有Samuel P.Huntington,Samuel Edward Finer,Morris Janowitz,Eric A.Nordlinger,William R.Thompson等。历史虚无主义则往往否认不同事物或系统的结构性差异,不注重不同的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政治和意识结构对于人类历史的不同的影响力因素,因而对于事物发展的真实因果联系采行回避和否定态度。的研究仍显不足,有些研究对于中共在革命年代锻造的特有的结构性优势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混淆了动员型强意识形态革命政党及其军队与一般政见认同型政党及其军队的根本区别。本文认为,长征胜利在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特有的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联系紧密,互相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产生奇迹般合力 。
一、强意识形态的结构性优势:中共和红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坚定的信仰并在长征中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政策
(一)加强思想理论的内化,不断升华红军对于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忠诚,长征中中共和红军在意识形态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政治过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共作为强意识形态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导,不仅有助于政治体系结构的稳定,而且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过程中,不断向军队官兵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单纯军事观点、军阀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强调红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最新式的军队”,要“使每个红色战士成为苏维埃政治的与革命的公民”,“成为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前锋军、完成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使之以“牺牲自己以确保党的生存、成功和胜利”*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教育与管理》大纲(1932年1月),中央军委档案馆藏。为己任,使官兵形成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信仰与价值遵从,成为中共及红军生存发展、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的结构性因素。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转移后因国民党军重兵“追剿”不能尽快落脚而走向长征,加之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西移,使得留在长江以南的红2、红6军团难以承受强大的敌情压力而于1935年11月实行战略转移。红军的战略转移遂由局部转移发展为红军主力分别长征,土地革命战争遂由“围剿”和反“围剿”,变成“追剿”和反“追剿”。红军失去苏区战略基地的支撑,要克服万水千山的艰难险阻和上百万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各地方军的围堵。红军长征行程之长,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长驱数万里,其路途之险,困难之巨,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穿越了五岭、乌蒙山、横断山、秦岭、六盘山等高山约40座,征服了湘江、乌江、沅江、资水、金沙江、大渡河等江河近百条,通过了人类难以生存的雪山、草地,攻克了娄山关、剑门关、腊子口等险关要隘。长征中,红军经历的战役、战斗共600余次,虽损失了约18万人之多,*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辑室):《关于一九三三年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的专题报告》(1985年2月14日);该数据系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人员依据档案等历史资料研判而得出的。但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各主力红军的骨干得以保存,实现了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红军由分散在南方各自为战到集中于西北大本营的战略性转移。这一奇迹,只有具有强意识形态结构性优势的中共和红军才能创造。
长征中,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鼓舞着红军将士赴汤蹈火。“事到万难须放胆”“狭路相逢勇者胜”,17勇士率先强渡大渡河,成为红军官兵的精神符号。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喋血娄山关;红25军政委吴焕先血洒四坡村;红34师师长陈树湘于湘江战役负伤后掏腹断肠。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说,长征中“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等4位师长壮烈牺牲,倒下去的红军战士更是成千上万”。*《张震回忆录》(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82页。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长征战斗中腿部负伤,他以“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的决心拖着伤腿随军长征。*《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8页。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中左眼中弹,4天4夜昏迷不醒,苏醒后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指挥部队;开国少将、红四方面军师政治委员李中权一家9人投奔红军,长征中牺牲5人,到达陕北的只有李中权及弟妹4人。*《李中权征程记》,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74—75、89页。红四方面军团政委余秋里为掩护团长负重伤,由于缺乏医药,他带着伤臂在192个日夜中走过了万里路程,直至6个月后锯掉伤臂才保住了性命。*《余秋里回忆录》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41页。1936年6月开办的抗日红军大学,受训的红军师、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每人身上3处伤疤。*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5页。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讲得最多的话语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正是这种坚强的政治信念,将红军官兵聚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而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和军队无法想象的。
现代政治学在讨论马列主义革命军队“以党领军”机制时,仅仅把“以党领军”看作是以党的组织控制军队的形式,其实“以党领军”的关键在于以政党的意识形态贯注于军队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列主义革命军队具有其他军队所无法形成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信念,具有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意识及精神力量。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想寻找红军长征胜利之道,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认为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徐特立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对长征作了最具权威性的注释,他说:在长征中“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夏宏根:《中共党史珍闻》,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413页。
(二)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对于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列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它在中国具体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军事战略战术。俄国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列宁主义,传来了苏联红军建军的先进经验。然而,苏联国家形态、社会形态与中国全然不同,中国社会和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红军的建设与战争的开展有着自己的形式和规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王明等“左”倾错误领导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因而在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上推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政策和策略,并对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等人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处理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的联合行动与各国共产党在本国的革命斗争关系上又出现指导上的原则错误。*中共自1922年7月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57个支部中的一个支部,1934年7月为65个支部之一。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2页。因而长征前的中共中央政治上尚未走向成熟,仅孕育着走向成熟的因素。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其基本标志就是能够奉行一条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指导革命的科学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军事战略战术。长征前中共已涌现出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及中共一些领导者通过对中国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农村环境下建党、建军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又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总结出了一套红军特有的战略战术原则等等,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具有这一正确认识的领导者的存在,是中共走向思想上理论上成熟的基础。
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一系列失败后,在比较中党和红军认识了毛泽东,其正确思想路线成为人心所向,血的代价也使“国际路线”失去了灵光,能否以正确理论和策略引导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成为中共及红军判断主义与思想是否正确的标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完全展示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最终动摇了李德的“太上皇”地位,遵义会议上中共自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和红军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对红军长征胜利和中共进一步走向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创新性政治战略的结构性优势:中共及红军在长征中能够高擎统一战线的旗帜化敌为友,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断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及联合一切抗日力量
(一)推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一些地方军建立政治联盟
中共成立后不久即提出了以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敌人的思想,这也是马列主义革命政党有别于其他形态政党的显著特征。也正是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战略的科学运作,使得中共及红军在长征中凸显了其强大的引航力和感召力。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后,又宣布在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3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4年红7军团和红25军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移前后,中共中央郑重表示只要国民党接受中共所提出的3个条件,红军主力“即可以在先遣队之后”,“同全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中共中央要求红军及基层组织“大胆的与各种反动派别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与一切狭隘的爱国主义团体结成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秘密通知(不列号)——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1934年7月2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第377页。但由于蒋介石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内战政策,对红军接连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战争,使红军不得不殊死进行反“围剿”作战。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毛泽东察觉粵军陈济棠在“剿共”中不甚积极的态度,反对中革军委重创粤军的计划,于1934年6月22日发出《关于粤赣地区作战及七军团在瑞金待机问题给恩来电》,建议不去主动刺激粵军。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互相借道、粵军后撤40华里让红军通过。*何长工:《难忘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7页。红军与粵军谈判成功,对于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方向以及顺利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起了重要作用。长征前期,中共和红军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略,和一些地方实力派达成谅解、协议。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境内之前,曾向湘军部队发出了“自动派代表到红军中来,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的口信。*解放军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红军进入湖南、贵州,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向湘、黔两军及地主武装提出了 “共同停战”等口号。在云贵川地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开始突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所规定的统战仅限于敌下层的戒律,而把联络和争取敌中上层人物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1935年1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向部队下发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对开展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提出要求。同年3月下旬,中央红军对扼守北盘江的黔军将领犹国材部进行统战工作,结果犹部让出渡口和通道。红军进入四川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以故交旧友的名义先后给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徐剑霜、川康边防军第20旅旅长邓秀廷写信,劝其勿与红军为敌。6月上旬,红军总司令朱德与集结在雅安、荥经一带堵截红军的川军主要将领杨森所部达成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使中央红军顺利长征。
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后,中共和红军更加积极地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5年12月25日,朱德发出致川军各将领的公开信,呼吁“川军与红军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也曾于1936年1月下旬致信川军领袖刘湘等人,建议达成互不侵犯的合作协议。此后,朱德、刘伯承还争取川军第29军军长孙震对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康地区的计划采取拖延和消极应付态度。红2、红6军团长征停留贵州黔西、毕节地区时,通过白区邮局发给各方知名人士和西南各省军队高级将领大量信件,使“川黔边的各派反蒋力量,纷纷与我军接洽”。*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1936年2月,红2、红6军团争取了曾在北洋政府时担任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周素园,由他致函滇军领袖龙云以及将领孙渡。*《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萧克也致函龙云和孙渡,建议滇军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龙云和孙渡接受了红军的建议,在咸宁、昭通间按兵不动,为红2、红6军团的长征提供了方便。
中共及红军在长征中的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政略,争取了不少地方军事政治势力的支持,为红军长征提供了便利。
(二)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共二大至六大决议以及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遵循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原则,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中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一部分;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建立自治区域;注意落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与文化提高;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保障各民族的工农劳苦民众的信教自由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年)》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55页。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民族政策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成熟的产物。长征中,红军经过湘、桂、黔、滇、川、康、甘、宁等省区的苗、瑶、壮、侗、水、布依、土家、仡佬、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据统计,中央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为时1年的长征中,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所用的时间占总时间的1/3左右;红2方面军从湘西到陕北行程9000余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程为2800余公里,亦占总行程的1/3左右;红4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而其中有15个月的时间都转战在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郑汕等:《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长征期间的应用与发展》,《英雄史诗丰碑永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汉族和少数民族严重隔阂,加之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当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少数民族民众或者举家逃避,或者高度戒备,对立情绪严重,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还组织武装对红军进行袭击,能否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事关长征胜败的政略问题。
中共中央及红军在长征中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一是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基本原则,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1935年12月,毛泽东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宣告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二是少数民族拥有自决权。红军长征中提出“番人治番”“回人治回”“苗、瑶有民族自决权”等口号。三是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作为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目标。长征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生产的措施,如:保护贸易自由,开采矿场山林,开办工厂商店,发展农牧业生产,鼓励开荒造林,保护耕牛水磨,废除汉官的苛捐杂税,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等。四是把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作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认识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毛泽东就认为,对于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他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红军协助各族人民建立的民族自治政权,都吸收了当地的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中的爱国人士参加。五是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作为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的重要内容。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经堂、经书,不得擅入喇嘛寺、清真寺。同时,实行政教分离,不准喇嘛寺干涉各级革命政权。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颁布了《十要十不要》等规定。六是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与武装,并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尝试。红军在四川懋功、黑水、绥靖、崇化等地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藏民苏维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等。1936年5月在四川甘孜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由格达活佛任主席。博巴自治政府是中共最早建立的带有民族自治色彩的红色政权。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在四川大凉山,发动彝、汉群众成立冕宁县抗捐军,后又成立“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红2、红6军团转战贵州时,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苗民支队”。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藏族地区成立博巴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后又成立藏民骑兵师。七是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红军在进入川西北大草原时不得不就地筹粮,但部队仍然注意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利益。总政治部还发出《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指令》,规定在迫不得已收割藏民的青稞时对藏民的补偿方式。由于维护了少数民族人民利益,各族人民也给予红军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为红军作向导,当翻译,运送伤员、粮食,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
红军在长征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使各族人民看到了只有中共和红军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共中央及红军努力实践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取得长征胜利的又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三)忠实履行人民军队宗旨,极力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
红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与一切非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而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也是红军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早在井冈山及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毛泽东就为红军提出了遵纪爱民的要求。长征中红军从依托根据地作战变成高度机动作战,能否像在苏区那样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关系到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而且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为此,长征之初,总政治部就发出指示,强调要争取群众,发展新苏区。长征中,红军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总政治部明确告示群众: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把遵纪爱民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红军长征经过云南马龙地区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天没吃饭,警卫员未经允许从老乡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对此严肃批评,要求警卫员写检讨并按价付钱给老乡。在毛尔盖,虽然地里长满了即将成熟的豌豆、青稞,可官兵们宁可去挖野菜充饥也不动群众的一粒粮食。1936年8月,红2、红6军团进入川康藏区,当地粮食奇缺,只有喇嘛寺院里存有粮食,第11团部分官兵进入一座空寺院拿了一些粮食,总指挥部知道后,立即处分了该团政委。红军纪律严明感动了喇嘛,他们赠送红军青稞并帮助筹粮,使红2、红6军团战胜了粮荒,走出了川康藏区。
红军在长征中以实际行动向沿途2亿群众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人民群众也把红军当作自己的部队,积极要求参加红军。红军在长征中动员了近2万名青壮年参加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30页。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时,当地有3000名群众参加了红军。红9军团进驻云南东川县城后,不到一天多扩充了800名新兵。在甘肃境内,就有成千回教子弟加入红军,还有部分天主教徒出身的医生也自愿到红军部队服务。红军积极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各种群众组织也建立起来,如在湖南怀化、锡矿山等地,红军组织群众成立了抗日大同盟、义勇军、救国先遣队、职工联合会等团体,还成立了1000多人的工人团。红25军途经陕西洛南—带,组织了4支红军游击队,还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
长征中,中共和红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军政、军民团结的思想理论,充实和完善了军队群众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红军生存的根基、行动的靠山、力量的源泉,履行人民军队宗旨、遵纪爱民是红军赢得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夺取长征胜利的又一结构性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三、动员型组织形态的结构性优势:中共及红军组织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以及高度的组织原则,在长征中增进了中共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一)坚持党领导军队,使长征中的红军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统一
列宁在1904年曾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0页。实行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是列宁在苏联红军创建之初确立的一条基本原则。其原则来源于马克思关于工人政党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构建。其特点:一是将红军置于俄共(布)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二是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三是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而又功效极强的组织形态,中共复制了苏联红军的模式而构建起自己的组织。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将马列主义建军原则本土化、具体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造性地建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各级党委是部队的集体领导核心、实行军政“双首长制”。这种党军“共生”的有机体,使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也被限定在政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的以党领军模式。毛泽东确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他强调党的各级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要使到会人充分发表意见,“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提出不能用“党的工作”包揽一切,要把党与具体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区分开来。这里已经包含了党的会议要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和具体工作要分头负责去办的思想。这一制度,一方面确立了各级党委在各级部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保证了集体智慧和集体作用的充分发挥,防止少数人的独断专行特别是个人野心家的非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又使军政主官个人的智慧和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能够形成集中统一指挥。红军长征从通道会议开始,党的领导层按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会议决定重大问题。领导方式的这一变化,造成了领导层按实际所起作用形成核心而不是仅靠职权发号施令自封核心或由共产国际赠封核心。毛泽东开始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拥护,核心作用凸显出来。遵义会议后,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个人专断的领导方式在党内军内逐渐失去市场,危害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宗派集团瓦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
长征经验表明,“对组织的强调已成为共产党运动区别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标志”,“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的力量源泉”。*Franz Schurmann,“Organis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hina,Quarterly, 2 April-June,1960,P.47.红军长征在极为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靠的是组织形态的强大力量。
(二)大力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使长征中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跃升
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是列宁首创的一条建军原则。列宁建立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两项重大制度。中共借鉴苏联红军的经验,于1927年8月,在南昌起义部队中首先设立总政治部,随后又在军、师两级相继设政治部。1928年中共六大规定,红军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之后各地红军陆续建立起政治机关。1930年8月,中央军委建立总政治部。10月,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第193页。1930年冬,红军逐步建立起战时政治工作制度,至第三次反“围剿”时,战时政治工作已基本规范化。
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都视政治工作为红军的生命线。这为人民军队的发展、红军的作战提供了重要保证,也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红军长征中政治工作的最根本任务是持续不断地对红军战士进行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进行革命信念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使红军将士始终保持很高的政治觉悟和高昂士气。为了保证长征的胜利,部队走到哪,仗打到哪,激发精神动力的思想动员工作就做到哪。每当执行作战任务时,红军都进行充分的战前宣传鼓动。政治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党团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可以说长征的每一胜利都与红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密不可分。思想政治工作使远大政治理想和坚定信念深入红军官兵的心中,激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有力的政治工作铸就红军将士的牺牲精神,在红军面前,一切敌人、饥寒、疲劳、伤痛、风雪、泥沼、死亡,都算不上什么。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只要一息尚存,也要与困难和敌人战斗到底。长征中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历史充分说明,政治工作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使红军永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保证,是红军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和独特的优势,是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和长征制胜之道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三)中共中央和红军坚持团结一致的原则,各路红军互相支援、密切配合
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是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重要准则。*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译:《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第2卷)军队建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88页。列宁强调需要在一个“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组织”。*[美]塞缪尔·P·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10页。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强调高度一致,在大局下行动。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是红军建军以来确定的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团结是党和军队的生命,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得胜利。
长征的胜利首先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层团结一致的结果。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层的统一是团结的关键,为了克服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危机,长征中毛泽东抓住各种机会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实现了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层高度团结一致,博古虽然不再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坚决站在党中央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采取十分忍耐的方针,只要张国焘赞同和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其它问题可以作一些让步。甚至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中共中央除严肃批评令其立即取消外,仍然对他采取团结的方针,尽力避免使矛盾向对抗性转化。中共中央在批判张国焘错误中,把张国焘个人的错误同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区别开来。认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绝不应该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说成是反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强调“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红四方面军将领的使用也体现了这一点。红四方面军将领被授予元帅军衔1人,大将军衔3人,上将军衔17人,中将军衔59人,少将军衔156人。至1964年占全军比例分别为:元帅占10%,大将占30%,上将占29.8%,中将占33.3%,少将占12.9%。长征的历史表明,顾大局、守纪律、讲团结是红军长征中克敌致胜的保证。
长征的胜利也是全国各地红军互相配合、团结战斗的结果。长征中各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虽然是独立进行的,但在长征过程中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彼此之间在战略上互相策应,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分割红军、各个击破的阴谋。长征前夕,红7军团和红6军团北上、西进调动了国民党的“围剿”军,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减轻了压力。长征初期,红2、红6军团由黔东出发,发动湘西攻势,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4个旅,牵制了其11个师又2个旅,策应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和占领黎平。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歼敌10余个团,在向岷江地区的进攻时击溃邓锡侯部11个团的防堵并攻占懋功、达维,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徐海东率红25军主动出击甘南,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为策应红2、红6军团北上甘孜会师,南下雅江阻敌,保证了红2、红6军团北上的侧翼安全;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后,中共中央派西征军南下接应促成了红军3大主力会师于会宁、将台堡地区,无一不反映出红军团结战斗密切协同的奋斗精神。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所部红24师、十几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约1.6万人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红25军撤离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留下红74师转战20余县打击敌人。
长征的历史表明,强有力的组织结构、紧密团结顾全大局的组织特性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共产党在革命中的组织力量是长征最终胜利的结构性优势,组织出凝聚力,组织出战斗力。中共中央及红军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钢铁般的组织结构,是任何力量摧不垮、打不破的。
四、创新性军事理论的结构性优势:中共及红军在长征中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
(一)将中共及红军的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结为一体,确立北上建立抗日基地的战略方针
确立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关键。毛泽东从全国政治形势出发,认为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这个战略方向的确定使长征由消极行动变为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
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实际主持了中革军委日常工作。他请毛泽东参加通道军事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原定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不顾李德反对,支持毛泽东意见,会议最终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向贵州进军,这一重大决策挽救了中共及红军,为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之后的黎平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李德主张折往蒋介石已布罗网的黔东;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在激烈争论中通过了毛泽东等人还在通道地区时就提出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解决了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根据黎平会议的战略决定,中央红军横扫黔东,突破乌江,将数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南岸,赢得了进占遵义后的休整时间。毛泽东本人在长征中也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战略指导地位。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新的“三人团”是红军指挥的最高领导权威组织,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毛泽东成为红军行动的“总设计师”。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为重要的续篇。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将红军的战略退却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红军长征的军事战略指导问题。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避开国民党军队强大压力的错误主张,坚持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俄界会议后,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创造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
正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红军才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
(二)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确立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的指导地位,恢复运动游击战战法以制敌
红军创建之初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亟待新的战争理论指导,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对此进行过大量探索。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军事学说为指导,吸取了西方军事家华盛顿和拿破仑的机动战术、游击战术以及克劳塞维茨的积极防御理论,结合根据地反“围剿”战争敌强我弱的实际,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5页。由此产生了中共及其红军的最新作战原则。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主要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页。这些战术原则产生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和推广。这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原则,等到战胜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形成。*《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25页。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市武装起义发展为在农村组织长期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形成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且将这一战略理论发展至前所未有的境界。但这一理论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后为“左”倾中央所排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红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时,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指出了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总结的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创立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的结果。正是有了这一理论指导才使得中共转危为安,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
遵义会议后,为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重兵“追剿”,毛泽东一改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下所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六面出击”“短促突击”以及用阵地战的死打硬拼来对付敌人的“围剿”的错误呆板战法,指挥红军充分发挥运动战的优长,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战争奇观。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打”则使敌闻风丧胆,“走”则叫敌望尘莫及。红军以迂为直,善于以奇谋方略调动敌人。即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以高度的灵活机动,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毛泽东战略指导艺术被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奇就奇在间接战线,“以迂为直”的运用,迫使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判断,以致其接连失败。红军以战斗的胜利掩护逐段的转移,以转移来争取战场主动;并且凸显出善于夺隘、渡江和打骑兵的战术优势。为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重兵“追剿”,1935年3月,红军在云贵川地区展开了较长时间的大规模运动游击战,充分展示出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才干,最终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曾将此战誉为平生“得意之笔”。*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徐占权、姜为民、田玄执笔):《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72页。面对红军的运动游击战的胜利和国民党“追剿”军的不断失利,蒋介石对“追剿”部队薛岳指挥不力表示不满,并试图调顾祝同接手黔省军事。*黄自进、潘光哲:《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册,卷32,1935年2月至4月,台北:“国史馆”2011年。3月16日,蒋介石又怒斥“追剿”部队周浑元“不足教也”。28日再次指责周浑元“束手无策”,“屡令不进,屡戒不悛,孺子诚不可教也”,红军的骁勇使蒋介石十分恐慌。国民党军第1纵队司令吴奇伟两个师被歼后,蒋介石于3月20日写信给吴奇伟,要他“对飘忽不定的共军作战要极为慎重”。*《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53页。这从敌人方向反证了回归正确军事指导后红军游击运动战的威力。
很显然,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长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制胜之道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尹正达)
Structural Factors Paving the Way to Success for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Red Army’s Long March
TianXuan
(History Colle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The Long March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is the most difficult yet most glorious phase in both the CPC history and the military history. There are many things contribut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d Army managed to reach Northern Shanxi and achieved ultimate victory, but the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enabled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to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and enemies are as follows: the ideology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and their sinofication, the firm belief of the Red Army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theory of Marxism, the strict and compact organizational form of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the innovative policy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 highly flexible military strategy and operational doctrine. The way to success for the Long March has been valuable 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In this new historical era, it still carrie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PC that has transformed from a revolutionary party to the ruling party and for today’s CPC-led PLA construct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Red Army; the Long March; the way to success; structural factors
田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K26;E297
A
1009-3451(2016)03-0001-11
主持人语:80年前的长征,是20余万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人类战争史奇迹。如果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为背景来考察,长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红军在强敌连续的“围剿”和“追剿”中实现了军事战略上从被动向主动的转换,更是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经历诸多曲折后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这样一个改变了中共和红军命运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中外学者几十年来始终抱有极高的热情,从未停止过学理探析和史实追索的努力,推动了长征史研究持续走向深入。本栏目推出的一组文章,试图通过不同视角的考察,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于长征的认知。有关长征胜利原因的探讨,向来是长征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形成了许多普遍共识。从现代政治学注重的结构性因素角度切入,对长征的制胜之道展开多维度的探究和辨析,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由于战争环境等原因,留存下来的长征原始文献数量有限,亲历者的早期回忆因距事件发生时间近、准确性高更显得弥足珍贵,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信息值得重视,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挖掘。外国学者对长征史的研究总是独树一帜,饶有兴味。对约翰·瓦特研究成果的介绍聚焦于长征中的红军救护工作,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红军内部严密的组织力和高效的行动力。时光流逝无法消减红军长征的魅力,有关长征史的讨论还将继续,人们也会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