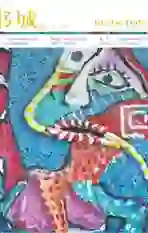穆旦的误译
2016-10-12杨志
杨志

睡前习惯读点东西,好久没读奥登,找出手头的英文选集,一翻,正是《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 Arts)。这诗,不记得读了多少遍,太熟了,迷迷糊糊重读,内心突然一动,感觉以前的理解似乎有问题,结果,睡不着了—
一、被误译的奥登
译介奥登,始于民国,有邵洵美、卞之琳、朱维基诸家,但大陆诗人(包括笔者)接触奥登,大都始于穆旦译本(收入《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我们读的奥登,其实多多少少戴了穆旦的“有色眼镜”。《美术馆》为英诗名篇,汉译很多,只我读过的,不算网上,就有穆旦、王佐良(收入《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与《奥登诗选:1927-1947》(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三家。搞过翻译的都知道,译前尽量不要读他人译稿,以免被对方牵着走。据我所知,后两家事先都读过穆旦译本,是受其影响的,王佐良为穆旦挚友,就称自己的译本即据穆旦译本略改而成。
现将原作及穆旦译文抄录如下:
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关于痛苦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深知它在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并不特别想要它出现,而却在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They never forgot.
他们从不忘记:
That even the dreadful martyrdom must run its course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Anyhow in a corner, some untidy spot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Where the dogs go on with their doggy life and the torturers horse
在那里狗继续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Scratches its innocent behind on a tree.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In Breughels Icarus, for instance: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the ploughman may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Have heard the splash, the forsaken cry,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But for him it was not an important failure; the sun shone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As it had to on the white legs disappearing into the green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Water; and the expensive delicate ship that must have seen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Something amazing, a boy falling out of the sky,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
had somewhere to get to and sailed calmly on.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穆旦还阐释如下:“本诗的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诗人在美术馆里看到勃鲁盖尔(1525-1569,尼德兰画家)的油画《伊卡鲁斯》,深感到它描绘的正是这一主题。‘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自制翅膀飞离克里特岛,在飞近太阳时,他的翅膀由于是用蜡粘住的,融化了,他也跌落海中死去。诗中描写的景色大多是勃鲁盖尔画中所有的。”这一阐释,其他译者无异议,我也如此,现在才发现事有不然。
奥登写诗,学究气重,晦涩难懂,《美术馆》流利易读,可谓少有,但结构还是学究气,如一篇论文,开篇提出论点,随即提出三条论据:第一条,为圣母玛利亚冒险生耶稣事,据《新约》,希律王听到预言,说耶稣要下世为王,为保住自己的权位,下令诛尽伯利恒两岁以下幼童,在此腥风血雨中,玛利亚冒险产下耶稣。此事为欧洲绘画常见题材,勃鲁盖尔也绘有《杀戮无辜》(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1567)传世,奥登在此慨叹后生小辈淡忘玛利亚之艰险,居然对圣诞节嬉戏待之;第二条,无画都猜得到,指耶稣殉道,勃鲁盖尔有《背十字架的耶稣》(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1564)传世,该画不同于其他耶稣殉难画的特色,是把背十字架的耶稣画得很小,周围是乱糟糟的大批士兵和百姓,各忙各的龌龊事儿,对殉难漠不关心;第三条,如穆旦所言,为伊卡鲁斯飞天坠海死事,出自勃鲁盖尔的名画《伊卡鲁斯落海》(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1558),伊卡鲁斯被后世视为科学先驱,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但勃鲁盖尔画他死时无人理睬—我们忙我们的,你死你的,于我辈何有哉?—勃鲁盖尔这人,向来愤世嫉俗,常把世人画得或如疯子或如小丑,此画最打动奥登心肠,所以着墨也最多。此三人—玛利亚、耶稣、伊卡鲁斯(出自基督教和古希腊,为欧美文化两大源头),都是为人类献身受难的神祇,无一凡人。由此可知,穆旦认为此诗主题是“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虽不算错,但更准确的解释当为“庸人对殉难者麻木无感”,意思跟鲁迅写《药》哀悼秋瑾(夏瑜)近似,只不过,鲁迅还在《药》的结尾故意添了亮色—一个花环,装作烈士还有人惦记,奥登则认为有甚花环?他们全白死了。
《美术馆》写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正是奥登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刻。当时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又来抗战中的中国,目睹志士仁人惨死如狗,又悲愤,又灰心,形之于诗。诗人的神奇,是往往能无心道破自己的未来。此诗,身为左派领袖的奥登已经透露了对左派的厌倦,既感觉殉难者徒劳,又厌烦左派青年的反基督倾向。诗中指责老辈热烈期待圣诞节,小辈却漠不关心,跑去溜冰,这一细节,泄露了他正从左派转向保守派的“政治无意识”。几个月后,他放弃左翼思想,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于一九四○年皈依基督教,成为轰动英国文坛的一桩公案。据Richard Davenport-Hines的《奥登传》(Auden),奥登生于基督教家庭,外表叛逆,内里软弱,因有个飞扬跋扈的母亲,这就难怪他才三十出头,便撑不住自己的叛逆,迫切要回归基督教的怀抱了。此后,奥登写诗,技巧越来越娴熟,宗教说教越来越长,但灵魂的某些燃料已经耗尽,“伪装的刺猬”蜕变为“油滑的狐狸”,令诸多粉丝伤怀不已(穆旦译奥登,只重前期诗;当代诗人,因生长于太平时期,更重后期诗,也是时势使然)。
弄清主题后,我们再审视细节,即可看出suffering一词,各个译本译为“苦难”或“痛苦”,跟原意有偏差,译为“受难”似更准确(译为“殉难”也可,只是因玛利亚受难而未殉难,稍有不合)。其次,穆旦把the miraculous birth直译为“神异的降生”,字面意思不错,但欧美人都清楚指圣诞节,于中国人则未免太“陌生化”,暧昧不明,从注释未提及希律王典故看,穆旦可能未想到其中关联。再次,译耶稣殉难(“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在一个角落”),把run its course译为“完结”,颇为败笔,奥登的意思,是耶稣白白牺牲,无济于事,作恶者照旧作恶,愚昧者也照旧愚昧,穆旦没译出这层意思,译为“自生自灭”更准确。最后,“迫害者的马/把无知(innocent)的臀部在树上摩擦”,有人译innocent为“无辜”,错了,“迫害者的马”的确没迫害耶稣,貌似可以说它“无辜”,但这样译是散文,而不是诗,更不是奥登的诗。奥登这里的意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叱责“红眼睛阿义”“阿Q”辈呢,我感觉,译为“愚昧”较准确,穆旦译为“无知”,也通,但奥登的火气就弱了。
从译文和注释看,穆旦对该诗主题的把握有偏差,对背后的基督教意蕴也稍嫌隔膜。
二、穆旦因何失误?
本文意不在挑穆旦译文的毛病—世间本无十全十美的译本,高手也难免失误,再说了,挑毛病谁不会?—而是想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穆旦在此失误?
照理说,他不该错的:穆旦终身钦佩奥登,深受影响,被视为“中国的奥登”,晚年译奥登,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已有三十多年的反刍,如挚友周珏良所说,他译奥登“纯粹出于爱好”,“下工夫很深很细”。此时期穆旦的译与写,均为“地下写作”,也不存在故意避饰的问题。
失误的根由,我想,是穆旦一生太苦。
穆旦小奥登十三岁,原非一代,但因二战,视为一代人也无大错。他与奥登一样,都是名牌大学的左派学生,出社会后,亲历二战前后的苦难,无比痛苦,迫切渴望精神依靠。奥登转向基督教,三十岁出头;穆旦走近基督教,始于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前后,随后,野人山战役,中国远征军大溃,穆旦险些饿死于溃败途中,据王佐良介绍:
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一个中国诗人》)
“从此变了一个人”的,不只是肉体,还有精神,穆旦的基督教情结由此激化,到内战时期,目睹“阴谋,说法,或者杀人。/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诗四首》)的现实,痛苦达到顶峰,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写了宗教长诗《隐现》(时年二十九岁),认为“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糅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野人山之战及国共内战,是穆旦苦难的第一次顶峰,却不是最后一次,更痛苦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被整,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发落学校图书馆“监督劳动”,“接受机关管制”,自己受了二十年的折磨不说,又因连累家人,时刻被内疚煎熬—“我已经走到了幻想的尽头……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智慧之歌》),绝笔的《冬》承认—“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如前所述,穆旦译奥登,在其晚年,因一生坎坷多难,受尽白眼,他对“人对别人的痛苦麻木无感”特别敏感,所以解读《美术馆》时“先入为主”,是不奇怪的。
但是,这个解释存在一个疑问—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甚至宣称要“投入上帝慈爱的胸怀”(《祈神二章》,1943)的穆旦,为何晚年译《美术馆》,对基督教如此隔膜?基督教思想家薇依不是说吗—人越苦难,越近上帝?新诗人里公认最具基督情结的穆旦,到了苦难透顶的晚年,他的宗教敏感哪去了?
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得考察穆旦的“心灵史”。一九七五年,穆旦读鲁迅《热风》,对四十一则特别共鸣,抄在了扉页—“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几个月后,又把共鸣转成一首《理智和感情》:
1 劝告
如果时间和空间
是永恒的巨流,
而你是一粒细沙
随着它漂走,
一个小小的距离
就是你一生的奋斗,
从起点到终点
让它充满了烦忧,
只因为你把世事
看得过于永久,
你的得意和失意,
你的片刻的聚积,
转眼就被冲走
在那永恒的巨流。
2 答复
你看窗外的夜空
黑暗而且寒冷,
那里高悬着星星,
像孤零的眼睛,
燃烧在苍穹。
它全身的物质
是易燃的天体,
即使只是一粒沙
也有因果和目的:
它的爱憎和神经
都要求放出光明。
因此它要化成灰,
因此它悒郁不宁,
固执着自己的轨道
把生命耗尽。
穆旦向来喜欢鲁迅,一九四○年的《五月》就说“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三十六年弹指而过,他依旧喜欢鲁迅,但我们拿一九四七年的《隐现》与一九七六年的《理智和感情》对读—耶稣却不见了。事实上,穆旦晚年的诗信,再没关心上帝(《“神”的变形》写了一个被“权力”腐蚀的“神”,其实是人)。一九四七年的穆旦,大声呼吁上帝降临,要投入他的怀抱;三十年后,境遇更凄惨的他,依旧喜欢鲁迅,却忘了上帝,“心不在焉”—所以译诗时格外生疏,也就不足为怪了。
穆旦的基督教情感是怎么磨损的?史料无载,我们只能揣测:
首先,他接近基督教的途径,估计主要来自书本。清末,传教士来华传教,早期信徒多为身边仆人,时人有“吃教”之讥,但是,水至清则无鱼,世间有完全脱离利益的宗教么?“利益”与“信仰”,未必完全敌对,也可能相互生发。宗教从来不是空泛的概念,脱离了生老病死,撇去了柴米油盐,任何宗教都如“纸上花”,容易凋零。即使“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若上无科举制度的“顶层设计”,下乏宗法制度的“草根组织”,也未必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从基督教传播史看,利益、家庭与铁血是主要途径。冰心、林语堂这类有基督教背景的作家不用说了,现代学人兼诗人洪业在基督教学校读书时,以儒生自居,讥笑其教义,后父亲突然去世,身为长子的他精神受创,因基督教校长及老师及时给予勉励,深受感动,不久受洗,两年后得资助出洋留学(参陈毓贤《洪业传》,该书实为洪业口述)。可见他的皈依未必无利益成分,但此后终身信奉。如果穆旦接受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是书本,并无利益纠缠其间,再加上士大夫的传统,反倒可能导致他虔信程度不深,遇事容易变更。穆旦留美期间的诗,现存两首,都批判美国,且特意抨击了基督教—“黑衣牧师每星期向你招手/让你厌弃世界和正当的追求”(《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1951)、“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感恩节—可耻的债》,1951)均刊发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七期。从诗风看,可能是回国后的“表态”,未必就作于留美期间,但其间对基督教的不满,或有渲染,却可能有真实成分。据穆旦妻子周与良回忆,留美期间,他“生活十分艰苦……选择了在邮局运送邮报的重体力活”,“有机会接触到了美国下层社会的人”,“非常同情黑人的处境”,且“资产阶级”在穆旦诗里向为贬义词,都跟两诗吻合。对于美国人,政府与教会是两回事;但对于中国人穆旦,两者是一回事。由此推测,他可能从反感美国社会开始,进而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怀疑情绪,否则似无必要在诗里特意提及。
其次,他未参与具体的宗教活动。信徒团体为宗教的“细胞”,对个人信仰的维持至关重要。现存史料,未见穆旦参与宗教活动的记载,早期不得而知,后期则可以断定没有。建国初期,国内对涉外教会怀有警惕,穆旦回国后,不太可能参加宗教活动。据陈伯良的《穆旦传》,“文革”期间,穆旦因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家被抄不说,就连母亲的朋友来串门,都要被胡同的革委会百般盘问,就更不可能参加宗教活动了。穆旦曾在《祈神二章》(1943)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他,/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其实,看不见上帝,原因未必在上帝,而可能是缺乏教友呼应。结果,上帝也就不能时时跟他对话,他也慢慢疏远了基督教,两年三年三十年,基督教在他心里就磨损殆尽了。实际上,老舍就是如此—今日我们几乎忘了《茶馆》的作者原先是正式受洗的基督徒。佛教向有“随缘”之说,意为个人能否信教得看缘分,有缘则来,无缘则去。穆旦先是对基督教有了怀疑,后是建国初期环境不允许,所以,他的逐渐离开,缘尽而去,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他渐渐亲近本土传统。穆旦为外文系出身,却跟长居海外的林语堂、洪业等不同,出洋已三十二岁,留美只三载半,说到底还是生于天津、死于天津的中国人,本土的影响更深些。身为新文化运动第二代的他,接触的本土精英传统有二: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一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士大夫。穆旦以叛逆传统的诗人自命,“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被围者》),反旧诗反了一辈子,但晚年苦难缠身,又痛于死亡迫近(晚年书信,谈死甚多,“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对杜甫和陶潜起了很大共鸣,渐觉亲近,颇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中国式感慨”。他于儒家教义有隔膜,但“孔家店”不只四书五经,士大夫如陶潜、杜甫的诗歌概莫能外,对其影响与日俱增—叶落归根,回归传统,叛逆者常见,奥登不也如此?
三、从“约伯”转向“屈原”
《理智和感情》这诗,我以为,也可改为“苦难和慰藉”,其实讲的是苦难的慰藉问题。《隐现》和《理智和感情》两诗,穆旦都以问答体来探讨这一主题。实际上,这也是中西方常见的主题及形式,欧美著名的如《旧约·约伯记》,中国著名的如《楚辞·卜居》。《隐现》的答案,是“约伯”;《理智和感情》的回答,是“屈原”—从“约伯”转向“屈原”,正是穆旦从壮年到晚年的“精神位移”。
如《约伯记》所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人遭难,未必有什么因果,也未必有什么补偿,但旁观者这么想可以,当局者不成—苦难必须有补偿,得慰藉,而不是冷冰冰的实话—这是人性。因为苦难,约伯谴责上帝,“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司马迁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史记·伯夷列传》);杜甫问“我生何为在穷谷?深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奥登的《美术馆》,同样痛恨于世人的“麻木无感”。穆旦此诗,也意在为自己“丰富的痛苦”(《出发》)寻找“苦难的慰藉”,虽然诗里也承认,这无关“理智”,乃“感情”需要。所以,约伯有苦尽甘来、多子多福的“大团圆”;儒家也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下》)的“浓鸡汤”。事实上,苦难慰藉貌似“虚”,却牵动人类神经,为一切文化的核心内容,慰藉不够有效的文化,往往被其他文化侵袭,古希腊罗马被基督教侵袭即一例,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甚至视为“文化灭绝”。
晚年穆旦写过一首《停电之后》,写停电后点起蜡烛,“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 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次日睁开眼,白日更辉煌,
小小的烛台还摆在桌上。
我细看它,不但耗尽了油,
而且残留的泪挂在两旁:
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
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
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
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
此处的“蜡烛”,意在自比,“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充满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怆;“太阳”指光明,却非上帝。在基督徒,“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是因神在,无神,人的努力就没了根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说的“怎么都行”,欧洲版的“礼崩乐坏”了。士大夫则是另一种传统,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理论上)遭难也不求神拜佛。屈原为士大夫先驱,被流放后,“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找太卜郑詹尹占卜之余,大发议论,说得对方“释策而谢曰”:“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卜居》),意思是你遭难,神也没辙,自己努力。关于苦难,司马迁找到的慰藉是“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没有神;杜甫晚年,漂泊无依,常有“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的自勉,慰藉是“丈夫垂名动万古”(《赤霄行》),也没有神;穆旦晚年给朋友写信说:“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当然也够可怜)”(致董言声,1977年1月4日),还是没有神。
千古艰难唯一死,苟存者,谁不渴望慰藉?
慰藉的源泉,于宗教徒,曰“信仰”;于无神者,曰“信念”,窃以为名称虽别,功能实一。包括穆旦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跟士大夫前辈的不同,是慰藉资源增加了欧美选项,由此产生了取舍的文化冲突。而知识分子中,诗人“以心为食”,最为敏感,是此种文化冲突的“心灵探针”。事实上,接受欧美宗教思想后,又被本土文化磨损的新诗人,为数不少,郭沫若、闻一多、冯至都是例子。曾崇仰泛神论的郭沫若不必说。闻一多清华读书时受洗,后放弃,自承“丧失了基督教的信仰”(致吴景超,1922年12月4日),最后俨然“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儒家人物。冯至早年仰慕鲁迅,又认同歌德的自然神论,抗战后转徙流离,继而迷上杜甫,一九四一年作《十四行集》,写自己的神性体验,同时赞美杜甫和鲁迅,到了一九八五年修订《十四行集》,却把“神”字统统删尽—如把“神,我深夜祈求”(第二十二首)改成“我在深夜祈求”—这么改,或出于时代顾虑,然而我们读其晚年诗文信札,虽还仰慕歌德,但宗教感已磨损殆尽,对杜甫和鲁迅的热爱倒一如当年,甚至更烈。
从基督徒看士大夫,是“无根基”,不信神,以罪人之身死扛—不信神,“固执着自己的轨道/把生命耗尽”,如河中凿井,有何意义?从士大夫看基督徒,是“拜神求佛”,效愚夫愚妇之习,求神不如求己。但我以为,两者殊途同归,上帝之有无,未必重要,慰藉之有无,却是命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主人公伊凡得知孩童惨死,对上帝的漠然痛心疾首,叛出教门,对上帝热讽冷嘲,托尔斯泰读后很生气,认为这个浑蛋的伊凡肯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苦难不得慰藉,“有神的教徒”也可能变为“无神的叛徒”(如许多俄国革命者就出身东正教家庭),而“名教的信徒”也可能变成“名教的叛徒”(如瞿秋白)。洪业是基督徒,又崇敬杜甫(按:其父洪曦谨守儒学,虽为县令,却常年穷饿,亦不改其节,极敬杜甫,评曰:“其人也,天假其时,则显;运命未济,亦不衰”,对他影响甚深),抗战期间被日军囚禁,自称于狱壁见耶稣显灵,同时在牢房反复背杜诗,认为:“《圣经》为绝世之书。而仅次于圣《诗》者,即为杜诗,每能慰余之大悲大喜。”(参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圣《诗》属于《圣经》,杜甫出于《论语》(按,杜甫早年,“裘马颇清狂”,纨绔子弟,也非真儒,困居长安后,始倾心孔门),耶儒并论,欧美基督徒或许不满,洪业则视为当然—这恰恰说明,士大夫之所以往往能自外于基督教,是因为本土文化的苦难慰藉也同样强大,足以“慰人之大悲大喜”。穆旦晚年诗,风骨胜于早年诗,正体现了此种力量之坚韧。
纵观历史,被苦难驱动的现代知识分子,“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为求慰藉,不但有从“约伯”转向“鲁迅”的,也有从“鲁迅”转向“约伯”的,还有从“约伯”转向“佛陀”的,更有从“孔子”转向“马克思”的……性格不同,时代不同,选择也不同,甚至相反。对于“苦痛不可逃”的他们,宗教正如道德哲学,道德哲学也如宗教;无神论者正如宗教徒,宗教徒也如无神论者—或许,这才是历史的庐山真面目。而穆旦的“心灵史”,让我们窥见的,正是此种彷徨于“上帝”“孔子”“鲁迅”等神祇或英雄之间,信之旋又弃之的“改宗现象”。
二○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