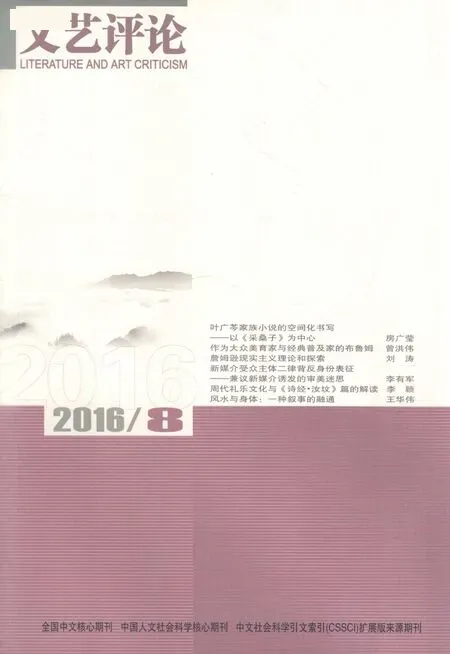从佛教量论看庄子的道言关系
2016-09-29范文彬
○范文彬
古典诗学
从佛教量论看庄子的道言关系
○范文彬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它的“无为无形”的特点能否像一般的知识与原理一样被理解和被传授,道是否可用语言表述清楚。庄子传承《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命题,在《知北游》中明确指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①但《庄子》一书的全部文字又似乎无不在言道,从表层上看,庄子似乎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之中。现代诸多庄学研究者都各抒己见,试图重新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来的一些论文与专著大都倾向于寻找《庄子》中的言道方式,进而化解所谓“道言悖论”。我们以为,庄子说“道不可言”自有其道理,并在此拟从佛教唯识学量论的角度来探究庄子的道言关系。因为,佛教哲学与道家哲学都是形上之学,其理论都是建立在实修与实证的基础上的。因此,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探讨应该会给庄子道言问题带来新的启示。
量论是佛教唯识学关于认识方法的理论,量论用“量”来说明认识世界的状态与程度,“量”是梵语prama^n!a的意译。唯识学量论中的“量”有多种,我们所涉及的主要是现量、比量、譬喻量等。
一、从佛教现量境看庄子的道不可言
现量,佛教中指认识者不经过思维而直接认识的现象。分为两种,一是普通人通过眼、耳、鼻、舌、身五根亲历的现象,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知觉。另一种是佛家修行者证道后所亲历的诸法实相,索达吉堪布《量理宝藏论释》中所说“有凡夫现量与圣者现量”②即指导这两者的不同。我们重点看圣者现量,圣者现量是佛教破除迷惘、觉了法性的境界。禅宗、唯识宗的重要经典《楞伽经》中说:“觉了自心现量,一切诸法,妄想不生,不堕心意意识。外性自性相计著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③这里的自心现量是“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的觉悟证道的境界,自心现量亦即圣者现量。这种圣者现量与凡夫的五根现量不同,凡夫的感观现量比较浅近,可以通过言语文字表述,而圣者自心现量则是证道者亲证的玄妙经验,难以运用语言说清。因此,《楞伽经》中接着说“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真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因。言说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④《楞伽经》的意思是说,圣者自心现量是玄妙空寂,是远离妄想分别。所谓妄想是指普通人在日常的情况下意识不停流动,杂念纷扰。所谓分别,是指人的思维对是是非非的分辨惴度。佛家认为,要达到圣者证道的自心现量,必须尽力排除“妄想”“分别”等意识活动。语言文字是与人的意识活动相应,也就是与妄想分别相应,就是上边说的“言说者,妄想合”。而语言文字却不能跟圣者微妙空寂的自心现量境相应,即圣者自心现量境界是超越意识活动、超越思维忖度的,因此也就超越了语言文字。这就是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的“诸佛妙理,非关文字”⑤。宋代永明延寿大师说得更清楚:“现量者,现谓显现,即分明证境,不带名言,无筹度心,亲得法体,离妄分别,名之为现。”⑥这种证道的现量之境,不可名,不可言,不可惴度,远离妄想分别。进一步说,意识活动是任何人都有的普遍的思维现象,属于“共相”,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表述并与他人沟通。而圣者现量境界是个人修行之证道境界,属于“自相”。自相为现量境,而共相则属比量境。古印度大乘佛教著名论师、佛教新因明学创始人陈那所撰、法尊译编的《集量论略解》中说的明白:“现量之境,谓自相;比量之境,谓共相。前品已说。现量之自性是无分别觉,比量之自性是有分别觉……若现量之境义,能施设名言,即由彼声,应成比量。故现量之自相境,不可以名言也。”⑦普通人的意识活动每个人都有,是共相,所以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相沟通,而远离妄想分别的现量境是自心亲证,无法通过语言文字与人沟通。
明确了佛家现量及其不可言说的特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庄子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命题。如果庄子的道与佛家之道具有同一性,就同理可证,庄子的道不可言之说可以成立。《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在这里点明了道的特征:有情,有信,不可授,不可见。成玄英对此的解释是:“明鉴洞照,有情也。趣机若响,有信也。恬淡寂寞,无为也。视之不见,无形也。”⑧首先,成玄英关于道的“明鉴洞照”的特征正与佛家的证道的现量境界类似。南朝梁代的僧佑在《释迦谱序》也说:“菩提之为极也,神妙寂通,圆智湛照。”⑨僧佑的佛学弟子刘勰也在《灭惑论》中说:“佛之至也,则空幻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⑩僧佑及弟子刘勰讲佛家终极的觉悟证道之境都说到“照”的境界:“圆智湛照”“玄智弥照”。这与成玄英解说庄子“明鉴洞照”基本同义,都是在指去除妄想分别之后的心灵的寂静状态,空寂为道境的基本形态,而明鉴洞照,或者说圆智湛照、玄智弥照是它的功能的体现,佛家称之为大圆镜智。与《楞伽经》的“微妙寂静”的现量境也基本同义,按佛家的说法寂静为体,观照为用,是证道之境的一体两面。正如隋代智凯大师的《童蒙止观》中也说:“曰止观,曰定慧,曰寂照,曰明静,皆同出而异名也。”⑪庄子在《天道》中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所说的由寂静而能鉴照就是道的特征,可以称之为道家的现量境。通过类比分析,可以证明,道家与佛家一样都有空寂湛然的现量境。因此,庄子的道境与佛家道境一样都有不可言说的特点。再进一步说,庄子的“有情有信”,是说道境的存在,但它又极其玄妙,无为无形,即老子说的“大象无形”,无法与语言文字相应。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强调说:“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这里的“彼”代指道,形色名声是感观可以感知的外在物象。而道之象并不是感观所感知的物象,正如佛家一样,是证道者“自相”,而非普通人的“共相”,因此不可以直接传之于人。庄子在《知北游》中断定“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也正是此理。
二、从佛教比量、譬喻量看庄子的道之可传
上文我们通过佛家唯识的现量理论印证了庄子的“道不可言”的命题。那么,既然庄子认定道不可言,《庄子》一书通篇所言又是为何呢?难道不是在言道吗?如果不是言道,那又是在言说什么呢?我们再看《大宗师》这句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这里在说道不可传、不可受的同时,也说到了“可传”“可得”。成玄英疏云:“寄言诠理,可传也,体非数量,不可受也;方寸独悟,可得也。离于形色,不可见也。”⑫成玄英说的“体非数量”的道体不是可量可数的东西,所以不可能直接授受,就是说,证道者不能将证道经验像物品一样直接送给他人。“离于形色”,是说道象无形无色,即老子所谓“大象无形”,所以不可以通过感观感知。而可传、可得在于“寄言诠理”和“方寸独悟”。诠理就是解说义理,独悟就是求道的修心方法。也就是说,庄子的道不可言是指道之体,可言者为义理与方法。庄子的不可言体道之境相当于佛家的不可言的现量境,那么庄子所讲的义理与方法则相当于佛家的比量境。
什么是比量境,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解释说:“比量,于不现显之境。比知分别而量知者。如见烟知有火。凡因明依第六意识之比量智而成也。”⑬第六识就是指人的意识,也就是人大脑的思维功能,“分别而量知”就是逻辑思辨的方式。因此,比量就是通过普通人逻辑思维可以理解的方式讲述义理与方法。佛家经典众多,卷秩浩繁,所言大部分内容都是释迦牟尼讲义理与方法,都是比量状态。如《无量寿经》:“庄严众行,轨范具足。观法如化,三昧常寂。”⑭这是讲的佛家的义理。还有讲修行方法方面的,如《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⑮由此可见,所谓比量,完全不同于现量,所言皆是理论和方法。在《庄子》的诸多文字中,基本上都是讲理论与方法。《庄子》中解说道家义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从道的高度解说概括世界的本质,如《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这是在解说“万物一齐”的道理。而万物一齐之理是从道的高度观照现世世界的结果,即庄子说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角度看,宇宙万物本无差别。这里所说的不是体道的现量境,而是从道的高度对现世世界的体认,可以运用语言概括表述。第二,讲述庄子对现世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如《齐物论》:“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第三,讲解庄子自己的人生态度:如《至乐》:“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第四是讲修道的方法与途径。如《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前三种为义理,第四种为方法。旨非现量,通属比量,所以可以用语言阐发说明。
庄子中除了运用语言直接地讲述求道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另一种表述义理和方法的言语形式,那就是寓言故事与比喻语句。寓言是庄子讲道的重要方式,《庄子·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对此的解释是:“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这是说明不是直接言说道理而是借助与言说者无关的人而言之。寓言的本质是隐喻性的。如《应帝王》中的这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通过这个故事,是在讲自然之理。中央之帝浑沌与南北二帝不同在于他没有七窍,而南北二帝按照自己的标准为了浑沌凿成七窍,然而浑沌却死了,就是说南北二帝以人为的方式破坏了浑沌的先天的自然。庄子借此寓言意在说明以有为之法破坏了无为之法,寓言中庄子以南北二帝喻有为,以浑沌喻无为。还有那个“朝三暮四”的寓言,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并无本质差别,而众狙却执持早晚三四的变换。庄子借此而喻世界万物一齐,而世人智慧不开,执持无用的变换。总之,庄子寓言大都如此,借故事来讲道的义理。在寓言之外,庄子也直接运用了不少比喻式的语句,如:《天道》中的“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这是以鉴与镜比喻圣人纯净无染,且可以观照万物的心地。再如《养生主》中的:“指穷於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是以火比喻人的精神,以薪比喻人的身体。
佛家讲道也类似寓言和譬喻的方法,都属于譬喻量。《佛学大词典》说:“譬喻量,即以譬喻方式显示教法。”⑯譬喻本为佛教十二分教之一,印度音译为“阿波陀那”(Aupamya),是佛教中重用的言教方式,譬喻量在佛经中随处可见。如《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⑰。这是譬喻人生的空幻与无常。再如《无量寿经》:“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若须弥。自身威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⑱这是比喻菩萨的智慧、愿力、心地等诸多方面的殊胜特征。除了单纯性的譬喻,佛家也有类似庄子寓言式故事,如《百喻经》《杂譬喻经》等都是寓言的形式言说佛家义理。寓言的本质也属譬喻方式,所以也是譬喻量。譬喻量同比量一样,都作用于人的思维,都属于现量之外的重要说理方式。在《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中指出了譬喻量的作用:
尔时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义,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⑲
这段话是佛陀对舍利弗说的。意思是:我先前不是已言明,十方诸佛以种种因缘譬喻、巧妙之辞说、方便法门,莫不为了无上正等正觉而说法吗?只为教化众菩萨故,而说各法之因缘,我现在以譬喻解释这道理,有智慧者就可从喻中领略其中之奥旨。《妙法莲华经》中的这段话强调了譬喻量是开释佛家义理、引领修学者悟道的重要方式。
总之,佛家的比量、譬喻量与现量不同,现量是悟道都亲证道境的真实体验,而比量、譬喻量则是作用于普通人的逻辑思维,使之从道理的层面去领会义理与方法。《庄子》一书中的大量语言都属于比量和譬喻量。《大宗师》中说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可传与可得者,是义理与方法,是比量或譬喻量;不可传与不可爱者属现量,必须通过心斋、坐忘等修学途径,达到体道境界而亲证。
综上所述,通过佛家量论与庄子道言关系的比较与印证,我们认为,所谓的庄子“道言悖论”其实是不存在的。庄子《知北游》中“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指的是体道者亲证的玄妙道境,是不可言说的;正如佛家的觉悟证道之境,是无法言说的现量境。而《庄子》一书所言内容大都是讲述道之理与道之法,如同佛经讲法一样,属于比量和譬喻量。真正的道是不可言的,所言的并不是道本身,而是导入道的途径与方法,所以又不得不言。正所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筌只是导入体道之途的工具符号而已。进一步说,庄子的道言关系问题的本质,也正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早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触及到了西方哲学近世才重点思考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⑳维氏在20世纪初意识到语言对人类认识的限制,而庄子则早就告诉人们,语言之外的世界可以体验,只是需要亲证,而无法言传。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0页。
②索达吉堪布《量理宝藏论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251页。
③④南怀瑾《楞伽大义今释》(《南怀瑾选集》第五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页,第657页。
⑤丁福保《坛经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⑥[宋]释延寿《宗镜录》(卷第四十九)[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页。
⑦[印度]陈那《集量论略解》(卷二)[M],沙门法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⑧⑫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7页,第247页。
⑨《中华大藏经》(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33页。
⑩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A],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3页。
⑪[隋]智凯《童蒙止观》[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⑬⑯丁福保《佛学大词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第2135页。
⑭⑱《净土五经一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第32页。
⑮⑰丁福保《金刚经笺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67页,第156页。
⑲《妙法莲华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⑳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9页。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庄子道与言的关系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5]第1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