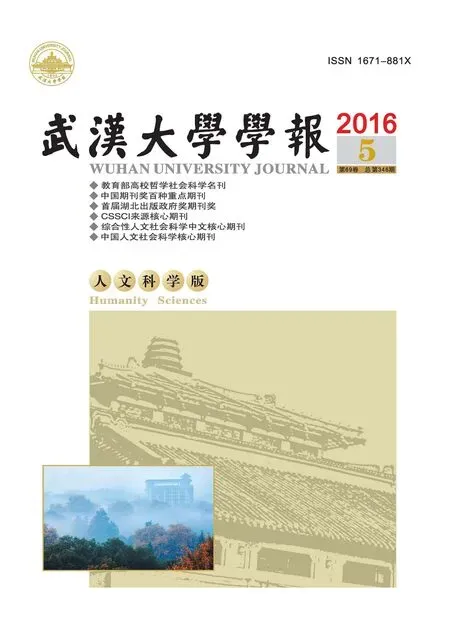论钱钟书的神韵观
——兼与曹顺庆先生商榷
2016-09-28刘涛
刘 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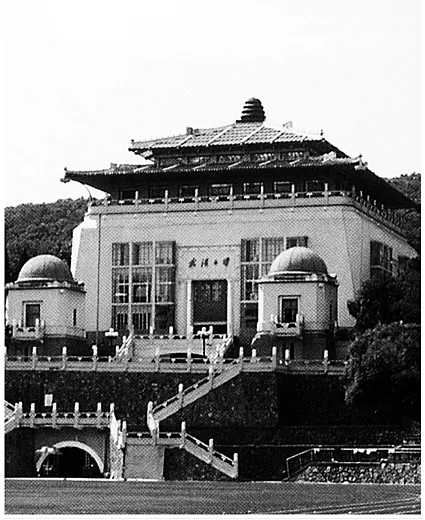
论钱钟书的神韵观
——兼与曹顺庆先生商榷
刘涛
曹顺庆先生认为,钱钟书多处征引《沧浪诗话》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一语,既弄错了“神韵”的时代和出处,也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事实上,钱钟书认为“神韵”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优游痛快,各有神韵”。按照钱钟书对“神韵”的理解,《沧浪诗话》已经阐明了“神韵”的核心内涵。这一论断直接关系到钱钟书对《沧浪诗话》学术价值的判定,也关系到钱钟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总体评价。因此,对钱钟书而言,这是一个很难改动的“大判断”。
钱钟书; 曹顺庆; 《沧浪诗话》; 神韵观
“神韵”是中国古典诗论的一个核心范畴。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借朋友郑朝宗之口断言“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第108页。,并多处征引《沧浪诗话》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一语。然而,《沧浪诗话》从未提及“神韵”这个术语。曹顺庆先生、郑澈博士在《钱钟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以下简称曹文)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钱钟书误解了《沧浪诗话》:“其一,钱钟书认为南宋的严沧浪提出了所谓‘神韵’,从文献上考证,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其二,钱钟书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而由于钱钟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对学界事实上构成一定程度的误导。”*曹顺庆、郑澈:《钱钟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第118页。以下凡曹先生的观点均引自该文,不再专门注释。曹文认为钱钟书的论断在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难以成立,“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笔者确曾有过相同的疑问,也曾认同曹先生的观点。但是,反复研读钱著之后,笔者对曹先生的结论又产生了怀疑。依笔者浅见,“神韵”一语虽然在《沧浪诗话》中查无实据,但钱钟书的“误解”却是事出有因。本文认为,按照钱钟书对“神韵”的理解,严羽的确已经道出了“神韵”的核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并没有误解《沧浪诗话》。
一、 对“钱钟书致曹顺庆书信”的不同解读
曹先生在文中透露,他曾在1985年写信给钱钟书,“指出宋代的严羽是没有提出‘神韵’的,希望钱钟书能够在《谈艺录》再版之时改正过来”。钱钟书回信说:
拙著承勘订引文误漏,极感精心惠意。诸例皆在拙著旧本中,此类必当不少。旧本未用新式标点,当时意欲仿古人引文之旧习,求意足便了,不惮删节。此番重印,加新式标点,便见割裂矣。渊明诗云:“所云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一叹。按照曹先生的说法,钱钟书在“信中承认这是一个失误”。但是,笔者对这封信的理解却有些不同。第一,钱著所引“诗之有神韵者”确属字句讹夺,但并非由于轻心失检所致。《谈艺录》《管锥编》皆为“忧患之书”,征引中外文献数千种,引文误漏之处甚多。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信中也谦虚地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后面的解释却并非针对一般的“引文误漏”而发,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钱著的著述体例上承宋元以来的诗话和笔记传统,顺带将古人征引文献“以意为之”的习气也承袭过来。钱氏所引“诗之有神韵者”见于初版《谈艺录》,又见于《管锥编》“说‘韵’”条。这两处征引时隔几十年,皆有删节字句、改易语序的情况,即所谓“当时意欲仿古人引文之旧习,求意足便了,不惮删节”。《沧浪诗话》不是稀见文献,钱钟书亦曾多处提及“入神”,之所以用“神韵”替代“入神”*参见钱钟书:《谈艺录》,第109、265、514、642、677页。,乃是以己意为之。第二,钱钟书有世故的一面,信中“所云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云云是客气话,没必要太当真*参见孙玉祥:《如何读钱钟书的信》,载《书屋》2005年第1期。。当然,这也不是假话,因为确实应当感谢曹先生对引文的勘订之功。其实,钱氏的书信有时婉转曲折,含混多义,不能完全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里不妨举个例子。陈子谦评价钱钟书的文艺批评“得‘唯物辩证法’之髓”,自感颇得钱学之要领,并用钱氏写给郑朝宗的信来作旁证:“子谦同志抉剔之微,具见细心,贯穿之密,备征通识。此才未可限量,惜牛刀割鸡,用违其器,弟真受宠若惊,所谓‘感愧’者也。然‘感愧’不敌‘悚惧’……生平独学冥行,幸获知己如兄及子谦者数人,其他或则钦宝莫名其器,或则随声浮慕。”据陈先生的理解,钱钟书感到“慄慄自危”,所谓“‘感愧’不敌‘悚惧’”,原因在于“他认为评价如此之高,是将自己与马、恩、毛相提并论了”*陈子谦:《我与“我们仨”——读杨绛〈我们仨〉》,载《新时代论坛》2005年第3期,第80页。。然而,在给汪荣祖的信里,钱氏却批评说:“于区区手眼,尚未窥识。弟之所谓辩证法,本于老庄禅宗及黑格尔,乃马克思所斥唯心的辩证法。书中直言不讳,诸君以唯物的辩证法品目之,使弟受宠若惊而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矣。”*《钱钟书与汪荣祖书》(1985年3月12日),载《钱钟书诗文丛说——钱钟书教授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300页。或许,我们对钱氏的书信是有必要思量再三的。第三,钱钟书说严羽开了“神韵派”*参见钱钟书:《谈艺录》,第677页。钱钟书笔下的“神韵派”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严羽开创的诗论流派,见于《谈艺录》《宋诗选注》;二是指以王、韦为代表的神韵诗派,缩写为“神韵派”,仅见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有其内在的逻辑可循。钱氏对“神韵”有独特的理解,对以“神韵”谈艺的源流也梳理甚详。他很可能认为虽然清人王渔洋明确标举“神韵说”,但是南宋的严羽已经道出了“神韵”的核心内涵,只是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这正是下文要证明的核心问题。另外,钱氏自号“文改公”,并不介意改正过往的错误。《谈艺录》(补订本)在1984年出版以后,他又多次“补正”是书,却始终没有修正曹先生所说的失误,恐怕另有缘由。如此看来,“求意足便了”一句才是理解这封信的关键所在,曹先生可能忽略了这层意思。
二、 钱钟书释“神”“韵”“神韵”
古人对“神韵”这个概念似乎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对其理论内涵、适用范围等问题往往不说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无形中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按照王小舒的观点,“神韵”有广义狭义之分*参见王小舒:《神韵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王渔洋倡导“神韵说”,论诗以“清远”为尚;郭绍虞说:“由后天言,所谓神韵,又是所谓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之意”*郭绍虞:《神韵与格调》,载《燕京学报》1937年第22期,第103页。;吴调公认为神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吴调公:《神韵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以上诸论皆侧重于“优游不迫”,故可称作狭义的神韵观。比较而言,胡应麟以花喻诗,认为“色泽神韵,犹花蕊也”,“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6页。;翁方纲曰:“神韵乃诗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翁方纲:《坳堂诗集序》,载《复初斋文集》卷三,清李彦章校刻本。,“徹上徹下,无所不该”*翁方纲:《神韵论》,载《复初斋文集》卷八,清李彦章校刻本。;钱钟书指出:“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尽善尽美”,“优游痛快,各有神韵”*钱钟书:《谈艺录》,第109页。。以上诸家对神韵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神韵是各种风格的好诗都能够达到的境界,故可称作广义的神韵观。
借助新近的相关研究,曹文简要梳理了“神韵”和“神韵说”的理论渊源,认为“在中国古代‘神韵’理论的发展史中,严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文论中的‘神韵’这一概念提法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因此,“严羽的诗论主张是‘神韵’说的理论来源之一,但并不等于‘神韵’说”。“到清初王渔洋总结了历代主张清远之韵的论述,概括为‘神韵’说,并自觉地加以申说发挥,‘神韵’说这才最终被诗坛广为接受,因此王士禛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神韵’说的倡导者。”据此推测,曹先生大概是以王渔洋的“神韵说”作为标准去衡量钱钟书的神韵观,殊不知钱钟书对“神韵说”有过相当激烈的批评,并不认可王渔洋的所谓“神韵”。从根本上说,曹先生与钱钟书对“神韵”内涵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差异,故而认为钱钟书误解了《沧浪诗话》。这里有必要首先厘清钱钟书对“神”“韵”及“神韵”三个相关概念的界说,然后在此基础上去辨析他对《沧浪诗话》的阐发以及对“神韵”渊源的考证。
(一) 钱钟书释“神”
钱钟书通过《庄子》之论“神”区分了古代文论中“神”的两种含义,并分别与佛教、宋代理学、西方哲学和美学概念进行平行比较,对“神韵”之“神”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因钱氏之论散见于著述中,涉及中外资料太多,读来颇为缠杂,故此处代为分辨而使之明朗*相对比较集中的论述可参见钱钟书:《谈艺录》,第111~113、666~668页。。
《庄子·在宥》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这段话的主旨是“绝圣弃智,天君不动”,即放弃感官的知觉。此处的“神”以耳目为用,与“形”相对,近似于宋学家所谓知觉血气之心,《文子·道德》篇中“以耳听之”的“下学”,《法藏碎金录》中的“觉触之觉”*参见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年,第218页;《大藏经补编》第27册,(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735页。,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Soul(与Mind相对)、Seele(知觉)。

英语中有Spirit一词,通常被译作“精神”。钱钟书指出,切不可望文生义地把西方文评所谓Spirit等同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神”或“神魄”。Spirit跟Letter相对,“所谓精神完全是指文章思想或意义方面的事,而我们所谓‘神采奕奕’、‘神韵盎然’,一望而知是指的文章风格”*钱钟书:《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7年,第63页。。对照而言,Spirit近似于宋学家所谓义理之心,《文子·道德》篇中“以心听之”的“中学”,《法藏碎金录》中的“觉悟之觉”;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Mind(理智,与Soul相对)、Vernunft(理性),白瑞蒙所云Animus ou l’esprit(智巧之心)。Spirit可以译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意”,“即‘意在言外’、‘得意忘言’、‘不以辞害意’之‘意’字”*钱钟书:《谈艺录》,第111页。朱光潜在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认识的心灵’(cognitive spirit):克罗齐所用的Lo spirito,英译即用spirit,中译通常为‘精神’。这个字与德文的geist相同,与英文mind相当,应译为‘心’或‘心灵’。spirit源于拉丁,本意为‘呼吸’。古人迷信人的神魂就是呼吸的气,人死了,气断了,神魂就随之飞散,因此spirit又有‘神魂’的意思。”参见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39页。。按照这种理解,诗歌仅具“言外之意”、绘画仅能“意余于象”而未能诉诸直觉,则尚未达到“神韵”的境界。
(二) 钱钟书释“韵”
钱钟书认为神韵的“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本取譬于声音之道”*钱钟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4页。。他指出北宋范温“论韵”之文“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并推断说“严羽必曾见之,后人迄无道者”*钱钟书:《管锥编》,第2121、2122页。。范温依次否定了“不俗之谓韵”“潇洒之谓韵”“生动之谓韵”“简约之谓韵”的说法,下结论说“有余意之谓韵”。“有余”与“不足”相反相成,“有余”乃源自“不足”。唯诗文中言之不尽,方能生出言外之意。钱钟书称赞范宽“论韵”“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钱钟书:《管锥编》,第2124页。。
钱钟书还广泛征引了古印度及西方艺术理论对“因隐示深、由简至远”的论说,指出“古印度说诗,亦有主‘韵’一派,‘韵’者,微示意蕴,诗之‘神’髓,于是乎在。西方古师教作文谓幽晦隐约则多姿致,质直明了则乏趣味”*钱钟书:《管锥编》,第2119页。。音乐之“余音遗响”与绘画之“意余于象”、诗文之“含蓄省略”一脉相贯,实为同一艺术原理在不同艺术门类里的体现。钱钟书“综会诸说,刊华落实”,将神韵之“韵”解说为:
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曰“取之象外”,曰“略于形色”,曰“隐”,曰“含蓄”,曰“景外之景”,曰“余音遗味”,说竖说横,百虑一致。*钱钟书:《管锥编》,第2118页。此处尤须注意与神韵之“韵”异名同指的“含蓄”。钱钟书论“言外之意(extralocution)”,有“含蓄”与“寄托”之辨。“含蓄”是指“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钱钟书:《管锥编》,第186页。按:extralocution是钱钟书自创的一个英文单词。。“不尽之意”之于“诗中之言”,如形神难离,顺诗利导即可领会。那么,诗歌的“不尽之意”究竟指什么?“夫言情写景,贵有余不尽。然所谓有余不尽,如万绿丛中之著点红,作者举一隅而读者以三隅反,见点红而知嫣红姹紫正无限在。其所言者情也,所写者景也,所言之不足,写之不尽,而余味深蕴者,亦情也、景也。”*钱钟书:《谈艺录》,第562页。也即是说,“有余不尽”之意并非抽象的道理或者说教,而是诗中之“情”“景”的余味深蕴。
钱钟书论“韵”而诗画通论,基本观点也深受范宽的影响。他认为依稀隐约的写意画与刻画细谨的工笔画皆可产生“画尽意在”“意余于象”的审美效果*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135~1140、2116~2117页;钱钟书:《谈艺录》,第509~512页。;与之相类,优游不迫的“神韵诗”与沉着痛快的“非神韵诗”皆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概言之,“含蓄”是一种具有通约性的艺术风格,不能将其局限于南宗写意画与王韦一脉的“神韵诗”中。
(三) 钱钟书释“神韵”
我们将钱钟书对“神”“韵”的解说综合起来,发现诗、画、乐要达到“神韵”的境界,至少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余音遗响”,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隐露立形”“袅袅不绝”的效果;第二,超绝语言文字、笔墨形迹、音响节奏,最终可诉诸“不可明言”的直觉。然而,“神韵”绝非是虚无缥缈的空寂之境。就诗而言,“神韵不尽理路言诠,与神韵无须理路言诠,二语迥殊,不可混为一谈”,“去理路言诠,固无以寄神韵也”*钱钟书:《谈艺录》,第242、237页。。这样说来,对“神”的体悟来自于对“韵”的领会*吴调公对于“神”与“韵”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神与韵,原来是浑然一体。但细细分析起来,却有一个由‘神’生‘韵’的过程。”参见吴调公:《神韵论》,第24页。。古人曾赋予“神韵”许多神秘色彩,往往说得玄乎其玄。通过贯通中外艺术理论,钱钟书截断众流,明确把“神韵”解说为:
宋人言“诗禅”,明人言“画禅”,课虚扣寂,张皇幽眇。苟去其缘饰,则“神韵”不外乎情事有不落言筌者,景物有不着痕迹者,只隐约于纸上,俾揣摩于心中。以不画出、不说出示画不出、说不出,犹“禅”之有“机”而待“参”然。*钱钟书:《管锥编》,第2118页。
尝试把这段话与《沧浪诗话·诗辩》中的语句两相对照,不难见出它们的一致之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只是说不以议论为诗,不以文字为诗,并非禅宗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同样,‘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并非说好诗产生的美感像佛经所说‘如幻如梦’的‘虚妄见’,只是说这种美感可以体会而难于分析;因为‘空中之音’分明听得见的,尽管瞧不到,‘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也确实瞧得见的,尽管捉不着。”*钱钟书:《宋代的诗话》,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88页。严羽“一意数喻”以避免读者囿于一喻而生执着,目的是要说明好诗达到的心理效果是超越思虑见闻的“无迹可求”,这正合于钱钟书对“神韵”之“神”的解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得更加明白,简直就是“神韵”之“韵”了。通俗点说,严羽“开了所谓‘神韵派’,那就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7年,第434页。。另外,《谈艺录》中有如下二语:“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诗至李杜,此沧浪所谓‘入神’之作”*钱钟书:《谈艺录》,第109、248页。。显然,钱氏已将“入神”与“神韵”等同视之。二者“貌异心同”*“貌异而心同”“貌同而心异”出自刘知几《史通·模拟》篇。钱著中经常使用这一对隐喻。其中,论及“貌异心同”的内容,可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36、87、161、442、806、1187、1568、1932、2405页;钱钟书:《谈艺录》,第155、261、656页。,是异名同指的关系,正所谓“可名非常名”。因此,这里不妨得意忘言。曹先生说“即使按钱钟书广义的‘神韵’概念来衡量的话,严羽也没有在《沧浪诗话》中提出钱钟书所谓‘神韵’的,钱钟书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确错了”。这个判断恐怕失之武断,并未真正理解钱钟书的本意。
正是基于对“神韵”内涵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在梳理以“神韵”谈艺的源流时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标准。“画品文评先后同标‘神韵’,将无如周人、郑人之同言‘璞’而一以名玉、一以名鼠耶?尝观谢赫以至严羽之书,虽艺别专门,见有深浅,粗言细语,盍各不同,然名既相如而复实颇相如者,固可得而言也。”*钱钟书:《管锥编》,第2116页。这里是说古人虽常以“神韵”谈艺而言人人殊,但在某些方面也还能有相通之处。钱氏旁征博引,论说颇繁,此处只取谢赫、张彦远与司空图为例。他认为吾国以“神韵”谈艺始自南朝谢赫,《画品》中“神韵”与“气韵”同指,皆为“‘韵’之足文申意,胥施于人身”*钱钟书:《管锥编》,第2113页。。第一,谢赫之言“气韵”主要着眼于人物画,“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以‘生动’诠‘气韵’,尚未达意尽蕴,仅道‘气’而未申‘韵’也”*钱钟书:《管锥编》,第2112、2126页。。第二,谢赫之言“神韵”与“气韵”通为一谈,“神”即“韵”,指有别于可见形体的容止风度。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数言“气韵”,亦与“神韵”通为一谈,强调绘画须生动传神而不应“空陈形似”,实近于谢赫之“气韵”。概言之,谢赫、张彦远“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钱钟书:《管锥编》,第2126页。,“皆指作画时之技巧,尚未知物之神必以我之神接之”*钱钟书:《谈艺录》,第141~142页。,皆未道及直觉之“神”。但是,钱钟书也肯定了谢赫的开创之功,“严羽所倡神韵不啻自谢赫传移而光大之”*钱钟书:《管锥编》,第2112页。,而真正以“神韵”论诗而开沧浪之先河的是晚唐司空图。钱氏早年下论断曰:“《与李生论诗书》所谓:‘味在酸咸之外,远而不尽,韵外之致’,即沧浪之神韵耳”*钱钟书:《谈艺录》,第514页。;晚年之论说愈加细密,指出“象外之象”“生气远出”(“气”者“生气”,“远出”为韵)诸语重在说“韵”,“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句则重在说“神”。钱钟书总结说:“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钱钟书:《管锥编》,第2126页。若根据他对严羽的评价看来,这里不妨再添补一句,“沧浪毕其功而总其成”。
三、 钱钟书论严羽的理论贡献及“神韵说”
在《谈艺录》的补订部分,钱钟书说:“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钱钟书:《谈艺录》,第683页。“上庠师宿”大概是指民国时代的朱东润、郭绍虞、方孝岳等数位学者。朱东润认为沧浪之论出自司空图,“以禅喻诗,最易倾听,核诸名实,往往不能相合”,其病在“以深微譬粗浅”*朱东润:《沧浪诗话参证》,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1年第4期,第706页。;“平情论之,沧浪之评,要不失为名家,若遽以大家许之,殊未能称”*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按:是书初版于1944年。。方孝岳认为:“严羽以禅喻诗,在根本上已经差以毫厘,而又专在‘境’上立言,所谓‘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这种玄之又玄的境界,也令人难以理会。”*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7年,第172页。按:是书初版于1934年。他们普遍认为《沧浪诗话》沿袭前人成说,并无多少创见;“以禅喻诗”则多有弊病。钱钟书所说的“李光照”当为“李光昭”,是嘉庆年间的一位小名家。所谓“一拳打蹶”,是指李光昭读书不细而误于俗说,其《诗禅吟示同学》一诗自命正沧浪之失,而其议论实合于沧浪*参见钱钟书:《谈艺录》,第637页。。此处所举“李光昭”当是泛指,意在隐晦地批评当时否定《沧浪诗话》价值的学术风气。其中,民国时代“一拳打蹶”沧浪者,当非郭绍虞先生莫属。
郭先生在1937年所撰长文《神韵与格调》中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两部著作,一部是《文心雕龙》,一部是《沧浪诗话》,都极得一般庸人的称赞,实则由见解言,都没有什么特见。他们都不过集昔人之成说,而整理之,使组织成一系统而已。”*郭绍虞:《神韵与格调》,第59页。郭先生在“沧浪以前之诗禅说”部分胪列出昔人之论,以说明“禅悟之义,原不始于沧浪”。郭先生将沧浪之“诗禅说”分作两途:一是“以禅论诗”,即所谓“不涉理路”“羚羊挂角”云云,“其说与以前一般的诗禅说同”;二是“以禅喻诗,乃是以学禅的方法去学诗,所以与禅有关”,“这才是沧浪的特见”*郭绍虞:《神韵与格调》,第64、62页。。与之对应,沧浪之所谓“悟”,亦分作两义:一是透彻之悟,“由于以禅论诗,只是指出禅道与诗道有相通之处,所以与禅无关”;二是第一义之悟,“由于以禅喻诗,乃是以学禅的方法去学诗,所以与禅有关”*郭绍虞:《神韵与格调》,第64页。。
从《谈艺录》对《沧浪诗话》的论说看来,钱钟书与时贤,尤其是与郭先生论辩的意图非常明显。钱钟书评价说:“仪卿之书,洵足以放诸四海、俟诸百世者矣。”*钱钟书:《谈艺录》,第682页。这样的语句在《谈艺录》中极其罕见,揄扬之情溢于言表。郭、钱两位先生之所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根源在于他们对“以禅喻诗”(即郭先生之“诗禅说”)的理解与阐发存在较大的分歧。
钱钟书认为沧浪“以禅喻诗”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用“神韵”来品评诗歌。“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并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超绝语言文字。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钱钟书:《谈艺录》,第642页。明白点说,严羽的创举在于“指出好诗产生的心理效果是‘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读者获得的感觉就仿佛参禅有悟的境界”*钱钟书:《宋代的诗话》,第688页。。纵向地与前人相比,沧浪较司空图更进一步,将“神韵”与参禅联系起来,“挂了禅的招牌,就仿佛文艺理论在一个有势力的思想体系里打下基础,创作的心理活动和作品的心理效果可以不费力地贯串起来”*钱钟书:《宋代的诗话》,第688页。。横向地与西方诗论相比,沧浪之论神韵与白瑞蒙的神秘主义诗论及象征派论“诗妙入乐不可言传”等观点“宏纲细节,不约而同,亦中西文学之奇缘佳偶也哉”*钱钟书:《谈艺录》,第682页。。正是基于此,钱钟书肯定了《沧浪诗话》的学术价值。
对于沧浪将学诗比作参禅的“以悟论诗”,钱钟书也认为这是宋人的常谈,意在强调作诗之参悟工夫,“比之参禅可也,比之学道学仙,亦无不可也”*钱钟书:《谈艺录》,第641页。。“妙悟”也并不神秘,不过是学道学诗的平常境界。沧浪虽主张“妙悟”,但也强调“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说得本圆融周匝。后人舍诗书而空言妙悟,误解了沧浪。不过,钱钟书也坦率地承认“妙悟”之说滋生了后来的学步之弊,“单就这一点说,‘以禅喻诗’是个很蹩脚的比喻,因为禅宗提倡‘得无师之智’,不但否认妙悟会从师法古人得来,而且以为学习经典只产生教条,不会引起妙悟”*钱钟书:《宋代的诗话》,第687页。。曹先生说“严羽的‘妙悟’观主要就‘妙悟’这一层面把诗的创作与参禅作了类比,并不是将禅与诗的一切层面进行类比”,因此认为钱钟书说严羽“通禅于诗”“其实是钱钟书对严羽的一个误解”。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钱钟书所谓“通禅于诗”,是说严羽把创作的心理活动和作品的心理效果贯穿起来,并不是说严羽将禅与诗的一切层面进行类比。“‘借禅以为喻’与其说是一项美学原则,毋宁说是一种宣传策略;‘借’和‘喻’这两个字是不容忽略的。”*钱钟书:《宋代的诗话》,第689页。如果再参照他对“引喻取分”*参见钱钟书:《谈艺录》,第32、133页;钱钟书:《管锥编》,第69、1774页;《钱钟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的论说,则更为圆通。第二,钱钟书也承认以禅喻诗“意过于通”,严羽谈禅论诗都有些错误,但是说“招钝吟之纠谬,起渔洋之误解”并非是批评严羽,而是指“渔洋未能尽沧浪之理,冯班《钝吟杂录·纠谬》一卷亦只能正沧浪考证之谬”*钱钟书:《谈艺录》,第526页。。
王渔洋倡导“神韵说”,算得上是严羽的隔代传人。郭先生认为:“沧浪只论一个‘神’字,所以是空廓的境界,渔洋连带说个‘韵’字,则超尘绝俗之韵致,虽犹是虚无飘渺的境界,而其中有个性寓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载《小说月报》1928年第1~6期,第133页。渔洋神韵之说虽不免有些空寂,但“渔洋所论并非全属空际飘渺之谈”,“所以空寂不足为渔洋病,不足为神韵之说病”*郭绍虞:《神韵与格调》,第109、110页。。与郭先生相比,钱钟书对“神韵说”则持批评态度,认为“神韵说”改变了“神韵”的理论内涵,只将其视作诗品中之一品。渔洋论诗主清远一派,“知淡远中有沉着痛快,尚不知沉着痛快中之有远神淡味,其识力仍去沧浪一尘也”*钱钟书:《谈艺录》,第109页。。也即是说,按照“神韵说”的审美趣味来品评,“写景工密的诗、叙事流畅的诗、说理痛快的诗都算不得‘风骚流别’里的上乘了”*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7年,第21页。。因此,“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钱钟书:《谈艺录》,第109页。。曹先生推论说:“王渔洋讲‘神韵’时,常常提到严沧浪,这也许正是钱钟书致误的重要原因。”显然,这种说法没有顾及钱钟书对“神韵说”的批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短诗才能有神韵。这种误解与严羽有关,“沧浪才力甚短,自有侧重近体之病;故《诗法》篇谓:‘律难于古,绝难于律。’”*钱钟书:《谈艺录》,第507页;另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第434页。袁枚受到沧浪的影响,认为短诗可借助“半吞半吐”而得弦外之音,而长篇很难有“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之“神通”*参见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73页。。郭先生说袁枚“以为神韵说只是小神通,七古长篇五言百韵便无须乎此,则道个正着”*郭绍虞:《神韵与格调》,第70页。。与之相反,钱钟书批评袁枚是“浅尝妄测”,原因有二:第一,“长篇不尽神韵,非不须神韵,是则所谓‘难’者,篇幅愈短,愈无回旋补救余地,不容毫厘失耳。”第二,“长短乃相形之词。沧浪不云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意若曰:短诗未必好,而好诗必短,意境悠然而长,则篇幅相形见短矣。”*钱钟书:《谈艺录》,第507~508页。因此,诗歌之“神韵”与篇幅之长短并无直接关系,短诗可能有声嘶力竭之病,长诗亦可有“篇终接混茫”之感。
郭先生似乎轻信了所谓“五城十二楼”之类的说法,故而对渔洋的“妙悟”之说颇为赞赏*参见郭绍虞:《神韵与格调》,第102~103页。。钱钟书却尖锐地指出:“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磨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钱钟书:《谈艺录》,第233页。郭绍虞后来改变了对渔洋“妙悟”的看法,认为钱钟书这段话“正中渔洋病痛。后来学作神韵诗者亦往往坠入肤廓空滑恶习,即此关系。”参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6页。他认为渔洋作诗多出于惨淡经营,空言妙悟乃是为了掩饰才薄,实在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欺人之举,遂滋生末流“失调”之弊*参见赵执信:《谈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页。,使后学以为可以捐思废学、空诸依傍,徒依“妙悟”而作诗,“妙悟云乎哉,妙手空空已耳”*钱钟书:《谈艺录》,第233页。王渔洋作诗刻苦之情状,可参见田同之:《西圃诗说》,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0页。。
钱钟书对“神韵说”及袁枚的批评重在说明“神韵”是各种风格的中国古典诗歌都有可能达到的一种境界,并不拘囿于“神韵诗派”和短诗。但是,钱钟书并没有回答《沧浪诗话》为何只以“入神”许李杜而不列王孟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疏漏*参见严羽:《沧浪诗话校笺》,张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谈艺录》的研究范围以清末民初为下限,似乎只是一部谈古之作。其实,是书对民国学者的著述常有论难之处,只是极少指名道姓而已。从钱钟书与郭绍虞对《沧浪诗话》与“神韵说”的阐发与评价来看,他们的主要观点确实是针锋相对的。钱、郭二先生的学术论争由来已久,分歧也不限于“神韵”一题。钱钟书《论复古》(1934)曾尖锐地批评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郭先生也很快以《谈复古》(1934)做了回应;《谈艺录》(1948)与《论性灵》(1938)*郭绍虞:《论性灵》,载《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第47~92页。对《随园诗话》与“性灵说”的解说与评价也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如此说来,钱钟书对郭先生的著述相当熟悉,上文所言“上庠师宿”应当包括了郭先生在内。
四、 结 语
总的说来,钱钟书持有一种广义的神韵观,故而将“神韵”的提法归于严羽。如果要证明钱钟书误解了严羽,就必须先要推翻他对“神韵”的界定,这殊非易事。对钱钟书而言,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判断”*参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915页。,很难轻易改动。首先,这个论断直接关系到钱钟书对《沧浪诗话》的理解与评价问题。他认为严羽通禅于诗,沟通了“妙悟”(创作的心理活动)与“神韵”(作品的心理效果)。论“神韵”而将悠游不迫与沉着痛快并举,故无偏废之弊;倡“妙悟”而不废诗书,并无空寂之病。如果将这些观点放到民国学术史中去考察,那么钱钟书对《沧浪诗话》的褒扬实在是“有所为而发”。在后来的著述中,他依然坚持了这样的看法:“整个宋代没有第二部诗话像它那样系统完整、纲领鲜明、议论痛快而富于含蕴,酲人耳目而又耐人思索。”*钱钟书:《宋代的诗话》,第689页。其次,这个论断还关系到钱钟书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总体评价。既然严羽以“入神”许李杜,则渔洋仅推崇王、韦一派的“神韵诗”就显得狭隘了。事实上,钱钟书认为“神韵诗派”在旧诗史上算不得正统,王维只能算“小的大诗人”,韦应物则只是“大的小诗人”;杜甫才是旧诗的“正宗”“正统”,一直是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诗圣”*参见钱钟书:《七缀集》,第21~26页;《钱钟书英文文集》,第286~287页。。推衍开去,“词气豪放的李白、思力深刻的杜甫、议论畅快的白居易、比喻络绎的苏轼”皆可有“入神”之作,那么神韵就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另外,这个论断还关乎他对“言意之辨”“言外之意”“含蓄与寄托”等问题的论说,这里不再展开。
曹先生的文章已发表有年,但迄今未见有回应者。本文并非是要将曹先生所持的狭义神韵观与钱钟书所持的广义神韵观一较高下,只是认为以前者为标准去衡量后者,可能会得出不太妥当的结论;本文梳理和对比了钱钟书与郭绍虞等前辈学者在阐发和评价《沧浪诗话》时的学术分歧,也并非是要厚此薄彼,只是想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澄清这个学术公案的本来面目。需要特别申明的是,笔者并非是要以钱钟书的是非为是非,想要借抬高研究对象的价值来增加本文的分量,只是希望在钱著的“语言天地”中来考察钱钟书将“神韵”归于严羽这一论断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
●作者地址:刘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Email:ltccnu@126.com。
●责任编辑:何坤翁
◆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5102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