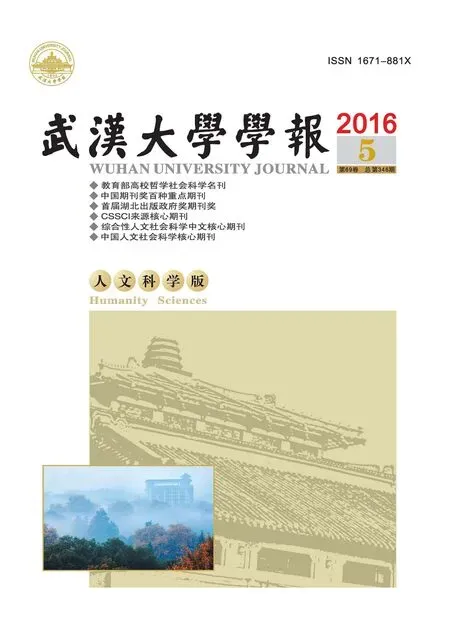再论钱钟书对“神韵说”的误解
2016-09-28曹顺庆芦思宏
曹顺庆 芦思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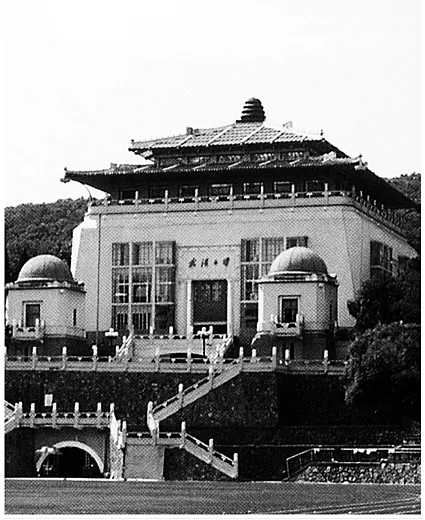
再论钱钟书对“神韵说”的误解
曹顺庆芦思宏
钱钟书论“神韵”存在着两方面的误解。其一,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多次征引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但据《沧浪诗话》原文考证,这在文献上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其二,钱钟书在著作中论述的“神韵”,并非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而是严羽主张的“入神”,二者虽有理论上的继承关系,但并非是同一概念,因此钱钟书混淆了二者的理论内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不能仅在钱著的语言世界中阐释其论述的合理性,更不能将钱钟书的文献资料错误解释成正确的,而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分析“钱钟书论神韵”这一问题的失误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中蕴含的理论意义。
钱钟书; 神韵; 《旧文四篇》; 《谈艺录》; 《管锥编》
一、 问题的缘起
“神韵”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从《旧文四篇》到《谈艺录》再到《管锥编》,钱钟书始终关注这一问题。在1984年版的《谈艺录》中,他写道 :“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几通无字天书。以禅拟诗,意过于通,宜招钝吟之纠缪,起渔洋之失误。”*钱钟书 :《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100页。当笔者阅读到此处时产生了疑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实之中,“神韵”说产生于宋代以后,定型于清代的王士禛处,为何钱钟书把“神韵”归于宋代的严羽?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神韵”的产生年代将大大提前。笔者仔细核查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全文,发现并没有“诗之有神韵者”这一句,显然,钱先生在此句的引用上出现了谬误。出于慎重起见,1988年笔者特向钱钟书先生致信,指出这一错漏之处,希望钱先生在《谈艺录》再版之际对此加以改正。钱钟书回信说 :
顺庆先生著席 :奉到来函并新年贺柬,贱躯迄今尚未痊愈。拙著承勘订引文误漏,极感精心惠意。诸例皆在拙著旧本中,此类必当不少。旧本未用新式标点,当时意欲仿古人引文之旧习,求意足便了,不惮删节。此番重印,加新式标点,便见割裂矣。渊明诗云 :“所云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一叹。
钱钟书信中谦虚地承认了这个失误,但在多年后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改正,以致笔者所担心的“以讹传讹”大量出现。不得已,2011年笔者在《学术月刊》发表《钱钟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一文,论述《谈艺录》《管锥编》两书引证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是文献上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并进一步指出钱钟书对于“神韵”的相关论述,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及其理论渊源。论文发表多年,学术界并无异议。直到2016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收到刘涛先生的投稿《论钱钟书的神韵观——兼与曹顺庆先生商榷》。鉴于该作者要求商榷的话题仍有讨论的必要,编辑部希望笔者能够回应,以便推进“神韵说”的相关讨论。
笔者认为刘涛先生有勇气,文章写得也有深度。他勇于思考,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虽然笔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愿意与刘涛先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韵”问题,是一个不得不辨明的重要问题。如果严羽《沧浪诗话》就已经提出了“神韵说”,那么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必须改写,所以有必要再写这篇商榷论文。当然,笔者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引起学界对“钱钟书论神韵”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因而搦笔和墨,回应商榷。
首先,刘涛先生在论文中指出 :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借朋友郑朝宗之口断言“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并多处征引《沧浪诗话》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一语。然而,《沧浪诗话》从未提及“神韵”这个术语。曹顺庆先生、郑澈博士在《钱钟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以下简称曹文)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钱钟书误解了《沧浪诗话》 :“其一,钱钟书认为南宋的严沧浪提出了所谓‘神韵’,从文献上考证,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其二,钱钟书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而由于钱钟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对学界事实上构成一定程度的误导。”曹文认为钱钟书的论断在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难以成立,“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笔者确曾有过相同的疑问,也曾认同曹先生的观点。但是,反复研读钱著之后,笔者对曹先生的结论又产生了怀疑。依笔者浅见,“神韵”一语虽然在《沧浪诗话》中查无实据,但钱钟书的“误解”却是事出有因。本文认为,按照钱钟书对“神韵”的理解,严羽的确已经道出了“神韵”的核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并没有误解《沧浪诗话》。*凡刘涛先生观点,均参见刘涛 :《论钱钟书的神韵观——兼与曹顺庆先生商榷》,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该文未刊稿,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编辑部提供。下面不再一一注出。
刘涛先生这段话的关键是“查无实据”和“事出有因”,并进一步推导出钱钟书的失误“并非是由文献失检和理论失据所致”这样一个结论。刘涛先生认为,钱著的著述体例上承袭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和学术笔记的传统,继承了征引文献“以意为之”的习气,所以对“诗之有神韵者”此句的征引,也是出于“己意为之”,而不是征引文献的失误(“这个文献失误并非一时疏忽所致”)。对此结论笔者是不能赞同的。
先谈“查无实据”。任何学术研究,如果“查无实据”,就必须否定,绝对不能够将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是有根有据的。笔者认为,“神韵”一语在《沧浪诗话》中查无实据,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肯定翻不了案。在文献上,错就是错,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本事将引错了的文献辩解成正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钱先生圆照博观的研究成果中,也曾出现过字句讹夺、失检错漏的错误,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校正与勘误,并取得了相关的成果。在对《谈艺录》《管锥编》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发现了某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钱钟书对于“诗禅观”“意象说”的理解均有存疑之处,以客观的角度对钱著进行分析探讨,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但是,如果不顾及客观事实,得出虽然“查无实据”却是“事出有因”的结论,并由此推导出钱钟书的失误“并非是由文献失检和理论失据所致”,这是笔者无法赞同刘涛先生的第一点。
其次,刘涛先生还指出 :
按照曹先生的看法,钱钟书在“信中承认这是一个失误”。但是,笔者对这封信的理解却有些不同。第一,钱钟书所引“诗之有神韵者”确属字句讹夺,但并非由于轻心失检所致。《谈艺录》《管锥编》皆为“忧患之书”,征引中外文献数千种,引文误漏之处甚多。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信中也谦虚地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后面的解释却并非针对一般的“引文误漏”而发,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钱著的著述体例上承宋元以来的诗话和笔记传统,顺带将古人征引文献“以意为之”的习气也承袭过来。钱氏所引“诗之有神韵者”见于初版《谈艺录》,又见于《管锥编》“说‘韵’”条。这两处征引时隔几十年,引文皆有删节字句、改易语序的情况,即所谓“当时意欲仿古人引文之旧习,求意足便了,不惮删节”。《沧浪诗话》不是稀见文献,钱钟书亦曾多处提及“入神”,之所以用“神韵”替代“入神”,乃是以己意为之。(同上)
这段话的关键之处是,“《沧浪诗话》不是稀见文献,钱钟书亦曾多处提及‘入神’,之所以用‘神韵’替代‘入神’,乃是以己意为之。”这实际上是认为钱钟书是故意引错的!“乃是以己意为之”,钱钟书先生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其著作尽管在体例上承袭了中国古代的写作方式,但其多年的留学经历也造就了他极高的西学素养,《谈艺录》和《管锥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在于钱钟书对于中西文学的汇通。因此,深谙中西方学术规则的钱钟书在文献的引用上是否会故意引错,以便求得“以己意足便了”呢?学术根底如此深厚的钱钟书先生,绝非如此轻率的人!刘涛先生将钱钟书先生的文献征引错误辩解为故意引错,这样的曲解显然是不妥当的。恰如纪昀所云 :“故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说钱先生故意引错,钱先生九泉有知,恐怕也不会认同!
第三,刘涛先生指出,钱钟书先生给笔者的回信有其隐含意义,可以进行不同解读 :
钱钟书有世故的一面,信中“所云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云云是客气话,没必要太当真。(同上)刘涛先生认为钱钟书在信中的回复多半只是客气话,没必要当真,并以钱钟书的书信往来证明其世故的一面,把钱钟书描述成一个言不由衷的世故老滑头,这是非常不妥当的,笔者认为此观点更为偏颇。通过钱钟书的生活轶事可知,其人恃才傲物,极具童心,不屑于对社会世故妥协,这种高尚的品格、简单质朴的个性也是成就其“学术昆仑”地位的重要原因。在学术上,钱钟书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言不由衷的世故滑头。笔者与钱钟书通信之际,他早已成为当时的文坛巨擘,而笔者刚过而立之年,是晚辈后学。在年纪、辈分差距悬殊的情况下,钱钟书对于笔者提出的问题是否会使用如此隐晦的“春秋话语”进行解答?显然,刘涛先生的论断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钱钟书的回信不存在歧义,刘涛先生提出的解读有断章取义、郢书燕说之嫌。
那么钱钟书对“神韵”的理解是否有误呢?笔者对此仍持原有论点。在文献的征引上,钱钟书弄错了“神韵”的出处,将“神韵”的概念归于严羽。在“神韵”的内涵上,他混淆了“入神”与“神韵”的概念核心。
二、 钱钟书“神韵说”的两个失误
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严羽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页。钱钟书在引用此句时说道 :“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钱钟书 :《谈艺录》,第100页。。对比两处引文笔者发现,《沧浪诗话》中并未出现“诗之有神韵者”一句,即严羽并未提出“神韵”这一概念,钱钟书误将“神韵”归于严羽。针对此处错漏,笔者对钱著关于“神韵说”的论述进行了仔细的校核,发现钱钟书的这一失误并非偶然,而是一以贯之地存在于其著作之中。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引用《沧浪诗话》“诗之极致有一 :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并随后展开了论述 :“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钱钟书 :《谈艺录》,第40页。可见,钱钟书将“入神”等同于“神韵”,然而二者在内涵上是否完全一致?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下文将有详细分析。又如,钱钟书说 :“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之境界,妙悟之外,尚有神韵。”*钱钟书 :《谈艺录》,第258页。“妙悟”说出于严羽,此论当无异议,而钱钟书将“妙悟”与“神韵”作为一对并列的概念来论述严羽的诗学思想,正是将“神韵”归于严羽的误解。在《管锥编》中,同样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证,如“严羽所提倡神韵不啻自谢赫传移而光大之”*钱钟书 :《管锥编》第4册,三联书店2008年,第234页。,“严羽《沧浪诗话》称‘诗之有神韵者’ :‘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钱钟书 :《管锥编》第4册,第242页。此外,钱钟书在论述“神韵”概念时,也经常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例,由此可以看出钱钟书对“‘神韵’说出自严羽”这一论断始终秉持着肯定的态度。如果刘涛先生承认“‘神韵’一语虽然在《沧浪诗话》中查无实据,但钱钟书的‘误解’却是事出有因”(同上),那么首先需要肯定的就是,钱钟书在“诗之有神韵”这一句的引用上确实是出现了谬误。这是钱钟书关于“神韵说”的第一个失误。
据上文所述,钱钟书在文献征引上的错误已是确实无疑。那么,钱钟书在“神韵”的内涵上是否存在理解偏差呢?笔者认为答案也是肯定的。钱钟书认为的“神韵”更多是严羽所提出的“入神”,而非王士禛所倡导的“神韵”。尽管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入神说”也确为“神韵说”提供了理论来源,但二者在核心观念上却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并不具有可通约性。这是钱钟书关于“神韵说”的第二个失误。为了阐述“神韵”与“入神”的概念差异,我们还是有必要对二者的概念进行简要的溯源与厘清。
(一) “神韵”
“神韵”一词最早是用于品评人物,用于形容人的风度神情。据蒋寅考证,“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宋书·王敬弘传》),“子显神韵峻举,宗中佳器”(《梁书·萧子显传》),是“神韵”的最早用例*参见蒋寅 :《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世说新语》多次以“韵”来评定人物,如“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世说新语·任诞》),“好饮酒,气韵标达”(《世说新语·杂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世说新语·赏誉》),在人物品鉴方面均与“神韵”有相近之处。南齐谢赫则将“神韵”用于绘画鉴赏,他在《古画品录》中评顾骏时说 :“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 :“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使得“神韵”概念在画论中固定下来。宋代的沈括、黄伯思、何薳、吴曾等人用“神韵”论书法,明清之际山水画兴起,“神韵”逐渐融入了画论中的“气韵”说,演变为山水画专用的美学概念*参见蒋寅 :《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
用“神韵”论诗,至迟在元代就已出现。倪瓒《跋赵松雪诗稿》中说 :“今人工诗文字画,非不能粉泽妍媚。山鸡野鹜,文采亦尔斓斑,若其神韵则与孔翠殊致。”柳贯《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殊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评高克恭“画入能品,故其诗神超韵胜”*参见蒋寅 :《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时至明代,“神韵”的内涵基本定型,薛蕙、孔天胤、胡应麟、陆时雍在诗歌批评时经常使用“神韵”这一概念。《诗薮》《诗境总论》中对“神韵”的描述,与王士禛所主张的“神韵”趋于一致。明末清初之际,“神韵”这一概念已得到广泛传播,频繁出现在诗歌创作和评论之中。王夫之的诗论多次提到“神韵”,大都是指神理自然、风韵飘逸的艺术境界。如他评嵇康《赠秀才入军》时说 :“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又如论徐孝嗣《答王俭》一诗云 :“神清韵远,晋宋风流,此焉允托。”但此时“神韵”所指涉的风格过于宽泛,没有形成特定的美学指向,尚未得到整合提炼。
据此可以看出,“神韵”一词早已出现,其用于诗文评论至晚在元代也有据可考,那么文学批评史上为何将“神韵说”归于王士禛呢?尽管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较少,但对于区别“神韵”与“入神”这对相似的概念来说,却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士禛论神韵,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发展,他以“神韵”为核心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美学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做了总结。王运熙先生曾说 :“王士禛对神韵说的丰富和发展并非表现在他增加了运用‘神韵’评诗的频度,也不是对该说作了明确的理论总结,事实上这两点他都未见得比前人有多少突出,而是表现在以神韵论的批评眼光,继承并运用前人的有关诗论,通过选诗与评诗结合的方式,充分而直观地展示出神韵的优美形式和意境,及对一般‘神韵’诗论某种偏颇的一定矫正。”*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8页。张少康先生也说 :“王渔洋的神韵,作为一种理想艺术境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审美传统的总结,着重体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特定创作原则和美学风貌,所以它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也存在于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中,不像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中所理解的那么狭隘。”*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王士禛的创作一生三变,但对“神韵”的坚持却贯穿于他毕生的诗歌理论之中。在24岁时,王士禛将自己的诗编成《丙申诗集》,并在序言中表达出了他的诗学思想,尽管此时他还未正式提出“神韵”的概念,但在他提出的“典、远、谐、则”的四种创作原则中,已可初步窥见“神韵说”的萌芽。尤其是“远”的提出,表达了一种新的美学倾向,提倡一种意在言外的表现手法,对王士禛后来所倡导的“清远”风格起到了先导的作用。此后,王士禛通过选诗和评诗集中表达了“神韵”的诗学思想,尤其是他的《论诗绝句四十首》,集中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王士禛晚年对“神韵”进行了完整的概括和整合,将“神韵”理论发展推向了高峰。在《池北偶谈》中,王士禛明确提出了“神韵”概念 :
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妙悟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池北偶谈》卷十八)。
“神韵”作为一种美学风格和艺术境界,其基本特色是自然天成,韵味悠长,因此王士禛在创作题材上提倡山水自然,风格上推崇清新淡雅,这也是他赞赏王、韦的重要原因。在诗歌理论上,王士禛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中“虚实相生”“意在言外”“味外之旨”等悟性思维的概念核心,在诗歌的构思方面发挥“虚”的作用,使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得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效果,这也是他对严羽“以禅论诗”“妙悟说”的继承与发展。另外,王士禛认为“神韵”这种诗歌境界,只有在诗人兴会神到之时才能创造出来,一味模仿学习、强调句法是无法写出具有神韵的诗歌的。因此,王士禛十分注重“伫兴”的作用,他在《渔洋诗话》中说 :“萧子显云 :‘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源序孟浩然诗云 :‘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平生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可见王士禛对“兴会”的强调,主张创作须循乎自然,不可刻意为之。钱钟书曾批评王士禛说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掇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做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钱钟书 :《谈艺录》,第97页。钱钟书对王士禛的批评,源自《谈艺录》中所记 :“《啸亭杂录》卷八记渔洋诗思蹇涩,清圣祖出题面试,几致曳白;兹事虽小,可以见大。观其词藻之钩新摘俊,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钱钟书 :《谈艺录》,第98页。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钱钟书只因王士禛不能即兴而作而对他进行批评,忽略了王士禛早已强调过“兴会”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这种否定是有失公允的。
(二) 入神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第28页。严羽的“入神”观受到了钱钟书的高度赞赏,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神韵说”论述。例如在论陆游诗时,钱钟书说 :“放翁《与儿辈论文章偶成》云 :‘吏部、仪曹体不同,拾遗、供奉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到同时已有功。’窃谓倘易‘已’字为‘始’字,则鉴赏更深一层,譬如沧浪之论‘入神’是也。”*钱钟书 :《谈艺录》,第41页。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引用严羽的“入神”观后,进而评论道 :“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钱钟书 :《谈艺录》,第40页。可见,钱钟书将“入神”与“神韵”视为同一概念。然而,“神韵”与“入神”在内涵上是否可以等同呢?笔者认为二者虽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并非是同一概念。下文就“入神”的理论来源进行简要梳理,以此辨析“入神”与“神韵”之间的异同。
严羽所说的“入神”,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重直观、感悟等悟性思维的总结。“神”这一范畴也是古代哲学和文论的重要研究内容。“神”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中 :“阴阳不测之谓神”,“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这里的“神”指变化莫测的意思。在《庄子》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神”的论述,如“用心不分,乃凝于神”“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认为“神”是事物内在的生命力,对“形”有绝对的统摄作用。至六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神”的艺术想象论 :“古人云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刘勰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93页。刘勰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构思的重要作用,描述了“神思”与外界事物相连时的特征,“神”在此指代的是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至唐代的杜甫,强调诗画创作不仅要传形,更须传神,如其诗中所谓“韩干画马,毫端有神”(《画马赞》),“醉里从未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严羽认为“入神者惟李杜得之”,杜甫关于“神”的诗学思想自然对其产生过深远影响。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说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强调了诗文创作中灵感的决定作用,同时将“兴”与“象”结合,使之成为主客交融的艺术形象。唐末的司空图标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说明诗中的景象与现实中有所不同,是构造于山水之外的一种特别的艺术境界*王小舒 :《神韵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此后,北宋范温在《潜溪诗眼》中对“有余意之谓韵”的相关论述,对“韵”的内涵做出了更为深入的阐述。林英德指出,“范温以‘韵’为极致,亦正合《沧浪诗话》 :‘诗之极致有一 :曰入神’”*林英德 :《钱钟书论神韵》,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钱钟书也极为肯定地说 :“严羽必曾见之(指《潜溪诗眼》)”*钱钟书 :《管锥编》第4册,第247页。。
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之上,严羽提出了自己的“入神论”观点 :
诗之法有五 :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 :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 :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 :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 :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第7~8页。
在这里,严羽探讨了诗歌创作的技法、风格,进而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即“入神”。陶明浚在《诗说杂记》中释“入神”时说 :“万事皆以入神为极致。……一技之妙皆可入神。……魁群冠伦,出类拔萃,皆所谓入神者也。”*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第9页。程小平说 :“入神说实际上是以具体的艺术形式及技法为依托,与传统的形神理论大体相似,同时严羽的入神也包括了几分‘技进乎道’的意味。”*程小平 :《〈沧浪诗话〉的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严羽谓“‘入神’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并不是说其他诗人的创作中没有“入神”的作品,只是说其他人“入神”的作品较李杜为少。对此,严羽特别强调 :“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第168页。可见,严羽本意并非抹杀其他诗人,而只是重在强调李杜诗歌对后世的启迪作用。严羽论诗讲究“别材”“别趣”“妙悟”,主张诗歌与其它文体不同,要求诗人具有特别的创作才能,从而创作出别具趣味的诗作,这也是诗歌作品与一般的议论、说理文章最大的不同之处。严羽将诗歌的艺术特点归为“兴趣”二字,而“兴趣”并非全部由学习而来,它需要创作者以“妙悟”来领会,这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代表思想。严羽认为,写诗需以技巧的学习积累为基础,并结合“妙悟”等感性直观的悟入方式,才能达到“入神”的至境。严羽的“入神”论强调诗人的直觉与自然的高度契合,在此境界中,诗人与世界得以融合为一,因此能够感悟到万事万物的本源意义,而在诗歌作品中呈现出的即是其所谓的“入神”。
严羽的“入神”对王士禛的“神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入神”与“神韵”二说在内涵上有相似之处,这可能也是钱钟书对“神韵”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王士禛对严羽的继承,集中体现在他的诗话作品中,如“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所未发之秘”(《带经堂诗话》卷二)。杨绳武曾说 :“公(王士禛)……尝推本司空表圣味在咸酸之外,及严沧浪以禅喻诗之旨,而益申其说,盖自来论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悉举诸此矣。此固《诗品》之最高者矣。”(《王渔洋神道碑铭》)在这段表述之中,可以看出王士禛的“神韵”源自严羽的“入神”,但王士禛进一步指出了“风格”“才调”“法律”三者兼备,才能使诗歌具有“神韵”的艺术风格,比之严羽只谓“诗之极致曰入神”,显得更为客观具体。针对南宋当时的文坛风气,严羽提出了“妙悟”“兴趣”“入神”等观点借以纠正江西诗派的弊病,但却并未师法于生活和现实,因此严羽的诗学思想是有明显疏漏的,这也是钱钟书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童庆炳先生曾经说过 :“(严羽)在注意诗歌的独特对象、审美本质和创作的直觉性的时候,只强调以盛唐诗人为师,以自己的性情为师,而没有考虑如何以生活为师,这一点上,他不如陆游,也不如杨万里。”*童庆炳 :《严羽诗论诸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总之,“神韵”与“入神”这两个概念,虽一脉相承却意旨有异,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三、 “神韵说”的流变及钱钟书误解的原因
通过上文的比较论述可以看出,“神韵说”的流变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悟性思维发展的不断递进,至南宋的严羽,提出的“妙悟”“入神”“以禅喻诗”等相关概念,对后世的“神韵说”起到了理论的奠基作用。王士禛的“神韵说”集古人之所成,对中国古代的审美习惯和传统进行了提炼,使“神韵”成为论诗和评诗的一种重要标准,“神韵说”在其时得以大成。对此,钱钟书曾说 :“渔洋论诗,宗旨虽狭,而朝代却广。于唐、宋、元、明集部,寓目既博,赏心亦当。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巨子,诗学诗识,尚无有能望项背者。”*钱钟书 :《谈艺录》,第106页。那么,钱钟书论述的“神韵”是严羽所谓的“入神”,还是王士禛主张的“神韵”呢?通过钱著中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钱钟书说 :“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钱钟书 :《谈艺录》,第40页。,“诗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钱钟书 :《谈艺录》,第42页。。这些表述与严羽所说的“诗之极致曰入神”如出一辙,将“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至境,而非某一种诗歌风格,因此钱著中的“神韵”其实是对严羽“入神”观的阐发和延续,而非是王士禛所论的“神韵”。刘涛先生认为“钱钟书持有一种广义的神韵观,故而将‘神韵’的提法归于严羽”(同上),事实上这种观点早已有人提出,如王小舒就曾说,“钱钟书将神韵归之为中国诗歌普遍具有的一种特质”。如果说钱钟书秉持的是一种广义的神韵观,就钱钟书关于“神韵”的论述,笔者倒也可以认同此种观点。然而,王小舒也指出了,这种广义的“神韵观”也是承自古人,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翁方刚均认为“神韵”是诗歌共有的特质*参见王小舒 :《神韵诗学研究百年回顾》,载《文史哲》2000年第6期。,可见在严羽时是绝未提出过“神韵”一说的。若钱钟书认为严羽之“入神”已具有广义神韵观的内涵,那么也应在论述的时候加以说明,而非使读者一再产生误解,据此可以断定钱钟书弄错了“神韵”的理论渊源和内涵。
对于“神”与“神韵”二者的区别,郭绍虞先生早有论述 :“神韵说虽亦本于沧浪以禅喻诗之旨,但是不同。何以故?盖沧浪之说全重顿悟,初学钝根易滋误解,所以较多流弊,而神韵说则于此方面加以修正,所以较为切实。……渔洋不局于沧浪之说而善为运用,此所以施愚山反谓‘神韵’之说足矫明代模拟之风也。”“此其别,全在于沧浪只拈出‘神’字,而渔洋更拈出‘韵’字,只拈‘神’字,故论诗以李杜为宗;更拈‘韵’字,故论诗落王孟家数。”*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载《小说月报》1928年第1期。郭绍虞认为,严羽“入神”尽管道出了诗歌的艺术至境,但这种境界除李杜外很难达到,明代的前后七子落入严羽“以盛唐为法”的窠臼之中,所以造成其诗的“肤廓之音”。而“沧浪论诗只论一个‘神’字,所以施空廓的境界,渔洋连带说个‘韵’字,则超尘绝俗之韵致,虽犹是虚无缥缈的境界,而其中有个性寓焉”*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郭绍虞以个性来解释神韵,道破了“神韵”与“入神”的差异所在,王士禛提出“典远谐则”四言,使得在诗歌创作中入“神韵”之境更具可操作性,他倡导的“以清远论神韵”,也是对“神韵”这一美学风格的高度概括。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王士禛所持的是狭义的“神韵观”,因此后世对其“神韵说”多有诟病。但应该注意的是,王士禛的“神韵说”本就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神韵”是指其以“神韵”论诗的相关内容,而广义的“神韵”则包含了他的“兴会”“根柢”“逸品”等相关论说*参见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第260页。。若论王士禛之“神韵”仅持狭义,则不免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根据上文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钱钟书论“神韵”时,弄错了“神韵”的提出时代和理论内涵,他是以严羽的“入神”论展开,而非是王士禛所主的“神韵说”,二者虽一脉相承,但在理论核心上却是有很大差异的。钱钟书在论及“神韵”时,不仅出现了文献引用上的失误,同时混淆了“神韵”的渊源和内涵。至于钱钟书在多年间为何没有修正其“神韵说”的失误?笔者对此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基于前文,我们可以做出一种合理的推测,钱钟书在论述“神韵”时弄错了其理论来源,先入为主地认为“神韵”出自严羽,并以“入神”论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神韵说”论述。与王士禛的“神韵”相比,“入神”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所以钱钟书自然会认为王士禛所主张的“神韵”较为狭隘。刘涛先生自己也认为 :“如果要证明钱钟书误解了严羽,就必须先要推翻他对‘神韵’的界定,这殊非易事。对钱钟书而言,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判断’。”(同上)正是缘于钱钟书对“神韵”的理解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如果他修正了与“神韵”有关的全部论述,那么他对严羽、王士禛,甚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总体评价都要进行更正,而这对于晚年的钱钟书而言可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直至钱钟书去世也未能对这一错误进行更正。但若承认钱钟书的观点,将“神韵”归于严羽,那么现有的文学批评史专著均需重新撰写。据笔者考证,现在较为通行的各种文学批评史教材,均将“神韵”归于王士禛而非严羽,有关“入神”的介绍,在严羽诗学思想中也是较少论及的部分。钱老已逝,其对于“神韵”的理解只能靠我们的推测而断,对于我等晚辈弟子而言,也只能以先生治学之精神为指导,从而进行更为严谨细致的研究探讨。
四、 结 论
笔者《钱钟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一文发表已有5年时间,关于钱钟书对“神韵说”的误解问题,笔者仍持原有观点。钱钟书对“神韵”这一概念的引用,在文献上出现了确凿无疑的失误,并且他对“神韵”的理解也有失偏颇,钱著之论述是以严羽的“入神”为基础,而非王士禛所倡导的“神韵”,二者虽有理论上的继承关系,但并非可以通约的概念。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大多创作于艰苦时期,因此在资料收集和查证上必然会存在疏漏之处,学界对此也多有讨论*关于钱钟书的失误,参见曹顺庆、郑澈 :《钱钟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刘涛先生指出,对钱钟书关于神韵的辩护是“希望在钱著的‘语言天地’中来考察钱钟书将‘神韵’归于严羽这一论断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同上),对此观点,笔者也有不同的意见。就“钱钟书论神韵”而言,钱钟书在论点的确立上就出现了失误,他误将“诗之有神韵者”一句归于严羽,而围绕这一失误选择的论据和相关论述,势必也会与“神韵说”产生很大偏差,绝不能仅在钱著的语言世界中为其寻找合理性,而是应以客观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辨析。
需要说明的是,白璧微瑕无损于钱钟书“一代鸿儒”的地位。他坚持中国文论的写作传统,吸收西方文论的话语方式,将中西方的文化与文学进行完美贯通,使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得以化用,此卓越贡献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笔者在多年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始终坚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 :《谈艺录》,第1页。的治学思想。就“神韵说”的中西对比而言,钱钟书将“神韵”与西方的相似概念作了类比,提出“西洋文评所谓spirit,非吾国谈艺之所谓神”,认为中国的神韵说有一种超于直觉和理智外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特质与西方哲学中“直觉”这一概念相通*郭绍虞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页。。钱钟书先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选取中西方文论中的相似范畴加以比较,为中西诗学的有效对话提供了良好典范。
●作者地址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Email :shunqingcao@163.com。
芦思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0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