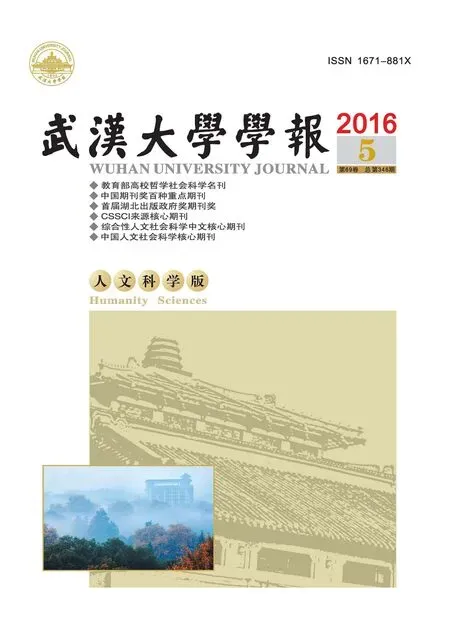荀子德福观的再分析
——基于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
2016-02-21孙伟
孙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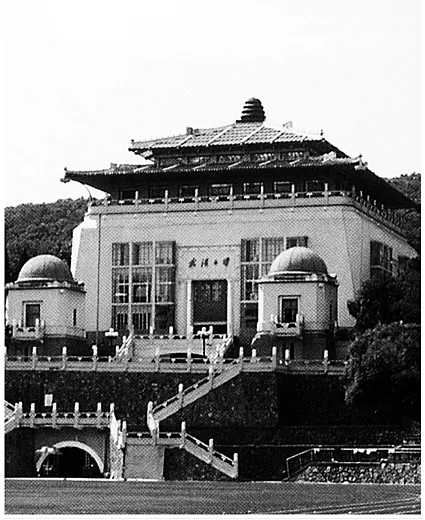
荀子德福观的再分析
——基于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
孙伟
在东西方哲学中,“德”和“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有德之人能否获得幸福?如果不能获得幸福,那又为何要行善而做有德之人?荀子关于“荣”和“辱”的观点可以成为折射这一问题的一面镜子,并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与荀子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能否获得幸福的关键既在于人们的德性修养,也需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把握并充分利用好外在的机遇,从而使“德”与“福”相一致。
德福观; 荣辱观; 荀子; 亚里士多德
一、 问题的提出
无论在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德”与“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辩不休的话题。有德之人是否一定能获得幸福?无德之人是否一定不能获得幸福?这些都是困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果有德之人不能获得幸福,而无德之人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那哲学或伦理学将如何劝服人们行善而做有德之人呢?因而,对“德”与“福”关系问题的回答关涉到哲学或伦理学自身能否成为一种指导人们日常实践、引导人们走向德性生活的实践学问。人们对于个人修德和外在幸福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感促使着哲人们去反思个体道德修养与外在物质幸福之间的关系。虽然哲人们可能更关注个体道德修养和由此而能得到的内在精神性的幸福,但对于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人来说,如何因个体道德修养而能获得外在物质幸福终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对此,西方道德哲学代表人物康德认为,当道德行为不能确实地带来幸福时,人们就很难继续保持道德行为。在康德看来,这种德福之间的不确定关系阻碍了我们在道德生活上的努力。虽然出于尊重道德律令的要求我们可以不管能否得到物质幸福,而这对康德来说也已经是“至善”(the supreme good),但“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的实现还是要求德福能够相配。康德通过假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灭来解决“最高善”的问题。对于康德的这一解决方案,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批评的:“若说这是神底事,他自能使你的德福相配称,你只要信他祈祷他就可以了。若如此,这等于未说明……这一‘说明圆善所以可能’的说明模式完全是顺习惯依宗教传统而说者。其中难解处,虽以康德之智亦习焉而不察也。”*牟宗三:《圆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卷,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236页。因此,康德并没有真正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牟宗三先生认为康德并没有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他提出以“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来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牟先生的这一思路主要解决的是道德幸福,也即是精神领域的幸福,并非康德圆善思想所要保证的物质幸福之原意。见杨泽波:《从德福关系看儒家的人文特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在中国先秦儒家思想中,“德”与“福”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偏重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解释有德者如何能够上承天命,获得道和生活的幸福。然而,这种解释的路向虽肯定了人通过德性修养能够获得精神层面的幸福,但在人如何因德性修养而获得物质幸福方面显得解释力不足。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先秦儒家后继者的荀子。我们想考察的是,荀子对德福关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做出了何种回应呢?
二、 荀子的德福观
要讨论个人修德和外在幸福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在外在物质幸福这个层面来对德福关系加以解释和补充。作为先秦儒家后继者的荀子,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儒家学说更加适应理论和现实的需求。
就外在物质幸福而言,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比如财富、地位、荣誉等等。而荀子对个体道德修养和幸福关系的论述,正是以“荣”与“辱”两个概念为基点的。在《荣辱篇》中,荀子较为集中地论述了个体道德修养和幸福的关系。“荣誉”或“羞辱”具有典型的外在物质幸福(或不幸福)的特征,是一个人能够呈现在社会和他人眼中的幸福(或不幸福)。正如荀子所言,“荣”和“辱”看似是在描述一个人外在的状态和所处的形势:“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必不遇其所恶焉。”(《荀子·荣辱》)喜好荣誉而厌恶耻辱是人的本性,君子和小人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君子和小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君子能够用道德的观念(如“忠”“信”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能够最终获得荣誉。小人却是用不道德的观念(“诞”“诈”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最终也将会遭受耻辱。然而,在现实中,虽然君子能够用道德的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获得荣誉,但并不能保证在每种境况下都能获得这种荣誉。而小人虽然是用不道德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有时小人所获得的荣誉可能比君子还要多。
荀子对“荣”和“辱”分别进行了类别上的划分。对于“荣”来说,有“义荣”和“势荣”之分。所谓的“义荣”就是能够培养自己的道德,持之以恒地进行道德修行,这就是内在的“荣”;所谓的“势荣”就是外在能够获得爵位和财富等等,这就是外在的“势荣”;所谓的“义辱”就是道德败坏,贪得无厌,这就是内在的“辱”;所谓的“势辱”就是外在所受到的刑罚和束缚,这就是外在的“辱”。对荀子来说,一个道德君子显然应该选择“义荣”,也就是道德修行的内在途径而舍弃“势荣”,也就是外在的爵位和财富;同样地,他也应该不要回避“势辱”,也就是外在可能会受到的灾难和肉体所可能遭受的痛楚,因为这只是外在的权势所导致的结果。他真正应该躲避的是“义辱”,也就是那种内在的道德败坏和贪得无厌(《荀子·正论》)。
所以,在荀子看来,君子虽然不能保证自己会在每种境况下都能获得外在的“势荣”,但只要他能获得内在的“义荣”,他也就实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也就得到了“荣”。外在的荣誉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此并不是真正的荣誉。同样的,君子有时还会遇到“势辱”和外在的灾难,但这种“势辱”是完全外在的,不能改变一个人内心所坚持的道德方向。总之,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外在的“势荣”,甚至遭到“势辱”,但只要他能够坚持内在的“义荣”,他就能够成就君子的道德理想。相反,如果一个人只获得了外在的“势荣”,而没有坚持内在的“义荣”,即便他没有“势辱”之患,但也可以称得上是“义辱”,因为他的内心已经不能坚守道德,成为骄暴贪利的根源。
这样,荀子就将“荣”和“辱”的问题与内心的道德完全联接起来。“荣”和“辱”不再是对一个人外在声名、地位、荣誉等的评价,而是对一个人内在道德的衡量。这也与荀子在《荣辱篇》中所提到的义利思想相一致。荀子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荀子·荣辱》)在这里,荀子将荣辱的问题与义利这个传统的道德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能够将义放在利之前,为了追求道义而放弃名利,那这个人就能够得到“荣”,而如果一个人将利放在义之前,为了追求名利而忘记道义,那这个人就只能得到“辱”。这里的“荣”和“辱”显然是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道德上的“荣”或“辱”,而不是外在名利地位上的“荣”或“辱”。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在德福关系上的基本立场是:一个人应该首要关注自己的道德修养,而对于外在的荣誉和地位的关注应居于次要地位。这样一种立场似乎与孔子的儒家传统德福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同样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普通民众在面对外在荣誉和内在道德的二元选择时,很可能选择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后者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外在的荣誉和地位。
然而,荀子的思想并没有停留于此,虽然他认为君子不一定能够获得外在的“势荣”,或者免除“势辱”,但他依然相信,持之以恒地坚持道德的方向,克服自己的欲望和私利,最后一定能够获得幸福而不是不幸。在《荣辱篇》中,荀子接着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荀子·荣辱》)虽然喜爱荣誉厌恶羞辱是君子和小人相同的,但二者求取荣誉、躲避羞辱的途径是不同的。君子能够待人忠诚,善良而正直,考虑问题明智,做事稳妥,就必然能够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荣誉,而不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因此,他们在穷困时名声也不会隐没,通达时就会名声显赫。而小人则恰恰相反,自己欺诈别人还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做出禽兽一样的行为还要别人善待自己,这样的人必然会在考虑问题时难以明智,而做事时也难以稳妥,就必然得不到他所期望的荣誉,而必然会遭遇他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因此,君子必然会获得最终的荣誉,小人必然会遭受最终的耻辱(《荀子·荣辱》)。这样,荀子认为道德修养最终必然会带来荣誉和地位等外在物质幸福,而道德卑劣的人则最终必然会遭受耻辱等祸害。这其实就清楚地指出了,德与福是一致的,无论这个“福”是精神性幸福,还是物质性幸福。只要人能够通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就不仅能实现精神性幸福,而且能实现物质性幸福。
荀子在其篇章中对德福关系也有更多的解释:“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离道而内自择,是犹以两易一也,奚得!”(《荀子·正名》)荀子认为,道是古今任何时代的人们行为的正确标准,如果离开道而随心所欲地去做事,那就不知道自己的祸福所依托的地方。人们都希望能够拿一个东西换两个东西,而不希望用两个东西换一个东西。如果遵循道的方向来行动,那就像是用一个东西来换两个东西,能够得到最后的幸福而不会有损失。在这里,荀子认为遵循道就一定能够获得生活的幸福,而幸福的涵义不仅包含了道德的实践活动,其中也包含了外在的财富、荣誉等,虽然后者并不是幸福的本质内容。荀子认为,人如果能够做到仁智而不被自己的欲望所遮蔽,就会得到与管仲或周公那样多的荣誉、财富、地位等等所谓“名利福禄”(《荀子·解蔽》)。这就明白地指出了人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就能够获得外在的物质幸福。
我们可以看出,荀子与先前儒家的解释路向不甚相同,虽然他也强调人通过德性修养获得精神层面的幸福,但也并不忽视从现实物质的层面来解释为何得道者能够获得幸福。正如前面所言,荀子认为遵循“道”就意味着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从事道德的行为,为他人的利益考虑和着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点,那受益的就不仅是他人,也包括了自己。因此,这就像用一个东西来换两个东西一样,做出道德表率的人并不会吃亏,相反,会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一种从现实角度为道德行为进行的辩护似乎能够更有效地说服普通的民众。荀子虽然在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对于个体道德修养与内在精神性幸福的思想,但同时又做出了极大的创新性发展,认为个体的道德修养不仅能够获得内在精神性幸福,而且能够最终获得外在物质性幸福。这无疑是对孔子以来的儒家德福关系思想做出的重要补充和解释。
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观
德福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是如此,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审视,西方哲学也是如此。其中,西方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德福观来自亚里士多德。
要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福观,首先就必须了解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幸福”究竟为何。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直接渊源于更久远的古希腊哲学传统。早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就提及:“我的好朋友,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或思考真理、智慧和灵魂的德性,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参见Plato:Complete Works.Edited by John M.Cooper.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p.27.译文有一定调整。可见,对苏格拉底来说,拥有德性以及真理和智慧才是人真正需要追求的目标,它要比拥有财富、荣誉等外在名利重要得多。据色诺芬的记载,在与欧蒂德谟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幸福就在于善而不在于外在的名利。欧蒂德谟问:“苏格拉底,至于幸福,那无论如何可以说是一种毫无疑义的善的东西了?”苏格拉底答道:“是的,欧蒂德谟。倘若我们使它寄托在本身好得无容争辩的事情里的话。”欧蒂德谟又问:“可是在构成幸福的事情之中有什么是好得还有疑问的呢?”苏格拉底答道:“没有的,除非我们把它联结着美、强壮、财富、光荣,或别的类似的东西。”*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1页。很明显,对苏格拉底来说,幸福绝不在于外在财富以及欲望的满足,幸福在于通过一个人的道德努力所获得的灵魂德性,也就是善。只要一个人具有了德性,就必然会拥有幸福。因而,苏格拉底主张从内在德性的角度实现幸福。
柏拉图也同样认为幸福在于人的德性和智慧的实现。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说道:“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柏拉图:《理想国》,第281页。由此可见,对柏拉图来说,德性的完满和至善以及智慧、正义才是构成幸福的基本要素。
亚里士多德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承继着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德性幸福观的传统,但对之做出了极大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幸福”的核心内容也同样是“善”。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所探求的,正是这能为人所实行和取得的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那么,实现了道德上的“善”,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的最终生活目标就已经得到实现了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或德性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在他看来,人生的最终目标是“幸福”(eudaimonia),但“幸福”并不等同于“善”,幸福是“最高善”。德性是一种品质,而幸福则不是一种品质*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4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德性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在获得“幸福”的过程中,拥有德性只是第一步。人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4页。。因此,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幸福并不只是拥有德性这种品质,而是在于德性这种品质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就是德性活动。人生幸福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德性具体地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而不在于仅仅拥有这种德性。正如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7页。。
另外,除了以上条件,人还需要其他的条件才能到达“幸福”的终点。在这里,其他的条件就是指“外在善”。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的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吗?还必须加上,他不是短时间的,而注定终生如此生活,直到末日的来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9页。这就是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除了合乎德性地活动,还必须要具有“外在善”,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那么,所谓的“外在善”究竟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看起来幸福也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通过朋友、财富以及政治权势才做得成功。其中有一些,如果缺少了就会损害人的尊荣,如高贵的出身,众多的子孙,英俊的相貌等等。……从以上可知,幸福是需要外在的时运亨通为其补充,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幸运和幸福等同。”*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5页。
在这段话里,亚里士多德充分界定了“外在善”。“外在善”包括了朋友、财富以及政治势力,还包括好的出身、健康、子孙和相貌等,当然也包括荣誉。这些外在的善往往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幸运的帮助。通过外在善的辅助,一个人再合乎德性地生活,这才能称得上是“幸福”。
我们可以看到,与苏格拉底的德性幸福观相比,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幸福并不仅仅在于按照德性要求来生活,更要有外在善的帮助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幸福除了德性的要求外,还需要有幸运的帮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外在的机遇或幸运促成了外在善的获得。外在的机遇看似是随机的,是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支配的,但在机遇发生时,一个人怎样去利用这种机遇就成为决定其幸福生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说,“作为真正善良和明智的人,我们一切机会都要很好地加以利用,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永远做得尽可能的好……事情果然如此,一个幸福的人就从来不会倒霉了……因此,他不轻易地离开幸福,除非他有重大多发的坏机遇,偶然的坏机遇并不使他失去幸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9页。可见,一个善良且明智的人应当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所有有利条件来从事活动,这样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这样看来,幸福生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主观努力分不开。面对外在的机遇和可能遇到的危险,一个人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利用外在的条件去抵御可能遇到的危险,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
四、 德福如何一致
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来获得幸福,但个体的道德修养只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就是说,要实现幸福,除了个体的道德修养,还要充分地利用各种外在的机遇来获得“外在善”。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一个人才能获得对于机遇的最大化利用,也才能形成对于灾难和危险的回避,也就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荀子不谋而合。
在《荀子》的语境中,“外在善”包含了诸多自然和人为条件的综合。荀子认为天的运行有其自然的规律,不会因为君主的贤明与否而改变。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它,就会产生良好的结果,而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方式应对,就会造成不良后果。所以,无论是出现了何种自然灾难,都不能责怪天—“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对荀子来说,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的水旱、寒暑等等自然灾害都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灾难的发生可能源于人类没有遵循“天”的自然规律。但是有时候,即使当我们遵循了“天”的规律,一些自然灾难还是会发生。这样,我们就应该努力去缓解这种灾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在人为的灾难中,我们就更应该把这些灾难归因于不负责任的政府(《荀子·天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去抵御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人的主观努力要比机遇本身重要得多。
在荀子看来,命是人时时遇到的各种外在时机。这样,在荀子眼中,“命”与“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要掌握天命并积极地利用“命”,使之为人服务。人与其在不幸的命运来临时被动地期待时运的到来,不如积极地去应对这一具体遇到的时运并充分利用它(《荀子·天论》)。这样,与孔子和孟子相比,荀子不仅从现实的层面解释了为何具有德性之人能够获得幸福,更从如何利用外在机遇的角度拓展了幸福的内涵,使幸福的概念容纳了更多“外在善”的元素。对荀子来说,人所以能够获得幸福,并不仅仅在于进行德性修养,还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外在的机遇和时运,使之能够导向最终的幸福。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在“外在善”的观点上相当一致,都认为外在善既是德性实践,也是圆满幸福人生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人只有通过主观的德性努力,充分利用各种外在的机遇,回避各种灾难的侵袭才能实现“外在善”。亚里士多德承认幸福的构成需要幸运的因素,但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说到:“听从命运的摆布是不对的吗?生命中的成功或失败并不依靠这些,但是人类生活,正如我们所说,需要这些作为伴随物,然而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原因,相反的活动则导致相反的结果。”*参见Aristotle.Ethica Nicomachea.Translated by W.D.Ross.i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Edited by Richard McKeon.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1,p.947.中译文由笔者依据该英文译文译出。因此,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道德修养才是塑造幸福生活的主要方式,与其不切实际地期待幸运的到来,不如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同样,相对于外在的自然和人为条件,荀子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礼法来培养人们的道德并指导人们如何依据礼法来行动。只有依据礼法的德性实践活动才是幸福生活最终的保障。
五、 结 语
总之,自孔子以来的先秦儒家在德福关系的问题上虽强调了个体道德修养与内在精神层面幸福之间的联系,但却忽视了德行修养与外在物质幸福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历来重视“知行合一”的儒家哲学或伦理学来说是一个必须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德性修养不能确定地带来外在的物质幸福,儒家的哲学或伦理学将很难对社会民众形成道德的规劝力量,而儒家的道德主张和政治蓝图也将难以实现。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将德性修养与荣誉等外在物质幸福关联了起来,认为人的德性修养虽在一时一地未必能导致世俗眼中的“幸福”结果,但从长远看来,人所能获得的荣誉等外在物质幸福一定能在人们德性修养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这就为孔孟以来的儒家德福关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补充和发展。
相对于荀子,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既存在于神性思辨的至善中,也存在于实践中的德性实践活动和外在善中。对于前者而言,幸福无疑需要通过具有神性的思辨而获得;而对于后者而言,幸福则不仅在于具体的德性实践活动中,还在于能否获得外在善的辅助。
无论是荀子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在各自的哲学传统中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都既关注精神层面的道德幸福,也同样关注物质层面的幸福,认为通过人的德性努力和利用一切外在机遇,人必然会获得最终的幸福。这使得幸福终究能成为尘世之人所追求和实现的目标。这无疑是二者对各自所在的哲学和伦理学传统做出的极大贡献。他们都把人的德性修养和塑造作为评判生活是否幸福的主要标准,而对于荣誉等外在善的获得与否,二者都强调了人把握机遇的重要性,而不能将机遇归于运气或天意。他们都相信,只有自己进行切实的道德努力,并努力地把握好自己面前的一切机遇,才能获得幸福。这无疑凸显了人在获得幸福生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从而使得无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不仅与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超越境界联系了起来,而且也与个体的世俗生活和外在物质幸福联系了起来,哲学因此而成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问之道。
●作者地址:孙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Email:philosun2012@163.com。
●责任编辑:桂莉
◆
Reanalysis on Hsun Tzu’s View of Virtue and Happiness: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Aristotle
SunWei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East and West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is always a debatable topic.The focus of the debate lies in that whether a virtuous person could acquire the happiness at last.If a virtuous person could not acquire the happiness,why should he be virtuous? Hsun Tzu’s views of fame and shame might be a mirror reflecting this problem and could possibly become an approach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Both Hsun Tzu and Aristotle argue that whether a person could acquire the happiness or not lies not only in the moral cultivation,but also in the person’s efforts in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external opportunities so as to make virtue consistent with happiness.
virtue and happiness; fame and shame; Hsun Tzu; Aristotle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12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ZXA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