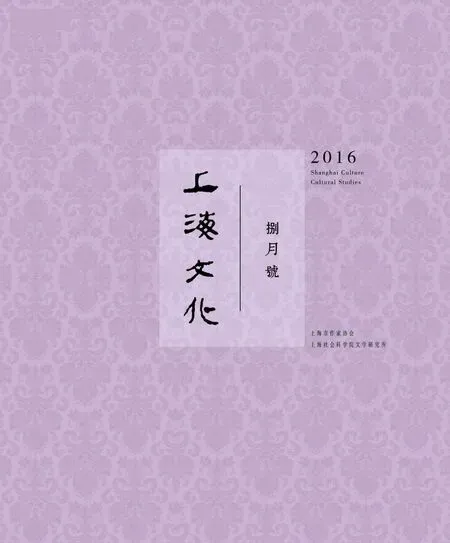中国画的“死”与“生”
——以姜永安的水墨创作为中心
2016-09-16刘旭光
刘旭光
中国画的“死”与“生”
——以姜永安的水墨创作为中心
刘旭光*
中国画的观念在过去100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艺术探索上也经历了复杂而多变的实践演进,纠缠在革命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古典、现实与理想之间,其审美特性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间,曾经由于趋向西方的写实化而丧失民族特性,但最终,以姜永安为代表的当代国画家,在审美现代性与民族传统的笔墨观念和审美特性中,找到了融合点,创造出了既富于笔墨意蕴,又具有高度写实性的水墨艺术,从而起死回生。
中国画 水墨 笔墨 姜永安 写实
从1918年陈独秀与美学家吕澂在《新青年》上号召“美术革命”,到现在已近百年,在这100年间,我们的民族绘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艺术语言还是艺术观念,无论是绘画艺术的功能还是观看艺术作品的方式,都发生了惊人的变革。百年之间,中国画纠缠在革命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古典、现实与理想之间,观念冲突之大,风格变化之烈,令人惊讶。问题是,经历百年变革,我们得到了什么?
2013年,国画家姜永安完成了他的作品《成长》,这似乎就是革命后的国画所取得的成就。但问题是,这还是“国画”吗?

姜永安,2013,《成长》
“国画”这个词产生于20世纪初期,它的对立面是西方绘画,如油画、水彩、水粉等作品,但这个词没有明确的内涵,似乎凡中华民族的绘画作品,都应当叫“国画”,比如文人画、工笔画、壁画、年画、界画等等,相对于“西洋画”,这都应叫“国画”。但在实际的应用中,这个概念的内涵又有所收缩,大概指以水墨绢纸为载体的民族艺术,特别是以笔墨为主导的山水画和以线条为主导的人物画,以及工笔画与写意花鸟画,实际上狭义的中国画就是文人画,但是这个概念的狭义应用不断地受到挑战。挑战的背景是:中国画在百年之中的变革,一个目的是为了能在造型与表现性上和西画比肩,另一个目的,就是革文人画的命,扩大“中国画”内涵。这两个目的既有交集,又各有所向。
姜永安的这件作品还算是“国画”吗?
这张画从材料的角度讲,当然是国画:宣纸、毛笔和水墨这都是真正中国的材料,但抛却材料的考量,这件作品如果还是“国画”,那就意味着,它应当具有我们在说“国画”这个词时所预设的那种风格与美感。这张画有一种灵动、飘逸的韵味,这种味道源自“水”与“墨”、“纸”之间的相互作用,写意绘画所侧重的笔墨功夫,墨色的层次与变化,墨与水之间的渲晕,留白的应用,对线条的简洁、准确与流畅的呈现,特别是对“意”的捕捉与传达,都体现出对以文人画为基础的写意美术的承续,它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国式的”审美感受:含蓄,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
然而姜永安的这张画,还有一种超越于写意精神之上的新的气质,超越于我们对于中国画的预期而发生了。
传统的中国人物画,简约者不求形似,但求“气韵”,以线条勾勒出五官轮廓,也以线条勾勒衣服与身体的形状,于简略中现“神气”;精细者能根据面部固有之凹凸和结构关系,淡墨勾勒后积染赋色,虽无明暗块面变化,但也能得其形似。但姜永安画面中的人物不是以线条的方式勾出轮廓,而是通过墨块与留白完成块面造型,然后借助水墨之交融所产生的层次感,以及墨色五分所构成的明暗变化,完成富于立体感的,甚至是塑造感的形象。
这个形象令人震撼,笔墨交融之处,墨法丰富而多变,韵味实足,笔法精致,线条准确生动。同时,笔墨塑造出了一个具有心理真实感的意象,从而把笔墨的艺术语言的美感与真实感交织在一起,达到虚实相生之境。“虚”在于由水墨变化和留白所营造出的空灵之感,“实”在于水墨塑造出的富于真实感的形象。同时,对于形象之神韵的呈现,对于情感状态的呈现,生动细腻,画面中有一种源自令人惊叹的造型能力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冲击,水墨的写意性与造型的精准交相辉映,这显然呈现出古人未达之风貌。这似乎就是中国画革命的结果。
1918年在陈独秀呼吁美术革命的时候,他认为革命的理由是国画没有写实性。这个观点康有为及其信徒徐悲鸿都坚信不已。1918年之后,刘海粟东渡师法印象派、徐悲鸿西渡攻晚期古典主义油画,两人归国后以西式的艺术观念重新建构中国的美术体制,强调造型能力在美术中的基础作用,强调色彩与明暗的表达;与此同时,鲁迅等人倡导能够反映人生、反映社会的美术,要求美术能介入生活,而不仅仅是审美的,这就要求绘画在题材与艺术语言上的改变。这些主张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画造成了强烈影响,当一批受过西式造型艺术训练的油画家由于现实的诸多因素拿起毛笔画“国画”的时候,国画的风貌为之一变。变化之一,由于良好的素描与速写能力,使得画家们能够描绘出准确而生动的形象;变化之二,由于具备了造型能力,画家们可以去写生,可以对外部自然进行准确的摹写;变化之三,“色彩”这个传统国画相对较弱的部分,受到西方印象派的影响而趋于强化,并进入到国画之中。这三个变化,形成了国画领域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以中西合璧为旨,实际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美术形式。
但这种变化对于“国画”意味着什么呢?这构成了中国画在观念上最核心的问题——洋化了的国画还是国画吗?在这种变革求新的同时,有一批传统文人画家还在坚守,最初是任伯年、虚谷、蒲华、吴昌硕等人以传统的技法,在题材与笔法上稍作更新,以海派之名恪守传统国画之旨,之后有金城、陈师曾、吴湖帆、张大千、黄宾虹、齐白石等人,坚守与弘扬国粹,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师古法,体己心,仿古而不泥于古,坚持文人画传统。
当然还有一批国画家,去发现国画中的富于现代性的部分,与西方的现代艺术观念结合在一起,加以弘扬与改造,创造出具有现代性的美术,比如林风眠、朱德群等,但这些现代美术作品实际上没有被纳入到“国画”的体制中来。
有人变革,有人坚守,有人折中,有人立足现代而融会中西,所有这些探索都是在“国画”这个框架中完成的,这种创作上的多元探索必然反映为观念上的多元甚至混乱。俞剑华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概括过人们对于传统国画的不满:“一、以国画为出世而非入世也。二、以国画为临摹而非写生也。三、以中国画为崇古而非进化也。四、以中国画为不合时代也。五、以中国画不合西法也。”①俞剑华:《国画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这五条意见大概可以涵盖激进的批判立场的主要依据,这种批判自陈独秀、康有为起,经徐悲鸿、江丰,再到吴冠中、李小山,绵延近百年,构成了对于“国画”的总体性否定,但这种否定却没有精细划定“国画”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不会认同这种否定,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疾呼:“画有民族性,无时代性。虽因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今非注重笔墨,即民族性之丧失,况因时代参入不东不西之杂作。”②黄宾虹:《黄宾虹艺术随笔》,卢辅圣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纯粹的民族性,是对国画的最主要的辩护辞。但这一辩护并不有力,坚守笔墨,会最终把国画定格为“老人墨戏”。问题是,观众看不懂笔墨,除了那些程式化的意象,观众还要求艺术有更多的内涵。不能满足这两点,国画必将沦为同仁圈子的游戏与文人自我标榜的手段。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是对的,俞剑华所概括出的那五条意见是必须要正面回答的!但黄宾虹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如果放弃了笔墨传统,国画和水彩画又有什么区别?
这种纷繁的探索与观念冲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强制性地打断并掩盖起来,徐悲鸿建立在西方造型观念之上的国画观,借助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引领作用而成为正统,在新社会对于绘画的现实需要面前,国画家们不得不走向写实性,走向写生,走向对社会场景的呈现。从学科体制上,国画成为绘画专业的一个方向,而西方的造型观念与方法,如素描、速写、色彩、透视等课程成为所有绘画专业的基础。山水画在李可染、张仃等人手中为之一变,对画面构成的经营与结实的造型结合在一起,再佐以明暗处理与光影效果,加上自然写生,形成一种新的山水风貌,这种山水画可以为党的文宣工作所用,可以对时代的境况有所反映,这就正面应答了俞剑华所概括出的那五条批判意见,从而使国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这种新国画或许也还在笔墨的传统语境中,但如果把这些创作放在文人画的历史传统中,可以坦率地说——意境全无。
人物画的发展显然更直接地走向对造型能力的追求,走向写实性。徐悲鸿、方增先等人的国画人物画,实际上是用毛笔完成的“速写”与“慢写”,虽然有扎实的造型能力支撑,虽然保留了传统的经营布局,但是这种人物画更像是速写与水彩的结合,实有余,韵全无。
很难评价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80年代的中国画。如果说它在“进步”,那么进步的指向显然是“造型能力”,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创作强化了国画的技术性,却不再是个体心灵的自由呈现,不是写意,不可“澄怀味道”,不是“卧游”的对象,更不是写胸中逸气,民族绘画的审美精神,一变而为写实精神,虽然面貌一新,但离“国画”之旨已远,因此,人们更愿意称之为“水墨”,或者“彩墨”,而非“国画”。这似乎意味着,“国画”已死!
但是从国画向水墨的转变,显然创造出了一种更加新颖,更具有创造性,更具有当代性的艺术形式——水墨。
水墨的诞生,意味着“文人画家”的退场和“国画艺术家”的诞生,这种变革有一个显见的好处——国画艺术家的专业化!不同于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传统国画,在新的艺术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国画家,在其训练过程中,摆脱了文人身份而专业化了。国画的学习者们接受传统的国画教育,他们在临摹古画、书法的学习中,在对传统国画形式的学习中,构成他们的专业性,但他们又接受西方的造型艺术训练。他们有不错的素描功底,有良好的速写能力;他们也学习过基本的油画技能,对于色彩以及肌理与质感有深入的体悟;他们有近代之前的国画家所不具有的造型能力。同时,他们又学习文人画之外的中国美术、壁画、岩彩、民间美术,凡是这块大地上发生过的美术形式,他们都不拒绝,他们所理解的国画,早已超越了文人画的狭小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美术学院体制培养出的国画家,具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形式感,他们不断地尝试新材料、新技术,追求新的表达效果,他们的艺术语言极其丰富,他们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同时他们又以一种真正的后现代状态,不断地把诸种艺术语言混合在一起,手段丰富,效果新奇。由他们所创作出的“国画”,以画面效果为指归,不拘泥于材质,不拒绝诸种艺术语言,随物赋彩,随心所欲。应当说,在经过近60年的积累之后,一种新的“中国画”似乎已经孕育成型了,它以中国诸种民族艺术形式为主导,杂糅种种艺术语言,有强烈的民族意味,却又与传统截然不同,这里包含着一种真正令人期待的新艺术样态与新美感的萌芽。
这就意味着中国画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了突破:一是造型能力,二是材质技法。这两个层面的突破汇集在“水墨”这个范畴之中,水墨的诞生,还意味着对于水墨这种媒介形式的更深入的探索与开拓。传统国画对于笔墨的执着,实际上转化为现代国画家对于水墨的坚守。
水墨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如何掌控和使用这种语言,是需要专门探索的。对水墨语言的探索,构成了这门艺术的自律性。水墨本身是一种艺术语言,无论画什么,笔力墨色,以及笔墨之和,永远是水墨艺术的艺术性所在。水墨无关时代。对于艺术语言的探索,艺术在技艺与风格方面的创造,有一种超越性——它无关城堡上旗帜的颜色,也无关世间冷暖,艺术家可以把艺术技艺与艺术语言的追求乌托邦化,变成一种宗教般的执着与追求,无关世事,有益精神。
从艺术自律性角度来看待水墨,意味着水墨创作在题材上是自由的,它究竟呈现出的是山水,是现代都市,还是古典人物,这无关紧要。即便用水墨来描绘现代人的欲望情调,也应无所挂碍,水墨无关时代。但另一个方面,水墨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每一个时代都有与时代的社会形态相关的形式感、节奏感、美感。特别是,人的情感及其结构本身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宋人观看山水的方式与我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元人观看艺术作品的方式也与我们不同,因而何必执着于宋元或者明清?模仿永远不是艺术,既然水墨艺术面对的时代的眼睛与心灵,都会发生改变,为了能够让这些时代之眼在水墨艺术中获得愉悦,就应当引领与满足这种时代之眼。
用水墨这种民族性的媒介,去呈现与表现当代生活、当代心灵,这当然可以。水墨创作真正困难的,或者真正具有艺术性的部分在于:找到水墨最独特的话语方式,找到水墨最适合的表现领域,以自我之声,说属我之事,水墨将因此而解放,也将因此而自律。对水墨媒介的这种自律与自觉正是姜永安创作的意义所在,但对于水墨这种民族性媒介的坚守还不能算是对于国画的传承。我们回到姜永安的创作,再来看看这些作品在什么意义上克服了国画的局限,使国画跟上时代的要求,在什么意义上,这些作品又是国画精神的传承?
姜永安的水墨画显然有一种强烈的反映现实的能力,水墨的自由使得它可以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需要像传统国画一样囿于固有的意象系统与符号系统,这是国画的真正解放。而水墨同样具有反映与介入现实所需要的表现力,比如姜永安创作的《中国“慰安妇”写真》,这种表现力显然是传统国画所达不到的。

姜永安,2014,《伤逝的肖像·中国“慰安妇”写真》
国画创作的方法在这些作品中显然有重大的变化,古人的创作方法,无非是以下几条经验:第一,“师古人”。这是最便捷之路。师古的好处在于通过对古人的模仿,以一位大师为追随的对象,可以用最集中最直接的方式,达到与大师同样的高度。艺术中的复古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让一位初入门者很快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水准,攀上巨人之肩,当然会有不同眼界。虽然“笔墨”可仿,“功夫”难得,但只要有恒毅之心,倒也可成一家,虽然不见个性,但易见成效。第二,“师自然”。用古人的话说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尽管古人说这句话的本意或许与我们现代的理解还有不同,但是从近代以来的绘画观则直接把这个观念与西画的写生观结合起来。通过对自然的临摹,可以间接地解决师古观带来的程式化、僵化,解决创造性不足的问题,自然的形式永远超出人的想象,跟随自然的脚步,体味自然的四时变化,然后把观察与体悟的结果诉诸笔端,通过写实性来弥补传统国画创作程式化的问题,创造出与古人不同的国画景致。这种观念由于现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美学的胜利而得到强化,也由于学国画者往往也受一些西画的造型能力的训练,因而有比古人更强的写生能力而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自然是没有灵魂的,对于绘画而言,自然是一个有待填充的空白,只有把精神性因素赋予自然,自然才能成为“美的”。因而,单纯地跟随自然,是无能的表现。自然所呈现出的,必须被心灵点化之后,才能成为“属于艺术的自然”。第三,“师心”。“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我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一画论”,这些古人的名言,表明古人知道,无论是自然还是前人,都只是创作的手段,艺术的目的是“我”,而“适我无非新”,要出新,只能返身而诚,回到自我当中去。化千里河山于咫尺,尽四时变化与一方,以须臾纳无限,以沉静纳生成,创造出一方心灵之境,这才是国画艺术的真谛,它需要以师古的方式掌握技法,以师自然的方法获得素材,但真正重要的是,它需要一颗自由与饱含深情的心灵来掌控两者。这是中国画的诗性与哲性之所在。但“师心”的困境在于,胡思乱想与肆意放纵是不是师心?
这三种创作方法如果能够融合,当然最好,但师古难出新;写生如果没有造型能力作为支撑,实际上无法实现;师心之法,前提是创作者具有笔墨技法和写生造型能力,能够心手相应,从而实现自由表现。从以上三个角度看姜永安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是把写生与造型放在了最基础的部分,而把师古隐含在笔墨之中,最终实现自由表现心灵,而不仅仅是摹写对象。
水墨在姜永安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表现力和创作力,显然已经把古人抛在身后,让水墨画成为反映时代的手段,并且,从造型能力的角度来说,卓绝而完美。这是新创作,这是新艺术,那么,这是不是“新国画”?
从材质与技法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国画,传统国画对于水墨的应用与技法上的探索,被继承在这些作品中,在师古方面,当代国画家并不逊于任何时代,由于复制技术与图像显现技术的应用,当代国画家们甚至比古人更了解他们自己。从作品所呈现出的造型能力来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是,必须承认,即便是传统的国画,也不排斥精准的造型,“真”一直是古人的理想,只是不易达到罢了。从这个意义上,造型能力应当是国画应当达到的,而不是要排斥的,是否具有造型能力,恰恰是专业性与业余爱好的分水岭。从意蕴与意境的角度来说,笔墨功夫所体现出的“境界”在当代水墨艺术中要不要去表现,这是个矛盾焦点,吴冠中强调造型能力与画面效果,所以他认为“笔墨等于零”,这个观点从争论的角度来说,实际上犯了大忌,笔墨这种基础性的技艺,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否定和放弃。从笔墨的角度来说,当代的水墨艺术在墨法上不逊古人,甚至别开生面,当代国画家为了追求墨色的特殊效果,可以往墨中填加其他物质,这一点无可非议,古人也是填加的,只不过他们可加的东西少。但对于笔法,这恰恰是水墨艺术的弱项。由于国画的专业化,对造型和绘画能力的要求提高了,但对书法的要求放松了,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代的国画发展中,书法与国画分离了,但这也不应当成为否定水墨的理由,因为在宋代之前,国画和书法本身就是分离的,它们的结合也只是在文人画这个狭小的领域中。分离意味着绘画性的强化,国画首先是“画”,这种分离,虽然可惜,但结果可喜。
最后,关于意蕴与美感——水墨的特质,在于含蓄而隽永,它有层次,但不结实,它有实在的造型能力,却又营造出虚幻的效果,轻盈而通透,朦胧而冲淡,虚实相生,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美感,不正是中国的山水画与写意画的目的吗?在下面这张人物画中,不正是包含了“国画”这个词所应具有的美感与意蕴吗?

姜永安,2013,《顾城》
过去100年关于国画的所有指责,都在这些作品中被超越了,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数代人的努力,也是文化选择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姜永安们,以及他们的前辈与后贤的努力,使得国画如凤凰浴火般重生,虽然冲突和争议不断,但笔者相信,这正是中国画的方向与未来。国画在百年之中,经历数次革命,这些创作或许就是革命的成果。
责任编辑:沈洁
*刘旭光,男,1974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