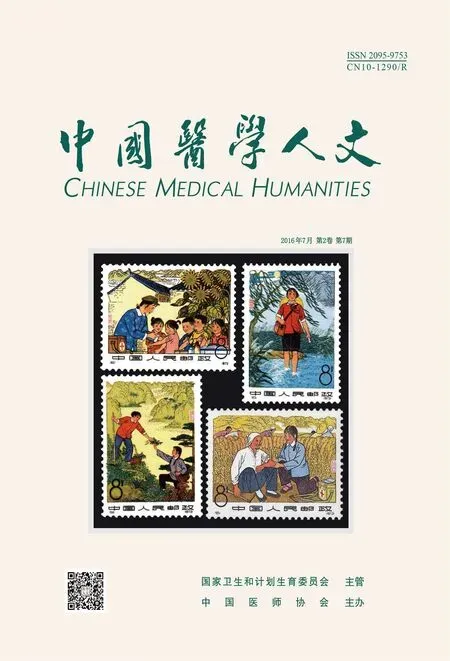最初 不曾辜负
2016-09-13叶圣龙
文/叶圣龙
最初 不曾辜负
文/叶圣龙

总是听到圈内抱怨经年未变的数元挂号费抵不过宠物医院动辄几百的诊金,甚至有人上纲上线,直指这背后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
然而,仅仅数元的挂号费,又有几多辛酸滋味呢?
我记得一位老师提醒我们,挤来三甲医院看病的很多人,已经一拖再拖,实在是被折磨得忍无可忍才来求医的。我也在春运的北京西客站,见到躺在门板做的担架上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进京就诊的一家人。整日摩肩接踵的挂号大厅,嘈杂喧嚣的候诊区,等待之中有多少期待。
就这么几块钱的号,也许是他全家总动员熬上几个通宵才抢到的,也许是忍痛从黄牛手里翻了百倍买下的,也许是一辈子没用过电脑的老人颤颤巍巍在凌晨刚学会的电脑前“侥幸”拍的……
然而在我们的诊室,在只有几分钟的交流里,他们来不及告诉我们诊室之外的辛酸,正被疾病折磨着的他们用所有的希冀,迎合我们有些麻木和生硬的问诊,痴痴地用虔诚与无助等着我们鲜有的目光交汇。
几分钟的仓促里,他们给予了医生最大的宽容——我们没用名字称呼他们,我们累得早忘了什么微笑,我们一时心急催上几句,我们忙得来不及仔细嘱咐……他们都默默容忍,甚至反过来关心我们喝水、吃饭、上厕所。
小小的诊室,他们所渴望的不过痛苦中的一丝安慰,尽管这也不一定就能得到。
我们向他们发牢骚抱怨在今天当医生的苦,他们又能去哪里抱怨现在当病人的不易呢?
每次想到这些,我会愧疚,我能给予他们的,值那几块钱的挂号费么?
当我们在纠结7块钱的专家号和300块钱的宠物门诊时,却忘记了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超脱世俗量度的,就像我们从不会去考虑父母之爱究竟价值几何,“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世俗与金钱不过身外之物的度量。
疾病危难之前,你给我多少钱,我们都不能承诺能救回你这条命;而救回的这条命,对于我们也是多少钱都不能衡量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脆弱,与死亡搏弈中的瞬息万变,然而我更知道生命之重,那是我们入学誓词中对生命的敬畏。
入学的时候,我们答应过前来祝贺我们成为医学生的所有人,会当个好医生。
而忙忙碌碌,我们习惯了抱怨;骂骂咧咧,我们辜负了感动;麻麻木木,我们忘记了最初“偶尔治愈,有时缓解,总是安慰”的信条……
生命之托,回天仁术,生死之交,妙手丹心,究竟价值几何,身为医者,其实更加明白。在我们第一次被唤作医生,第一次亲手复苏成功,第一次面对患者和家属的由衷感激,在忙碌所积累的麻木之前,那一次次暖流涌过全身的感动与触动是只有这个职业能给予我们的体验,这些体验同样是超越金钱所能衡量的。
几十年,医生的门槛从中专到学士、从硕士到博士,而患者还是患者,上至精英大亨下至社会底层,五谷杂粮逃不过生老病死,专业信息不对等是客观存在的。从希波克拉底就要求医生,无权抱怨患者的素质、认知和文化程度,医生要有近乎圣人的情怀。
在卫生制度完善之前,今天中国的医患关系,正在以超负荷的畸形状态运行在有限的资源上,勉强维持着巨大人口的卫生负担,医患双方都付出了很多,既然我们说,“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而不是彼此”,那就让我们别任性地抱怨,辜负了绝大多数患者的善良与隐忍,辜负了我们的最初……
渴望赢得社会的尊重,起码不能在抱怨与麻木中先丢失医者的自尊。
救治之术疗发肤之疾,救赎之心解庸愚之鄙,皆因我们是医生,是这个时代的医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