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及其演进研究
2016-09-08金太军张健荣
金太军 张健荣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及其演进研究
金太军张健荣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现有文献注重规范分析和单个案例研究,而对NGO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演进鲜有具体探析。通过对汶川和雅安芦山地震中一个连续参与的联合行动案例的解读,不难发现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NGO的参与演进规律,即危机需求回应精细化,角色功能定位明晰化以及政社合作带来的身份认同。尽管如此,NGO在参与机制、资金来源与管理及其自身建设方面仍存在着现实障碍。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NGO参与演进的机制,即参与的发生受到“个体情感—组织职能—社会责任”的路径驱动,参与的发展符合自组织演进机制,参与的拓展动力则来自于政府与NGO之间的资源交换。
重大公共危机; NGO参与; 演进机制; 危机治理; 政社合作
在一个多维结构、多重风险、多样矛盾叠加的当下中国,危机频发成为转型期的一种常态。危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远非任何单个主体能力所能驾驭和消弭,因而公共危机的治理呼唤着多主体力量与智慧的合力。不论是从概化的理论探讨,还是层出不穷的创新实践,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①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愈发不容忽视。中国的NGO组织发端于改革开放,成长于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历经曲折,但公民志愿精神日渐凸显,特别是在历次重大公共危机中更能充分展现志愿主义的人性关怀。
重大自然灾害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公共危机。本文选取了一个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3年雅安芦山地震中连续参与的联合行动案例来比较探讨。在两次危机中,中国NGO的集体亮相,充分展示了公民社会之力量,也清晰的暴露出缺陷与不成熟。NGO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学界研究已有关注。历经2010年的玉树地震,再到2013年的雅安芦山地震,NGO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参与方式和能力是否有所发展?这种发展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演进机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或许能带给我们对中国NGO的进一步认识。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中国NGO的起步与发展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被当作是除了国家系统(第一部门),以及市场系统(第二部门)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②,“公民社会组织在寻求介于仅对市场信任和仅对国家信任之间的‘中间道路’”③的过程中具有战略作用。国外学者认为,中国NGO的发展归因于国家难以应对经济转型与政治分权带来的社会挑战④,国内研究者如王名归纳了我国NGO发展的几个重要影响因素⑤:首先,政府体制与职能的调整为NGO腾挪了空间,在多领域内双方的创新合作,将为NGO带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乃至政治空间;其次,市场逐步成熟和经济持续增长促使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却催生了大量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反映出“现代性的阴暗面”⑥,同时又塑造了致力于公益事业之群体,独立、自主、志愿之精神也由此被广泛唤起;再次,制度维度的渐进完善形成更具化的行动框架,它不断调和“制度匮乏”与“制度剩余”的矛盾,收缩“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张力⑦;此外,通讯革命伴随不可逆的全球化加速,中国语境下萨拉蒙所说的“全球结社革命”出现了广度与深度上的深刻变革。
人们倾向于将2008年称为中国NGO元年,这种叫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准确。王名认为,我国NGO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兴起阶段”(改革开放初——1992年),自上而下释放的空间和自下而上迸发的热情相结合,产生了社会组织的爆炸式增长;第二阶段为“规范管理和新的发展高潮”阶段(1993——2007年),法律法规颁布后,以双重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形成并巩固,组织数量增速加快⑧;本文认为第三个阶段为“放松规制,鼓励发展阶段”(2008至今),简政放权在民政领域持续推进,旧规修订和新规出台,积极推动了地方开展直接登记,NGO再次涌现⑨,同时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走上正轨⑩。因此,2008年被称为NGO元年,强调的并不是其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而是NGO第一次在公众视野中的集体展示,此后,NGO得到了广泛关注。
(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

研究者对危机治理中NGO的功能与优势加以探讨,分析其现实困境并提出了路径选择。许多研究从危机发展的各阶段对NGO参与进行考察(陈秀峰,2008;徐祖荣,2008;李丹,2010等),其优势主要表现为组织机制灵活性,快速反应灵活调整;服务内容专业性,提供科学高效的产品;行动理念志愿性,强调奉献、责任与利他主义精神;组织定位民间性,通过广泛而细致的参与,关注细节,力量下沉(胡冰冰,2010;李丹,2010;马海韵,2011;李书巧,2012)。尽管如此,NGO参与仍然存在着合法性困境、参与困境、能力困境、合作困境、资源困境等多重障碍,究其深层根源,在于法律制度缺位、管理体制缺陷和合作机制缺失。基于此,研究者从政府和NGO两个维度提出了路径选择(徐祖荣,2008;孟甜,2014;胡冰冰,2010等)。

(三)汶川地震和雅安芦山地震中的NGO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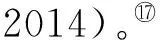
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不仅引发了学界关注,也成为公众视野下的重要话题。现有的研究就其背景和理论基础、功能优势、困境与路径等方面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线索和思路,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展现了主体间的动态调适和博弈情形。然而,历经多年更迭,在现实的再次检验中NGO参与状况是否有所改观,又呈现怎样的发展规律?现有研究并没有很好的回答;此外,这种变化背后的演进机制也值得关注,它预示了从改革起点走来的NGO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中成长的路径选择。而这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
二、对两次联合行动的纵向比较



在借鉴斯蒂文·芬克的经典“四阶段划分法”基础上,结合事件本身,我们将两次重大公共危机划分为危机爆发,危机过渡和危机恢复阶段,据此对两次NGO联合行动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具体见表1),并作比较分析。

表1 两次重大公共危机中NGO联合行动过程回顾

第一,危机需求回应精细化。基于科层制的政府救援响应,能短时间内汇聚大量资源与投入,却难以实现物资的精细化投放,呈现出“强力量”和“粗线条”特点。政府储备救灾物资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为帐篷棉被,而当政府物资到达灾区后,往往需要依靠NGO力量才能送到灾民手中。相形之下,NGO救援力量虽然微弱,却更为下沉,事实上更能够满足受灾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这一方面是由NGO本身关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的,另一方面,“船小好掉头”,NGO在危机应对中更为灵活机动。在汶川地震中,“5·12中心”联合行动通过考察当地灾民的实际需要(能细化到某种特定物资),有针对性进行物资的调度、安排和补充,不过这仍然属于反应式的需求回应。“4·20联合行动”则更注重对灾区信息和灾民实际需求进行主动获取和提前感知,为政府救灾需求回应网络的相对盲区做了较好的填补。
第二,自身角色功能定位明晰化。从无序到较为有序,从志愿者乱象到联合行动,NGO的危机参与逐渐反映出组织理性。首先,自身功能定位更清晰。一些专业的民间救援队伍有能力在救灾一线与政府成功对接,但大量的NGO“术业有专攻”,并不具备直接救援实力。“4·20联合行动”中,NGO第一时间就很明确,公益机构的长处在过渡安置和重建阶段,调查灾情并提供多样化的志愿服务。当然,民间一线救援力量如何被纳入应急响应机制中去,而不是仅作为临时性伙伴,值得进一步关注。其次,与政府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更明确。政府主导、社会互助、灾民自救是危机救援主基调,超越外部现有制度约束和内部自身能力约束,既是困难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之“协助政府、助力灾区、有序参与、有效服务”成为联合行动共同使命,始终明确作为政府助手的角色。
第三,政社合作带来身份认同。在全球视野下,多主体共治是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2008年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自组织自合作过程的产物,能实现联合原因在于部分本地组织具备一定合作基础,通过联合倡导能迅速达成共识。联合行动主动向政府汇报工作内容和进度,以获得官方认可。而在2013年,共青团省委第一时间加入,联合行动成员与官方的紧密互动成为了新的现象,继而一个完全草根的自组织联盟,在缺乏正式制度的前提下,转变为准“政社合作”性质的联盟。对NGO来说,官方的认同是展开行动的一项重要资源,而对政府来说,通过管理与引导,处于风险管控之下的NGO及其联盟可以成为危机应对的有力助手。

(二)内在动因与机制。演进规律是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NGO参与的方式能力、广度深度等表层变化的展现,而究其深层机制,这种成长与变化在发生机理、发展轨迹和合作拓展中,有着特定的内在逻辑,也即参与的发生受到“个体情感—组织职能—社会责任”机制路径的驱动,参与的发展符合自组织演进机制,参与合作的拓展动力则来自于政府与NGO之间的资源交换机制。



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也是其自组织系统演进的结果。危机信息能量的外部输入,促使“个体情感—组织职能—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生效,而在参与过程中NGO主体间既有竞争倾向,又显示出协同的意愿与行为。以“5·12”联合行动、“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4·20联合行动”等为代表的自组织合作的出现打破僵局,显示了NGO有序参与的新趋势,这种由涨落冲击平衡状态所形成的序参量产生示范效应,从而能够逐步构建有序参与结构。


首先,外部合法性认同是最基础的资源。较之于韦伯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系统合法性,组织合法性则属于更宽泛的范畴。对于NGO组织来说,内部合法性易于获取,成员大多基于自愿凝聚在一起,外部合法性获取则存在挑战。长期以来,国家凌驾于社会积重难返,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在常态管理中独当一面,压缩了社会自治空间。当面临重大突发危机时,在西方看来的“父爱式”的政府,便成为人们除自救以外寻求帮助的首要对象,如此这般,NGO自下而上的外部合法性获取自然艰难。广大NGO认识到在危机参与中如若没有政府认可,或是寸步难行,或是剑走偏锋。与其说,联合行动的拓展将官方组织吸纳进来,毋宁说是政府将NGO自组织联盟纳入其危机应对救援体系中,两者通过交换过程,整合了危机应对的全社会资源。
其次,制度空间是参与行动的重要资源。危机中NGO参与的制度空间,既是一种行动框架,也是一个行为边界。就现实来看,这种框架是不完备的,边界也并不清晰。缺乏足够的制度供给,无法明确制度预期,成为NGO行动的重大障碍,并不明朗的局面,带来了交换的动机和机会,NGO或是主动依附,或是积极配合,当然也有部分出于其他考虑坚持单打独斗。制度缺失下NGO的多样化策略实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三、构建NGO危机参与机制
不可否认,志愿精神能够在危急时刻凝聚很大范围内的社会力量,并且较之于政府动员,它的号召更能充分引起社会共鸣,发挥着超乎预想的作用。在大灾大难面前,NGO代表着一种来自社会自身的能量,对原子式的个人予以重组。然而,缺乏组织与引导的志愿力量易被自损消耗,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需要进一步规范,有序而有效的参与才是发挥其最大功能,实现其最优价值之途径。从政府和NGO自身角度,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构建和完善NGO危机参与机制。如何将NGO纳入国家的重大灾害响应和应对体系中,2011年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11年10月16日修订)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没有完备的参与机制制度条件下,NGO行动更多的受到信息不对称的误导,或者政府力量的挤压,再者缺乏整体自合作的能力与经验,其参与质量尚有很大提升空间。政府应当帮助NGO在危机状态下的响应建立规范路径,这种机制强调以社会自身为主导;同时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社合作协同机制。
其二,加大对NGO行动的资金支持。除部分官方NGO与公募基金会之外的其他民间组织尚不具备接受社会募捐善款的法律资格,大量草根NGO的经费只能来源于个人捐赠、上游基金会或者国外的资助,政府的支持十分有限。由于规范性和透明性受限,不谨慎的募捐容易招致“非法集资”嫌疑,这对于本身生存能力羸弱的草根组织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风险。对有能力参与危机治理的民间组织,政府应当对其加强组织培育,加大资金支持,同时完善危机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民间善款可逐步放开交由社会自身运作,而强化对其规范性、公开性、透明性的监督要求。

政府与NGO的互动与交换,若能通过合理赋权来提升其合法性,改善制度容纳以厘定其行动预期,辅以信息共享与资金保障等配套支持,同时NGO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那么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双方功能互补的优势才能得以更为有效的彰显,实现由“管理”转向“治理”,由“政府支配”趋于“政社协同”。


注释
①“NGO”概念被广泛使用,和“非营利性组织”、“群众性团体”等称谓相比,更多的强调的是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的角色特征。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存在着一些重要的NGO与政府关系密切,有的被称为Gover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NGO)。尽管如此,这些组织也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②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和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③莱斯特·M·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贾西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④Jennifer Y. J. “Hsu,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GeographyCompass, 8/2 (2014): 98-110.
⑤⑧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⑥大量的社会问题不单单体现为市场带来的外部性,从更深层次来说,他们属于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后果”。生态环境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些社会学的缔造者们并没有预见到,“生产力”的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2月,第7页)。
⑦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和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民间组织管理缺乏一般性法律,存在“真空地带”,此为“制度匮乏”的集中表现;重复、交叉、繁琐的规范性文件造成双头或多头管理,意欲实现“双保险”的制度实际却可能造成推诿塞责,此为“制度剩余”。公民社会的现实空间大于制度空间也是制度环境一大特点,由此呈现大量NGO 的制度外生长。
⑨民政部修订与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四类直接登记社会组织认定标准》和《全国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暂行办法》。从明确开展直接登记以来,全国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约3万个,占同期登记的社会组织40%以上。参见《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全国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约3万个》,中国社会组织网,2014年9月25日,http://www.chinanpo.gov.cn/1940/80512/prepgindex.html.
⑩《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中国社会组织网,2014年12月18日,http://www.chinanpo.gov.cn/6061/86116/pgindex.html.


























责任编辑王敬尧
On NGOs’ Participation in Major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and Its Evolution
Jin Taijun Zhang Jianr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The NGOs’ participation in major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has been attracted broad attention. Most of current documents focus on normative analysis and cases study, lacking concrete analysis on the participation evolution of NGOs in major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ases study of the joint operations in Wenquan Earthquake and Lushan Ya’an Earthquake, the evolution rules of the NGOs’ participation in major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can be obviously found, which is, refined responses to the demands in crisis, clear role definition, and identity brought by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commune management.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practical obstacles for NGOs in the aspects as,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he sources and management of funds, and self-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participation evolution of NGOs in major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that is, the occurrence of the participation is motivated by “individual emotion—organization function—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icipation conforms to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comes from the resources exchang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NGOs.
major public crisis; NGOs’ participa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crisis management;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commune management
2015-08-1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14JZD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