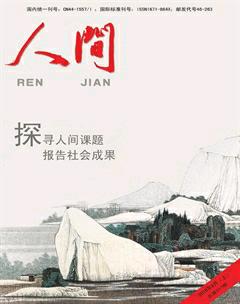司马迁对孔子天命观念的继承与突破
2016-08-15黄旭峰
黄旭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司马迁对孔子天命观念的继承与突破
黄旭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孔子思想中的天命观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其中孔子关于天命观的二分法以及“畏天命”的主张对于司马迁影响颇深,司马迁推崇天命决定论以及主张个人内在修养的思想因素正源于孔子的天命观,然而另一方面,受当时社会意识和家族环境的影响,司马迁的天命观中产生了否定天命决定论的因素,这可以看作是对孔子天命观的一大突破。
孔子;司马迁;天命观
一、孔子关于“天”、“命”及“天命”的观念
杨伯峻《论语译注·试论孔子》中分析,《论语》中“天”字出现了18次,其中孔子说了12次半,“天”主要有三个意思:即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而“命”出现了五次半,“天命”出现了3次。
(一)关于“天”的记载。孔子江天分为了三种: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以及命运之天。孔子认为天为自然物,即天又是自然之天;而在自然之天之上,把天所具有的规律、准则上升为先天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为义理之天,此外天还为命运之天,具有主宰命运的能力。
1.自然之天。
关于自然之天的论述出现了三次。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2.义理之天。
关于义理之天的论述出现了一次。如: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3.命运之天。
关于命运之天的论述则出现了8次多。如: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二)关于“命”的记载。孔子认为“命”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指 “天”决定人长寿或夭折、生或死的符合自然生死规律结果,其次:指人“道”能否实现,人的使命能否最终完成等这类非人力的结果。关于“命”的记载在《论语》中出现了5次半。如: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雍也》)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三)关于“天命”的记载。在对于“天命”的看法中,孔子将“天命”分为了两层:知天命和畏天命。
1.知天命。所谓知天命,指认识内在于人的、人能够认识掌握的天命 ,认识上天赋予给世人的特别使命,指“成人”——使现实的人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这里“懂得天命”必须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达到的。
2.畏天命。所谓畏天命,指现实的人应该敬畏外在于自己的、非自己所能认识掌握的天命,这样的“天命”,就是命运,而不是一味地屈服、服从命运。如: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贵的人,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也不敬畏,不尊重地位高贵的人,轻侮圣人之言。这里的“畏”并非畏惧、屈服,而是敬畏、尊重之意。
由以上可见,孔子思想中的天命观将外部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同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相结合在一起。首先孔子思想继承了从殷至周“敬天事鬼神”的传统思想,即对客观的自然规律存在着敬畏之心,即“畏天命”,但同时孔子更主张“知天命”,即不要过度关注于未知的自然世界,而是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屈于命运,不畏惧“天命”,即对于天命观的两分法。孔子所谈到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这种天命观的集中体现。
孔子的生死观对于后世的儒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之思想影响颇为深刻。
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及其天命观
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交代自己创作《史记》的意愿:“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单从字面上讲,“究天人之际”即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天”这一概念,有学者讨论,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时,其含义大致有四:一是自然之天;三是天帝的代称;二是天命神道的代称;四是义理之天,强调天与德的同一性。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既意欲探讨“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亦欲探讨“天”与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究天人之际”与司马迁史学家族传统的关系。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典天官事”的先祖事迹,《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甚详:“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一再表述自己的决心。父亲临终前,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继任太史令后,他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由此可见,司马迁先祖的职责是“绝地天通”,协调与沟通天和人关系,这同样也是作为史官的最为基本的职责。而这一职责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从重、黎时代,一直延续至司马迁,可以说之所以司马迁会产生“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同他本身所处的职业环境和家族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司马迁天命观的两面性。
在“究天人之际”的大框架下,司马迁在著书之时对于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主张天命论,即上天决定命运,而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论说提出了猛烈的批判和质疑。
1.司马迁推崇天命决定论。
司马迁在论述不同人的命运之时并没有给出更为明确的答复,而是将这些都归因于天命。在天道与政治的关系上,即人类社会发展与天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史记·天官书》)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继而以规律总结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上天之助,并非人力。
另外,在《五帝本纪》等文中叙述王朝更替时都反映了司马迁推崇天命决定论的思想:“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在史记中还有介绍占卜、卜筮重要性的篇目《龟策列传》等。
又如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在他看来,刘邦能在秦末众起义军中崛起,建立汉朝,也是天命的眷顾。
2.司马迁对“天命论”提出质疑。
司马迁虽然在一方面推崇了天命决定论,认为上天决定人的命运,然而在另一方面,他还大胆的对天命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在《伯夷列传》中,他对于天命决定论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抨击。传中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
对于历史上众多仁人志士、正人君子遭受了与之人格不相配的的命运,司马迁针对天命决定论提出了猛烈的质疑和抨击。
三、“究天人之际”思想同孔子天命观的关系
以上通过对司马迁家族背景以及其论史的特点可以看出,他很好的继承了司马家族自古以来“绝地天通”的史官职责,同时对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天命观又有着极其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司马迁推崇天命决定论,认为上天可以决定人的命运,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抨击。
(一)对于孔子天命观的继承。
1.对于孔子“天命观”二分法的继承。孔子对于个体命运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天命观,一方面承认了个人的生死等外在环境是受天命的影响的,个人无法左右,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的内在德性和修养等是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提高和完善。而司马迁则正好继承了孔子关于“天命观”的二分法。
首先,承认上天对人命运的主宰,如秦将白起在同一中国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结果被要求自尽,白起在自刎前曾仰天长叹:“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尔后便回答道因自己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数十万众,自己也死不足惜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是相信上天决定命运的,既然白起曾对赵军犯下罪行,那么最后被迫自尽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司马迁对于天命决定论的批判也继承于孔子的天命观。虽然承认了上天主宰人的命运,但人的内在修养和德性是人靠主观能动性决定的。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等都被视为是司马迁质疑和抨击天命论的篇章。
2.对于孔子“畏天命”的继承。孔子的“畏天命”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即天命存在着敬畏之心。如:《论语•述而》中写道:“子不语乱力鬼神”;《论语•雍也》中也谈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以看出,孔子主张对于天命、对于鬼神需常怀敬畏之心。司马迁虽然对于天命决定论产生怀疑和抨击,但从未有过藐视、否定天命的语句。如《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等等都体现了司马迁对于孔子“畏天命”思想的继承,对于天命鬼神常怀敬畏之心。
(二)对于孔子天命观的突破。
司马迁虽然继承了孔子关于天命观二分法以及“畏天命”的思想,然而司马迁关于天人关系方面还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同当时的社会意识以及家庭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西汉初年,惠帝高后以及后来的文景二帝都相继采纳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与民休息的思想观念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同样是一位有名的黄老理论家,因而他的思想中带有一定的道家思想色彩也不足为奇。在《史记•天官书》中曾谈到天与地相对,是日月星辰等自然天象的总成,不具有任何神秘色彩,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因此在谈到国家兴亡、个人命运的时候将其原因归结到个人自身,而并未依赖于天命。
从这一点来说,司马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思想中将“天命”神格化的主张,而采取了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素,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孔子天命观的一大突破,而正因为如此,也可以理解司马迁对于天命决定论提出质疑的缘由了。
四、总结
司马迁作为西汉初年的史学家,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他的“穷天人之际”的天命观同孔子的天命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迁的天命论有着非常对立的矛盾,其一:他推崇天命决定论,认为天命决定人的命运;其二,他又对这种天命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司马迁矛盾的天命观可以从他和孔子天命观的关系中得到启示,一方面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天命观中的二分法的主张,以及敬畏鬼神、敬畏上天的“畏天命”的思想,但同时,因当时的社会意识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司马迁的天命观或多或少受到了来自道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这一方面对于孔子的天命观有着一定的突破。
[1]杨伯峻. 论语译注•试论孔子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2]【春秋】孔子. 论语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朱俊艺. 孔子天命鬼神思想研究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6
[5]张守东. 论孔子的天命观 [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1)61-65
[6]聂石樵. 司马迁论稿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7]钟书林. 《史记》“究天人之际”与史官传统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10-13
[8]江淳.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初探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4) 56-59
Sima Qian’s inheritance and breakthrough on Confucius’view of“Tian Ming”
B222.2
A
1671-864X(2016)08-0141-02
黄旭峰(1993~ ),男,汉族,籍贯:湖北省武汉市,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