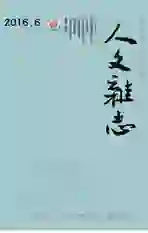十七年文学选本编纂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学考察
2016-08-02徐勇
徐勇
内容提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期出版的十七年文学选本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之间关系密切。这不仅仅表现在文学资源的取舍上,还表现在其有效地参与了针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方向的构想。如果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是以一种“作品选读”的方式既重构了十七年文学传统,又指向了创作上的种种可能的话,那么《重放的鲜花》则成功地实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接,并以此重申一种新的时代主题的文学。《短篇小说选(1949-1979)》等则通过对30年来短篇小说的编选完成了对建国30年文学发展的叙述,以此达到对转折时期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建构。综合看来,十七年文学选本编纂,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针对新时期文学的命名和构想。
关键词社会转型选本出版新时期文学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6-0044-07
自“四人帮”覆灭及“文革”结束以来,建国十七年乃至民国时期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纷纷重版再版,其中很多都是当时遭到批判的“毒草”之作。这些作品的重版或重新发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彼时“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甚至成为当时文学观念的更新先锋,在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当中,有关建国后十七年文学选本的编纂出版,尤其值得关注。
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较早出版的有关建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中下三册。这套选本的出版,“拨乱反正”的意图十分明显。出版说明中写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文艺出版部门在整理、出版、介绍中外优秀文化遗产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对推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过贡献。
但是,在“四人帮”控制文艺界期间,他们严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他们不仅扼杀出版古代和外国的优秀文艺作品,还公然制造什么从《国际歌》以来一百年间文艺创作“空白”论,把毛主席的光辉诗篇和一系列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包括鲁迅和高尔基的不朽著作,都一笔勾销。……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得到大发扬的今天,我们出版《文
学作品选读》丛书,目的在使广大业余作者有所借鉴,能对当前文艺创作起一点促进作用。丛书将选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在今天有一定学习借鉴价值的作品;同时也适当介绍一些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在文学史上都有一定代表性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按类陆续分册出版。(一九七八年一月)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是《文学作品选读》系列中的一种,按照其下册《编后》的说法,“本来准备出上、下两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下册付型的时候,我们感到有必要增补一些作品,决定改出上、中、下三册,因此在体例上有些混乱”。也就是说,该书中册,应是原来意义上的下册,上册和中册是一个整体。联系上、中两册出版的时间1978年初(正式出版时间是1978年5月,出版说明中的标记时间是1978年1月),这里所说的“形势的发展”,应该是指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展开的大讨论及其思想解放运动。如此,这套作品选,以中册为分水岭,彼此之间实际上构成一种潜在的张力对话关系。可见,表现在这套作品选中,时代转型的症候特征十分明显。
关于这一症候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综观三册,特别是下册,虽然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编辑出版,仍没有选入某些被后来的文学史家颇为赞赏的作家作品,诸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斗》等。应该看到,这套作品选虽有拨乱反正的诉求和意图在,但并不能夸大,其受时代的限制十分明显。第二,这套作品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小说创作纳入编选的范围之列。小说选取了诸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宗璞的《弦上的梦》等发表于“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作品。换言之,这既是一部过去时态的作品选本,也是正在进行中的文学形态的反映。选本把两个时代的文学——“四人帮”“文革”时期没有作品入选——连缀一起,不仅表现出试图重构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意图,还表现出把当时正在进行的还未被充分接纳的伤痕(反思)写作纳入这一传统中的努力。两者之间的并置及其内在关联,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伤痕写作的合法性基础:因为拨乱反正,十七年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其与转型期的作品并置能起到阐发后者并为其合法性辩护的客观效果。如若联系伤痕文学写作在当时引起的争论,这一意图更易显见。第三,这一套选本创造出一种“作品选读”的选本编纂模式。所谓“作品选读”,是指作品选的编选中没有导言,只有简短的出版说明或“编后”之类的文字。有读者在拿到《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后曾指出:“按照一般习惯, 很想看一看记述本书编选经过的‘前言 或‘后记,然而找不到。虽然有一篇‘出版说明,但它是关于出版整套‘文学作品选读丛书的总说明,对了解如何编选本书帮助不大,因而也失去阅读本书的指导作用。”刘争义:《读〈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有感》,《出版工作》1978年第16期。这里所谓的“一般习惯”主要是指50-70年代。就那个时段的选本出版而言,选本前的导言部分并非可有可无。彼时较有代表性的郭沫若和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1959)、1956年前后出版的系列年选,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新作选》(1965),都有编选者就如何编选作品而作的较长的导言。而即使是面向农村的“农村文学读物”之《短篇小说》,也有《开篇之前——向读者交代几句》这样的“指导”性质的文字。对于这些导言来说,导言其实就是导读,其既在于文学观点/观念的表明,文学史秩序的建构,还在于阅读方向的引导。换言之,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和主流意识形态“询唤机制”的意图呈现。对于《建国以来短篇小说》这套作品选而言,却没有这些。至于前面的出版说明,是“整套‘文学作品选读丛书的总说明”,其既简短,只有不到650字,也并无意于引导。一方面是在“拨乱反正”的框架内编选作品,一方面却又是意识形态引导机制的有意隐退,两者间的张力构成了整套选本的过渡时代特征。而事实上,下册的补缺和随后出版,也表明这是一个处于过渡形态的具有包容性的选本:容许有后续作品不断来填充。反过来看,入选作品的不稳定性也是作品编选时的小心谨慎,和空间定位(文学史秩序)上举棋不定的表征及其导言阙如的部分原因,而这恰恰就是转型时期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不稳定背后体现的是判断上的权宜与游移,以及政治气候的不确定性。endprint
但这是否说明作品选的出版就没有意图而是纯客观的编选呢?显然,不能这么认为。事实上,正是这种看似客观的呈现,其背后隐藏着过渡时期的文学变革的渴望与信号。“作品选读”的出版,颇有点类似于福柯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文献”,“传统形式的历史仅致力于‘记忆过去的各项遗文遗物,将这些‘文物转化成为‘文献”,其目的正在于“藉着重创一历史的话语以求取其意义”。[法]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湾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75页。首先,“选”的功能赋予这一套三册选本中所选作品以一种正面积极的评价显示自身,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各类选本编纂的通例,此一套选本虽名为“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却不是建国以来的什么作品都可以入选。当时有读者提议要适当选辑一些“文革”期间的反面作品以供批判用,参见陈艰:《要一双永远睁着的眼睛》,《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这对认识那个特定年代的文学写作当然有参考价值,但却与历来的选学传统不符。而如果收入“文革”期间的反面例子,势必要加以阅读导向性的说明,这也与这一套选本的编选策略(导言的阙如)相冲突。
其次,对于那些内含导言(包括前言、导读之类)的作品选而言,导言建构了一套秩序和规范,其既针对写作者,也指向读者。相比之下,“作品选读”中导言的阙如则意味着某种敞开和多种可能。两个时代的文学并置一起,虽使传统得到有效地建构,但至于传统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规范,却是不得而知。可以说,正是这不得而知,预示着多重可能,并引导着人们(包括作者和读者)去创新。这是导言的阙如所带来的客观效果。另一方面,导言的阙如也意味着读者(包括写作者)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个人感受出发阅读、理解作品,而不必沿着限定的方向展开阅读。从这个角度看,这套作品选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重建读者主体性的尝试:它以敞开的方式呼唤读者的主体性发挥,而这,在上世纪50-70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呼唤,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彼此呼应,应被看成后者在文学出版及其选本编纂方面的表征。
二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1979)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期出版的另一个重要的十七年文学选本。需要看到,这是1956-1957年“百花时期”发表的影响较大并在随后遭到批判的小说汇编。选本的出版虽也有“拨乱反正”的意图,参见吴舒洁:《〈重放的鲜花〉与“拨乱反正”》,《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但并非仅仅如此。因为显然,十七年被批判的小说很多,为什么独独选取“百花时期”的作品重版?其意图何在?在这里,孤立地考察《重放的鲜花》的编选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从选本中作品反映的时代(1950年代中期)和选本出版的时代(1980年代初)两个时代间的关联这一角度综合考察。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编者指出“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声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音、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编者:《重放的鲜花·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前言第1~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重版这些作品并非仅仅意在“拨乱反正”,其意还在于这些作品背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就是说,有无“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是被批判的作品能否重新绽放(即“重放”,而不是重版)的重要前提。可见,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重放”,而不在于曾经是否“鲜花”,其涉及的问题显然不仅仅只是拨乱反正。“百花时期”被扼杀的“鲜花”能够“重放”,是因为其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个集子里反映的社会矛盾,二十年来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陈思和:《捍卫诚实的权利——读〈重放的鲜花〉》,《读书》1979年第8期。可见,这些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官僚主义仍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存在严重妨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主题上的前后连贯是保证这些作品能够“重放”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这一生命力还表现为不粉饰现实和不回避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扎根现实生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揭开掩盖现实的种种假象,探入发掘、深入认识,为那处于萌动中的新芽,献出你的爱情;对那在阴暗角落长出来的毒菌,投去你的憎恨……只有透彻的认识现实,理解现实,深入到现实的本质,才能启示未来”,参见李国权、汪剑光:《重放的鲜花仍然鲜艳——谈文学的生命力》,《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体现的是一种真和诚的文学,故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可以看出,“重放”其实也即意味着对曾经鲜花的“激活”并以此与当下“对接”。其落脚点是在“对接”上。具体而言,这一“对接”主要表现在:第一,呼应时代,中心转移。按照前言的说法,“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面对当时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一些作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进行探求”。⑤编者:《重放的鲜花·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前言第1、2页。对比《重放的鲜花》出版时的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全党工作重点也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两者间的呼应关系十分明显。如果说“新的形势”下的1956年文学的任务在于“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的话,那么其对于1979年的文学创作而言仍复如此且仍具有效用。换言之,当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议题是现代化建设时,文学的中心应该转移到围绕这一中心议题的转变上来。从这个角度看,《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其实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文学表现问题。因此,第二,对于这一文学主题,需要一种直面现实中的困难和矛盾的勇气与精神,而非仅仅流于对现代化美好承诺及其愿景的简单表现。如此种种都一再表明,《重放的鲜花》中通过对“重放”的凸显,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现实取向和当代意识。这样来看,第三,《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客观上就包含有(或表现出)对彼时文学创作的不满。我们知道,“四人帮”被打倒后,对“文革”创伤的记忆及书写一度主导着当前文学的创作,影响所及,曾有过文学“向前看”与“向后看”,“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参见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如果说“伤痕”写作是一种“向后看”的写作的话,那么指向现代化的文学写作则是一种典型的“向前看”的文学。现代化的伟大承诺,确保了这一相关的文学写作的青春气质和现代性倾向。从这个角度看,《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其潜在的意图还表现在挣脱当前文学创作的困境,提倡一种新的时代主题的文学主张。endprint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并不仅仅是在提倡一种改革文学,虽然说反映“四个现代化”的诉求与改革文学间有其内在的关联处。因为批判官僚主义,在新的时代还有其反思“文革”的现实指向,而“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多样化”诉求,也不仅仅意味着改革文学的写作。尤其是对爱情题材的提倡,其意还在于暗示我们,重大题材之外的“家务事、儿女情”等“‘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只要“遵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即政治思想的一般错误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引注)的原则”,⑤仍有其价值,题材禁区仍然需要打破。如果说对“干预小说”的提倡,体现的是两个时代的“对接”的努力的话,那么《重放的鲜花》中对爱情题材的倡导则在于提出了时代精神和总的主题下的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命题,从这个角度看,其对彼时潮起潮落下的文学写作和对“宏大叙事”的偏爱不啻是一种反拨和警醒。
三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折时期的选本出版而言,1979年是一个契机,当时有大量的关于建国30周年“献礼”式的选本出版,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8卷)、《散文特写选(1949-1979)》(3卷)、《诗选(1949-1979)》(2卷)等之外,各省市如山西、河北、安徽、山东、吉林、黑龙江、江苏、甘肃等很多省市都有30周年选本出版。事实上,国庆周年“献礼”式选本,早在1959年就有出现,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上海十年文学选集”,包括论文、短篇小说、特写报告、散文杂文、诗、儿童文学、话剧剧本、电影剧本、曲艺等十种。但30周年与10周年毕竟不同,因为这30周年中包括“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的过渡时期,因而如何评价“文革”十年文学和过渡时期就成为国庆“献礼”选本的难题和关键所在。
而实际情况是,在建国30周年之际的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后,关于“总结三十年”的话题也一度成为焦点,其中对诸如如何评价建国以来30年、建国后“十七年”、“四人帮”覆灭以来的“三年”等三个时段的文学运动的成败等问题,在批评界和创作界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参见刘锡诚:《“十七年”和“三年”》,《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339页。《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这一套选本从1979年5月开始出版,一直到1981年最终出完),正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得到理解。虽然说周扬在1979年11月1日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十七年文学和三年来的文学成就,参见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7~241页。这对选本的编选工作并非没有影响,但从其《短篇小说选(1949-1979)》各本间的内在关联来看,选本以其特有的编选实践从侧面回答了上述争论。
《短篇小说选(1949-1979)》是一套8卷本的短篇小说集,在这套短篇小说中,“文革”期间的作品只有四篇(收录于第6卷),时间是从1972年开始。也就是说自1966年至1971年间的作品没有收入其中。这一时段文学的空缺表明了选本对“文革”十年文学的基本评价:这并不是说“文革”十年没有文学创作,而只意味着文学跌入低谷,只是到了1972年才逐渐有了起色,慢慢开始回升。在这当中,1972年是一个分水岭。而至于为什么要以1972年为分水岭,则要联系1972年的社会上下文。1971年的林彪事件,及其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使得“文革”在1972年以后实际上已经走向末路;参见李洁非:《1972:国家与革命》,《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15~269页。另一方面,1972年,对于文学写作而言,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在1972年之前,除了‘革命样板戏外,创作基本处于无序状态。1972年新创作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金光大道》等小说的出版,‘文革文学的话语建设进入了积极而有序的状态。”王尧:《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新时期文学“源头”考察之一》,《彼此的历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1972年对于“文革”时期的文学而言,其意义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如王尧所说,“‘文革文学的话语建设进入了积极而有序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提供了可能,“在‘文革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有着双重的‘原罪,既有‘阶级的原罪也有为‘文艺黑线服务的原罪。1971年以后,知识分子重新有了写作的可能”。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和研究》,《彼此的历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这几部作品中,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1975)和浩然的《一担水》(1972)很有代表性。浩然是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农业题材写作的代表作家,其《一担水》的主题仍旧写的是农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这部作品写于1972年,但收入这篇作品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六卷的出版时间是1981年5月。如果说选本的编选行为也是一种批评实践的话,那么可以说,浩然的《一担水》被收入其中,既是对作者“文革”期间文学写作的部分认可,也是对作品所反映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某种肯定。
我们知道,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自“文革”结束以后逐渐被废除,并在叙事上失去了其应有的合法化,这一进程与实践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相伴随。就中央一级的决议来看,虽然说迟至1982年才正式发文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早在1980年9月的一次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形式也已得到充分肯定。参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3~510页。这里,我们需要看到,中央一级的会议和决议之间的差别。就1980年9月的情况来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农村改革首先是在农民的实践中展开,而后引起全国的关注、讨论,乃至最后形成中央一级的决议(文件)的。这是一次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换言之,其合法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而是表现在实践上的探索、理论上的讨论以及决议(文件)等形式上,表现在文学实践中,其合法性叙事则显得相对滞后上。叶辛的《基石》创作于1982年(《拔河》还要更晚些),鲁彦周的《彩虹坪》1983年出版。“四人帮”被打倒以及“文革”结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书写大致经历了表现农村党员干部抵制“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生产上的极大破坏,以及恢复农业生产的过程的这一主题的变化,鲁彦周的《桂花潭》、成一的《顶凌下种》(被收入于《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七卷)、浩然的《老人与树》、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以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浩然的《一担水》被收入其中,与《桂花潭》和《顶凌下种》等农村题材小说有其内在的关联,都是农业合作化叙事的一部分,其虽写于1972年,但并非什么“极左”路线的表现。endprint
相比浩然的《一担水》中的农业合作化书写,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则写的是工业战线上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新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被提出,只不过当时是被限定在“抓革命、促生产”和“大批促大干”等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机电局长的一天》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上述意识形态的烙印,但其通过设置一个冷战两极思维的框架以表现现代化的生产激情(即用“打仗的劲头搞生产”),客观上有效地规避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这一点上看,其与新时期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之间,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但也因此,小说发表后随即遭到了批判,并被指责为“宣扬了‘惟生产力论”,参见张学正等主编:《文学争鸣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百通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霍大道也作为“醉心于文化革命前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走资派而被点名批判。罗进登:《〈机电局长的一天〉宣扬了什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6年第1期。从这个角度看,《短篇小说选(1949-1979)》把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收入于第8卷)和《机电局长的一天》置于其中,不仅有为后者“拨乱反正”的意图,也带有赓续并重建现代化叙事传统的客观效果。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一担水》被收入其中的意义在于接续传统,并建构十七年以迄于“文革”结束后的农业题材小说的脉络的话,那么《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意义则在于开启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现代化叙事的开端。两部小说分别从工业题材和农业题材两方面建构起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学脉络,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文学正是沿着回归十七年文学发展传统而建立起合法性地位的。
事实上,就30周年选本的编选而言,除了以所选小说内容和主题间“历时”性的关联暗含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三年”来文学的褒贬态度外,这一态度还体现在选本的编排上。对于这套短篇小说而言,“四人帮”被打倒后至1979年这一过渡时期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第7卷和第8卷,第6卷中也有三篇,加起来一共收录55篇。过渡时期的作品所占比重为235%(8卷一共收录234篇)。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占30年短篇创作选的将近四分之一,可见过渡时期的“三年”在这套作品选中的分量之重。从这样一种编排方式和所占的比重来看,这套作品选的出版,有其明显的当代意识和当代性特征。而这其实也是在充分肯定“三年”来的文学成就。如若联系《人民文学》编辑部刘锡诚的回忆文章来看,参见刘锡诚:《“十七年”和“三年”》,《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339页。这一意图更其明显。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这背后重构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潜在意图:通过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和浩然的《一担水》置于其间,沟通了“十七年”和“三年”来文学间的内在关联,十七年文学传统由此得以赓续。这其实是在从事新时期文学“起源性”工作:落脚点在当下,并以此往回溯源,重建起一个脉络和线索。建国30年的文学,在这一套作品选中,被建构成稳步向前发展,而后经历了“文革”时段的低谷,乃至反弹,最后在“四人帮”覆灭后迎来了高峰的发展进程。显然,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文学发展史。从这套作品选的出版可以看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期以来的文学不需要以通过回到“五四”式的颠倒或断裂的方式获取其合法性,其合法性的获得建立在自十七年来的文学传统的接续上。
四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曾用“风景的发现”以及“认识装置”的“颠倒”来指称转折时代的文学写作,对于他而言,风景发现后的回溯其实是一种以果塑因的逻辑。“谈论‘风景以前的风景时,乃是在通过已有的‘风景概念来观察的”。[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0页。 但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而言,情况则可能要复杂得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期,“四人帮”被打倒,“两个凡是”出台,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文革”的正式宣告结束——这一历史的错综复杂,使得当代文学写作中存在一种威廉斯所说的“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三种文化的说法借鉴自威廉斯,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136页。间的互相糅合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三者间的构成也并非彼此泾渭分明,“主导文化”就常常介于“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间,而“新兴文化”又常常依靠“残余文化”建构其合法性。此外,所谓“残余文化”“主导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那种简单的时间线性发展的逻辑,而是以多线纠缠并进的方式展开。《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选》(8卷)等建国30周年文学选本中不同时段的文学的并置形态,体现的正是其中错综的时空构成关系。换言之,这既是历时的文学形态的发展展示,也是不同形态文学的对接和对话;既是在新的文学观下对文学史秩序的重构的体现,也是新的批评原则得以确立的合法性论证;既是互相阐发又是互相扬弃,既是互为前提,又是互为结果。如此看来,所谓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发生,就不仅仅是柄谷行人所谓的“风景之发现”,更是“风景的构筑”问题。所谓“新时期文学”这一“风景”,其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毋宁说它是一个想象或能指,其以指向的多重可能及其敞开的姿态,有待包括选本出版在内的文学实践“赋形”并给它命名。从这个角度看,十七年文学(选本)出版,实际上参与了针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命名和构想。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策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