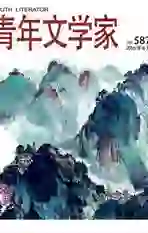来,我们跳小拉
2016-08-01陈琴
陈琴
摘 要:对于苏童,了解更多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在他的短篇小说里坚持不懈地给我们展示了温暖潮湿的江南,而这江南就像一副华美的皮囊,里面裹着流淌着脓。而对于以短篇小说见长的苏童来说,长篇小说大概是他的突破和梦想,但长篇小说带给他的并不如短篇那样容易。从《蛇为什么会飞》、《碧奴》、《河岸》到《黄雀记》,相对于苏童诸多的中短篇收获到众口一致的赞誉,他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发表带来的是困惑和疑问。《黄雀记》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在快餐式阅读及功利性写作充斥的今天,苏童还是给我们呈上了一部具有沧桑感的象征式作品。
关键词:苏童;快餐式阅读;象征式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一、关于黄雀
《黄雀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用苏童自己的话来讲,“这部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所谓街区生活。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青少年强奸案,通过案子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或者说是这三个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的命运,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作品分成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黄雀记》以保润爷爷的故事开始。保润、仙女和柳生三个从少年到青年的命运纠葛情仇爱恨,到最后扼人喉咙的命案,仿佛漫长的一个时代过去,而在故事的最后,历经数劫的爷爷却安然无恙抱着仙女产下的红脸婴儿安详地坐在水塔旁边。
书名为《黄雀记》,通读整个作品却发现没有出现明确的“黄雀”指代意象,三章大致来说,讲的就是命运轮回因果报应,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谈到“隐喻”就容易令人想到“整体象征”,“整体象征”或多或少会扯上“寓言色彩”,自然而然地,杰姆逊的寓言体系或者关于赛义德的东方学就会被莫名其妙地扯进来。在我看来,这场看似略显无所事事的故事和寓言、主义毫无关系,更多的是苏童在小说探索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下的人生思考及有点无可奈何的把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蝉、黄雀刚好是三个指代符号,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三者谁都不是黄雀,这三者在三章中轮流坐庄。在这样的前提下,故事仿佛就在象征意味的基调下富有诗意地进行。故事的开端,非常明显的意义指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穷孩子保润(蝉)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了跟草民女儿仙女(螳螂)约会的机会,做媒的是同龄小康小子柳生(黄雀),结果保润约会未遂还要向仙女讨债,就这一80元人民币的债务造就了一个保润在水塔捆住仙女然后一气而走的机会,做媒的柳生趁着这个就会把仙女强奸了。故事的开端,非常明显的意义指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要再细致地进行角色划分,大概可以勉强这样理解,第一章的小结局来看,仙女是蝉,保润是螳螂,柳生是黄雀;第二章中保润是蝉,柳生是螳螂,仙女是黄雀;第三章中柳生是蝉,仙女是螳螂,保润是黄雀。在故事的最后,失去灵魂却长寿的爷爷抱着红脸婴儿安静地坐在水塔旁,一老一少,轮回似乎至此完成,爷爷从始至终都是蝉,却走到了最后,成了黄雀,但也许爷爷一直都是蝉,禅。
看到这里的时候,《黄雀记》能够或多或少地带给我们惊喜。因为我看到了恰到好处有力量的象征,看到了诗中有失、哲中有折、玄中缺悬但却是耐人寻味的文字。而这三个人便如黄雀螳螂,互相轮流角色,在不断向前的时间轴上此起彼伏,最终抱团成一起,坠入失魂的深处,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故事。
二、关于人物
《黄雀记》的封底宣传文是这样写的:“保润、柳生、小仙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从本然之爱开始,以悲剧贯穿终了是《黄雀记》的故事主线。遽变吊诡的是这三位少年间的危险关系,无常青春。一宗荷尔蒙气味刺鼻的强奸案,战栗地歌吟着那个时代的历史,还演绎出无尽的留恋在香椿树街的罪恶渊薮。”这种为博大众眼球故意拔高作品内涵的官方行为很是让我反感,这三个即使到了三十岁却依然心智不成熟的主角,根本无法负载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从不缺少这样的堕落之人,他们更无法演绎罪恶,因为他们的卑琐被幼稚包裹严实了。除此之外,我还是觉得这三个人物形象算是成功的,在生活里并不是荒谬至无迹可寻的。
保润的眼神会让所有的女孩害怕,不管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眼神即是一个人内心性格的投射。他对家庭的态度随意又叛逆,母亲的市侩和父亲的懦弱组成无爱的家庭,保润自然是缺爱的。他的心是阴郁敏感的,敏感让他容易受到伤害。保润的十年牢狱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出狱后的他变得更加偏执,更加阴郁,甚至如同无人居住的家宅一样有了潮湿腐朽的气息,阴森到让仙女害怕。他找仙女报仇,把她捆起来跳小拉完成少年时的愿望。他恨她,却终究是爱她的。从年少到最后,仙女一直都在挑战保润的底线。然而保润似乎除了少有的愤怒,更多的是无奈,是高于一个家族的隐晦情感。他爱错人,也信错了人,无处宣泄,沉默和压抑始终是保润的内心主调。保润的魂在绑起仙女要回80元的时候就丢了,丢在水塔之下,之后十几年的行尸走肉,只是回光返照的另一种形式。
柳生的心是沸腾的,多情的,却由于过度而产生罪恶。年少时的柳生不见得喜欢仙女,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利用仙女喜欢自己将仙女出卖给保润,接着玷污仙女却免去牢狱之灾。对于柳生强奸仙女的动机我一直很好奇。仙女喜欢他,如果想得到仙女,通过正常的手段一点都不难,却要用这样的方式让三个人都走入绝境。当仙女以白小姐的身份出现在柳生面前时,柳生想起当年的肌肤之亲不禁颤抖,瞬间觉得自己占有过仙女是一件骄傲的事情。这并不是喜欢,也不是爱,而是在水塔被绑住的仙女给他的不可复制的感觉。绝大部分的强奸事件并不是由于对女孩的喜欢,而是某种情况下某个因素刺激了男性做出的犯罪行为。我认为,在这里大可以理解为柳生内心深处的SM倾向,此种性心理在作品中的体现可以进行再细致的探讨,保润的绳子不仅是无法逃离的命运,更可能是人内心对感官刺激的迷恋。他要的并不是仙女,很有可能是因为被保润捆绑后的仙女给柳生带来了不一样的刺激感,从而让柳生引发了强奸的念头。另外,柳生对保润是愧疚的,然而这种愧疚却不彻底,也不尽心。柳生被迫照顾保润祖父,他对保润的愧疚转接在祖父身上,心安理得。他替代仙女出头,去讨债要抚养费,安置她住在保润的房子养胎。他的赎罪有自己的方式,是最世俗的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只是补偿而非救赎,他从没有真正忏悔。
很对人认为苏童对仙女的塑造是不成功的,觉得仙女的形象扁平,作为人的深层个性无限趋近于零。仙女很难让人产生怜悯是真的,但在今天,真的能找到仙女这样的人。她放荡,贪婪,从小就口出狂言,张扬跋扈,为了蝇头小利把自己卖给柳生,同保润约会。拥有莫名其妙的自信,不断践踏保润,一次次挑战这个少年的底线。她一直都在伤害别人,伤害保润,伤害柳生,伤害庞太太,最后被世界排斥抛弃。仙女的失身甚至有些咎由自取,是非混淆的价值观,如果她不贪小便宜、不爱莫虚荣、不莫名其妙地践踏别人的尊严,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她用封口换来一个人的堕落,一个人的胆颤,自己的新生。她远赴他乡,做了无数达官显贵的小情人。仙女深谙年轻美貌是她唯一的资本,享受于男人拜倒其裙下。仙女自私自利,每每在别人帮自己陷入困难的时候,不顾一切自己拔腿就跑,她从来不知道廉耻为何物,尊重又为何物,极没教养。她把自己活得比婊子还颠簸,吞噬了庞老板的魂,驯马师的魂,保润的魂和柳生的魂。她还不满足,终于吞噬了自己的魂。她是这场小丑戏的导火索,也是受害者。苏童认为小仙女沦为妓女是因为她被玷污了,这大概是苏童关照女性的一种方式,而在我看来,这样爱慕虚荣、极致追求物质、看不起“屌丝男”的女人就算不失身,依然会走到成为追求金钱财富而出卖自己的人。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身边找到这样的女性,看似主权独立,却丧失人格三观不正自私自利的女性,不就是像仙女这样,性格扁平、目的简单、性格可悲的女性。
三、关于人性
一直都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恐怖内核,是对病态对象在病态环境里的病态迷恋,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者,都喜欢展示和挖掘人性之恶。很多作品是厌恶什么道德缺陷,而是无法适应湿漉漉、阴沉沉的“江南”像癣疥一样黏着在身上,挥之不去,这与生我养我、什么都可以随海风而去的江南太不一样。
个人认为,苏童的先锋与莫言不同,并不体现在他在“新时期”重新发现了人性之恶(虽然他反复强调这是其文学的首要原则),而是他为此种“恶”寻觅到了可以疯狂生长的沃土。《白鹿原》虽恶,但黄土、庄稼和历史依然保持神性,《丰乳肥臀》虽恶,但母亲的光辉和旺盛的原始的生命力依然保持神性。但《妻妾成群》之恶,仿佛梅雨一样,不由分说地笼罩一切。水乡、绅士、静谧、幽远……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引诱读者以为并接纳其美好,但旋即就发现美好的皮囊下流淌着无尽的脓水。《黄雀记》中,白小姐溺水,与垃圾一同漂向下游,但却并不脏、臭。还有对强奸现场的回避,对谋杀现场的回避,除了保润家老屋和水塔这两处被屋顶覆盖的“室内空间”外,苏童的“江南”第一次不以一种溃疡状态下的面目示人。但其腐败、糜烂的空气就轻易地摧枯拉朽般突破了我心理的防线。
仙女之恶直接断送了两个少年的美好前程,她自私自利,从不在乎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灾难,都觉得别人是活该,从不反省自己,她身上带给人的是一种毁灭在咄咄逼人地敲门的气息。柳生之恶在于从未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到底有多深,用所谓的弥补来安慰自己掩盖罪行,当保润出现的时候,害怕的是保润报仇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后悔和愧疚。他的情欲和幼稚送葬了自己和保润。保润这一无辜之人,苏童剥夺了他自我辩护的权力,无法将自我的生存境遇讲给别人听,但也只能将这个归咎到保润的自我性格的问题,他没有朋友没有背景没有亲人,走上不归路也全是因为爱错了却放不下。香椿树街上的人们各有自己的恶,柳生的母亲托关系、让仙女放过柳生却让无辜的保润当了十年的替罪羊,这种自私草率剥夺别人自由及生命的行为让这三个命运纠缠的年轻人有了可预见的未来。也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苏童和余华的不同,如王德威所说,《第七天》所能触及的极限就是虚无主义,是对(中国)生活的彻底决裂,而《黄雀记》则是苏童开始试着追问造就并捉弄亿万黎民起伏挣扎的“命运”究竟具有怎样的复杂性。
四、结语
《黄雀记》并非完美之作,但在当下充斥着功利性写作和快餐式阅读的环境里,苏童还是呈上了一份带有沧桑感的象征式文本。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故事,并非小丑们闹一场就散了,其间纵有百般不完美,但作者凸显岁月张力的意图和努力着实可辨,对生活和命运的追问亦是发人深思。苏童不是全然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个人创作中还是蕴含了不少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恰恰正是这些东西给予了苏童一定的区分度——仪式化的场面、寓言式的情节和对老旧时光的眷恋,也是其标识性的特征,如若一定要将其拿出来与所谓现实去较真的话,不免失却了意趣和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