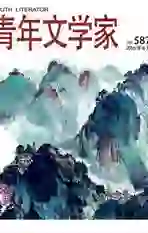元白诗派诗歌中的“风雅”传承
2016-08-01樊梦瑶
樊梦瑶
摘 要:本文从“风雅”的文化内涵,元白诗派诗歌中“风雅”传承的社会背景说起,重点阐述了元白诗派诗歌中的“风雅”传承与创新。并且证实,盛唐诗歌之所以繁荣发展,经久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风雅精神”的继承。
关键词:元白诗派;风雅精神;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一、“风雅”的文化内涵
“风雅”,原是指《诗经》中的篇目“国风”,“大雅”与“小雅”。风、雅、颂是《诗经》从音乐上的三个分类。其中,“风”为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方的歌谣;“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是周王室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即正之义,又称正声,“大雅”和“小雅”只是时间上的区别。《诗经》中的“风”、“雅”部分又集中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因而被中国诗歌一脉相承,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主线。
《诗经》的写作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它的成书过程有所谓的“采诗”一说,也就是由各地史官走向民间,去采集诗歌。因此《诗经》的创作可以说是取之于民间,具有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现实主义特色。历代诗歌继承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仁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写作传统,突出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倾向,传递乐观积极的道德与风尚,突出文人心怀天下的胸襟和抱负,谓之“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后来被广泛运用于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更有利于诗歌的传诵与发展。
二、元白诗派“风雅”传承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自隋朝形成,到唐代武则天时首创“武举”,达到鼎盛时期。首先,在唐朝科举考试的明经一科中,对于“四书五经”的背诵成为主要的考试手段。进士科考试注重考察考生对诗赋的积累程度,诗赋的写作注重文采,因此《诗经》也就成为了衡量考生文采的重要依据和手段。其次,唐代文化格局十分开放,君主非常重视士人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准的提高和对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鼓励诗人创作,诗风盛行。这为“风雅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文化基础。再者,唐代经济社会繁荣,商品和货物经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互通有无。此外,经济的繁荣也为诗人的漫游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外交流也开阔了诗人的眼界。这为“风雅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社会保证。
另外一个方面,六朝诗歌形式主义之风泛滥,诗人追求词藻华缛和对偶工整,更有人追求玄学,追求隐逸不羁,突出诗歌自我抒情的一面,抒一己之情。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诗坛文风“淫靡”,背离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主旨,诗人在“四声八病”等形式主义的桎梏下,诗风低靡,严重地制约了诗歌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初唐诗人即站出反对六朝诗风,到了中唐,元白诗派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诗歌传承“风雅精神”,反对六朝形式主义诗风。
三、元白诗派诗人对“风雅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中唐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因为长久的战乱而民生凋敝,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面对这风雨飘摇的局势,许多有识之士已经从消极的心态中摆脱出来,想要通过针砭时弊的改革挽救时代危亡。于是,这场改革在文学领域便集中表现为贞观至元和年间出现的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由元稹、白居易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是中唐诗坛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一生写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中期的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并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国的疆土,把唐代诗歌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自觉地传承了中国诗歌的“风雅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大力提倡新乐府运动,要求诗歌干预生活,并身体力行,反映劳动人民疾苦,揭露统治阶层暴行。他的诗歌“重写实,尚通俗”,其现实主义高度,远远超越了杜甫,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块新的里程碑。
如他在《红线毯》一诗中写道“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作为全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秉承其“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创作主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全诗主旨——鞭挞统治者的黑暗腐朽,和他们对蚕丝的浪费。这句诗的意思是,地本不知道寒冷,却要为其织上红线毯作为覆盖;百姓是人,知道冷热,却没有衣服穿。在这样的对比中,诗人客观地描述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冷静而激烈地对奢侈浪费这一在当时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白居易对“风雅精神”继承的具体表现之一。
另外,白居易对《诗经》“风雅”的诗学观念的继承主要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他认为,在诗歌的创作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意”。还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1]他在解释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说,如果把诗歌比作一棵果树,那么情感就是它的根基,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语言是它的枝叶,也是它得以开花结果的重要保证;声韵是它的花朵,也是它的外在形式的体现;而它的果实,则是诗歌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创作中也十分重视情感的抒发,他抒发情感是借助于“根基”的,这点与《诗经》的创作一脉相承;其次,白居易发现了“风雅精神”中所具备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大力倡导后人学习和继承《诗经》的创作传统,要“泻导人情,补察时政”。还要求诗人在诗作中关注民生疾苦,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大胆抨击社会的黑暗腐朽,努力创作出属于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作品,发挥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警醒后世。白居易的诗有两大威力,一是敢于揭露时政的阴暗面,有的诗直指朝廷和皇帝,体现了白居易的远见和气魄。二是讽谕诗,他针砭时政毫不留情,解决了杜甫所未引起重视而又在其实践中做了的事,对后代诗歌创作影响很大。因此,“风雅精神”也是他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的核心所在。笔者认为,他最后之所以被列入“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也与其继承“风雅精神”的创作传统密不可分。
此外,他还提出了“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所谓“五为一不为”的创作主张,更为深刻地强调了“惟歌生民病,愿为天子知”的诗文创作理想,强调进行诗文创作应该关注民生疾苦,并且有所兴寄,且诗文创作的题材和语言等外在形式的部分应该尽量为诗作的内容服务。这都可以视为对“风雅精神”的深刻认知,即以内容为创作核心的继承,就是进行“风雅”传承的体现。他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上承《诗经》,下继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元白诗派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元稹的诗学理论不及白居易那样深刻,也没有超越白居易的精辟观点。他对“风雅精神”继承的贡献表现为与白居易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推动了中唐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在具体观点上,他充分肯定了《诗经》中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蕴含于其间的教化功能。这点,在他的《元氏长庆集》中体现的尤为明确。他说:“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2]从中可以看出,元稹十分欣赏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作,赞同他“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创作方法,肯定了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风雅精神”的核心具有的一脉相承的联系。元白诗派诗人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批判形式主义,在捍卫和发展中国诗歌“风雅精神”中的现实主义原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元稹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谈到,“为诗意如何?六艺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可见,在他的诗文创作中,相当重视对“风雅精神”的继承。他认为运用《诗经》“六艺”创作出的诗文才能做到言之有物;反之,不继承“风雅精神”的诗文因为缺乏兴寄,所以没有灵魂,就显得空洞乏味。很显然,他个人是比较推崇《诗经》中风雅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一点也可以看作其风雅传承的重要表现。
可以说,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首的一大批诗人在中唐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社会发展渐渐走上下坡路的时代高扬起“新乐府运动”的旗帜,主张诗文创作中的“风雅精神”和兴寄理想,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先驱性的改革,对后世诗歌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风雅传统,元白诗派的诗人在继承的同时,也时刻高扬着创新的大旗。
元白诗派的诗人把对于中唐时期社会的思考融入其中,不单单是对“风雅精神”的内核进行机械地照搬照抄。他们热烈地抨击中唐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以诗歌作为与之对抗的武器。
不仅如此,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对“风雅精神”的创新有着十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创作似匕首、如刀枪的讽喻诗。还有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传世。在这些诗作中,他不仅挥洒自如地抒发个人请感,同时又能做到有所兴寄。
例如,他在闲适诗《问刘十九》中这样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试想,在一个寒冷的雪夜,作者问友人能否与自己在温暖的火炉边对坐,小酌一杯。可见诗人的兴致之高,这样的写作手法也使得闲适之情溢满全诗。诗人在这首诗里,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一杯浊酒之中,寄托在深夜与友人对坐相谈的深情里,让人读罢倍感暖意,仿佛诗中所描写的并不是一个雪天,而是温暖的春夜。这样的诗歌,正是因为有所兴寄而言之有物,所以脱离了空洞与无味。此诗将闲适之情与风雅兴寄完美结合,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堪称上乘之作。
而且,白居易又将叙事诗写到了极致。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比较有名的长篇叙事诗,在唐以前只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寥寥几首,到唐代,杜甫诗里的叙事成分明显增加,而到了中唐,出现了一大批叙事诗,尤以元白最为突出,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刘禹锡的《泰娘歌》等。这批诗人中,尤以白居易的叙事技巧最为突出。[3]
元白诗派诗人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作为诗文创作改革的核心,以“风雅精神”作为改革的内核,大胆地唱出了期盼时代复兴的慷慨之音,带来了中唐诗歌的一次中兴。它虽然不及盛唐时诗歌那样繁荣鼎盛,却也在当时的诗坛,乃至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着无法替代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见《白氏长庆集》卷45.
[2]见《元氏长庆集》卷23.
[3]袁行霈.《琵琶声中的幽怨》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集》198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