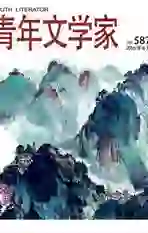行走于“乡土”的吟哦者
2016-08-01王格林
王格林
摘 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炜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他不以追赶时代潮流为其文学创作的根本,而且还常反其道而行,一直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和文学理想,以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进行着文学创作。文学史家在书写文学史时,对张炜有多重归属,很难把他纳入一个思潮,但张炜在创作中一直坚守着“乡土”这一理念,并贯穿着他文学创作的始终。
关键词:张炜;文学思潮;乡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2
一
张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既不是某一种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且他本人对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也常常反其道而行,因此文学史家们在归属张炜到底属于哪种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时存有很大的分歧。不同的文学史家把他归属于不同的文学现象中。诚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版)中所说,包括张炜在内的几位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和文学史叙述中,常有多种“归属”。他们有时会被放进“知青作家”的行列,有的则曾寄存于“寻根作家”名下。在90年代的文化精神语境中,一些作家又被归入高举理想旗帜的作家群落之中。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年版),则尝试在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热潮下找寻张炜的位置。认为从1986到1987年,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和张炜的长篇《古船》先后面世,“可以看作是寻根思潮的转型或终结”。朱栋霖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版)主要把张炜的创作归入“改革文学”的范畴。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3年版)置张炜于“乡土小说”一派中。可以说,不同的文学史家有不同的叙述意愿,不同的文学史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框架。于张炜我们很难界定他到底属于哪种文学思潮,很难把他纳入一个思潮,这也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存在有关,或许不是从文学思潮看张炜,而是看张炜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张炜在各个时期的创作是不同的,而且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张炜的一直沿着“乡土小说”这一脉搏在创作,一直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从其小说中一直出现的“葡萄园”、“野地”、“田园”等意象我们可以发现张炜本质上是一个“乡土小说家”。
二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张炜归入一种具体的文学思潮,而应以他各个时期的创作来对其定位,但要抓住其一贯坚持的“乡土”、“大地”等理路。张炜以《声音》、《一潭清水》等颇具“小清新”笔调的短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注意;随后以《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护秋之夜》等中篇确定了自己的风格,表达了对社会的独特观察和思考;长篇小说《古船》的发表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文学声誉,此后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古船》开始,他往往处在富有争议的作家之列,对于张炜创作的讨论,每每都可能引起对当时文学创作观念新的嬗变。80年代《古船》的发表引起了文坛的热烈讨论,这一时期张炜属于何种文学思潮存在极大的争议。如朱栋霖、刘勇等人的文学史把张炜的《古船》等归于“改革文学”,但张炜却“记得在80年代之初的创作过程中具体到一部作品,比较起来‘改革如何想得很少,而总是为生活、为人的历史,为人性,为屈辱和荣誉,为爱情,为诗意这一切所激动。”[1]且《古船》主要写的是胶东半岛洼狸镇隋、赵、李家族在四十年间社会历史事变中的浮沉纠葛,展开作家对当代历史、政治、文化心理、人性的反思。可见仅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上也不能把其归于“改革文学”范畴。笔者非常认同王庆生、洪子诚等把张炜归入“乡土”一说,尤其是《古船》发表后在文坛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学界也主要把它当作中国当代乡土题材中的“突破性”的小说来认识。且张炜也说:“写作《古船》是我心潮难平的日子,又是我呼吸深沉的日子,这样一部书需要这样的状态:沉浸、感动、冲决,却又需要尽可能地沉着,不要变得呼吸短促。”[2]因为张炜在创作中始终把“朴素、真实”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所必备的品质,而且认为“朴素”、“劳动”等概念在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炜或许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乡土小说家。
到了90年代,发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声音渐渐进入低潮,虽有“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身体写作”等文学思潮的呐喊,但很少有文学史家对张炜应该归属于何种文学思潮再发议论,此时文学史家与张炜的蜜月期搁浅了。但是,张炜依然沿着自己80年代以来的文学倾向:一是在现实层面上的思考与人文关怀,《柏慧》、《外省书》;二是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精神,在想象世界的精神飞腾,《九月寓言》。张炜为文学史贡献的《九月寓言》再次对乡土中国进行叙述。如果说80年代的《古船》是刻意烹制的一盏清茶,越品味道越淡;那90年代的《九月寓言》就是经过时间酝酿的一杯烈酒,越尝越醇香、浓厚。确实,“《九月寓言》显示出张炜思想一个较大的转变——对现代文明发展的批判态度。通过‘小村最后陷没,村民失去了最后家园的故事,作品清晰地传达出这样的思想: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但作品认同的价值选择却是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乡土文明。作品中的‘小村尽管也会滋生贫穷和罪恶,会上演政治和道德的悲剧、惨剧,但‘大地足以承载、吸纳和化解,将其转化为精神的欢悦与飞扬,它的总体形象是美好的,是代表着善和美的。所以,它的毁灭必然是一种悲剧,是恶对善的战胜。”[3]张炜不仅写了现实生活真实发生的事,还写了“想象中的生活”;不仅写了“小村”现实的苦难,也写了小村人精神的欢愉,可以说张炜以自己的极大热情为这个小乡村唱了一曲饱含深情的大地之歌。张炜似乎像一位“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语),他坚守着自己的田园,游弋于齐鲁大地的河流、大海、野地上,呈现出回顾、寻找的精神取向。
到了新世纪,张炜的《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以及他花费了22年书写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等,虽然触及到了都市,但作者对都市大都抱有反感的态度,并以对都市的逃离来对抗都市的丑恶。在这些小说中,“流浪汉”这一独特的形象是一个显著的存在。他们大都是一刻也忍受不了都市的污浊、丑恶、虚伪,犹如鲁迅小说《坟》中的“过客”一般,态度是如此决绝、如此执拗,一直在逃向远处,逃离这个污浊之地。如《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在都市每遇到一次心灵上的挫折,都会逃离到长满蜀葵的小乡村独自疗伤,那里的人们干净、纯洁、朴实、善良;那里的环境纯净、优美、安详。在作品的结尾,作者写了淳于阳立在遭受了经济上的破产、艺术上的枯竭、心灵上的极度创伤之后,独自一个人只带着自己年少时画的一幅“蜀葵”远行,去了一个谁人也不知道的地方。这难道不就是以“对都市的逃离——对乡村的皈依”来呈现作者一直追寻的乡土之路吗?正如张炜曾说的:“我觉得,四十多年了,自己一直在奔向自己的莽野。”[4]此外,在作者耗费了22年心血的长篇巨作《你在高原》中,作者更以极大的笔墨描写了“我”的逃离,“我”的奔走,“我”一直在寻找曾经生活过的平原。这种强烈的奔走欲望,犹如是命运的强力牵引,推着“我”一直在不停地出走,犹如是一种戒不掉的嗜好、毒瘾,总是在“我”的意识中悄然踏至,并不得不迈动着双脚行走于平原、行走于大地。或许“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生命的背景——人生既有一个舞台也就会有一个背景,于是他的一切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滋生和繁衍。”(《你在高原·西郊》p5)这种背景不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平原?“我”一直魂牵梦绕的小乡村?“我”生命质地中不可或缺的底色吗?于是,乡土在他独自沉思的世界里,变成了一个与乡村有所联系,而又完全不属于乡村的诗意化世界,他所向往的乡土世界有着梦幻般的纯朴与高尚、洁净和美丽,他过滤掉了那些丑陋与浅薄、自私与狭隘,保留下的是人性中最富有诗意的光辉。[5]
三
纵观张炜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张炜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方向,坚持着自己的最高文学理想。他一直从自己生长的土地中直接汲取灵感,始终站在拥有土地的劳动者一边,站在故土的亲人一边,站在弱者一边。”(张炜语)他犹如大地的精灵、故地的使者、弱者的武士,以自己的笔抒写着大地的困难、人们的喜怒悲哀及自己的心灵。确实,张炜的笔犹如他的一颗心,他以自己手中的笔为自己的心找寻一个可以停靠的方向。
参考文献:
[1][2]张炜.张炜与新时期文学.南方文坛[J]..2008.2,50.
[3]贺仲明.思想的作家与作家的思想——张炜[J].湖北大学学报.2015第5期,47.
[4][5]王尧.王光东与张炜对话录[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