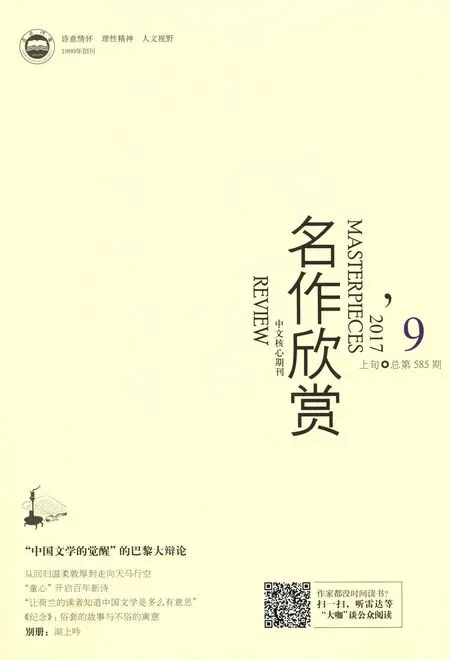“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六《尚书》:述三代以彰王道(下)
2016-07-29山西刘毓庆
山西|刘毓庆
《名作》视野 View
“五经”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六《尚书》:述三代以彰王道(下)
山西|刘毓庆
与《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主旨不同,《尚书》是“述三代以彰王道”之书。本文意在从《尚书》的性质、内容,它在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作用,它所提倡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等方面,探讨《尚书》这部上古典籍对于中国当代、未来的文化意义,以及它能给当代人带来怎样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力量。
《尚书》 王道 传统价值观 文化智慧 精神力量
(三)《尚书》展示了圣王的忧患意识
在《尚书》中,一代代的圣王明君,无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这样说,《尚书》尽管内容庞杂,但其主旨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警戒世人要常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敬天顺民,这种思想是一贯鲜明的。
这些上古的帝王们,他们都是为了天下百姓操劳,他们心里最大的忧虑就是如何能使百姓过上好的生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周书·康诰》),对待老百姓就好像保护小孩子一样,怕冷着又怕热着,怕饿着又怕渴着、撑着。用陈大猷的话说,就是“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则爱护无所不至,民必康且乂矣”(胡广:《书经大全》卷七引)。而且《尚书》中认为,上天是为百姓的利益才立君主的,能为百姓做主,上天就辅佐你;不能为百姓做主的时候,上天就不能辅佐你。所以君王要遵从上天的意旨,配合上天、帮助上天来安抚下民,这样才能保证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这种忧患意识,表现在君王的自我陈述中。《周书·君奭》中,周公对召公说:“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周公说,武王表明他的心意,文王的圣德,子孙们一定要继承光大,这将是无穷忧患的事业。《周书·君牙》中,周穆王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我心里忧虑畏惧,就像踩着老虎的尾巴,又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之上。周穆王认为,自己承继的祖业之大,自己才力不及,故心怀畏惧,诚惶诚恐,敬畏之心甚矣。
这种忧患意识,也表现在圣王对大臣的告诫中。《商书·盘庚》中记载商王盘庚在训示臣民时说,要“永敬大恤”,永远警惕大的忧患。也就是说,当国家遇到大的忧难之事时,上下要同心同德,这样才能御忧患、克艰难,而不能离心离德。盘庚还说:“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如果你们不怕将来或眼前会有大灾难,就像懒惰的农民一样自己寻求安逸、不努力耕作,就会没有黍稷收获。《周书·旅獒》中,武王灭了商朝,安定天下,开通了周边诸国与外族的通道。西方有个叫旅的国家,向朝廷进贡了獒犬。召公害怕武王玩物丧志,专门写作了《旅獒》,劝诫武王要继续修德慎行,重视贤能。召公说:“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被歌舞女色所役使,百事的处理就会适当。戏弄人就丧德,戏弄物就丧志。《周书·周官》中,周成王说:“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身居宠信之位,凡事都要有畏惧之心,不知畏惧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周王多次告诫将要派出的一方之长,要以“德”来治理一方。比如《康诰》中,成王告诉康叔:“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你要大显仁德,用来安你的心,呵护你的德,增长你的智慧,光大你的作为,人民安宁,你的瑕疵就消失了。而作为受武王亲托的为周成王辅政的周公,曾诚恳地对他的弟弟召公说:“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周书·君奭》)你知道民众的秉性,做事开始不难,难在善始善终。我们要慎重对待这个问题,从今以后,以恭敬的态度治理好国家。
《尚书》中,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仅存在于圣王的内心,同样也存在于辅佐圣王的重要大臣内心之中。《尚书》有多处记载大臣对圣王的提醒和告诫。《虞夏书·皋陶谟》中,皋陶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不要贪图安逸享受,诸侯处理政务要怀有戒慎恐惧的心态,警惕万事的兆头,因为事物天天变化万端。《商书·伊尹》中,伊尹劝说太甲:“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慎行你的节俭美德,考虑长久之计。《商书·说命》中,傅说进言商王武丁说:“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做任何一件事都应当有准备,有备才能无患。《商书·仲虺之诰》中,仲虺说:“慎厥终,惟其始……钦崇天道,永保天命。”慎终要像它的开始,才会有好的结果。敬重上天规律,才能长久保持天命。《周书·旅獒》中,召公劝谏武王说:“明王慎德……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圣明的君王都敬慎德行,从早到晚不能有不勤奋的时候。不慎重自己的微小细节,终究会损害大的德行。好比堆积九仞高的土山,只差一筐土,也不能说大功告成。
当然,圣王和这些重要大臣忧患意识真正的来源,大多还在前代社稷灭亡的历史教训。《尚书》中的君臣们不断反思那些帝王败亡的原因,从而更加警觉,不让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商书·伊尹》中,伊尹引用成汤的话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胆敢沉溺在宫室里歌舞、酗酒的,就是巫风;胆敢贪求财货和女色,沉溺于游乐田猎的,就是淫风;胆敢有侮慢圣人之言,拒绝忠直规劝,疏远年老有德之人,亲昵愚昧顽劣小人,就是乱风。这三种风俗十种过错,卿士大夫如果身上有一种,家室必然丧失;诸侯国君如果身上有一种,国家必然灭亡。这是商汤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夏桀就是因为犯了这些过失中的多种,所以导致国家的败亡。而到了周朝,周王及辅佐大臣们总结的又是夏桀和商纣的历史教训。在《周书·多士》中,周公借成王之口向商之旧民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失有辞……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阙失,罔顾于天显民祗。”夏桀不节制自己的放纵行为,于是上帝便降下威严的教令,劝诫夏桀。但他不听从上帝的教导,大肆放纵,并且说了许多侮慢上帝的罪辞。后来的商纣王也犯了与夏桀一样的毛病,根本不显扬上帝的旨意,更谈不上听从那些勤劳于殷国的先王的教导。大肆放纵淫乱,不把天命和民众的疾苦放在眼里,结果亡了国。《周书·多方》篇中也有类似的警告:“有夏诞阙逸,不肯戚心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阙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于民。”夏桀大肆地安逸享乐,不肯慰勉百姓,竟然大肆淫逸昏乱,一天也不能勤勉地按照上帝的教导办事。他败坏天命,不能体谅民众的灾难,上帝便大大降下惩罚,重乱夏国。这是因为夏桀习于为非作歹,又不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只知道残暴地搜刮民财,大肆荼毒民众。《无逸》中,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逸乐、荒废懈怠政事时说:“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即要成王不要像商纣王那样迷惑昏乱,酗酒作乐。
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社稷永存的理望追求,使他们把这种忧患的重心落在了“保民”上。只有“保民”,才能做“民主”,才能保王业永存。即《周书·梓材》所说的:“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保民”与“忧患意识”的结缘,培养了周代君子的“不朽”理想。只有居安思危,敬德保民,才能获得“不朽”。 关于周代君子的“不朽”理想,我们在有关周人的典籍与记述中,几乎随处可见,只是其表述方式不一而已。《周书》有“祈天永命”“至于万年”等,《诗经》有“永锡难老”“君子万年”等。特别是两周金文中,像“万寿无疆”“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子子孙孙永保四方”“永命令终”“眉寿永命”之类词语,更是习见。所谓“永命”“永保”“万年”“难老”等,无一不是对“不朽”的期冀。但这种不朽理想并不只是简单的心愿或祝福,而是与周人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以血缘为核心的氏族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其不朽的本质是氏族福禄的永恒延续,其不朽的保证是“德”的建树。《天保》第五章就明确地提出:“神之弔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这里呈现出了周人意识中的人神关系网,最上者是“神”,这是赐给人间幸福的主宰者;中间者是“尔”,即周王,也即诗人祝福的对象;在下者是“群黎百姓”,也即所谓的“民”。周王的德泽遍及群黎百姓,百姓为其所化,故而获得了神灵的赐福。“德”是建立神、民、王之间联系的枢纽。只有怀有此种忧患意识,才能去实践“敬德”“保民”,才有可能“受天永命”。因此“忧患意识”与“不朽理想”绾结在了一起,支配着他们的道德实践。
(四)《尚书》树立了天下观念与世界精神
细读《尚书》我们发现,活跃于其中的圣王,在他们的表述体系里,他们胸次所及的疆域范畴,常常不是一家一姓,而是“万邦”“四海”“万方”等宏大概念。
万邦。《尧典》中,尧以“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的个人修身为起点,最终落实到了“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是以天下所有小国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天下所有百姓的风俗教化为目标的。《皋陶谟》中,“烝民乃粒,万邦作乂”。正因为大禹治理了水患,才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商书·仲虺之诰》中有言:“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德行日日更新,万国就会归附;如果骄傲自满,亲戚也会疏离。
四海。《尧典》中,尧去世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尧心怀天下人民,天下人民也感激和怀念他。《禹贡》中有这样的句子:“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因为禹划分了九州,开辟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通道,帝王的志向,就不仅仅是接受四面八方的进贡,还希望教化遍施,将文明传播到四海。《大禹谟》中,禹和伯益评价尧的功绩,伯益说:“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正是因为帝尧德布广远,圣明神妙,英武华美,所以上天顾念,让他尽有四海,而做天下的君主。
万方。《汤诰》中,商汤“归自克夏,至于亳”后,“诞告万方”说:“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夏王灭弃道德、滥用威刑,向你们万方百姓施行虐政。你们万方百姓遭受他的残害,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他才起兵灭夏。然而对此,商汤一直惊恐畏惧,如落深渊,不知自己的行为是否得罪了天帝,所以他祈求:“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你们万方有过失,原因都在于我;我有过失,不会连及你们万方诸侯。
然而在这些“大词”背后,有一个问题也让我们疑惑,这一点在研究中也常常被忽略,即:三代更替在《尚书》里都有记载,当外来武装力量要颠覆自己国家政权的时候,自己的国民与外来势力合作推翻自己的君王,在《尚书》里,这种行为是被认可的,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种价值观呢?
我们从《尚书》及以《尚书》为中心的主流记载中可以看到。夏朝末年,夏桀无道,天下大乱,成汤领着军队惩治邪恶,铲除夏桀及其羽翼。这时各地的人民不是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是急着盼望成汤的军队先来解放自己。“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仲虺之诰》),成汤所到之国,百姓相庆贺。当时的夏民发出的两种最强音,一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要与自己的统治者夏桀同归于尽;二是“徯予后,后来其苏” (《仲虺之诰》),把成汤当作是自己的君主,认为只有成汤做君王,人民才能有活路。夏和商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起码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国家,夏朝的百姓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君王反而帮助外来武装?在商周易代之际,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武王的军队东征,所到之地,人民不抵抗,而是“篚厥玄黄”,用筐子装上礼品来迎接。当攻到商郊牧野时,商的军队不是誓死卫国,而是“前徒倒戈,攻于后”(《武成》),调转枪头与周人共同对付纣。据《史记·周本纪》说:“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为什么会这样呢?按说,周和商这两个民族,从血统上来说差距也比较大:他们的崇拜物都不一样,商朝人崇拜太阳,周朝人崇拜月亮;而且商周的语言体系也不完全一样,商的语言是现在汉书的祖语,故商的先公的名字,如昭明、相土等,都是可以用汉语解释的,而周先公之名有些很怪,如不窋、庆节、皇仆、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公叔祖类等,很难晓知它们本身的含义。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时的臣民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而是天下观念,他们是在“天下”这个大范围内思考问题的,所以这里频繁地提到“万邦”的概念和“天下”的概念。《礼记》里提到了“大同世界”的问题,这是一种世界观念、天下胸怀。《墨子》中还谴责没有道义的爱国行为,以为人各爱其国而不爱人之国,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举其国以伐人之国,这样天下就不会和平。这种思想显然是有传统的,它是从上古三代就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
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胸怀,比起外国人来还是很明显的。像我们今天倡导的爱国主义,是20世纪才培养起来的。20世纪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在重重灾难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观念。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西方人的爱国主义从根本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是以道义为原则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人们把道义看得比国家政权要重得多,这道义是天下的,不是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柳宗元说:“恃乎力而不务乎义,非中国之道也。”(《非国语》上)郝经说:“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所谓中国之道,就是天下大义之道,是《尚书》所建立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蒙古人、接受满族人的政权?和这种观念也是有关系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里,我不管你是谁,只要能推行道义我就认可你的政府,我认可的是道义而不看你是何血统、何来路。这是一种天下观念和世界精神的体现。当下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世界大事的关心,远过于西方普通民众对世界的关心;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过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几十年前,中国的一位学者到法国访问,连问几个法国的普通民众,他们都不知道中国有周恩来总理,而且这位学者提醒他们周恩来在法国留过学,是一个连任多届、深受民众爱戴的总理,法国人一点也不关心这些。相反,如果是类似的情况,中国人就会传为佳话的。这反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
《尚书》之王道与西方民主
明白了《尚书》的性质、内容及其文化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探讨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尚书》所代表的文化思想、价值体系与西方观念的冲突。更具体点说,是《尚书》所确立的王道政治观念与西方所说的“民主”观念的冲突及比较问题。我们从以下三方面来谈。
(一)“王道”的本质及对三种关系的处理
我们前边谈到《尚书》里确立了王道政治典范,并以“王道”为核心而形成了圣王系统。这个圣王系统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组成,其建立者是孔子。因此习惯称“王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周公没有称王,而曾摄行王事;孔子非政治上的王,而后人认其为“素王”。战国时代的孟子在周游列国时,言必称尧舜,其目的就是宣扬“王道”,施行王者之政,即“仁政”。汉朝之后,“王道”便成为一种高于皇权的意识形态,为全民族所接受。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中国古代是一个专制社会,从秦始皇以来一直就是专制政权,我们往往用“封建专制”来表述,其实这种表述不是完全合适的。第一它不是“封建”,既没有“封”,也没有“建”,何来“封建”?第二也不是“专制”,“专制”是一种制度,它既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也没有被社会所认可,如何称得上“专制”?当然关于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需要做必要的说明。在秦汉以降,皇帝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领袖,大多数情况下不具体操办政府事务,行政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宰相或贵族集团手里。皇帝的周围设有谏臣监督皇帝的行为。皇帝有最高发言权,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也是事实,但他并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如果感兴趣,我们不妨从汉朝到唐朝做个统计,看看有多少皇帝是被大臣换掉的。如果是“皇帝专制”的话,大权本来就在皇帝手里,大臣如何能换掉他?比如唐明皇,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皇帝,可是他连自己的一个爱妃都保护不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所以有些问题我们就得思考。除了秦皇、汉武、唐太宗等少数才能卓绝的君主外,大多数皇帝其实是受贵族集团或大臣制约的。在古代,皇权之上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道”,也就是“王道”,如果你这个“王”违背了这个“道”,大臣们就要用这个“道”去要求你。比如汉光武帝要出去旅游,他的大臣申屠刚就在车前挡住,说天下未平,你不能走。皇帝就有点恼火了,心想你管得倒宽!于是命令手下人不必管他,往前走!申屠刚马上跪倒在地,用头把车轮子顶住。意思是你想走,就从我身上压过去!皇帝没办法,只好返回去。再如,隋文帝鞭打一个侍卫官,有个叫刘行本的大臣上前去劝阻,文帝不听,仍继续打。刘行本于是过去挡在前头,拦住皇帝,接下来他就给皇帝讲了一通道理,说如果我说得对你就听我的,我说得不对,你把我送到司法官那里,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皇帝没办法,只好放弃了。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大胆与皇帝作对?就是因为他们倚仗着“道”。皇帝权力再大,也大不过“道”。你遵从这个“道”,就是有道明君,我就拥护你;一旦你违背了“道”,我就要用“道”来纠正你。如果你完全不顾“道”,那就是无道昏君,天下百姓都有权利把你推翻。再如唐朝的三省制度,中书省代表皇帝起草的文件,门下省就有权利驳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皇帝并不是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你必须服从“道”,“王道”高于皇权。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宋代以后,皇帝为了预防前代频繁出现的大臣废主、拥兵自重的历史重演,采取了削弱相权或取消宰相制的办法,分散大臣权力,加强防弊手段与独裁统治。故而宋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臣换皇帝的事件,这与皇帝独裁权力强化有关。
与“王道”相关的,有三重关系需要处理。第一是与民的关系,也即君民之间的关系。它要求“敬德保民,民为邦本”,把民放在首位。第二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事务处理上,它要求“协和万邦”,协调万邦的关系,使其和平共处。同时还要注意“兴灭国,继绝世”,有些国家灭亡了,要帮助它复兴起来,让它们延续血脉,不能就此去抢占他们的土地和人民。所以武王得天下以后,就把先王之后都封了疆土。据《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一直到春秋时候,这些先王的后代都还有,这就是“存亡继绝”。这是一种仁慈之怀,是“王道”主义的表现。第三是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要顺应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尧典》里说“钦若昊天”,就是这个意思。《甘誓》谴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武成》指斥纣“暴殄天物”,都是把违背天道、不能爱护自然认作了罪恶。《逸周书·文传解》讲“厚德广惠”,也是要“仁人爱物”,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西方民主与中国“王道”之比较
我们再来看西方所说的“民主”。“民主”是和“专制”相对举的概念,也就是说,“民主”是为反专制提出的。“五四”以来,倡导的就是“科学”与“民主”。把“民主”概念从西方引进来,并传播于广大民众之中,这是中国政治观念中的一次大变革,而且面对中国长期的独裁统治,“民主”传入犹如清风吹来,让人感到清新之极,因此很快便为全民族所接受。如今,从政府到民众,也都在高喊要推进民主进程,特别是民众,对此呼声更高。就当下的中国现状而言,倡导民主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民主”是一种“政治工具”,而不是“价值观”,我们在推行“民主”政治时,需要首先认识它的性能,分析它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应用它。
民主“反专制”无疑很正确,但是民主的立足点是利益,是当事者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每个人手里掌握着一票,要投这一票的话,首先要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根据自己利益所获得份额的多少,决定把票投向哪一边。因此民主的性质是保护集团成员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其所信奉的是“利益原则”,每个人以自己利益为原则,若将个体利益相加,便形成了“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就民主的积极意义而言,首先这是一种最有力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它能使得当政者无法为所欲为,也能使得大多数人有发表自己意见、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一制度面前权力是均等的,特权在民主的过程中没有市场。其次是保护集团成员的利益。一个群体,在利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形成一个代表大多数利益的意见,从而通过决策,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证。其三,民主是监督权力最有效的手段,它可以防止权力腐败,使集团保持活力。在当下中国的反腐败中,有许多贪官都是通过民众监督、新闻披露而落马的。其四,民主可以加强集团的竞争力。集团大多数人团结一心,向着一个方向发力,这力量是巨大的。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竞争的过程中,民主的程度就决定着集团的凝聚力与竞争力。在当下世界性的大竞争中,民主国家明显占有优势,恐怕就和这个原因有关。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民主的弊端。民主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是非观”和“道义观”,只讲利益,不顾是非,没有道义原则做制约。比如美国出兵打伊拉克,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行为,美国的一个高级军官就曾说:伊拉克简直就是在石油的海洋里,我们不打它没有办法。这样不道义的行为,竟然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支持,他们的国会也就能通过。为什么?利益!对美国有利,美国人就要干,他们也在算着成本账,怎样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认定利益之后,再找“道义”借口为其遮羞,然后实施侵略计划。美国当时找的借口是:伊拉克有核武器。伊拉克说没有,他说:你就是有。你再说没有,那我就说你是耍赖,我先消灭了你再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不要求其落实事实真相,而只是找开打的借口。因此事实到底如何,那就不重要了。所以把伊拉克打垮了,萨达姆被杀了,核武器没有找到,美国人也不脸红,更不会自咎,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希特勒是一个什么人,我们心里都应该明白,他给欧洲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德国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希特勒,为什么?它能给德国人带来利益。他们坚持的是“利益原则”而不是“道义原则”。
由此,我们看得很清楚,民主是不要道义、不讲是非,只讲利益的。但要知道,人类的行为如果失去了道义的控制,其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将千百倍于洪水猛兽。就以当下的世界来说,美国人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他们的价值观,把“民主”认作是普世价值,并且要伴随着武力来进行,结果把中东搞得乱七八糟,几十年来战火不断,制造了多少难民!又使多少无辜的平民死于战乱!再则,民主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的专制政权问题,使国家强大起来,但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纠纷,民主如何解决?而且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动战争的多半是民主国家,并不是所谓的“专制国家”。民主在利益驱动下的运动,那对世界和平将会带来多大威胁!所以对于民主,我们不能盲目崇拜。民主只有在道义的控制下运作,才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得到的是小利益,而带来的则是大灾难。同时,极端的民主主义取的是平均数,而不是高智商人的决策,民主决策,其所关注的只能是当下利益,不可能有前瞻性,也不可能有大胸怀、大智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设计。这“集中”,既可以避免民主决策的低效性,也可以保证道义的原则性,防止无道义原则的民主对人类善良性的伤害。
如果从“正名”的角度考虑,“民主”这个概念,顾名思义是“民众做主”,这未必是好的制度,也未必符合事实。在实际的操作中,“民主”更多的倾向是要人民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可以称作“民权”。廖仲恺《革命继续的工夫》一文说:“民权这两个字的解释,在政治上说,就是人民有参与立法、容喙政治的权;在法律上说,就是人民有不许别人侵犯他的身体、言论、信仰、住居、集会种种自由的权。”因此如果把“民主”置换为“民权”,可能更好一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没有“五四”最响亮的关键词——“民主”,而入选的是“民权”。他为什么不用“民主”而用“民权”?我没有研究过孙中山,但我相信他一定在选择过程中有过认真考虑的。“民主”不是非有不可的,但民众的权利则是一定要保证的。中国的“王道”政治排斥“民主”,但不排斥“民权”。如周代有专门的采诗之官,他们要把民间的声音采集回来,献给天子,其目的是让最高统治者通过歌声,“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据《毛诗序》说,在周时,天子与民众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民众可以对政治自由地发表言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是“王道”政治下的“民权”。这种制度应该是人类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比之西方所倡导的民主,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它既能使民众有自由,又能使人类获得持久和平。从汉唐到明清,大批的读书人研究经典,把目光放在修复三代制度上,原因正在于此。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古朴的文学》《朦胧的文学》《雅颂新考》《诗经图注》《从经学到文学》等专著二十余部。
编辑:张勇耀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