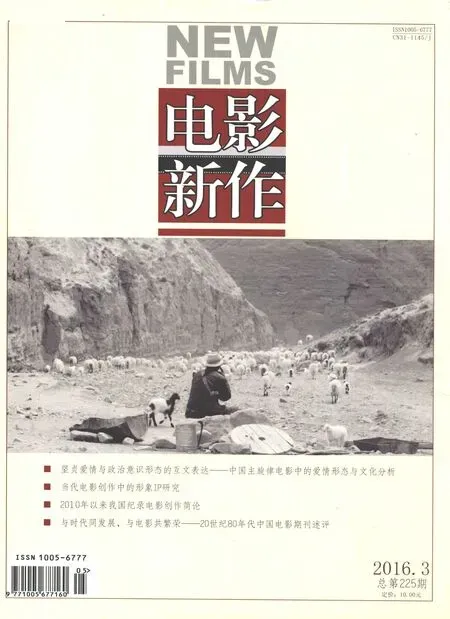断裂的民族性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访谈
2016-07-20朱鹏杰
朱鹏杰
断裂的民族性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访谈
朱鹏杰
访谈对象:万玛才旦(藏族导演,作家,《静静的嘛呢石》《塔洛》导演)
访 问 者:朱鹏杰
访谈时间:2015年4月30日下午
访谈地点:上影广场A座5楼
朱鹏杰(以下简称朱):你是怎么从作家成为导演的?文学创作对做导演有什么帮助?
万玛才旦(以下简称万):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和电影。小时候经常有放映队去放电影,主要是革命题材的,还有一些其他题材。我们的村庄在黄河边上,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施工队,他们会定期放电影,当时跟着看了一些国外的电影,像《狐狸的故事》《摩登时代》等,带给我一些不同的感受,我基本上就是看着大银幕上的这些电影长大的。初中的时候我到了县城里,周围也有很多放电影的地方。当时看电影就是大家共同的娱乐,在一个几百人的大厅,大家就买了瓜子带着进去看,边磕边看,整个放映厅都是嗑瓜子的声音,跟电影配在一起很热闹。我记得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看了两三百部电影,当然可能题材比较单一。
基本上看电影跟看文学作品是同步的,我看了很多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像《牧马人》等。还有,那时候也看了很多印度电影,因为印度在宗教信仰等方面跟藏区比较相近。那时候的印度电影跟现在的宝莱坞不太一样,虽然也是歌舞的形式,但也有很强的情节,比较经典的像《流浪者》。
高中的时候在州里读的,后来上大学,电影一直伴随着我。有时候我还去新华书店听电影的录音,或者放羊的时候带着录音机听广播剧,像我就是一直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然后就自己开始想象,去自己脑补那个画面,这对电影创作应该也有帮助,尤其培养对声音、空间的想象能力。
我学的是文学专业,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文学,还会看一些畅销书。其实我之前上的是一个中专,毕业后当了几年老师。那时候我们一般都不想上大学,因为中专出来后能分配工作。那时候我做小学老师,语文、数学、藏语什么都教。那时候不是很忙,有很多自己的时间,闲的时候就看看小说,看看电影,接触电影的渠道也比较多。
朱:你工作多久后去的大学?
万:应该是三四年吧。那期间我就在写一些东西,但没有投过稿。那时候觉得这样的生活太单调,就想改变一下,想着出去看看,而唯一的方式就是考大学,所以我去了西北民族大学上了藏语言文学专业。
后来比较偶然的机会,一次到北京实习的机会,接触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就写了一个申请,很快就通过了,当时有一个编导班,我就去读了两年。我在电影学院五年,先是两年的专升本,是文学系的。然后我又在2006年读了导演系的硕士。
朱:请你谈谈你从事文学创作对你从事电影创作的影响?
万:我觉得影响很大,包括对事情的认识,对叙事的帮助等。以前可能觉得文学跟故事片叙事差不多,但后来发现叙事的方法有很多不同,比如细节的描写,人物的创造。另外,文学创作对写剧本有很大帮助,有想法可以行诸于文字,不会说写不出来剧本。
朱:我发现你拍的几部电影,如《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等,基本都是围绕藏族生活、藏族人民展开,你的电影为什么以藏族题材为主?
万:一开始就是想的拍一个自己民族的电影,所以第一个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就是从一个30分钟的短片开始的。当时系里面觉得这可以做一个长片,于是我两年之后就开始长片的创作。因为对自己民族的题材很熟悉,所以就这样一直走下来。不是说刻意要去拍纯藏族题材的电影,像之前我拍过一个电视电影就不是藏语题材的,讲穿喇叭裤的80年代的故事,这部电影是《喇叭裤飘荡在1983》。
朱:据悉《塔洛》这部电影只拍了25天,这么短的时间拍摄这样一部剧情长片,你作为导演是怎么把控整个流程的?
万:这部电影实际拍摄虽然只有20来天,但是前期沟通、筹备花费了大量时间,在立项之后,剧本修改了好几次,从3月底建组,就开始搭景,就在我家乡附近。因为投资比较少,我们就希望景比较集中,像电影里的理发馆、派出所都是搭出来的景。
朱:看你《静静的嘛呢石》里,很多演员的表演都比较接地气,自自然然,身上拥有充沛的在地元气,这些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吗?此外,我还看到老喇嘛在做事情的时候嘴里也在念经,他们在现实中也这样吗?
万:对的。大部分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但是像里面的老喇嘛、演藏戏的演员等,他们虽然是演员,不过演的角色与平时的身份很接近,演的角色就跟自己生活中的样子差不多。至于做事情的时候嘴里念经,是僧人就会那样,此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也会这样。跟他们平时的转经筒一样,经筒里放着经文,他们就会一直转,他们会记这个数字,转多少遍代表了什么。所以电影表演的这些东西一直以来就在藏民的生活之中,我只不过是把这些表现出来而已。
朱:我发现在《寻找智美更登》里,里面有一个背对着屏幕的老人,在说话的时候像背书一样,很不自然,他是你剧本设定的角色吗?

图1.《寻找智美更登》剧照
万:这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人,本来剧本中没有写。那时候有几个同学来看我,他们就说到有一个活生生的智美更登,电影里他的故事有百分之九十是真的。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虽然这种精神存在,但这真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确实没有想到。当然他的故事也是有变化的,智美更登是没有任何条件地把妻子、孩子送出去,而这个老人是跟妻子商量过的。他说,是因为想到那个人是个残疾人,很难找到老婆,于是商量后把妻子送给了他。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也是不相信,后来去找到了他,跟他聊,他跟我们仔细讲这件事情。我们拍的时候背对着他,不拍他的脸。我们给他找了些道具,让他堆木柴,因为不是职业演员,一个人站着的话就很尴尬,有了事反而比较好,在构图上也比较好看。那些棍子我们都削得很尖,对着他,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定的含义。他的台词也是我们根据他聊的记录下来,经常一点点加工,让他背了之后念出来的。
朱:我发现《寻找智美更登》里全景镜头、长镜头和对白很多,不管是在汽车里的对话,还是在看藏戏演员表演的时候,都会用到大量长镜头,你是有什么考虑?
万: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场景。我认为在一个大的环境下,一个人的状态比他的表情更重要,他跟周围环境的关系,那个气氛要表现出来。对话也是,比如老板讲初恋的故事。当时也有人建议拍出来,用闪回,但我还是选择用讲述的方式。因为讲述的感觉是很好的,比拍出来的感觉更好。很多年再回想起初恋的痛苦,老板在这个时候再讲出来,他不是平静的,反而有一点愉快,仿佛在讲述一件很愉快的往事,这种感觉是很好的。这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佛教里的放下执著。里面的那个女孩很执著,一直跟着他们,但是听了老板的故事,以及智美更登的故事,她最后也放弃、解脱了。
朱:电影里那个导演接了几个电话,他是不是也有故事?
万:他肯定也陷入了一个困境,但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笑)。他也从老板和女孩的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虽然他一开始就特别能认定智美更登的形象,他的目标很明确,智美更登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爱情。但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藏戏的状况,接触到的别人的爱情,还有歌舞厅里别人的质疑……所以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反思,他到最后也对智美更登失去了把握的能力。
朱:《寻找智美更登》里有一个人扮演卓别林,这个人是不是你刻意安排的角色?
万:那个人是我上大学时的一个同学。当时他在学校里会表演一些节目,他有一套自己的演法。卓别林这样的人物在藏区不太常看到,这个人就比较能演一些现代的角色,而藏戏反而不太会了。所以我就把他安排进去,给整部戏提供一种张力。
朱:《塔洛》中大量篇幅刻画一个人在孤独的环境中的行为,有点类似于现代主义想表达的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安排这样的情节你是如何考虑的?
万:一切都是为了电影表现需要。我们是选择春天拍的,那时候没长草,经常刮风,环境的那种状态就特别接近塔洛的状态。我觉得一个人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才会发生电影里的事情,所以我放大了这个孤独的环境。这个电影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小说中这样的情节不是很多,但是电影里我觉得很必要,缺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人物就不成立。因此在情节上有一些特定的设计,在写剧本的时候本来有一个情节是他遇到了一个牧羊女,后来删掉了,改成了收音机,通过收音机学会了情歌,也印证了他的记忆很好。还有狼袭击羊群,羊的主人来羞辱他,包括他的发呆等情节,都是最后促成他卖羊的铺垫。
朱: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了他熬过一个个的夜晚,仅仅是因为爱情吗?
万:我觉得不仅仅是。爱情、纠结是有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信条,他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些东西深深影响了他,作为他人生的准则。所以他就一直拿张思德做他人生的导师。所以在他最后卖了羊之后,他说这下他不能像张思德一样死后重于泰山了,他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有藏传佛教对他的影响。虽然里面表现得不如其他电影那么多,因为这里面展现的是个人。但是电影中也有表现他早上做一些仪式、敬天地等,但是没有刻意去放大。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支撑着他,不然的话可能他第二天就把羊卖掉了。
朱:《塔洛》想传递什么样的主题?是社会变革对于传统的影响?还是探究一个人在绝对孤独状态时的内心世界?

图2.《塔洛》剧照
万:其实我不太喜欢总结主题,我觉得每一位观众看到的都不一样。不过,在这部电影里,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个身份探讨的问题。这个人物的设置就有一个身份的问题。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是漠视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岁,对身份是一个很暧昧的态度。他在电影里不是说,我自己知道我是谁不就好了吗?他到了县城就遇到了这些问题。但在一个官方认证的过程中,小辫子被剪掉了,反而变得不像他了。剪掉小辫子反而不是一种新生,而是失去了从前的身份。以前别人都叫他“小辫子”,这就是他身份的称呼。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想到这样一个人物,一个“小辫子”,后来才慢慢地去建构故事。他的身份在最后被女孩剪掉了,他想走向新生,那个女孩在那一刻也是想走向新生的。虽然刚开始女孩是在设计他的,他上了圈套。女孩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想到一个男人会为了爱情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她把钱放起来的时候,通过她的表情、动作也可以看出她有了触动。但是后来,她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朱:你的电影是有意识地去表现藏区的变化吗?是不是对你的小说的一种主题的延续?
万:我主要拍一些现实题材的电影。我的小说与电影的题材选择、表达方式其实差别挺大的。另一方面,其实藏区的现实就是这样,从《静静的嘛呢石》里面你们也能看到,变化越来越大,这不是我刻意呈现的,不是刻意要呈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而只是去呈现生活,所以电影里都没有我太多的立场。这可能就是以前的涉藏题材的电影里比较少见的。
朱:你觉得非藏族导演拍摄藏族题材电影如何?是否藏族导演才能更好地去拍摄涉藏题材?
万:其实这也是我想要去拍藏族题材电影的原因。像以前的一些其他民族的导演拍摄的藏族题材的电影,他虽然说的是藏族题材,但其实是一种汉族思维,其实就是穿着藏服的汉人在表演、说汉语,用汉族的思维做事,包括一些基本的细节、穿戴的讲究等也是有一些错误。
朱:你将来拍摄电影,从题材到结构及情节会向商业电影靠拢吗?
万:靠拢倒是不会,但是应该会尝试其他类型,主要是看题材。之前我拍的《五彩神箭》,其实是政府的一个项目,那个就是比较折中,有一些商业的元素在里面。
朱:你拍电影的初衷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诉求?
万:我觉得出发点重要的是个人的表达,是建立在这个民族、这个地域上的。你肯定是先有一个想法、故事,是与这片土地有关联的,因为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很熟悉。我并不是为了表现地域的特色,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应该拍纪录片、专题片。所以我觉得出发点还是看创作者的需求,这一点跟写小说是一样的,你有了一个想法,一个灵感,你是有冲动才去写的,而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诉求的话,肯定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看到,虽然是一个比较区域性的故事。比如《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如果只是针对藏族观众的话,智美更登的故事就不必那么细致地去介绍,因为藏族人都知道这个人物代表的是什么,情节是什么。但藏族以外的观众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你得把智美更登基本的情节、框架讲出来,通过分散到不同的情节点里。所以看了这两部电影以后,很多人知道了《智美更登》,还想去看原剧,这也就是我最基本的诉求。
朱:你的片子上院线会分区域考虑吗?
万:像《塔洛》的话我们是准备上院线,但可能藏区看到的人反而会更少。因为那边的影院比较少,他们可能就看盗版,在农村、牧区的人看到的机会就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藏区的人看到的很少,当然他们的意见也会更多。
还有他们的一个观影习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是看录像片成长起来的。所以在藏区普通的观众可能也不是很能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电影观念的普及,就像《静静的嘛呢石》里他们也是去录像厅看电影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类型时,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可能只有慢慢等电影文化的普及,需要时间。
现在电影票房越来越好,类型越来越多,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很大,像这次在北京电影节,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票很快就被卖光了,所以这样的电影还是有自己的市场的。
文字整理:陈昶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