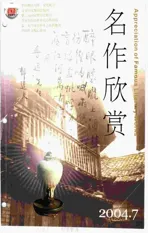还吾《论语》
2016-07-14上海沈善增
上海 沈善增
还吾《论语》
上海沈善增
摘 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老子、庄子以及孔子的思想精义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国学热”成为时下人们所关注的话题。本文通过深入浅出的说理,与读者探讨国学经典被误读的现状、“国学”在现实生活中带给人的启迪以及作者在编写国学经典中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国学热” 先秦经典 孔子 老子 庄子
与我十年前动笔撰写《还吾庄子》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国学应该说已经很热了。尽管学术界对“国学”这一名称是否合法尚有争论,对青少年要不要读经(指的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争论更为厉害,但大众对国学表现出的空前的热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希望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吮吸乳汁,来滋养今天美好的和谐社会。因此说,“国学热”作为“中华文明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应运而生,应日益昌盛的国运而生,应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时代需要而生,也是应世界新一轮游牧文化向农耕文明同化的历史趋势而生(今天的游牧文化就是工业游牧文化,我将在以后论述这一点)。
促使“国学热”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易中天、于丹、纪连海固然功不可没,倡导新道学的胡孚琛、提倡儿童读经的蒋庆、呼唤当代新道家的董光璧,还有余秋雨、金文明,以及郝明鉴与他主编的《咬文嚼字》等,也都有很大的功劳。即使是从根本上反对有“国学”这一说的,如舒芜,也因为他的反对意见,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鉴别走向了进一步深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热”其实也不是一日之功。就像烧水,沸腾前的加热,都是为沸腾这一刻做准备的。能看到的是沸腾时的泡沫翻腾,其实没有沸腾的水也聚集了足够的热量,沸腾只不过是把热量变成可以看见的现象。但我现在关心的,不是在“国学热”的形成过程中谁的功劳更大,谁的见解更高明,我关心的是“国学热”不是热闹一阵,如风吹过,而是将热能转化为持续的推动力。就像蒸一碗鱼,锅里盛了半锅水,蒸夹上放了一碗鱼,盖上锅盖,加热烧水,水沸腾了,冒白汽了,立刻揭开锅盖,熄了火,鱼有没有蒸熟呢?蒸鱼需要水先沸腾,这不错,但水沸腾了是不是能说明鱼已经蒸熟了呢?我看未必。但中国的事情往往热过了,事情就算成了。一些小事无所谓,就我的记忆而言,光健身方面,就有甩手热、喝红茶菌热、打鸡血针热、喝凉开水热、太极拳热、气功热、练功十八法热、木兰拳热等;但如果“国学热”也是昙花一现就成明日黄花,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且不说国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而且也是人类待开发的巨大的精神宝藏;就说今天这“国学热”实在是来之不易。就在十年前我动笔撰写《还吾庄子》时,老子、孔子、庄子(以出生年岁为序),还是戴着各种帽子,至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的老古董。所以,对我来说,要还《庄子》的本来面目,因为“一千七百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一个被注出来的伪庄子”,遭遇最多的问题,除了“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有什么意义”的质疑,我当时就回答,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很有意义”。说“没有意义”,是没有我认为的什么实用意义,或者说,我怕过分地强调《老子》《论语》《庄子》的实用意义。《老子》《论语》《庄子》我认为对做生意、炒股票、处理官场和职场关系等,就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现在有很多讲老子、孔子、庄子思想的实用意义的书、讲座,说得都不错,但其实去掉其中引用的老子、孔子、庄子的语录(往往还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错误引用),所讲的道理在其他的书里也可以看到,老孔庄的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包装。中国人因为历史悠久,也因为是农耕民族,历来尊重传统,所以写书的、讲演的引经据典,人们往往就对其肃然起敬,觉得他的话便很有道理、很有文化,但从接受学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可取的。
对此,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有过深刻教训的。“文革”前夕,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出现了庸俗化倾向,当时就编了一本书,叫《学习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里面都是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辩证法,解决工作、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例子。不是说这些例子不对,也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以为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可能出大问题了。当时党内有理论家注意到了这个苗头,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倾向,在“文革”中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都遭到批斗。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学习、普及时的庸俗化倾向特别敏感。老孔庄的伟大,绝不在于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观点、结论,甚至某一句话,像数学公式、物理定理一样,可以现成拿来一套就解决实际问题。说“很有意义”,就是老孔庄的思想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老孔庄思想就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学习老孔庄思想,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素质。
举个例子来说,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打倒孔家店”以来,就一直是孔子桎梏人心的一条罪证。其实,这段话是对士大夫说的,礼是对士大夫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所以,孔子又说:“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也一直是作为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罪证,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对不是士大夫的普通人,不要有那么多礼义的要求,但你要做官,掌握一定的权力,就一定要严格约束自己。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就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普通老百姓就不用,当然,你如果以党政领导干部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是好的,但你不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党政领导干部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譬如,我们小百姓帮人办事,事情办成了,别人送点礼,给点钱,你接受了,没什么;领导干部给人办事,办成了,别人酬谢他,他接受了,就不可以,甚至是刑事犯法行为。我看到过一则材料,有个管基建的乡干部,项目做成了,验收也通过了,承包商送他线,他开始不拿,但后来知道承包商在这个项目里要赚得多得多,给他的只是个零头。他为搞项目没少吃苦,但只拿些清汤寡水的工资,他心里不平衡了。他想,我不拿,这钱还是落进承包商的腰包里,我拿了,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穷人。所以,他后来就拿了,也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资助,但终究东窗事发,因受贿罪而锒铛入狱。他觉得有些冤,从他的角度来说,好像振振有词,但他为什么拿出一部分赃款来做慈善捐助呢?说明他心里知道这是“非礼”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摆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士行规矩的约束,使他犯了罪,但孔子建立起来的这套士行规矩终究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也为他犯罪以后迷途知返而不是破罐子破摔提供了条件。
再说个正面的例子。我有个当年农场的同事,现在是上海某局的党委书记,名字我就不说了,就称他K吧。六七年前,他在当上海某县县委副书记时,我的另一个在外贸公司做总经理的农场同事W去他家里看他,回来对我用非常惊讶的语言描述他的清廉。说他住三间平房,还是水泥地,湖绿色涂料刷的;家具很简单,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他结婚时凭票买的。两个儿子读大学,他给的生活费很抠。W说,他带去一点礼物,两件衬衫,K的老婆还不肯收,W要K说一句,我们是什么关系,我的礼物可不可以收,这样才把礼物收下了。后来K调到上海某局来了,我去看他,说起这事,他说,我们做干部的,凭良心说,生活总比一般老百姓要好多了,还要贪什么呢?孩子还是从小让他们过得苦一点好,他们比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多了,我对他们要求严格,他们现在都很争气。
这就是孔子提倡的“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精神。我们今天尤其需要继承、发扬我们民族古代圣贤的这种精神。
我看到有反对研究国学、反对青少年读中国古代优秀经典的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你们把老孔庄的思想说得那么好,为什么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苦难深重,到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天,中国要富强,中华民族要复兴,靠老孔庄的思想行吗?这样的质疑,到今天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我就不展开辨析了,只说一点:根据我对老孔庄本意的考证、认识,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时期,都是老孔庄思想比较得到统治者认可并能实行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都是老孔庄思想受到遮蔽、歪曲的时期。
但十年前我写《还吾庄子》的时候,对老孔庄思想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定位、这样的质疑,好像是占据了主流话语,理直气壮。所以,除了得到极少数搞古典文学研究的老先生的鼓励,如当过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认为我写出一本《还吾庄子》,比写十本长篇小说还要有价值(当然这也说明我的小说写得比较差);其他人都认为我这样不务正业,放着赚钱的小说与更赚钱的电视剧本不写,去写可能出版不了,也可能出版了还要赔钱的《还吾庄子》,是脑筋搭错、走火入魔了。但今天看来,我当年好像是有先见之明了。就为了使自己能保持一份先见之明的好感觉,我也希望“国学热”能是一种真正的热,是能把鱼蒸熟的热,不要被反对国学的,认为中国不能有国学、不该有国学、不配有国学的人不幸而言中。
但就我看来,“国学热”被不幸而言中、方兴即艾的概率很大。为什么?因为用来加热的柴不行,都是些湿柴。湿柴生火,你不想让火熄,火也很容易熄。我说的湿柴,指的是从古到今,一两千年来《老子》《论语》《庄子》等或权威或流行的注释本。这些注释本的错误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还吾庄子》只还了《逍遥游》《齐物论》两篇(今本《庄子》共有三十三篇),以前注译,《逍遥游》平均两句中一句以上存在问题,《齐物论》平均三句中将近两句含有错误;《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有错,而且整篇结构几千年来都被人误读了。今天有好多人出来批评于丹、易中天,说他们哪儿说错了,哪儿是戏说,什么说法庸俗化了,甚至说“戏说文化是犯罪”。其实,他们明言他们说的是读后感,于丹说明是“心得”,易中天的“品”,品赏回味,也就是读后感。读后感是完全可以自己怎么感就怎么说的,只要他说出来有人听,写成书有人买,“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读后感来说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靠些读后感,哪怕是很精彩的读后感,恐怕是建立不起来的。于丹读《论语》心得,在我看来就有很多错的地方,而错误中很多是因为采用了错误的注释造成的。当然,于丹并没有表示她从此要成为一名国学研究者,她只是一名国学票友,为普及、推广、弘扬国学摇旗呐喊。这也很好。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国学票友。问题是研究国学的专家,如果也是在错误的注释本的基础上提倡读经、捍卫经典、发表见解、构建体系,那么,就像在沙滩上造房子,要房子不倒也不容易。现在有人从今天的“国学热”,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曙光,这希望正是我所希望的,但就今天“国学热”的现状来看,从国学专业人士的素养准备来看,说这句话还早了点。新儒家如果从康有为算起(这个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一出手就写《新学伪经考》,为变法制造基础理论,有人认为是新儒家的发端),有一百多年了,新道家从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算起,也有年头了,但都还很难说已成气候,因为他们都难以回答一个问题:说“新”,到底“新”在哪里?不能说后来发生的一定就是“新”的,也不能说引进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概念对儒家、道家思想进行解释就是“新”的。然而,我认为新儒家、新道家、新道学,乃至新经学都是应该能成立的,而且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因为对《老子》《论语》《庄子》等原典的注释变化了。如果新的注释能够确立,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儒家,是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异化,道家是对老庄思想的曲解、异化,那么,还孔子思想本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就一定是新儒家;还老庄思想本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家就一定是新道家;还《老子》《论语》《庄子》等经典本意的学术一定是新经学。所以这希望、这曙光不是能等来的,而是要我们去争取的,也是可以去争取的。
然而,从十年前开始的先秦经典“还真”工程,虽然《还吾庄子》的第一卷与《还吾老子》已经出版,得到的学术界和读者的反应、鼓励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但我却感到越来越难。按说通过十年寒窗的苦读,对先秦的语境熟悉多了,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找到相关的印证材料,应该有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之感,确实在具体问题上,我也常常感到了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的愉悦,但在整体上,我是真正体会到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正如俗话所说:初学三年,天下可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虽不至于寸步难行,但可以说有点步履维艰,因为我越读越感到老孔庄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纯粹高远。他们是深入浅出地言说,而我们对浅说的把握,既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可能认指为月,使人执着于字面义,而不能由此进入思想的奥义。所以,指出前人的注译错误,在今天的我看来还是容易的;而要使我提出的新注译做到“信、达、雅”,既在语意层面上可靠,又能引导读者去体会揣摩语辞背后的不尽之意,则是非常困难的。
就以我三年前开始着手做的《还吾论语》的工作来说,之所以到现在还迟迟不能动笔,就因为我越读越觉得有更多的书需要精读,有许多课必须得补上,而且不是一般的补课,是要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琢磨,我这才知道工程的浩大,取巧不得,我原来靠“好读书不求甚解”积累的一点文史哲知识根本不管用,而现在的阅读速度、记忆力、持续工作的精力、思维的敏感与活跃度,都大不如前了。
工程浩大,是由《论语》这本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到宋代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定“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名目,《论语》的地位才逐渐超过《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成为儒家第一经典;而在孔门弟子编订《论语》的当初,本来是作为读经的辅导教材的,所以《论语》又有“传”的别名。“传”的地位超过“经”,朱熹固然功不可没,但如若没有文化心理的深层原因,就是皇帝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论语》地位的超越上升,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中华民族的教育观有关。至少从西周立国、周公治礼以后,教育就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官办学校教育的对象是贵族子弟,以培养合格的贵族、政权接班人为目标,贯彻的是精英教育的理念。精英教育,以品德素质教育为主,以知识技能教育为辅。孔子办私学,虽然受教育者的范围扩大了,普通士人、农、工、商民的子弟都可以来学,但精英教育的理念,孔子还是全盘接受,他是要使民众获得精英教育的权益。孔子把品德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为“君子儒”,只求知识技能的就是“小人儒”。要有效地进行品德素质教育,就要采用与知识技能教育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教育学生,是有教材的,“六经”(前述“五经”加上《乐经》)就是教材,和官办学校采用的教材大同小异。但学到“六经”所载内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够举一反三,运用于实践。毛泽东同志总结学习是要学立场、观点、方法,其理念,可以追溯到老孔庄。在立场、观点、方法中,老孔庄认为方法是最重要的。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就可以超越“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立场局限,也可以不受经验、重言(权威之言)等具体观点的束缚。但方法的教学比具体的知识技能的教学要难得多,因此,孔子采用的方法,是学生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学生听老师阐发教材的观点,听老师运用一些观点、原则分析现实问题,学生提出疑问,老师来回答,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一些问题。正因为这些内容是教材上没有,而对造就君子儒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尽管孔子在世“述而不作”,但一去世,他的弟子门人就替他“作”了。与《论语》相似的还有《礼记》与《易大传》,都是弟子根据记录或回忆整理的孔子教育的精髓所在,说“精髓”,是可以从中体会到孔子所持的立场(基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民本立场)与思想方法。而《礼记》讲礼,《易大传》谈易,比较专门,《论语》是综合性的,所以它更利于普及推广。
在《还吾庄子·齐物论·题解》中,我对“论”“议”字做了一番考证,简而言之,“论”与“议”,是依止于“伦”与“义”而来的。“论”是“伦”之言,“议”是“义”之言,“伦”和“义”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客观规律的两个方面的认识。“伦”反映了规律的先验性、第一性、永恒性与不可抗拒性;“义”反映了规律的逻辑性、可利用性、具体可变性与有效性。“论”说的是“伦”,所以它只是描述与评价,即指出意义,不对言说对象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因为先验性、第一性、永恒性是无法通过逻辑来论证的,对它只能作为公理全盘接受下来。故而,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孔子及其弟子门人的言谈辑录称为“论语”。而“议”说的是“义”,就一定要进行逻辑思辨,探讨义理必须遵守逻辑规则,且“议”的指向也很明确,要做出决定,付诸行动,以求获利。至于“语”,当时是指因问而答,含有教导的意思。其时把这本孔子等人的言行结集定名为“论语”,是指里面所记都是一些结论性的教导性的话。
《论语》地位的提高,表明了在皇权专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以“代圣人立言”的方式,来阐发他们的独立思考成果的自觉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也是老孔庄重在思想方法的教育理念的自然延伸,本无可厚非。观点的具体语境的缺失,正为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以子学(包括《论语》注释在内的“论语”学其实是儒学中的子学)是中国学术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负面影响的第一点是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阐释、发挥混同乃至取代了对原著本意的严谨的求索。因为经典的结论、观点不容讨论,所以就各取所需,任意解释,为我所用,致使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严密、考证周密、方法科学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难成气候。
其二,造成了孔子只有一些睿智的哲思,而没有博大完满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假象。据我迄今为止的研究心得,孔子是有哲学思想体系的,其哲学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春秋》《易大传》《礼记》中,所以,要对《论语》中的语录正确解读,必须精读《春秋》《周易》《易大传》与《礼记》。尤其是《周易》,可以说是中国最深奥、最神秘、最难解的一本书,我本来是想绕过去的,现在看来绕不过去,非但绕不过去,不能绕过去,还可能要写一本叫“周易摸象”的专著。就是写不成“周易摸象”,以准备写研究专著的态度去啃《周易》,才可能对《周易》与《易大传》中体现出来的孔子哲学思想有比较深入、正确的认识。但这样一来,完成《还吾论语》的时间就要大大推迟了。
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有关方面提供机会,要我把酝酿中的《还吾论语》里选出几条大家比较熟悉的,而我认为本意受到严重歪曲的“子曰”(孔子语录)来说一说,我欣然答应。如果大家听了我的解释以后,能够感受到,哦,假若孔子这句话的本意真是这样的,那孔子的思想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接受的更要高明得多,或者我们过去对孔子的不好的印象,完全是因为误解;从而感到中华文明其实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先进、要辉煌、要博大精深,身为中国人,其实有继承这份精神遗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如果把你对孔子思想的新感受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的孩子,让他们对我们中华民族圣贤的思想产生兴趣、产生好感,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根据我撰写《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的经验,在写作过程中,直到出书以后,还会发现前人注释的错误被漏检了,所以,现在所说的,在《还吾论语》中可能会有所修改。欢迎大家对我的解释提出批评,以帮助我更好地弄清孔子的原意。
作 者: 沈善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正常人》、中短篇小说集《心理门诊与魔鬼》、长篇文学随笔《上海人》、随笔集《不惑是一种境界》、学术著作《还吾庄子》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