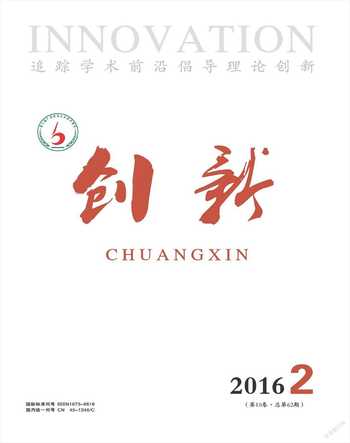存在主义视阈下的《祖乐阿拉达尔罕》研究
2016-07-13哈布日图娅
哈布日图娅
[摘 要] 蒙古史诗作为人类幼年时期的文化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逻辑和思想状况,向我们展示出那个时期人与自然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存在主义作为对于技术化的反思,致力于澄明出一个最本真的存在。蒙古史诗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正是在存在主义意义上的。通过用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对蒙古英雄史诗《祖乐阿拉达尔罕》进行剖析和解读,能够为我们展开一个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世界,从而启示我们换一种角度和立场来看待世界,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存在主义; 蒙古史诗; 英雄; 象征; 存在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6)02-0021-06
一般来说,史诗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形式,其内容的表现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反映了史诗创作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而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对于文学创作背后所深藏着的人们的心理逻辑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心理逻辑与思想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结构与内容之间的张力关系可以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整体把握。蒙古史诗作为世界史诗中璀璨夺目的一个分支,不仅有着生动优美的故事描写,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存在主义力求去揭示被存在者所掩盖了的真实的存在,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恰恰是历史上对存在者的追寻遮蔽了存在本身,使得存在沦为一种无根的存在。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来已经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之中。” [1 ]6只有通过“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发问,才能够使得存在澄明起来。而萨特更是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来彰显出人的自由性,以其为代表人物的存在主义文学派别也强调人在于极端或者荒谬境遇之中的自由选择。从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原始的史诗和神话有着大量的契合之处,比如萨特的戏剧《苍蝇》就取材于古希腊悲剧《报仇神》。而在思想上,存在主义也可以看作是向古希腊哲学某种形式的复归。因此,我们就有理由用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对蒙古史诗进行诠释,因为蒙古史诗同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一样,都反映了一个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原初生活状态,由此我们也能够窥探作为人类幼年时期的古代人民的心理逻辑。具体到蒙古英雄史诗《祖乐阿拉达尔罕》(以下简称《祖乐》),其包含的存在主义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蒙古史诗的开篇一般是对自然环境的描述,这种背景鋪垫首先就将读者置于一种生成性的世界架构之中,这个存在主义视角下广阔的背景之中蕴含着无尽的意义,在如此烘托之下,英雄人物的出场具有了稳定的根基。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让显现和显示敞开的敞开性”,即“林中空地”。存在主义认为只有敞开的发生过程才能够使得存在者获得“允诺”,所有的存在者都是在展开的过程中来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比如《祖乐》的开篇描写:“在久远久远的过去,世上的人们尚未在这里栖息,浩瀚的乳海只是一片泥泞的湖沼,高峻的须弥山只是一座矮小的山丘,古枫老檀刚长出幼嫩的树苗,遍野是雪白的绵羊,满坡是珊瑚色的牛群,高山上,一片片灰色的山羊,草场中一群群枣红色的马儿,水草丰美的杭盖满是黑枣骝马群,高峻的阿尔泰山上到处是花色的马群,莎棘丛中布满一峰峰棕黄色的骆驼。阿拉达尔罕……” [2 ]作为“存在者”具象性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场,正是由于草原、山脉这些显现之所的“允诺”。山岳河流这些背景性的存在随着英雄的现身逐渐清晰明朗起来,在场的与未在场的、现身与未现身的、规定与未规定的是相互勾连的关系,只有通过“此在”的存在,存在自身或者说整个世界才能获得了理解和澄明,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海德格尔是这样描述的:“仅当被展现性存在,亦即仅当真理存在,存在才被给出。仅当那开启着、展现着的存在者实存(以致这一展示自身属于该存在者之存在方式),真理才存在。我们自身便是这样的存在者,此在自身便生存于真理之中。一个被开启的世界在本质上属于此在,因而此在自身的被开启性同样也属于此在。” [3 ]这一点在蒙古史诗的开篇就以恢宏壮阔的背景描写向我们展示出来了,即草原、山岳和河流是孕育着英雄这个存在者的隐秘的真实存在,而随着作为“此在”的英雄出场,背景性的存在也开始被揭晓并出现在人们眼前,从而构成了一个因缘整体性。
海德格尔在后期著作《筑·思·居》中指出,只有在天地人神的相互映射下,才能形成一个本真的和谐世界,“在大地上”也就是“在天空下”,这两者共同指向的是“在神面前持留”,包含“进入人的并存的归属”。在这个四重结构中大地“承受筑巢、滋养果实、蕴藏着水流和岩石,庇护着植物和动物,是永远自行闭锁者和庇护者的无所促迫的涌现。” [4 ]1192在蒙古史诗中,大地同样也是英雄所栖居的地方,自行封闭的大地孕育滋养了英雄。但是英雄只有离开家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时,他的内在本质才慢慢显现出来。而天空正是英雄获得自身展现的澄明场域,海德格尔将天空描述为“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季节轮换,天是昼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白云的飘忽和苍穹的湛蓝深远。” [4 ]1193英雄消灭了蟒古思,也就是将对立面纳入自身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而当英雄重返家园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内在丰富性的现实存在了。如果说英雄成长的背景是被照亮的林中空地的话,那么蟒古思的出场背景就是被遮蔽的黑暗之所,英雄的征战之路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去蔽”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作为存在背后真正的神也就获得了澄明,神“是通过对神性隐而不显的运作,神显现而成其本质,诸神是神性暗示的使者,神不是人借以逃避存在的庇护所,而是将人引向存在自身的本质。” [4 ]1193
在蒙古史诗中除了英雄和蟒古斯这一对外部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自身内部一种矛盾,即英雄夫人与英雄之间的冲突,这也类似于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对比。当英雄沦为常人状态时,就会陷入闲言、两可、诱惑和安定的被抛状态,从而蒙蔽了最真实的存在,“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以‘对事情’不深入为根据,是因为公众意见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一切差别毫无敏感。” [1 ]148而通过英雄夫人不合时宜的预言或预感,可以对英雄进行“良知的呼唤”,从而使英雄惊醒,超出常人状态,实现“向死而生”。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讲的“良知”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层面的。存在主义指出人容易与自身相异化从而沉沦在一种“日常”的状态之中,蒙古史诗中就描写了英雄在举办大型宴会时的一种沉沦于常人的意见中的状态,但是与公共意见相悖的是,夫人预测到了蟒古思的到来,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先行筹划”,是来自本体界的呼唤,将人呼唤至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中,从而达及自身本真的“能整体是”。在《祖乐》一书中,祖乐罕的夫人美丽贤惠、聪明先知,她恬静地放牧、为祖乐罕生下双胞胎小勇士,她能述说百年往事、她能预测未来的吉凶。在史诗中她预感到了破腿白发妖魔要来侵袭他们的家园,但是祖乐罕不信还打骂了她。在蒙古史诗中英雄的夫人普遍都有未卜先知的超凡能力。这是受了萨满教文化的影响,萨满女巫都有先知的本领,因此把这种特殊能力加在夫人身上,能使夫人的形象更加美好,也使得史诗充满神秘感,从而更加吸引人。
存在主义的世界是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性域所,人时时刻刻处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之中,因此存在者的存在只有通过“此在”才能够得以澄明。“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确乎不是对一个免于此在的永恒观察者现成摆在那里,而是在此在的寻视操劳的日常生活中来照面。” [1 ]123在蒙古史诗描述的世界中,各种器物不是简单的质料性实存,而是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也就使得英雄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生机勃发的因缘世界整体。
首先,在蒙古史诗中英雄的名称是有考究的,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弗雷格指出专名具有含义和指称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对于一个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除要考虑被表达物,即可称为符号的意谓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那种我要称之为符号的意义的、其间包含着给定方式的联系。” [5 ]“祖乐阿拉达尔罕”指代和指称的是一个特定的英雄人物,而这个符号本身也携带着深层的含义,“祖乐”在蒙语中有“圣灯、光明”的意思,而“阿拉达尔”却有“不真实、虚荣”的含义。因此,从这个名字上也能反映出祖乐罕的一些性格特征,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沦为常人的一面,这也符合人的本性。正像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形象一样,英雄也有一意孤行、脾气暴戾的一面。当祖乐罕生日宴会举行了四十天的时候,他的女儿告诫他不要再继续欢宴,因为有敌人要来侵袭,可祖乐罕没有听他女儿的话,还责怪了女儿,说他不应该参政议政。从这里能看出祖乐罕对于女人参政很反感,而且也不听善意的劝说,这也是史诗英雄性格典型的特征。英雄也会受到诱惑,也会陷入无助彷徨,也会耽于自大,就像存在主义文学所刻画的人在极端境遇中的选择一样,英雄也不断地面临着各种考验,正是在这种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和抉择过程中,英雄才一步步圆融了自身的生命,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从“祖乐拉达尔罕”这个名称上,我们就能够想象出一个光明与阴暗、理性与非理性的整体存在背景。
其次,蒙古史诗中用“骏马”“天鹅”“猎鹰”等形象来传达象征意义。与干瘪瘪的理性概念相比较,上述具象性的文化符号是以丰满充实的形态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这些形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它们是与人们处于日常的因缘关联中的“上手之物”,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体。对于文化程度高的听众来说,这些形象增添了内容上的灵动性;而文化程度低的听众又易于从具体形象中抽象和领悟出形象中的含义,从而实现一种传达上的共通感。在史诗《祖乐阿拉达尔罕》中,神驹是先于两个小英雄出生的。夏天祖乐罕在狩猎返回府邸的途中发现他的两色马群中降生了两匹神驹,而此时他的府邸中也降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该史诗中的骏马与小英雄先后出生的情节是在原有母题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即两匹神驹与它们的两个小主人先后诞生。蒙古史诗中像“这种英雄的骏马先于自己的主人神奇诞生的母题,暗示着主人的特异诞生及其非凡英雄的神圣身份”。[6 ]对于骏马的象征意义,巴·布林贝赫这样指出:“蒙古史诗中马的形象是兽性、人性和神性三重特性的结合。” [7 ]在蒙古史诗中,天鹅常常以信使的身份出现,她传达的是上天的旨意。史诗中,当出现紧急危险的情况或者预示有危险将要发生的时候,天鹅都会警醒英雄,给英雄报信。在祖乐罕带领将领尽情围猎、欢聚一堂、通宵达旦、欢乐畅饮的时候,一对雪白的天鹅从天空中飞过:“祖乐阿拉达尔可罕,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是因为营地太多,使你迷失了方向?是因为畜群腾起的尘埃,挡住了你的目光?是因为饮酒无节,你已大醉酩酊?是因为奶酒过量,美丽的夫人,也被你遗忘?是因为人们的喧嚣,使你把理智丢在一旁?白天鹅嘎嘎叫著飞向远方。” [1 ]5因此,史诗中的各种动物形象也就被赋予了人性或者神性,从而构建出一种能够进行互相交流、沟通和作用的环环相扣的世界整体,这个世界也比现实世界多了一层生机和活力。
最后,蒙古史诗中各种数字也更多的是在象征意义上使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数字“三”的使用,这里的“三”是不同于数学和科学意义上的纯粹抽象概念,而是包含着具体内容的象征性用法,因为从经验实证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存在三岁已经成年并出征的人。因此这个“三”应该是浓缩着小英雄成长过程和生活点滴的象征性用法。海德格尔指出“‘半个钟头’并非三十分钟,而是一段绵延,而绵延根本没有时间延伸之量那种意义上的‘长度’。这一绵延向来是由习以为常的‘所操劳之事’得到解释的。” [1]123因此,蒙古史诗中的数字不是一种科学计算意义上的数字,而是一种与生存境况相关联的存在论上的数字。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引申出一种作为言谈的逻各斯的概念,这种逻各斯能够将言谈所指向的存在者从它遮掩的状态中澄明出来,从而在人面前展现成为一个无蔽的东西。即是说,如果一个存在者想使得自身从被蒙蔽的状态之中显现出来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能够被言语所切中,只有通过言语的命名和谈及,这个存在者才能够成为无蔽的存在。伽达默尔这样写道:“语言能让某种东西显露出来和涌现出来,而这种东西自此才有存在。” [8 ]海德格尔才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然而语言如果被定做的话,就会成为信息,从而使得天空被分割,神性被褫夺,从而使人们丧失真正的家园。然而蒙古史诗的口头性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自由性。史诗是神圣的,具有固定的一些程式。但是史诗又是一种即兴化表演,歌手表演时的声音、乐器、曲调以及停顿更多的是一种感悟性的应运而生,顺势而发,同时听众作为参与者也加入这种活动中去。这是一种在神的感召的具体情境下自下而上的回归,而不是一种强制的规定性。在谈论到古希腊悲剧的时候,尼采说:“必须时刻记住,阿提卡悲剧的观众在歌队身上重新发现了自己,归根到底并不存在观众与歌队的对立,因为全体是一个庄严的大歌队,它由且歌且舞的萨提尔和萨提尔所代表的人们组成。” [9 ]通过这种相互交融的理解过程,存在的意义也就以自由的方式,而不是强制性的方式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祖乐》这部史诗存在着多种流传版本,这些文本之间不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千差万别的情节,内容形式各有特色。有的文本内容则与其他文本截然不同。这种情况反映了卫拉特史诗在它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种复杂的变化,并且也反映了口头文学的突出特点,即变异性。这种变化也受社会历史原因、地方特色、演唱艺人的状态、情绪、当时的社会现状、演唱场景、听众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同一部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在语言表现形式或故事内容上出现不同的变化。就如《祖乐》这部史诗虽有与它同名的作品,但是在人物、故事内容、表现形式及情节结构上存在差异。这种现象存在于大部分史诗中,《汗青格勒》等史诗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也是口头文学的魅力所在,通过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的传播能让口头文学作品充满各种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也能体现出口头传统的活力,而这正符合伽达默尔对于艺术作品的解释学观点,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口头文学的解读是一种“视域融合”;而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将作为口头文学代表的蒙古史诗视为是一种存在的不断展开自身的过程。
蒙古史诗的表演性主要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蒙古史诗演唱也被认定为是为了取悦神灵,而史诗演唱艺人在请山神时所进行的表演活动与萨满教中的巫师在神灵附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论,甚至连弓箭都是有生命的,这体现出一种对于万物生命的肯定和尊重。通过与这些生命体融洽相处,人们能够在不同情境中聆听到神的声音,并且实现向生命整体的回归,这种个体生命向原初生命的复归也是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的目标所在。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个规定中,‘世界’根本就并不意味着一个存在者,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而是意味着存在之敞开状态。……‘世界’乃是存在之澄明,人从其被抛的本质而来置身于这种澄明之中。毋宁说,人倒是在其本质中绽出地生存到存在之敞开状态之中,而这个敞开域才照明了那个‘之间’,在此‘之间’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才有可能‘存在’。” [10 ]因此,通过史诗演唱中的表演和萨满教的仪式,人们重新与神取得了联系,获得自身存在意义上的澄明。
存在主义是对科学崇拜的一种反思,毋庸置疑,理性确实对科技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片面强调理性的话,就会导致唯理性主义,从而丧失了人的丰富的生命体验,人也沦为技术化的工具,而非一个圆融的整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是在诸神隐遁以及现代科技拜物教的背景之下,以“此在”为出发点,揭开人们关注存在者而非存在的真相,提醒我们要不断去蔽,才能直逼本真,进入澄明之境。与存在主义思想相契合,蒙古史诗向我们展现出一个与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同的生活情态,在这个世界中充满了生机和可能,蕴含着交融和矛盾,人的整体生命的灵动性似乎也比现代社会要来得更加丰满。蒙古史诗中所描述的人们对于世界整体抱着一种“畏”的态度,而非现代人对于具体化和碎片化事物事件的“怕”,因此古代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原初和本真,而不像当今被技术所遮蔽的天人关系。最后,蒙古史诗启示我们需要以一种母性和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对待自然,才能愈合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赵文工.祖乐阿拉达尔罕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1-2.
[3]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1.
[4]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
[5]弗雷格.论涵义与意谓[M]//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
[6]烏日古木勒.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2.
[7]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诗学(蒙)[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153.
[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89.
[9]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30.
[10]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12-413.
[责任编辑:丁浩芮]
The Research on Jor Aldar H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Haburituya
Abstract: As the cultural creation in the childhood of human being, Mongolian epic reflected psychological logic and thought condition of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showed us the way which people dealt with the nature. As the reflection of technology, existentialism manages to show the real existence. The world picture which the Mongolian epic depicts is in the sense of existentialism.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analyses and interprets the Mongolian epic to show us a world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to let us see the world with another perspective and standpoint; to ease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Existentialism; Mongolian Epic; Hero; Symbolize;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