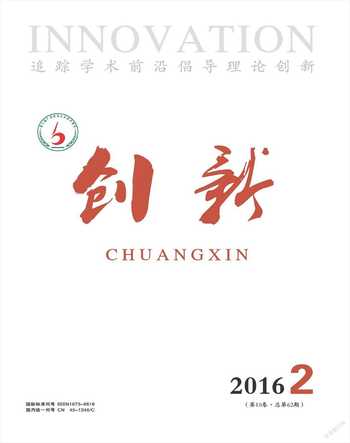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哈特与富勒论战新探
2016-07-13陈记平
陈记平
[摘 要] 哈特与富勒论战不仅是两大法学研究方法的正面交锋,也是西方法治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争论体现了法治两大要素的对抗,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分析。哈特关注社会事实,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事实判断,提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富勒则着眼于价值分析,认为法律规范必然与义务道德发生联系,提出“程序自然法”。哈特事实上主张的是形式法治,而富勒主张的是实质法治。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对立是法治理念内部存在张力的结果,无论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都是“良法之治”的必备要素。探析论战发生的背景、争论焦点,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哈特与富勒; 实然与应然; 分离命题; 法律目的
[中图分类号] D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6)02-0114-08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是伴随着对二战的反思产生的。二战之后,各门社会科学都力图撇清与纳粹思想的关系,而在法学界,各法学流派也做出了回应,有的改造,有的坚持为自己辩护。其中,新自然法学派,在坚持传统的应然与实然、法律与道德不分的基础上,改造了应然与道德的内容,提出“程序自然法”,使自然法思想具有了形式主义的特征。程序自然法实质上为法律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部评判根据,弥补了传统自然法由于标榜自身的正义和合乎道德而逃避批判可能性的缺陷,而正是这种缺陷可能成为纳粹政府为自己“恶”法辩护的工具。战前法律实证主义的风行与战后的冷落,形成强烈反差。实证主义不仅在法律界受到批判,而且可以说,战后的所有思潮的矛头都在对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成了众矢之的。人们认为正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逻辑——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法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的优劣是另一回事”,鼓励了纳粹政府肆无忌惮地制定邪恶的法律。法律实证主义似乎因此被“打翻在地”,不得人心,但是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实证主义,重新筑起理论的城墙,勇敢地面对来自各方的攻击。哈特因此先后与新自然法学派人物富勒、德富林、德沃金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多次的交锋后,产生了诸如《法律的概念》《法律的道德性》《法律帝国》等優秀的法学名著,成为促进西方法哲学发展的引擎。富勒与哈特的论战是论战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探讨传统法哲学的遗留问题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只有解决这个经典命题之后,才能开启随后与德富林关于“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问题”的论战,以及与德沃金关于法律构成的论战,可以说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为其后的论战做了理论的铺垫。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首先是以论文的形式共同出现在1957年第71期的《哈佛法律评论》,哈特的《实证主义和法与道德的分离》是其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学术演讲,富勒的《实证主义和对法的忠诚:答哈特教授》是对这次演讲的回应。哈特在演讲中坚定地区分法律与道德,主张“恶法亦法”;富勒批判分析了实证主义传统,认为道德可以分为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法律与外在的义务道德具有相当的亲缘关系,与内在道德具有必然的联系,但不与愿望道德发生联系,因此要理性地确定法律与道德的界限。1961年,哈特写了《法律的概念》一书,作为对富勒的回应。哈特在此书中指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规则体系,法律规则的效力来自于其内部的承认规则,而不是外在的道德。同时,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做了妥协,提出了法律体系中存在“最低限度自然法”。1964年,富勒则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作为再次的回应,他分析了法律所应具有的8种内在道德,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主张。
这次论战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法理学界一个重大学术事件。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促成了新分析法学与新自然法学的形成,并拉开了当代西方法哲学蓬勃发展的序幕。
哈特认为法律研究只有采用概念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析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然的法,其任务在于描述法律并使法律概念更清晰,只着眼于法律的语义分析,摒弃价值判断。哈特指出,传统的自然法学派在概念上混淆了法的实然与应然。传统自然法学派共同认可的是存在一种超越于实定法之上的普遍永恒的“高级法”,所有的人定法都要与之符合,否则丧失法律效力。但是这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应然观念,对实定法的要求有内在的逻辑矛盾。因为遵循此逻辑的实定法不可能破坏应然法,应然法既然类似于自然规律是必然的,那么“说科学家所发现的法则能不能被破坏,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星辰违反那描述其规律运动的科学法则,那么这些法则并没有被破坏,而是失去了‘法则’的头衔,必须重新建构”。[1 ]自然法的这种内在逻辑缺陷,容易消解法律的批判可能性,自然法没有为实定法提供外在批判的客观标准,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现存的法律可以取代道德作为行为的最后标准而逃避了批判”。[2 ] 64
富勒从实然与应然统一的基点出发,认为法律的价值就是实现法律背后所体现的基本伦理道德、民族习惯等。如果没有应然观念就无法理解实然的制度。在富勒看来,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法律规则所要实现的应然目的,就无法理解法律规则本身。“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将我们置于规则起草者的位置上,以便知道他们认为‘应当是什么’。正是按照这个‘应当’我们必须来决定规则‘是’什么。” [3 ] 192
富勒指出,实证主义所说的“描述”的任务,其本身已经不自觉地表达了一种理想或者应当,因为描述不仅仅是对一些经验材料的简单反映,而是指出人类努力的方向,否则实证主义进行“抽象”或者“分析”就没有了意义或者目的。富勒实际上表现出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内在张力,二者虽有区别,但骨肉相连。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妄图撇开价值只谈事实,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富勒还从社会常识上对哈特所坚持的法律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批评。因为在常识或者经验里,我们很难区分法律与道德或伦理习惯等。法律必然会体现与道德的一致性。这种区分实际上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努力分析”的结果,只有在科学抽象化、专业化的法律职业技术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而在人们的经验或常识中是无法区分的。[2 ] 43
富勒与哈特方法论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富勒的观点明显强调法律科学必须以法的应然为出发点,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康德“先验预设”的概念之下,才能使法律作为一种表象而呈现于人的先天认识能力范围之内。而哈特以法的实然为出发点,以概念分析作为基本手段,这种分析的方法易过于强调形式逻辑,从而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窠臼;而法律的实证思路,以归纳的实然意图推导出抽象的应然,也会增加法律内容的不确定性。但是富勒由于过于强调法律的前提性预设,随后演变为法律的内在道德,这种道德实质是形式理性的表现,然而在这种形式之下,由于对经验道德的忽视,而不免会导致出现符合内在道德却具有邪恶内容的法律。
哈特继承分析实证主义的传统,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优劣则是另一回事”,法律与道德是分离的,道德并不能成为法律有效性的依据。但是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论,是概念逻辑意义上的分离,而不是历史或社会事实上的分离。哈特指出,基于人的生存目的这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就会产生一些“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种自然法的内容虽然与传统自然法的箴规几乎完全一致,但不同于传统自然法建立在价值判断上,它们来源于事实判断。所以,哈特并不否认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上的联系,而为了追求概念的科学化,须将二者区别开。
哈特的法律与道德分离主义的命题,被标签为形式主义或本本主义而遭到指责,但哈特认为,分析实证主义并不是概念法学派或注释法学派,法官不应当机械式的适用法律,在法律的空白地带,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做出创造性的选择。这种选择,并不一定是道德的权衡,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政策或利益的衡量。“在阴影问题中,一个明智的裁决是不应当机械地做出来的,而必须依据目的、效果和政策,尽管它不是必然依据任何我们所谓的道德原则。”这些目的和政策也要纳入到法律规则之中,因为它们被看做有确定含义的法律规则的核心,也仍然是法律。
富勒指出哈特对内核与阴影暗区的区分,对法官来讲毫无助益。因为法官在遭遇法律与良知冲突的疑难案件中,实证主义只能提醒他要严格遵守制定法,而這种责任的要求对他的尴尬境地是毫无用处的。他会因此陷入违背良知的痛苦中。富勒强调:“除非我们的法官将忠于法律的义务与制定应然法的责任前后协调起来,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其两难境地的满意方法”。[3 ] 168
富勒认为法律秩序的基础必然建立在道德之上。而哈特认为,法律规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来自于“承认规则”的检验。法律秩序的基础应当在法律体系内部寻找,承认规则就是“某些被接受的指明制定法律之必要程序的基本规则。”正如卡尔·威尔曼所言,法律权利的基础只是“依赖于那些法律,这些法律直接或间接地赋权于该法律体系下的人们”。[4 ]富勒认为,虽然被人们普遍接受是一种社会事实,但是所谓的“基本”“必要”,就是一个价值评判的概念。哈特的承认规则仍然需要道德上的支撑。即使把宪法规范作为法律秩序的根据,也需要符合某些正当性观念。“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所起草的这部宪法之有效性取决于普遍接受,为了使这种接受牢固可靠,必须存在一种普遍信念:认为该宪法本身必要、正确和有益。” [3 ] 161
哈特与富勒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都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哈特并未否认二者在事实意义上的联系,同样富勒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也是受到实证主义形式思维的影响。哈特与富勒在对待传统自然法的道德观念的态度上,存在契合的地方。他们都对这种观念抱怀疑的态度,都警惕具有实体内容的道德对法律领域的不良影响。富勒主张法律只与“义务的道德”存在亲缘关系,而不能臣服于“愿望的道德”的要求。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就是富勒“义务道德”的翻版,都强调基本社会秩序的维持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哈特也反对传统自然法的道德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缺乏批判可能性的弊端。富勒的内在道德,往往被看作一种程序自然法,已经与传统具有具体内容的自然法大相径庭,这毋宁是对传统自然法的背叛。
富勒借鉴科学发现认识论的“科学事业”观念,为理解法律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角度。他认为,如果把法律理解成有目的的人类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它便存在于“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中”。[5 ] 152由此看出,法律作为有目的的事业,这种目的“是一种很有分寸的、理智的目的,那就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一般性规则的指导和控制。” [5 ] 171
“服从规则之治”的目的,是一种程序价值的取向,是一种凡是法律体系都应当追求的目的。即使立法精神相异的法律制度,也能找出根据这种目的而具有相似的结构、关系或模式。我们才能发现,法律制度是清晰确定可理解的,否则我们会被一系列无形式的、具体而毫无关联的偶发事件所包围。凡是不能促进人类“服从规则之治”的规范体系,必然都不是法律。
“正是因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它才呈现出法律理论家们能够发现并且将其视为给定事实情境中的一致因素的结构恒定性。”因此,法官在以法律规则处理具体事实情境下的案件时,必然会依靠该规则的目的作为指导。“法官必然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使用自由裁量权时,还要依赖非规则标准,如政策原则等各种因素。” [6 ]科学和现实的法理学否认规则的“应当”面向,排斥一个确定的目的,那么法官裁决案件的过程要么被理解为机械式的适用,要么是对法官行为的预测。这就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伦理怀疑主义,进而消解法律和法院的权威。
相比之下,哈特对法律的目的则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法律追求应当,这种应当也无须与道德有任何关系,“应当”这个词语仅仅反映了某种批评标准的存在,这些标准的某一个可能是道德标准,但并不都是道德标准。“应当是这样”,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提出了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目标和政策。所以,哈特并不否认法律对目的的追求,但是这种目的可能是多元的,是被历史、道德和社会事实所接受的目的。目的论的开放性,决定了“承认规则”的开放结构。这意味着人们并不必然出于特定的道德理想,也可以出于个人利益或习惯的服从或政策而去接受其所属国的法律体系,使规则产生法律效力。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哈特认为富勒的理论诉诸的是激情而非理性,而这样的激情是法律之外的甚至是与法律无关的。“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而会使得各种观念注入到法律中,甚至是邪恶的。因此哈特冷静地批评富勒:“富勒一生钟爱于目的,这种激情像其他激情一样,既能激励人,也能蒙蔽人。我已经试图表明,我并不希望他中止对这种主导理念的坚持不懈的追求,但是,我希望这种高涨的浪漫情绪应当通过比较冷静的考虑而平息下来。如果这样的话,富勒的许多读者发现温度降了下来,但是,他们将会由于增加了明晰而得到足够的补偿。” [2 ] 51
哈特认为分析法学是对富勒所提出的法律目的或者法治理想的技术性补充,但在富勒看来法律技术不是法哲学,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只能牢牢控制在宗教、哲学和道德的手里,而不应当落入法律技术的手中。“试图以法律技术的方法来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哲学问题如果不是法律的堕落的话,那么一定是法哲学的堕落。” [2 ] 55
富勒认为逻辑连贯性与善的关系比它与恶的关系更具亲和力,因而符合内在道德的法律必然追求的是善的目的。但是富勒对他提出的程序性质的八项原则过于自信,即使具备了八项要素的法律也可能是非常邪恶的。因为逻辑的严谨、语词的清晰并不能保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即使完全符合形式理性的法律也可能是违背实质正义的。获得实体正义,最关键的是保证前提的正确性,也就是有一个关于正义的理想图景,将这种理想具化为明智的法律观念去指导立法和司法。
哈特在阴影问题上,为法官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这种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但哈特也许过了头。为了追求理论的自洽,为了保证法律体系的自治特征,为了筑成他的规则体系大厦,他不允许规则之外的目的指导审判,从而否定了法官适用原则的可能性。“法官的使命是裁断,而不是发现”, [7 ]然而,这对现实毫无助益,难道当法官面对错误或邪恶目标的法律,他只能做的是坚持“法律就是法律”这样机械的思维吗?这样的司法永远会落后于现实,也不会符合法治的精神。
在概述两位法学家的论战后,本文将根据其焦点来讨论它对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的启示。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是关于法律与道德界限的争论,他们并没有否认法律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哈特认为道德应与整体的法律秩序相联系,而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只有整体的法律秩序违背了道德,才能称为恶法,才能导致法律无效。富勒认为存在直接与法律规范相联系的道德规范,如果法律失去了这些道德品质,则其根本就不能被称作法律,法律规范的效力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了道德,既包括义务道德也包括内在道德。哈特的观点更倾向于形式法治的立场,在某些法律规范虽然违反道德的情况下,但只要整体的法律秩序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或者是整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仍然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富勒的观点更倾向于实质法治的立场,即任何违反内在道德的法律规范都是非法的。笔者认为,法治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辅相成的结果,我们既要重视对当下法律秩序的遵守,也要对某些立法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反思。形式法治提倡的是一种守法的公民精神,而实质法治提倡的是一种立法的道德精神。哈特强调了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要具有苏格拉底般的公民精神,才能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富勒强调了在立法的过程中,要有批判反思的道德精神,使得制定的法律本身是良好的法律。
目前我国的法学研究更关注实然层面的研究,无论是法教义学或者是社科法学,都摒弃对法律的价值判断,要么以规范为对象只做文本的教义学研究,要么采取多元的视角做跨学科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都是现代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产物,它们都不考虑法律规范背后的道德伦理价值,因此对它们的过分强调会导致法律至上主义,加之法律的本质就是权力,就可能导致权力至上的观念。建设法治国家,但不能建设因过分信赖权力而被异化的国家,法治国家应当有其终极关怀,法治生活应当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西方在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就没有出现过单一的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必然是多元的。例如三大法学流派就是事实的、价值的、规范的分析方法。最早对西方法治做出贡献的是自然法学派,在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学派,在推动“王在法下”这一法治的核心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果要在中国实行良法之治,首要的任务是开展一场以自然法学为核心的启蒙运动。这种自然法学并不是照搬西方语境下的自然法学,它主张要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看待中国的法治现实,要传播永恒正义原则的信念,并对法治现实做深刻的批判。如果只停留在对复杂的法治现实做实证研究的层面上,我们永远无法形成中国所特有的法治理念。只有对整个法律建筑的基础进行深刻的探讨,才能为现实的法秩序提供理性赞同的基础。这些探讨集中在对人性、正义、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探讨上,扎实地做好基础理论研究,不盲从西方前沿研究方法。当然,自然法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中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学的实证研究,使正义的理念能够融贯的体现在法律规范之中,使法律规范本身就体现某种价值,例如公开性、清晰性、自洽性,使得形式正义得到张扬。
分离命题是现代思想家对“良法之治”命题的反思,良法之治是自然法学派的核心主张,但面对什么是良法,各人确有不同的学说。甚至相同的推理方法,也能得到不同的自然法原则。良法命题的不确定性导致客观的法律秩序无法形成,从而产生理想覆灭的危险。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种十分重视道德理想而忽视规则权威的社会形态。“天理本乎人情”“王法本乎人情”这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的司法理念,天理、人情、王法三位一体是法律秩序的理想形态。但何谓天理、人情,莫衷一是,最后只不过是为既有法律秩序作辩护的手段或者对司法官员进行鞭挞的箴言。从现代法治理念的角度观之,其根本无法对客观的法律事实产生连贯的认知,而仍由司法官员个人能力或偏好所影响,从而偏向于人治。当然,对情理法和谐的追求,并不是说是错误的。这种追求恰恰能够适应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即用实体正义来评价社会现象,忽略程序的作用。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曾竭力指出,法律是民族习惯逐渐发展的产物,法律应当符合民族习惯。既然中华民族更倾向于实质正义的思维,那么将西方近代程序正义理念强加于之,未免不合实际。但是,鉴于法律与道德分离的思维方式在我国的贫乏性,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西方形式法治的理念,也是迫切的。法治是理性精神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关注实体正义的民族精神,也应对社会现实有理性反思的精神,追求某种程度的“规则之治”,否则该民族就不能擺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从而很难走向符合人性需求的法治。
哈特对法律的目的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可以是历史的、道德的、社会的,只要是被共同接受的都可以作为目的。事实上,哈特以一种契约论的方式表达了法律应该具有的目的,使得法律体系能够包容各种价值追求。法治应该秉承一种目的开放性的结构,各种人生目的都能在这个结构中体现为具体的规范,法律的目的不是推崇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为每个人的正当追求提供一个基础的平台。法律的目的就是提供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品”(primary goods),包括自由、平等、机会与财富等,这些基本善品应当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只有在一种不平等的分配能够促进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时,才是被允许的。法律的目的不仅仅体现为实现统治者的意志,满足某些集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法律应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法律虽然可以通过规范的融合自洽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体系,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仍然需要回应时代的价值需求。因此,法律目的论应是一种开放性的理论,最大程度地促进法治共识的达成。
哈特与富勒的思想都呈现出某些局限性。哈特把建立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区分的法律分析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法理学研究出发点,但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它必不可少的会涉及人文关怀,体现人类奋斗的共同理想。并且从法律调控人的行为来说,没有理想含义的规范是不值得人们尊重并照章行事的。富勒看到了这种理想地必要性,但却挫伤了人们对完美境界的愿望追求的积极性,因为富勒悲观地认为这种理想是不可知的。因此他反对用一个完美的标准评价现实的法律,认为即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完美的,也能知道什么是坏的。这虽然终止了传统自然法学派对于理想正义模式的争论,但也使得法律丧失了对实体正义的追求。他也许没有想到,人们之所以不能对完美的理想有一个同一的答案,并不是这个答案不存在,而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内心好坏的观念,若没有一个完美正义观念的指引便无法形成。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认识能力产生怀疑,但决不能放弃对完美认识的追求。纵览人类行为的历史,人们可能在某个时期认为这个行为是道德的,但是由于人类能力随着时代的不断进化,人类越来越发现这种道德义务仍然是不完善的,因此不断地提升,不断制定什么是“合理注意义务”的标准。若没有一个完美概念的指引,人类的道德水平将一直处于原始阶段。经验的因果关系本就是不确定的,我们从不确定的判断出发,当然也可以得到较为信服或实用的结论。在自由意志领域即行为领域,作为自由意志的人,他也完全可以追求完美的事物。我们可以说,经验世界中的一切,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人类完全可以体验到完美世界中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理念。人的自由意志,纯粹意志本身就是完美的。法律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其必然应当追求完美理想的目标,尽管我们对目标可能一无所知。
哈特承继的实证主义传统,是对形而上学的反叛。这种反叛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得以流行。随后的法律社会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都沿袭了这种传统。这些法学派着重对经验的考察,即便有价值理想的因素,也是根据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社会法学派的庞德将法律的目的看成是满足需求和利益,认为法律是经过经验检验过的理性,也是理性发展的经验。法律现实主义代表人物霍姆斯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因而法律实际上是对法官行为的预测。这些法律思想为法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这种实证主义方法论下,法学不再依附于哲学,而成为随遇而安、无处定居的边缘科学。法学似乎在其他门类科学的关照下,欣欣向荣。经济、心理、文学的方法造就了经济分析法学派、行为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这些学派力图模糊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而分析实证主义正是要抵抗这种潮流。但是没有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支持,这种抵抗无疑不会得到普遍的支持。实定法的研究,不仅要为人类提供形式化的法治理想,也要凭借美好的生活愿景吸引人们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因此,法治理想必须考虑人类的德性生活,“只有坚持以道德为滋养,法治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8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对这种理想的确认。
参考文献:
[1][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冠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75.
[2]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4.
[3][美]富勒.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何作,译[M]//强世功. 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2.
[4][美]卡爾·威尔曼.真正的权利[M].刘振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2.
[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2.
[6]於兴中.法理学前沿[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3.
[7]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0.
[8]雒树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M]//红旗东方编辑部.法治中国——新常态下的大国法治.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253.
[责任编辑:杨 彧]
Dichotomy between Fact and Value: a Comment on Dispute between Hart and Fuller
Chen Jiping
Abstract: The dialogue between Hart and Fuller is not only a dispute about two jurisprudence methodologies, but also constitutes the essential part of western legal thoughts. The dispute reflects a conflict between fact-judgments and value-analysis. Hart focused on social reality and thought that legal norm is a kind of fact-judgment; he maintained a concept called "minimum natural law". Fuller focused on moral value and thought that legal norm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morality of duty; he argued a concept called "procedural natural law". The dispute is very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 reform.
Key words: Hart and Fuller; fact and ideal; separation proposition; the object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