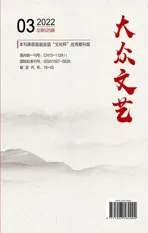论淮海戏现行常演传统剧目与古戏的相关性——以《秦香莲》《金锁记》为例
2016-07-12王思锦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21000
王思锦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000)
论淮海戏现行常演传统剧目与古戏的相关性——以《秦香莲》《金锁记》为例
王思锦(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21000)
摘要: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淮海戏,至今一直活跃于戏曲舞台上。而淮海戏常演传统剧目大多来源于其他古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等方面对古戏进行吸收与改造,淮海戏在古戏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成就了一门伟大的民间艺术。研究淮海戏剧本与古戏的相关性对于认识淮海戏剧本的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淮海戏;传统剧目;相关性
淮海戏,又叫“拉魂腔”“小戏”“三刮调”,是连云港、宿迁、淮安等苏北地区普遍流行的地方戏种。淮海戏始于清末,最初以地摊的形式进行表演,到后来逐渐发展为苏北地区最重要的舞台剧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淮海戏,它兼具北方剧种的粗犷豪放和南方剧种的温柔婉约,既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认知价值,又有着独特的艺术研究价值。它有着浓厚的“乡风野趣,爽朗明快,清新生动”的美学风格,是苏北地区的一枝奇葩。
淮海戏的传统剧目汇编共七册,有“三十二大本、六十四单出”。传统剧目有着浓厚泥土味,其大部分都是模拟农村中生活和物象而形成,所以表演程式带有泥土的馨香。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在观看淮海戏的演出后写道:“正因为它来自农村,所以演出中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无论曲调和表演都非常朴实……戏演得很生动,哏而不俗,嬉而不谑,蛮有风趣,也极具讽喻。”1传统剧目保留了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物象和事象,包括道德、伦理、信仰等民风民俗,成为我们认识历史,面向未来的重要文化遗产。
传统剧目的故事,基本来源于古代的著名剧作,还包括有名的民间传说、古典名著、历史故事等,有些剧目是从其他剧种移植改编而来。虽然故事取材相同,但淮海戏富于自己的特色,在语言、唱腔、念白、音乐、表演等方面都具有“淮海”特色,对于故事情节也作了“地方化”的处理。传统剧目的剧本与古戏剧本的关系基本可以概括为“继承与发展”,在继承古戏精华的基础上,赋予自己的本土文化色彩。本文以《秦香莲》《金锁记》为例,从故事情节与人物设置研究其与古戏的相关性。
一、故事情节的相关性
淮海戏的传统剧目,在故事情节方面基本沿袭了古戏,在古戏的基础上巧妙的融入地方特色。
《秦香莲》,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戏曲作品,据记载此剧原始版本是梆子戏《明公断》。据童德伦的《陈年谷秘史》考证,《秦香莲》这出戏最初是由曲剧《琵琶记》改编而成。改编后的《琵琶记》在舞台上演出获得一致好评,后又根据观众的愿望将故事改为包公戏,即陈世美最终被包公给铡了,因此戏名改成《铡美案》。
《秦香莲》讲述了陈世美离乡进京赶考而中头名状元,被招致东床驸马,妻子秦香莲带儿女进京寻夫,负心汉陈世美非但不认还痛打发妻。与古戏的不同在于:首先,淮海戏《秦香莲》之所以又名《琵琶记》不仅是因为《铡美案》来源于曲剧《琵琶记》,还因为秦香莲在认夫时假扮琵琶女。其次,古戏中将包公作为正义的化身,抨击了陈世美的忘恩负义,而淮海戏把王丞相塑造成推动故事演进的关键,
要赢也赢准了,今天,陈世美过寿,我跟你带到皇沙御府,好生说说,他就能把你认下来了。但是话也不能说满了,黄草布答头,拾到不喜,掉了不忧,认下来不必欢喜,不认也不必烦恼。2
王延龄充当了秦香莲幕后策划者;最后,在故事结局的选择方面,《铡美案》和《秦香莲》都采用了大团圆结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符合了中国人追求美满的戏剧心理,但在结局细节处理上有所差异,《铡美案》中陈世美被包公施以酷刑,绝命于法场。《秦香莲》中陈世美被发配充军,这样的结局属淮海戏剧本独有,富有鲜明的特色。
不好了!听相爷,把话明。功名革得干净净,官衣官帽忙除去,充军刑具载在身,悲叹一声罢了我,再想好处那怎么能?悲悲叹叹奔街道,柴桑店去充军,充军来了陈世美。3
这段唱词将陈世美凄凄惨惨的结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充军发配的结局远没有像《铡美案》中死于严刑惨烈,这种大团圆也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秦香莲》通过对故事情节的进行独特的地方化处理,更好地表现了农村的乡野趣味,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
淮海戏的传统剧目基本是对古戏的接受、扬弃、到再创造的一个过程。“文学艺术创作史上有这样的现象:一则简略的历史记载或一个简单的民间故事,被后世作家接受、扬弃并创造为艺术史上的另一类杰作;那些偏爱相同题材的作家在同一素材的接受、扬弃过程中,融会旧的经验,创造新的经验,积淀于文艺理论史中,以启迪后人。”4
二、人物塑造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戏剧一门是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而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戏剧的灵魂所在,是推动戏剧情节一步步走向高潮的载体,古今中外的优秀戏剧无一例外都塑造了形象丰满、深入人心的人物。
淮海戏剧本的人物设置与古戏就有所不同,《金锁记》人物丰富,约40人,庞大的人物设置使得戏剧角色丰满、内容完整。
其次,在人物称呼上也有所不同,《金锁记》中“蔡昌宗”“月娥”“赛庐医”“窦宝奇”“张驴子”等,这些不同,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文化差异。就比如“张驴儿”与“张驴子”就体现了地方方言的特征,而且淮海戏剧本大多由口述记录完成,因此与古戏有所区别。
《金锁记》在民间又叫《六月雪》,这部戏人物丰富。与《窦娥冤》中人物设置区别最大的有两个:第一,《窦娥冤》中张驴儿的父亲,在《金锁记》中变成了张驴儿的母亲;第二,《窦娥冤》中是窦娥的鬼魂向父亲哭诉冤屈,在《金锁记》中是窦娥母亲康氏。淮海戏《金锁记》中描述的最动人的人物形象还非月娥莫属。月娥一出场,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如花美眷,恪守礼节,尊敬长辈的闺阁女子形象就映入眼帘:
高楼惊动如花容,正是为奴描鸾绣,又听楼下脚步声,一闪秋波楼下望,还是生儿老父亲,插住花针盘绒线,绣头飘去五色绒,用手推去中交椅,走到跟前远去迎,袖头丢丢施一礼。5
月娥去蔡家之前的闺中女子形象与后来的软弱无助、遭受种种不公的妇女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不仅符合接受者的审美习惯和要求,又能为后续的情节发展添砖加瓦,让观众感受到世事无常、造化弄人的愤慨。就是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等待她的却是种种命运的捉弄,父亲进京赶考,无奈给蔡婆做童养媳,刚
进蔡家,丈夫便离乡进京,并传来丈夫溺水而亡的噩耗,月娥对这样的命运并没有产生斗争的念头,她只想在家中赡养婆婆,做一名贤孝妇。真正激发月娥反抗走上斗争道路的是:泼皮无赖张驴子的调戏与诬告,面对张驴子的调戏,月娥破口大骂:
骂张驴,你不要作。变人少,变驴多。卖罢枣子驮铁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睡在地下仰巴着,仰脸朝天够不着。明日禀报蔡奶奶,水湿皮鞭将你拖。”“窦月娥,怒气生。骂声张驴狗畜生。”6
命运将月娥变成了泼辣的女子。在公堂上,月娥被衙役施以钉心钉、打背花等酷刑时连连叫屈,拒不认罪,但面对宽衣衫逼供,月娥连说:“是我是我真是我,害死张驴妈妈也是我”,在她心里,贞洁比含冤受死更重要,她是贞女节妇的典型。
在这部剧中,另外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便是张驴子了,他成了泼皮无赖,人见人恶的反面人物典型。他一出场就是一副无赖的模样:
(倒呐子)抵动地,抵动天。两头吃饭把门关。苍蝇衔个米粒子,一翅飞到太行山,太行山上有个庙,花子跪倒胡祷告,张瞎子,李瞎子,他上南沟摸鸭子,摸个歪渣子,好像秃哥脑括子,脑括子!7
张驴子的唱词尽释其无赖相,极具地方特色的语言使得他的泼皮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符合农村人的审美要求。
淮海戏更擅长于用一些哗众取宠的丑角来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所以淮海戏的剧本向来不是严谨、规范的,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才是淮海戏塑造人物时的追求。
注释:
1.张寿山,李殿明.《淮安特色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158.
2.淮海戏研究资料《传统剧目汇编》之《秦香莲》.淮安:淮海戏研究会淮阴市文化局编印,1983:80.
3.淮海戏研究资料《传统剧目汇编》之《秦香莲》.淮安:淮海戏研究会淮阴市文化局编印,1983:154.
4.母进炎.《接受•扬弃•创造--<窦娥冤>与<金锁记>戏曲艺术经验传承比较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5.淮海戏研究资料《传统剧目汇编》之《金锁记》.淮安:淮海戏研究会淮阴市文化局编印,1983:2.
6.淮海戏研究资料《传统剧目汇编》之《金锁记》.淮安:淮海戏研究会淮阴市文化局编印,1983:45.
7.淮海戏研究资料《传统剧目汇编》之《金锁记》.淮安:淮海戏研究会淮阴市文化局编印,1983:34.
参考文献:
[1]王佳.《浅谈淮海戏的特色及价值》.艺术教育,2011(7).
[2]徐魏.《关于淮海戏语言念白的统一性及淮海戏未来发展的影响和忧思》.戏剧之家,2013(9).
[3]王正.《走近陈世美——兼评秦香莲和包公形象》.贵州社会科学,2007(5).
[4]郝青云.《元杂剧<窦娥冤>与明传奇<金锁记>的主题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王思锦,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硕士在读,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研究。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