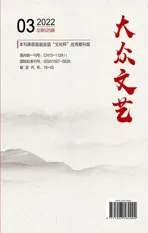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以性别文化研究为例
2016-07-12长江职业学院430074
程 瑶 (长江职业学院 430074)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以性别文化研究为例
程瑶(长江职业学院430074)
摘要:以性别文化研究为例,探讨文化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文化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发掘出研究上的“空白地带”,但将文化研究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面临着“被殖民”与“政治性”倾向的问题。而坚持“现代性”原则,将文化研究“本土化”“去政治化”,就能使文化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关键词: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性别文化研究
一、“文化研究”概述
“文化研究”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英国,之后扩展到其它西方国家及亚洲等地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领域。文化研究的源头可上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威廉姆斯、霍加特、霍尔为代表,其研究倾向是:“力图复苏并探索一种通俗的、劳工阶级的文化,使其成为边缘群体文化的表述,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1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对现代科技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工业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在后来的发展中,文化研究不断吸纳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这一开放性特征决定了文化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又没有统一限定性的知识探求领域,它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不断变化的。截止目前,文化研究的旨趣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2
1985年,美国学者杰姆逊到北大访问,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书将西方的文化研究带到了中国,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直到90年代初,它才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产生了强烈冲击。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开阔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机遇;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消解了文学边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泛文化”倾向。将文化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到底有何影响?是否存在问题?如何克服问题以充分发挥文化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本文将以文化研究中的性别文化研究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机遇:新视角下研究“空白地带”的发掘
从性别视角切入,可以发掘出之前被文学史忽视的某些女作家及其创作,从而可以填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空白,具有充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如人们通常在评价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作品时,往往称其具有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美,而铁峰则认为这种评价缺乏事实依据。她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学环境出发进行分析,发现东北沦陷区作家,除了沦陷初期的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金剑啸等描写过重大社会问题,表现了劳动者对剥削者的反抗斗争,其作品具有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美外,其他作家的创作视点与审美情趣并不具有上述特点。在性别视角的观照下,她不但分析出在对社会生活的审视视点上,东北沦陷区的男女作家之间差异显著:“男性作家多从男女情爱、人际关系、社会习俗、生存能力上切入生活。而女性作家基本上是从自我意识出发审视现实,多从女性的家庭生活,身边琐事切入生活,表现人格独立和自我完整。”3而且通过对但娣、梅娘、吴瑛、蓝苓等一批鲜为人知的女作家及其创作的重新发掘和解读,揭示出她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独特的审美情趣:表现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在逆境中独善其身的高尚品性。由此看来,在性别视野下,不仅可以发掘出在以往文学史中被忽视的女作家及其创作,而且能在客观上打破某些定论,从而起到还原历史的作用。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使得那些在现代文学的园地里默默耕耘着的、不时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娘子军们,如沉樱、陈衡哲、石评梅、林徽因、罗洪、方令孺等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因为这些女作家的加入,才显得更加完整、更加丰富多彩。
性别研究视野带来的批评视角的转移,不仅可以打破单一男性视角的局限,给以往被误读的那些文学作品以公正的评判,而且可以揭示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具有重写文学史的作用。在《两性写作比较与女性在本文命运中的转变——从凌叔华的<酒后>到丁西林的<酒后>》中,陈顺馨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了男女作家在创作中的不同:从语言表述上看,凌叔华(女作家)的小说,偏于对人物感情、心理的描写,基调是感性的,丁西林(男作家)的剧本偏于分析、评论,基调是理性的;从叙事主体来看,在小说中,妻子是叙事主体,在剧本中,丈夫是叙事主体;从表现内容上看,小说表现的是女性对异性的欣赏之情以及女性本能的冲动与现实的障碍,剧本表现的是男女关系上的妒嫉之情及其冲突。她还通过列举王家伦、赵园、孟悦对《酒后》中女主人公形象的三种不同解读:放荡不羁的淫妇、时代道德混乱的受害者、有女性独立意识的主体,说明了文学研究者在批评中的性别差异,并将文学批评者分为男性批评、传统的女性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三种类型。4不论陈顺馨的看法有无偏失,但不得不承认将性别研究运用到文学批评的确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义。陈顺馨对作家及文学批评者由于性别差异而在创作及评论中的不同表现的发现,揭示出了隐蔽在文学史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文学史批评的性别视角与批评主体的性别意识及文化立场密切相关。文学史书写者的性别观念和文化立场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史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以男性中心意识为标准编纂的文学史中,许多带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很难得到公正的评判。而性别视角的介入,则可以打破单一男性视角的局限,还那些在以男性中心意识为标准编纂的文学史中被排斥、误读的女性作家以一席之地,从而具有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可见,文化研究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而发掘出文学史研究上的“空白地带”,使得文学史上原先被遮蔽、压抑和淡出的许多研究对象“浮出历史的地表”,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善。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大众媒介、文人集团、都市文化、大学教育等角度来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无疑证实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体现出的活力。
三、挑战:“被殖民”与“政治性”倾向的问题
但将文化研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仍以性别文化研究为例来说明:
首先,性别文化研究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女性研究缺乏自身的传统,因此,如果本土接收者将其照搬进中国,缺乏消化和超越,缺少主动调整和建构,那么在运用性别文化研究来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种种现象时,就有可能陷入一种“被言说”的状态,从而使得性别文化研究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其次,性别文化研究始自争取妇女权益和社会地位的女权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反抗男权文化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使得性别文化研究一进入文学领域就面临着两难的局面,性别研究的政治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其学术性又要求性别研究必须独立于政治之外,并尽可能客观。如果性别研究过分强调其政治性,那么将它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可能会导致文学史文学性的丧失,成为“性别文化史”了。
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观念与思潮都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将文化研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必定面临着“被殖民”与“政治性”倾向的问题。
四、策略:以“现代性”为原则将文化研究“本土化”“去政治化”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显然是借鉴对话、将文化研究“本土化”,建构起符合中国特定历史现实语境的文化研究体系。“本土化”或曰语境化,它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现代逻辑以及全球化理论》中指出:“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5陶东风进一步解释道:“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的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6因此,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必须从中国具体历史与经验的特殊性出发,从中国特定的现实语境出发。
随着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随之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当下的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重语境交融,而中国的现代性还远远没有完成,“‘五四’所提倡的民主、平等、科学等价值从来没有成为过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7正如钱中文所说,西方文化研究是以后现代性诉求为特征的,其中包含着对文学的审美诉求的消解。而在中国,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中国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其中也包括坚持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诉求。8因此,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应该坚持“现代性”原则诉求。
贾振勇在《评判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中指出,”现代性一方面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实现了文学形式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所表达的历史内容和价值追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已成为挥之不去的文学事实,同时又成为理解作为文学事实的现代性的文学史期待视野;另外它们又共同促成了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模式的形成,如果抛却文学史研究话语各个时代的色彩,从理论内涵到方法论,中国20世纪文学史研究也展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探索。尽管对现代性的体认各不相同,但追求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及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目标。”9以现代性为价值坐标来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能复活中国现当代文学艰难曲折现代化进程本来面目,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阐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风貌。于是,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就在“现代性”这里找到了相通点。
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代性价值标准的确立又能在保持文化研究的文化批判性精神的基础上,有效避免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政治性”倾向。仍以性别文化研究为例,李小江在谈到怎样处理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方法的关系时指出:面对以男性为中心社会和文化,女性主义者在做科学研究时,在政治态度上首先必须是女性主义的。虽然每个人都是一个民族符号、性别符号,但要做科学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那个符号上,而要化到对象中去,不能纯粹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而要超越它,尽可能达到“真”。10也就是说,将性别文化研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时,若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女性主义者能尽量克服自身的主观局限,明确自己的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服务于女性,就能防止在批判男权文化时有过分的政治性倾向。以现代性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价值标准,并非来自研究者的主观态度,而是来自中国现代文学的客观过程,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因此,以这一价值标准建构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是最有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的。如果性别文化研究者批判体现在文学和文学史中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时,并非是为了达到提升女性地位的政治目的,而是以现代性中的平等原则为诉求,那么就有可能接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真实。
总之,坚持“现代性”原则,将文化研究“本土化”“去政治化”,文化研究定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注释:
[1]李俊.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J].当代文坛,2001(5).
[2][5][6]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童庆炳、钱中文.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71,81,82.
[3]铁峰,高智琳.东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及作品[J].学习与探索,1990(4).
[4]陈顺馨.两性写作比较与女性在本文命运中的转变——从凌叔华的《酒后》到丁西林的《酒后》[J].上海文论.1993(3).
[7]李明彦,李奎.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经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艺评论,2005(3).
[8]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J].文学评论,2001(3).
[9]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317-318.
[10]李小江.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