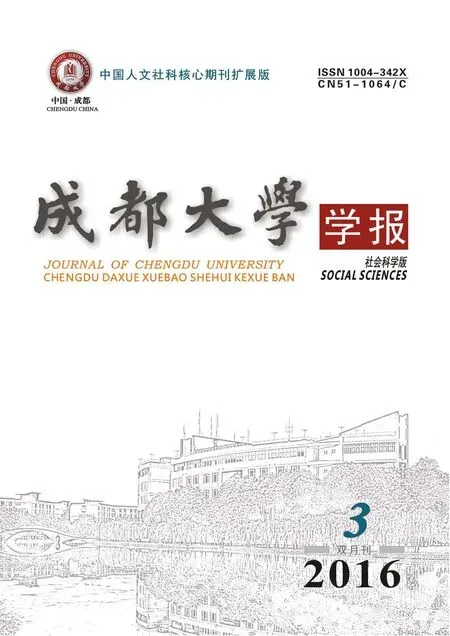晚清民间社会的观察
——以冈千仞《观光纪游》为中心
2016-07-08邱昭惟
邱昭惟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文艺论丛·
晚清民间社会的观察
——以冈千仞《观光纪游》为中心
邱昭惟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100871)
摘要:19世纪以来,随着外力入侵中国,中国古老的大门被迫打开,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之下,给予当时欧美国家的探险者来到中国游历的机会,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字记载,作为“他者”的观察角度,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建构19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现状,然而毕竟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理解,或多或少都带有些主观性的偏见或误解,还不若邻近中国的韩国人或日本人来中国之后所留下的观察,或许更来得客观一些。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升,他们眼中除了观察来自外洋的白人势力,也无时无刻不拿中国来做观察比较的对象,这种观察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政治或军事上的意图,然而冈千仞作为19世纪日本“兴亚论”的支持者,对中国的态度是亲善的,也因此在中法战争之际来华所留下的记载或对中国社会的批判,能更真实描绘出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情况,这也是冈千仞所著这本《观光纪游》最大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冈千仞;王韬;中法战争;市井风情
一、前言
清季之时中国由传统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有大量外国人进入中国,他们留下了许多文字或图像,这些对中国的观察可说是为19世纪中国市民社会的转变历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虽然这是一种他者的观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偏见,但也无疑提供给我们更多观察社会的角度,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种观察常能找出当时中国文人觉得习以为常而未加以记载的事情。而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观察之中,由于政治目的的需要,日本对中国的观察可以说是所有国家中最为深刻的,像冈千仞所著的《观光纪游》,被日本人称之明治时期日本三大汉文写作的游记专著。而冈千仞本人也和王韬、黄遵宪、何如璋、黎庶昌等人交往甚密,并曾在游历中国之前接待过王韬游历日本。对比王韬游历日本后所写的《扶桑游记》,此二书虽同为游记,但书中内容所体现出的观察可以说有很大的落差:王韬作为当时中国知名士绅,他所写的《扶桑游记》对日本的观察只是浮光掠影般的介绍;而冈千仞的《观光纪游》则是更深刻地介绍中国,此书中除了对山水景色的描述外,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观察。由于他到中国的时间点恰好是光绪十年(1884)中法爆发前夕,到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快结束时返回日本,因此他对中国的观察可说是对自强新政实行二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的总评价。在这一年中他游历了中国大江南北,因此记载的事情较为全面而非局促于一地,然而国内关注的人并不多,就连冈千仞的名字对多数人而言都是感到陌生的。本篇论文以冈千仞中国游记为地域横轴,辅以其他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资料,选择上海近代城市的发展作为时间纵轴的延伸,试图勾勒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黎明时期的一些社会现况,黎明前夕总是最黑暗的,透过冈千仞对中国的批判和观察,也有助于让我们了解清末时期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社会。
二、近代现代中国的市井风情
(一)城市观察
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之中,冈千仞造访许多城市和乡镇,对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城市或乡野有着不同的印象,笔者选择他所造访的三座城市来观察中国19世纪末的城市现况。
北京

以上引文是冈千仞1884年进入北京时对北京的印象。此时北京外围道路状况虽是石板路但大多毁坏,路况不佳乘马车行走犹如舟行怒涛之中;路旁巨室大户房屋高大如小丘般;而北京也有着宏伟的城楼,但由于缺乏修缮难免显得有些破落。进入城内,人口稠密道路宏大,出入乘车不像南方一样乘轿,但市街道路由于往来多车因此“尘土十丈”;由于城内多是泥土道路,因此下雨时积水严重,常“一车陷泥不动后车十数辆皆为其所阻街衢阗咽不可行”,由此可知当时的北京仍泥地当道,和上海当时道路状况是有所落差的。而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也让冈千仞感到讶异有很多乞丐,譬如他在琉璃厂附近逛就留下这样的描述:“丐徒赤裸或负或怀幼或火线香蹑客,客投钱取火吹烟,我邦维新以前无所无丐徒,唯未至陆续如斯。”[1]180这里他提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到处都是乞丐,但就算如此也没有像中国此时这么多,他的这句话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日本自改革以来,失业人口已大幅减少,唯中国虽实行改革已有二十年,但首都情况并未有太大的改善,就如冈千仞自己所说:“中土今日犹我邦廿年前,唯我邦国小乱亦小,中土国大故乱亦大,中人自负衣冠文物,不复讲自治自强之道。”[1]180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相比是大国自然问题比较难以解决,但他也指出国人自负衣冠文物,抱持文化优越意识,使得改革陷入停顿状态。
苏州

以上引文是冈千仞到达苏州之后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苏州是江南有名的大城,但经历太平天国之役之后,距冈千仞来到此城之时,已相距二十年的时间,但城市恢复非常缓慢,只及旧观十分之三,繁华和残破、富贵和贫穷、死亡同处于一座城市之中,城市街道狭隘臭气熏天。此后除香港和澳门每游历一城市都有如是评价。而在苏州这座园林之城,冈千仞对退休官员们个个大建园林,感到十分疑惑,问随行友人:“观察布政,任地方疾苦。超任此职者,必散贯金开花园,蘧园怡园留园,无园不然,中土大官,固如斯乎。”[1]57而友人对此则是默然不知如何回答。在苏州之行之后常看到城市的残破杂乱之景,冈千仞提出一个看法,那就是为政者不用心,城市因战乱破坏之后的重建应更有规划才是。因此他问及友人陈希道: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冈千仞的友人陈希道对城市街道的现状呈现如此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了解;冈千仞提出“龙动”即伦敦过往之时由于街道狭窄疾病丛生,于是改变城市的规划设计;陈希道则说中国的城市确实也是多瘟疫,但由于朝野对此已习以为常所以也未有改善的想法。对此,笔者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对中国城市的情况进行说明:过去在研读西方和日本的城市规划之时,发现中国和西方以及日本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西方和日本的城池比较多的性质是属于防卫型的城市(山城),就如冈千仞自己所说“我邦据形胜构城壁,而民庶皆家于城壁之外”,而被鲁迅认为是最了解中国人的内山完造甚至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城池结构的不同,也折射出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性格。[2]14-16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城市基本不存在日本山城这种性质的城市,除了少数如宋朝时抗元名城的钓鱼城外,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位于四周交通辐凑的中心位置,大多数城市以城墙作为防线,对于守城者而言,这样的防线确实过于薄弱。不整齐规划的城市街道虽有弊端,但也有其相对好处,那就是如真有不测外敌攻入之后,城市内部像迷宫一般有利防守者反击或逃脱,明末史可法守扬州或太平天国面对湘军攻进南京城时都有如是做法,也因此中国在宋以后放弃城市规划整齐的做法应具有一定的战略考虑。[3]119-120
上海
晴出观市街,分为三界,曰法租界、英租界、米租界,每界三国置警署,隶卒巡街警察。沿岸大路各国公署,轮船公司欧米银行、会议堂、海关税务署,架楼三四层。宏丽无比,街柱接二铁线一为电信线、一为电灯线,瓦斯灯、自来水道,皆铁为之。马车洋制,人车东制,有一轮车载二人自后推之。大道五条称马路。中土市街不容马车,唯租界康衢四通,可行马车,故有此称,市街大路概皆中土商店,隆栋曲棂丹碧焕发,百货标榜,烂然炫目,人马络绎昼夜喧闹。[1]20
这一段引文是有关上海租界地的情况,展现出现代化的风貌。当此之际的上海,其繁华更胜东京,人马络绎不绝百货齐备,可说是东亚第一,街道整齐洋楼林立,在1880年代之时水电瓦斯都已接通,交通工具有来自西方的马车、来自日本的人力车,还有独轮载二人的台车又称小车。这种小车出现于苏北地区而后在上海地区盛行,主要原因是因其灵巧适合上海老城区狭小的街道,车租是最便宜的符合大众需求;马车行走的地方主要是租界;至于人力车则租界和旧城区主干道皆可以通行。根据德国记者高萨满1898年在上海的记载,人力车起步价五分钱,小车只要三个铜板(而十个铜板才一分钱),至于马车则是上层阶级的代步工具。[4]163但上海城区到处纵横的小车也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这种小车数量众多,由于负重而行,对路面的破坏很大,其次轮轴转动摩擦出的声音也很刺耳,因此在1868年上海工部局就已要求小车应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噪音,像是多滴油膏或将轮轴换成铁制品。[5]55-56
看完租界情况之后,我们接着看上海旧城区的情况:
拿租界和上海旧城区中最繁华的城隍庙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新与旧的对比是如此的强烈,虽然租界和上海旧市街相邻,但因管理方式不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城市风貌。1880年代上海旧市街的情况让人感到意外,在原本的想法之中,认为上海旧城区在开港通商四十多年之后,城市风貌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理应有所不同才是,但结果却是让人大感意外。1862年日本明治初年,高杉晋作等人乘坐千岁丸至上海考察他们所见的上海旧城区如下:
上海市坊道路之脏无法形容,特别是像中小街道的通道,到处是垃圾粪堆,无插足之地,人们也不清扫……有人说一出城区就是野外,荒草盖路,棺材纵横,有的死尸用草席一卷到处乱扔。当时正值炎暑之际臭气冲鼻……此次上海之行感到最艰困的是饮水浑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江上还时常漂浮着人尸。……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据说上海街里只有五、六口水井,而且井水非常浑浊,因此人们都饮江水。……[6]106
对比1862年高杉晋作等人的出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上海旧城区与1880年代的旧城区似乎差别不大,街道依旧狭小环境依旧不佳,当然毗邻在旁的租界改变就很大了。至于大多中国城市内部的脏臭问题一直要到1901年前后之时,各地城市陆续设立相关部门和法律处罚之后,才获得基本改善。[7]
而在1880年代之际,日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开始逐渐热络起来,只是这种活动是和妇女有关的卖春行为有关。在1877年,租界工部局已有日本妓女出现的记录,甚至因强拉客人,引起日本政府重视,认为她们影响日本的国际名声,于1884年之时派人前来上海查办,到了1885年8月强制押送20多名妓女回国。其余在此一时期待在上海的一些日人,其表现在外人看来也甚为奇怪,如穿和服木屐、赤脚配刀等等。1890年之时,鉴于一些日本人穿着“奇装异服”到外滩公园游玩,影响观瞻,工部局还派员告知日本驻上海领事:“除非他的国民衣着正派,否则将不允许他们进入外滩公园。”[5]183-184而在1880年就在上海经营乐善堂药铺的日本人岸田吟香也对这些穿着传统服饰的日本国人反感,认为他们没有真正学习西方文明,由此可知,日本官方和士绅阶级在此一时期他们对传统的割裂是在于对西方的认同,也因此非常关注西方人是如何看待日本人。
实际上19世纪末中国城市在外人的观感不佳方面,和现代市政体系在19世纪末尚未建立起来有关。19世纪上海的中心,不是上海南市旧城区,而是在公共租界。租界的发展是在由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上海工部局”管理之下才发展起来的。这个组织起源于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清政府失去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之时,它的作用和新英格兰某村庄理事会或大公司的董事会相似。[8]146正因如此,上海租界这座现代化城市,在其管理之下才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当时除了管理机构外,现代市民精神的建立也是一个城市能有效运作的基础,光靠管理机关是不可能出现良好的城市环境的。
(二)农村及各地旅游观察
19世纪末正值新旧社会的转变时期,自强新政从1860年代实行以来,到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的变化情形如何?过往在讨论清末时期的城市和农村发展史之时,并没有将自强运动至中法战争爆发前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的社会变迁史抽离出来进行观察,而是以一个较大的时间段来进行讨论。这和资料的散布不容易集中于1884年自强新政实行近二十五年来情况有关,而冈千仞的《观光纪游》可说是弥补了这个空缺,恰恰使得我们可以观察自强新政实行以来至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社会的情况。从《观光纪游》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冈千仞游走中国南北各大城市之时,兼论旅行各地所见的农村情况,这可说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观察资料。譬如他在乡间游历之时,由于坚持穿着日本传统服饰,在乡间行动之时每每引起当地居民的围观,甚至引发一些排斥举动,例如,在绍兴游历之际,参观大善寺宋代所建的七层宝塔,游记中提到:“市人见余异服簇拥,有投瓜皮瓦石者,犹我邦三十年前欧人始来江户时。”[1]79连在绍兴这样的内陆较大的城镇都碰到这样的困难,不难想见在乡间活动之时,所存在的一些安全隐忧。而这也反映出日本开国之后,由于地域较小,日本举国上下历经三十年的西风影响,已普遍适应外国人的存在,但在中国,因地域辽阔,广大的乡间和自强运动之前相比较,其变化差异是有限的。正如他在南北村落的比较中所描述的:
南北农村之比较,在北方一路所经原野洞开土性肥沃而小民概辐粗笨愚鲁,无一知文字者,所在村落亦不多见润屋,唯男女尽力耕作,俭陋朴素各守其分,不知外慕,与南方游惰唯末之趋者大异其俗。[1]195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冈千仞认为北方土壤肥沃,人民知识水平低下,唯知勤俭工作各守本分过着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文中对于土壤肥沃这样的观察确实让人感到疑惑,如果是东北地区尚有可能,但冈千仞没去过东北只去了直隶所以他所指的地方,应当不是河北。因为就河北的土地情况19世纪初俄国的观察者即认为这地方“土地贫瘠,耕种得不尽心,居民显得不健康过分羸弱”[9]46-47。此外光绪年间(1877-1879)华北地区发生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受灾严重的省分,有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数省,连续出现严重旱灾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缓解,这使得1880年代之时华北地区地力呈现残破景象,冈千仞从南方上海一路北上到北京,所经之处不外乎河南、河北、山东数省[10]366-367,硬要说历经灾荒之年的土地土性肥沃,也未提及“丁戊奇荒”的大旱灾不甚合理。那这样对北方农村的观察结果,最可能的情形应当是他和旅居北京的日本侨民交换讯息而来,因为在游记中他自己也常提到与待在中国各地日本人交换各地讯息的情况。而对南方农村的评价则是指上海周遭地区,因为此时的他尚未到广东,因为他到了广东之后,对当地的风土民情的观察还是比较正面的:
广东诸水之所合注,不特民殷物阜,冠他省,其民忍劳役,务作业捷举动尤敏商事,被服净洁,家屋华美,亦不类他省,民间多解英语,妇女亦间为英语,此皆其地邻香港,日交外人正,耳濡目染不觉至此也……唯其恶外人,甚北人不知何故,余曰贱民无学故至此或溺读书或溺赌博其亡羊一也。[1]275
引文中能看到冈千仞盛赞广东物阜民康、人民勤劳、衣服整洁、房屋华美,比其他省份都来得好,民间多解英语,他认为是和香港近、和外人交涉得多的结果。但在仇外情绪方面,距二次英法联军都已过了二十多年仍是有非常强烈的排外意识,更甚于北方,按冈千仞的说法是认为这些下层民众所学无多所致。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成立,因为就算是北方省分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也未必比广州更高,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和历史上广州人拒“外人入城”的地方意识有关。[11]24-25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地方的传统意识型态是多么牢固地存在于地域之中,纵使外在的大环境已改变许多,但传统意识的改变却是非常缓慢的。
由于冈千仞出行的目的名为出游,因此遍览各地名胜也是必然,但如果冈千仞是在今日的中国出游或许他会感到吃不消,何出此言?主要因为在中国内地目前的情况,只要是景点莫不围起收费,费用也不便宜。对比清季时冈千仞游历中国之时,景点基本上都是旅人自行参观分毫不取,如苏州虎丘或是浙江兰亭鹅池等地,甚至连交通方面也有免费的交通工具可搭乘,如“至萧山度钱塘江一船,乘客四五十名,渡舟官置不要钱。”[1]81但也必需说明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景点大多杂乱无人整理,偶有例外的收费处,像是禹陵、圆明园和静明园这些地方。如冈千仞到浙江禹陵之时:
晨起,舟已泊在禹陵下,三面皆峻峰,所谓会稽山者,陵户掌门钥投钱入观,有碑蝌斗文字,曰衡山崩时,获裂土中,禹碑是也。[1]60
看了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陵户应是附近居民,应该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守陵人,他们自设门户,收钱让人入内参观,如果他们不是国家公务体系的人员,圈地收费也就不算收贿,只能说是圈地为王坐地喊价。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名胜之中是否普遍存在,还有研究的空间。而在北京原是禁地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中,冈千仞纳钱入内参观了圆明园和玉泉山的静明园:
至玉泉山,一名静明园,相传金章宗避暑地。元明二代,为游革之地,门兵四五名,观客求钱,此为八旗兵,旗兵犹我邦列藩轻卒。[1]161
归纳以上史料来看,他们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坐地圈钱,其二是投钱导观,其三是纳贿进入。而就冈千仞的游记之中所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当时的一些古建筑由于战乱之故,任由其在野地之上,没有加以修缮,也自然谈不上所谓的人员管理,就如他所说:“两浙被祸尤甚石门,本为大县,而居民四散,唯见七层塔巍立于荆棘之中尔。”[1]90类似于石门这样的地方古建筑矗立于荆棘之中的情况,在游记里常有记述,明十三陵无人管理也是如此。正因如此,读到这三处有人员收费的情况,让人觉得十分突兀,而收费的性质又有些许不同,让人感到有些趣味。参酌德国商人恩斯诺1888年在上海的旅行经验:他在当时去了上海城隍庙旁的豫园湖心亭游览,结束后在上海当地导游的引领下,来到附近的花园,这个花园平时只允许官员进去,一般平民是禁止入内的,但和门房交涉一番答应给小费之后,得以入内参观还在花园和友人喝茶欣赏花园美景[4]129。所以结合冈千仞在北京的旅游经验和恩斯诺的上海旅游经验,似乎这样的情况是一种常态,只是不被人们知悉罢了;而所谓的禁地至少在清代晚期也不是那么绝对,只要有钱都有机会入内一游。这是否和1870年代以来,社会封建秩序逐渐崩解有关也有待研究了。像是过去原本各阶层的服饰都有明确的规范,但上海自1870年以来,服饰已未照过去规范,《申报》上多有对如此事情的报导,如《申报》1872年7月19日即载有一首《洋泾竹枝词》:“佣奴亦效假斯文,衣履难将贵贱分,更有异言并异服,淡黄马褂着纷纷。”[12]由此可见之,在封建秩序崩解的情况之下,很多过去生活中的规范未必都能被遵守。
而在冈千仞逛中国各地市集之时他也发现一些情况,那就是中国人去日本大量收购书籍,回中国贩卖,像他在杭州城时就看到他的一个友人陈云台“前年游日东买求书籍,来此开书肆,满架图册一半东书”。另外也有中国人感到日本不珍惜中医的医书,将来必定为此后悔,但在此冈千仞并没有对大量日本图书流入中国或是对医书的流出感到可惜,反倒对友人说:“敞邦西洋医学盛开,无复手多纪氏书者,故贩原板上海书肆,无用陈余之刍狗也。”[1]67此刻的冈千仞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士也阅读大量的中国古籍,只不过他并未将中国的传统经典置为神圣不可挑战的地位,反倒鼓励中国士人多汲取西方有用的知识,不要拘泥于古书之中,例如有一位六十岁的老者对冈千仞说及卜筮,冈千仞说他不相信这个,使老者脸色为之一变,说“子不知周易为圣人书乎。”而冈千仞给的回答是“夫圣人作易发明天地之理,后说易者徒说象数惑卜筮,殆类巫祝之所为,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实有故也。”[1]70对于他在广东患虐以来,对中医的治疗一直抱有偏见,认为是庸医,急于回香港看西医,但在看西医的过程之中,治疗也不是那么顺利,但他对西医却也没什么怨言,从这也能看出他对中国的古典医书从日本流出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因为在他眼中看来不管是古籍或是中医书都是过往陈旧之物,没有什么值得去珍惜的!此外在中国的书籍市场也碰到友人向他抱怨“先人梓画谱,镂刻精密,艺林争传,贵邦人翻刻刷数千,折价贩上海,本版不复行,先人苦辛事业,一朝为东洋黠贾所利,真人间不平的事。”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说或许很难理解日本人也会做出盗版的事情,但实际上利之所在不管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都会干出同样的事,人性好逸恶劳这种思想无分民族天性使然,在过去的欧美地区发展初期也是如此。所以重点还是在于后来出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才逐渐有所改变。而在遍游中国大江南北后,冈千仞对中、日民俗之间的差异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服无衣裳之别,妇人涅齿。带广蔽腰围等,皆为外人所讶者。而中人辫发垂地,嗜毒烟甚食色,妇女约足,人家不设厕。街巷不容车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抑我与中土同文邻域,而犹异其风俗如此,况欧米辽远,人异种类,宗教文字,冰炭相反者乎,而今五洲往来,互订友谊,此真宇内一大变。[1]42
对于中日风俗的差异,此时的中国对日本的一些日常生活方式仍显得十分陌生,难免觉得有些奇怪,像是席地而坐,睡觉不用床、妇人染黑牙齿等等,但他也指出中国的一些问题像是嗜毒甚于食色,妇女绑小脚,家里不设厕所,街巷狭窄等等,对此无需以此讪笑对方,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尚且相近,风俗方面仍有那么大的落差更不用说是距离遥远的欧美,但在五洲往来互动友谊之际,这真是世界一大变化。从他的这一段话之中,我们能感受到冈千仞作为一个日本文士,他的世界观是很开阔的,不同的民族应该相互往来认识彼此,但他认为中国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是由于中国方面的错误所造成,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赞同!
三、结语
在北大图书馆特藏书库架上,偶然翻开尘封已久、一百多年前由冈千仞所写的《观光纪游》,原以为只是一般游记,但阅读之后发现这本以汉文写作的书籍很具社会观察力,由于这本书没什么知名度,甚或连冈千仞名字很多做近现代史研究的人都没听过,因此让我开始查询有关冈千仞的一些信息才让我对冈千仞有更深刻的了解,以研究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应该是很高的。透过游记对中国的他者观察,使我们了解在1884年之时,身为日本人的冈千仞已认为“日本已是小康之治,而中国尚处于幕末时期”,这样的评价对国人而言,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但就事实而论,中法战争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十年,此时综合社会各方面的比较即可知道中国和日本在此时已有落差,十年后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似乎在此之前早有蛛丝马迹可寻,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的根基不仅在外在的规模或军力的展现,更深一层次的应是国民和社会的整体素质。这篇论文以冈千仞在1884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为主线,配合其他时人的记载,来观察中国近现代社会改变的情况。外在的硬实力和内在的软实力同样重要,研究历史为的是鉴往知来,逝者已逝不可复追,21世纪的中国能否重新站回世界舞台的中心引领世界风潮,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努力的方向,告别百年以来悲惨屈辱的命运有待所有中国人的努力,历史上没有一场下不完的雨,相信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参考文献:
[1]【日】冈千仞.观光纪游[M].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2]【日】内山完造,赵贺译.隔壁的中国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5.
[3]【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王维江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5]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4辑)[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6]冯天瑜编辑,【日】纳富介次郎等著.上海杂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7]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M].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2010.
[8]【英】卡尔克劳,夏伯铭译.洋鬼子在中国——1911至1937在中国的回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9]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10]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11]【法】伊凡,张小贵译.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2]《申报》[N].1872年07月19日,1901年09月15日.
(实习编辑:徐雯婷)
收稿日期:2016-03-11
作者简介:邱昭惟(1978-),男,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313.076;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3-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