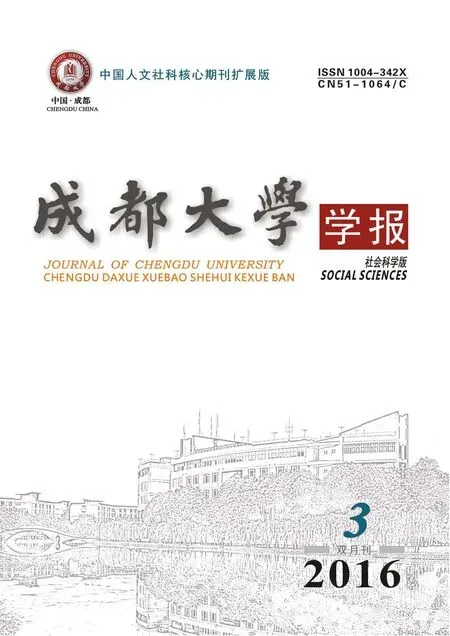大自然文学的文化“空间”*
2016-07-08王雅琴
王雅琴
(1.安徽行政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2.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文艺论丛·
大自然文学的文化“空间”*
王雅琴1,2
(1.安徽行政学院, 安徽 合肥230051; 2.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刘先平是我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在大自然文学中,自然与人是文学塑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作者着力表现的情感对象。自然与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体,更是作者文学观和价值观的隐喻体。自然的在场、人的在场;自然与人的关系存在、价值生成都远远高出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从而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的构成以文学作品为表征,体现出作家、世界与作品的关系,也展示了作品的文化生成和言说的开放性。
关键词:大自然文学;文化;在场;解构;建构
安徽籍作家刘先平致力于大自然文学三十余年,出版作品四十多部,多次获得各类国家级奖项并于2010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刘先平不仅著作丰硕、成就显著,更是在文学界中举起“大自然”文学的旗帜,以其“自然抒写”展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以及自然与人的生存之道。从1978年创作《云海探奇》以来刘先平就以人为本,探寻自然与人之间的奥秘,追求“诗意地栖居”的美好生存空间。这不仅是其文学观更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表现。因此对大自然文学的研究,就不能仅从文学性上来审视,更应从文化的视角来探寻其社会性和文化价值。在大自然文学中,透过那一层层“自然”的迷雾,我们可以发现在自然与人背后构建了诸多层次的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的构成以文学作品为表征,不仅体现出作家、世界与作品的关系,更展示了作品的文化生成和言说的开放性,从而使大自然文学具有经典气质。
一、在场——自然与人
刘先平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是直面生态危机,是用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来传达作者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大自然文学不仅是作者生态文学观的表现,更是作者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在大自然文学中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是文学表征,更是作者情感所指符号。在大自然文学中存在着诸多关系,其中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最为基本和永恒的关系项。
人类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探寻,从古希腊的神话中就已经开始。在古希腊神话中神就是自然的象征:奥林波斯山上的十二主神如天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丰收女神得墨特耳、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农业保护神雅典娜等等这些神都是大自然的化身,而神与人的关系就是大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表现,“万物有灵论”中自然不仅富有人的特性,更是人的创造者和庇护者。人与神的和谐相处之时正是世界的美好时代。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接受了埃及一个传统历史分期的看法,人类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中虽然人类已经产生,但“神—自然”无疑是占据世界的主导,而在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中人不仅逐渐取代“神—自然”成为世界的主导,更以其自身的各种矛盾成为人们书写历史的主要内容。从“神—自然”的主导到人的主导,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对自然的崇拜到自然的退场和缺席。大自然从人类“以己度物”的“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在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自然与人不仅在中心地位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更是一种哲学思辨的变化。
在大自然崇拜时期,人不仅是后于自然产生,更是自然产生的结果,大自然处于世界的核心和统治地位,正如宙斯作为天神的至高地位,人们以祭祀完成对“神—自然”的膜拜过程。当工具论出现之后,大自然经历了去魅的过程,成为人们生存和生活的手段和工具,征服自然和占有自然成为人类走向逻各斯中心的桥梁。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中心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变不居的,“中心没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而是一种功能,是一种无中心点,在那里无穷尽的符号——替换物开始投入到差异运动中”[1]。在解构主义理论中,逻各斯中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位于事物和结构内部一成不变的中心只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者的一种理论设想,“所以德里达说,没有中心在那里,中心不能理解为是以某一呈现物,中心没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中心不是中心”[2]。根据解构理论的理解,大自然和人并不是一种中心的置换,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心,“中心不是中心”。因此,在大自然文学中的大自然和人都并不是符号的象征,而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两个没有本源差别、没有等级差别的二元项,两者都是一种“在场”。

大自然在大自然文学中的主体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1978年刘先平创作第一部大自然文学作品《云海探奇》开始到2013年的《西沙有飞鱼》,大自然的形象不仅逐渐清晰、丰满,而且更富有了生态美学的意味,它不仅以客观形态出现更是富有情感色彩,是作品的主体。生态美学家曾繁仁曾说过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经历了“去魅”到“复魅”的过程,这种“复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及生态学发展的产物。后结构理论者德勒兹认为生成是一种弱势生成,在他看来“社会中的强势或弱势族群不仅以一种量的方式对立,相反,‘强势的’本身包含着一种表达或内容的常量、标准”[4],“强势族群被分析性地包含于一个抽象标准中”“生成是一种弱势生成”[5],如“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按照德勒兹的理论,自然的“复魅”并不是回到神的时代中的那个万能形象,而是人类逻各斯中心映照下的“弱势生成”,正如同女人、儿童、动物一样。自20世纪以来,生态危机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也逐渐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生态危机成为世界性危机。伴随着这一社会性现象的出现,各种应对措施包括生态保护的研究也逐渐出现,生态学也成为显学。在生态学视阈中,自然的“复魅”正是在生态危机现状中出现的,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人类强势族群下的弱势生成。但在大自然文学中,作者并没有将大自然作为人类的一种弱势生成,相反是将其作为平等主体的一项。正如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中所绘制的没有本源差别、没有等级差别、动态化多元化的世界,事物之间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延异”(difference)。“延异”这个词是德里达所创造的,虽然学者对这个词的内涵阐释并不统一,但“差异”无疑是该词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差异规定了事物间本质性的存在而不是规定性的存在。德里达还曾提出类似与德勒兹“弱势的生成”的“他者”理论,但德里达显然更重视多元关系之间的“延异”,因为这种“延异”是消除“他者”的方法之一,也是德里达追求的多元项共处的一种方法和原则,而这种关系恰好是大自然文学中作者所想要表达的大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刘先平所说的“我把考察大自然看作第一重要,然后才是把考察、探险的所得写成大自然探险纪实”[6]。不过在大自然文学中大自然显然是以一种外在的、表征的、能指的、场景的符号“在场”,而人则是内在的、内涵的、所指的、精神的符号“在场”。
2.人的“在场”。文字是“心灵书写”(psychical writing),这清晰地表达了文学作品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关系。刘先平说大自然文学是大自然对他的一种召唤,而他的作品都是在长期的自然探险中的心灵感悟。在人类活动中,文学就是一种注重亲身在场性体验的活动。刘先平几十部大自然文学作品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我”很少,作品中的人物也是融入大自然之中的,探寻大自然的规律,感悟大自然的奥秘,人似乎是大自然的追寻者,是一种“缺席”,但事实上,在大自然文学中,“人”与“大自然”一样都是一种“在场”的存在,只是,“人”的“在场”要更为隐秘、更为多元和丰富。
与“恶”的较量。大自然文学中,人的“在场”首先表现在与“恶”的较量中。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一种虚构的艺术形式,善与恶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创作内容,但在大自然文学中的这种善恶较量要更为隐蔽。大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显然是作者所追寻的理想境地,但与之相对立的则是现实中的“恶”——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的“在场”正是在与生态环境恶化的较量中充分体现出来。这种较量虽然并没有像典型的生态文学文本中那样鲜明、强烈的抨击生态环境的恶化,但却以人的“在场”来展示这种忧虑和思考,其中以“自然”为主要表现对象和情感传达的叙事生成凸显“在场的人”。事实上,“不存在作者声音丝毫不介入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创作中不直接现身向读者说话,却往往将自己的意图或倾向隐含于作品的叙事或抒情进程中,使读者不知不觉中领略到作者的牢固在场。”[7]大自然文学中人的“在场”是一种意义性在场,是价值的生成性在场,它以作者的情感为基调表现出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和斗争。事实上,事物的存在往往是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在与“恶”的较量中,“人”作为作者的代表,显示出作者的情感与爱憎。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对传统的作者概念作了层层辨析,进而提出作者不是一般的专有名词而是话语的一种功能,是把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从话语的内部影响外部”[8]。由此可见,正是“作者”将作者的生态文学观和价值观处于作品之中,在与“恶”的较量中体现出了“人的在场”。
3.教育的在场。文学有认识、教育、审美等作用,其中教育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大自然文学中的主人公多是少年儿童,从叙述视角来看,大自然文学可以被看成是儿童文学作品;但从接受视角来看,刘先平显然并不仅仅是将少年儿童作为教育的对象,更是将整个人类作为教育的对象,因为与大自然相处的是整个人类。自20世纪以来,生态危机已经波及到全球,一方面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灾难,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生态危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追求下,“拯救地球”似乎只是空洞的口号。在大自然文学中,作者却不是仅仅呼喊口号,而是以真实可信的现状来展现这种危机和灾难:被捕杀的黄鹂、十元进行的懒猫的买卖、鸟的买卖,因生态破坏动物食物的缺乏、竹子开花对熊猫的灾难性影响、山林的频繁起火砍伐等等,各种野生动植物数量的减少和消失。虽然作者并没有用过多的话语来抨击生态环境的恶化,但在作品中金丝燕、长臂猿、山乐鸟、白腰雨燕、麋鹿、大熊猫等野生动物数量减少、踪迹难觅就是最为深刻的批判。在大自然文学中作者不仅以这些令人震撼的文学书写来展现作者的忧虑,更是在教育读者要行动起来做生态保护的行动者,特别是作品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为保护大自然而做出的努力,像小黑河、望春、李龙龙、刘早早、蓝泉、小叮当、翠衫、林凤娟等这些孩子形象,护林员老邹、罗大爷、孙大爷、阿山等这些与大自然朝夕相伴的人物形象;陈炳歧、张雄、赵青河、王黎明、王陵阳,老杨、小罗、老范、小秦、小李、幕容、王三奇等这些为保护生态环境、探索生态规律而孜孜不倦辛勤工作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正能量。正是在这种人物和自然的互动中营造出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生存之道。因此,在大自然文学中作者一方面以“人的在场”展现出对生态危机的忧虑和痛心,另一方面又不断渲染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家园,在这两种对比中作品中的教育意义更为鲜明,同时也是在不断展现人类的在场。
二、建构——价值生成
大自然文学从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出发,深入探寻大自然与人的存在关系,力图寻找“美好家园”。在“美好家园”的建构过程中,大自然文学首先以文学的形式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搭建起大自然与人关系的桥梁,并通过生态道德来完成美好世界的图景构建。
1.二元解构。自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笛卡尔的理性传统,西方传统哲学都建立了一个逻各斯中心,而在中心的对立面中设定了一个次元项。由此,“主体与客体相分离,认知者与他所认识的对象相分离”[9],“在笛卡尔那里,自然贬低为‘广延的物质’,而人则被重新赋予‘思想的物质’,于是这种二元对立本体论上的鸿沟愈加深刻而永久”[10]。“二元对立其实是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模式,而且,两个对立项并非是平等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11]在自然与人的二元对立中,自然和人类也并不是地位对等的双方,而是人类中心主义之下的二元对立,也就是将自然置于人类之下,是工具理性世界观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渐在文化领域中兴起,成为一种文化思潮,影响了诸多方面。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解构”是其关键词之一,它“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以及机械划一的整体性、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12]。在大自然文学中这种解构首先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对将大自然作为人类的“他者”关系的解构,对大自然与人类二元对立的解构。在作品中大自然不仅是描写的环境,还是人物存在和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自然的壮美和野生动物的生活情境是作品展开叙述的主体部分,与由人物构成的情节相比,大自然所展现的魅力和奥妙显然要更为吸引人。作品中展现了野生动物之间的情愫:爱情、亲情甚至友情,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这些情感虽然是拟人化的,却生动地展现了大自然的魅力。作者着力渲染这种情感甚至淡化作品中人之间的情感,如陈炳歧与方玲、赵青河与王黎明、东岛上的小赵与小李的爱情,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大自然文学中,大自然并不是“弱势生成”,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他者”,大自然和人一样是美好世界的缔造者。在大自然与人和睦相处的世界中,人类中心主义被怀疑、颠覆、消解。
2.价值生成。价值的存在和肯定来自于对立面的存在和肯定。人类的存在价值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存在价值也来自于人类,两者并不是二元思维下的对立与抗争、工具与目的,而是整体主义下的相互肯定和融合。德里达说一个事物或结构的中心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其他的东西。“一个符号的意义根本不是根之于它自身的内在性,如概念、所指等,而是根之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它的意义是由它的‘他者’所赋予的。”[13]这也就是说差异并不是事物间的隔阂,更不是促成二元项对立的原因,相反差异是促成事物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事物间价值存在的必要因素。因此,无论人在场或不在场、大自然在场或不在场,两者都不是对立和抗争的,而是从差异中走向彼此、走向有机和协同,正如怀特海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中,而世界也在我们中”,而事物的价值和意义也在双方的肯定中实现。
1973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曾提出浅层生态学运动和深层生态学运动的说法。他认为:“浅层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层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14]从本质上来看,浅层生态学实际上仍然是将人类置于世界的中心地位,是从人类利益出发,关注的是非人类对人类的贡献和作用,在人类利益的终极目标下来看待大自然以及一切其他非人类事物,其思维方式遵循的仍旧是人类中心主义。正如“环境”二字,“‘环境’是在某个中心存在的外围围绕、服务、影响该中心存在的物质”[15]。事实上,“浅层生态学”也好、“环境”也罢,都是二元思维的产物,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而大自然文学则将从整体主义出发,将大自然与人置于世界的同样地位,不仅关注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更“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16]。“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之一,但在德里达的结构理论思想中,解构理论并不是单纯的消解性的理论,而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论指向,“他创立解构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突破这种静态封闭的压制性的思想文化系统以期开辟出新的存在空间”[17],也就是说解构指向建构,因此,大自然文学就不只是停留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上,更是在建构整体主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意识自觉和哲学思维,刘先平才能在近四十年的大自然探险和文学创作中明确提出自然与人相处之道——生态道德,从道德层面上来完成价值和意义的建构。
生态道德下的价值生成。生态美学从主体间性出发,强调关系中的存在。在大自然文学中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就是价值生成的基础,“关系”指向生成。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映照下,大自然是人类的工具和手段,两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平等的关系,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和谐和统一,正如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开发导致的生态危机。对于事物间的关系,德里达曾提出“踪迹”(trace)的概念来指代事物间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的关系,“踪迹指的是在场的不在场,显现的非显现,表述的是事物或语言符号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映照的关系”[18]。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万能大自然的“神的时代”中,还是大自然缺席的“人类之上”之时,真正能促使大自然与人价值存在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映照的关系”。因此,在大自然文学中并没有过多展现惊心怵目的场景,而只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忧虑来表现作者的情感,更多的则是自然与人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景。人对于大自然、大自然对于人,都是相互的一部分,不仅在护林员老邹、罗大爷、孙大爷、阿山等这些与大自然朝夕相伴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还在那些关心大自然、保护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人物如陈炳歧、张雄、赵青河、王黎明、王陵阳、老杨、小罗、老范、小秦、小李、幕容、王三奇等身上。正是在大自然与人平等关系的基础上,价值才逐渐生成。大自然文学中主要的关系就是大自然与人,但这些关系的连接并非是简单的结合,而是包含作者情感的道德指向。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凝聚着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中、对大自然与人关系的连接中,作者不仅完成了文学书写更提出了实践操作方法——生态道德。所谓的生态道德就是人和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19]生态道德首先就是一种道德的甚至是美学的、宗教式的目标,它注重自然与人相处时的关系法则,“只有生态道德才是维系自然与人血脉相连的纽带”。文学不是单纯地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本身。在刘先平的生态道德中体现了作者的整体思维而不是二元思维方式,看中的是大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立、抗争,约束于道德准则而不是法律内,体现的和谐、交融之美而不是占有、征服之霸权。从艺术形态来看,这是一种美的追求;从实践活动来看,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从形成结果来看,这是一种价值生成。
大自然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和感悟,与其说是一种艺术表达,更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探索。刘先平说过他把考察大自然看作第一重要,而在大自然文学中所设置的大自然场景由于是来自作者的亲身体验,因而显得格外真实和可信。虽然作为文学作品,虚构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大自然文学中纪实性、探险性显然要高于虚拟性,正是“目睹了大片森林被乱砍、乱伐、水土流失正在加重……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恶果”[20],作者才能将真情实感寄寓于文学创作,并能正确认识大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大自然文学中,大自然与人作为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都处于“在场”之中,不仅体现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更在文化的空间中探寻了大自然与人关系的构建、价值的生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自然文学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艺术性更在于实践性。也正因为如此,对大自然文学的考察就不能拘泥于文学的视角,而更应结合作者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以及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作品形成的文化环境中来考察和阐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大自然文学的真正涵义和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13][17][18]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6][20]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研究所.大自然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4][5][8][1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刘阳.构的在场与文学的在场——兼论德里达在场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反照[J].文艺理论研究,2011(1):125.
[9]【美】菲利普·克莱顿.从过程视野看作为后现代理论和实践的生态美学[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7):43.
[10][14][16]郭继民.生态伦理的本体论承诺——庄子与西方后现代生态哲学的会通[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6.
[12]刘文良.生态批评的后现代特征[J].文学评论,2010(7):81.
[15]刘青汉.生态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邵金峰.生态美学的后现代特征[J].社会科学家,2010(11):17.
(实习编辑:徐雯婷)
On the Cultural Space of Nature Literature
WANG Yaqin1,2
(1.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Academy of Governance, Hefei, Anhui, 230051;2.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Key words:nature literature;culture;presence;de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Abstract:Liu Xianping is the pioneer of the nature literature in China.In nature literature,nature and man are the main content of literature creation,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the emotional objects that the writer tries to show.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s not only the relationship of things but also the metaphor of the author'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values.The presence of nature and ma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value generation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iterariness an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thus building a rich cultural space.This cultural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literary works,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the world and the works, and also shows the cultural creation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works.
收稿日期:2016-03-10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安徽省2014年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王雅琴(1980-),女,安徽行政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吉林大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3-6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