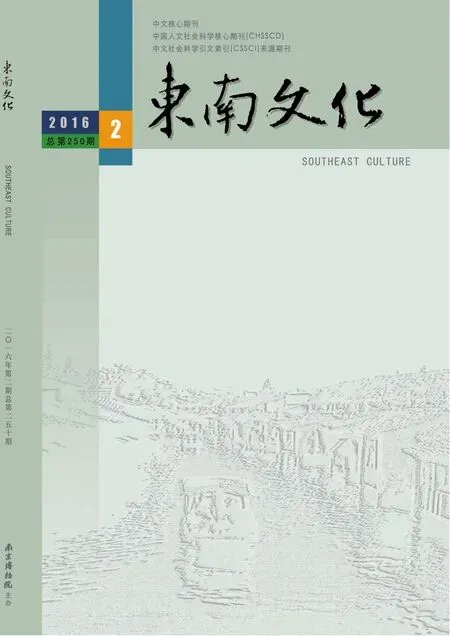古物陈列所的建立与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
2016-06-24王谦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王谦(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安庆 246011)
古物陈列所的建立与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
王谦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内容提要:民国初年,利用紫禁城开辟古物陈列所反映了清末民初教化兴国的社会舆论环境与北京政府欲通过新建公共空间以启蒙民智的努力。古物陈列所的建立,部分解构了紫禁城原有的封闭空间格局,开辟了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的休闲方式与活动场所,具有划时代的社会文化意义。然而,北京政府又利用高昂的门票对古物陈列所实行变相的空间控制,使它的公共性质受到了限制。
关键词:古物陈列所开放民初公共空间
1934年,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在回到英国后回忆他在紫禁城的生活时写道:“从前被包括在紫禁城内的一部分重要宫宇,如今也已丧失了它颇富于传奇色彩的权力。南面用围墙围起来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没有东西大门的守护),在皇帝退位后,即被民国当局占据。两个最大的宫殿建筑(武英殿和文华殿)变成了博物馆,收藏了部分以前用来装饰热河和沈阳行宫的精美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现在是被‘借’来而尚待民国政府购买的皇室藏品。”[1]庄士敦所指的博物馆,正是下文所要论及的民国成立后建立的中国早期官办博物馆——古物陈列所。
在近代中国公共博物馆的发展史中,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仅一墙之隔,然而,由于古物陈列所从1914年开放至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仅存在了短短的30余年,逐渐被历史所遗忘,它作为近代中国开辟公共空间努力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先后有学者通过搜寻相关的历史资料重现了古物陈列所成立的历程,如段勇细致地爬梳了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衰落历史[2],傅连仲梳理了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关系[3]。但是,在封建统治灭亡与民国新立的时代背景下,古物陈列所作为一个新型公共空间在北京出现的社会、文化价值还需要进行重新审视。
一 民初北京帝制空间的解体与现代博物馆的筹办
民国既立,清皇室失去了对紫禁城的管制权,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清皇室仍可“暂居宫禁”,虽没有规定居住的具体期限,却“划定了宫禁范围,在乾清门以北到神武门为止这个区域”,尽管末代皇帝溥仪在宫禁内“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4],但溥仪被允许的活动范围实际仅是紫禁城的“生活区”,而紫禁城宫禁之外的区域如三大殿等核心地带已归民国政府管辖,这些区域正是昔日皇权的象征。对于如何处置这块象征皇权的宫殿空间,民国政府业已有了新的计划。早在1912年1月,曾协助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梁士诒就曾致电给孙中山与黄兴,其电文就如何处理紫禁城的用途做出了安排:“腐旧宫殿,毋论公署,私宅皆不适用,将来以午门外公园、交通马车、三和殿为国粹陈列馆,与民同乐,则乾清门内听其暂居,亦奚不可。”[5]可见,将昔日的帝王宫殿辟为图书馆、博物馆等现代公共空间在推翻帝制之前就已有预案,这个预案的用意,正是着眼于开放原来的宫禁,与平民共享帝王空间,以体现新型国体的优越性。
无独有偶,曾力主创办博物馆的张謇此时也看到了紫禁城特殊的空间意义,又提出了利用紫禁城的空间优势创立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的必要性:“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则所以为地兴事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6]至于博物馆、图书馆的选址,则“以为博物院宜北海”[7],显然,张謇所看重的正是开放紫禁城封闭空间格局的特殊意义。从官方到民间,将民国所管辖的皇宫地区开放并加以利用已成为共识。
实际上,此时民国政府也确实开始了筹建博物馆的实践,教育部、内务部都在北京着手建立现代博物馆。
民国成立伊始,蔡元培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早年曾在德国学习,又游历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对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尤为注意,并认为博物馆与美术馆、动植物园、影戏院一样,都是发展社会美育应专设的机关,是科学研究、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8]。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聘请鲁迅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等事宜,很快在蔡元培与鲁迅等人的努力下,以“搜集历史文物,增进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北京国子监成立,收集太学的礼器为基本陈列品[9]。教育部选择国子监为创建博物馆之所有着实际的考虑。文庙与国子监在民国后由教育部接管,教育部认为,“国子监旧署,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亦均足为稽古之资,实于历史博物馆性质相近,故教育部即就设立历史博物馆,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0]。1914年,教育部又以“历史博物一项,能令愚者智开,嚣者气静,既为文明各国所重,尤为社会教育所资”为由[11],申请将文庙划归筹备处兼管。可以看出,教育部筹建历史博物馆的意图,是利用古物的文化功能对社会实施教化,将原来的帝王庙堂转变为新型的教化空间,这一意图在日后创办古物陈列所时得到了延续。
然而,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始终没有实质的进展,一是因为力主创建博物馆的蔡元培上任半年后就辞去了教育总长之职,其继任者又多频繁调动,走马观花,兴办博物馆的主张难以贯彻;二是缺乏创办经费,“历史博物品之搜集,欧式博物馆房舍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种种扩张计划则皆以绌于经费,未能大举兴办”,国子监原有的古物与其他所搜集的古物,“仅敷保存之用”[12]。曾参与过历史博物馆筹建的鲁迅先生后来回忆说:“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馆)’的意思。”[13]尽管历史博物馆未能在短期内正式对外开放,但博物馆筹备工作的展开已表明北京创办博物馆的社会、文化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也开启了利用古物筹建博物馆的先例。
另一个尝试筹建博物馆并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是内务部。如果说教育部筹办博物馆的出发点在于补助教育、开启民智,那么内务部所创立的博物馆(即后来的古物陈列所)则首先意在保存古物。民国甫一成立,内务部就以保存古物事宜向袁世凯上书:“查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至各省设立分所之处,应从缓议。”[14]设立古物保存所的动议很快得到了落实,内务部礼俗司经过紧张的筹备,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古物保存所的开放工作,于1913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虽然我们从现有的文献中没有见到官方开办古物保存所的公文档案,但由古物保存所发布在《正宗爱国报》上的开放公告记录了它的开放历程:
本所以保存古物为主,专征取我国往古物品,举凡金石、陶冶、武装、文具、礼乐器皿、服饰锦绣以及城郭陵墓、关塞壁垒、各种建设遗迹,暨一切古制作物之类,或搜求其遗物,或采取其模型,或旧有之拓本,或现今之摄影,务为博雅之观,藉存国粹之宝,爰就永定门街西先农坛屋宇,为开办地点。惟是规划伊始,征取各省古物,一时骤难运致,仅就京师原有旧物,择要陈列,以资观览。此外尚有评古社、古艺游习社、古物保质处、古学研究会、琴剑俱乐部、古物杂志社、古物萃卖场,以及秋千圃、蹴踘场、说礼堂等处,种种设备,以期逐渐推广,务使数千年声明文物之遗,于此得资考证,藉以发思古之幽情,动爱国之观念。兹订于民国二年一月一号共和大纪念之日起,至十号止,为本所开幕之期。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凡我国男女各界,以及外邦人士,届时均可随意入内观览。[15]
古物保存所的开放吸引了众多游人,鲁迅当天也前来游览,并在日记中记道:“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但人多耳。”[16]当时的民众对古物保存所持什么态度呢?有人在报上表文认为,开办古物保存所“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不要紧,其实存国粹,巩固国基,辅助共和,裨益教育,关系实非浅显,不可视为等闲哢。中国未变法之先,坏在好古而不考古,简直的是食古不化,才弄得国是日衰,自变法而后,又坏在弃古而不法古,把古人一笔抹倒,所以仍是杂乱无章,过犹不及”,“前人手泽所存,都要陈列起来,任人观览,还要从旁加上注解,说明此物之由来,为的是发起人民爱国之心,作后人前车之鉴,也颇有很大的关系呢”,“现在陈列古物,任人游览,正是一个近切的要图,要不然偌大的中华民国,将要忘却本来面目了”[17]。保存古物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利用中国古代的物质资源,培育民众的民族认同、爱国热情,这也正是博物馆的功能之一。
在先农坛设立古物保存所,既是解古物失散之虞,也是为将来创办博物馆做前期准备,后来成立的“保存古物协进会”的章程也明确规定:“本会为筹办博物院之预备,暂时附属于古物陈列所,专事征求中国历史上应行保存之古物,以协赞陈列所之进行。”[18]可见,尽管“古物保存所”与“古物陈列所”的称谓有别,功能有异,前者重在收藏、保存,后者重在陈列、展览,但保存古物只是手段,展览古物才是目的。杭春晓经过考证也得出了1913年9月之前的“古物保存所”是“古物陈列所”的前身的结论[19]。可以认为,民国初年筹设的古物保存所正是古物陈列所的原始形态。
尽管古物保存所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但内务部选择在前清的祭神场所先农坛开办古物保存所,对皇家的帝王空间进行改造、开放,实质上也是为后来的博物馆空间的选址进行了探索。无论是教育部在孔庙设历史博物馆,还是内务部在先农坛设古物保存所,这些新型公共空间的创建实践都宣告了帝都北京空间秩序的解构,同时也预示了一种新型空间秩序的到来。
二 古物陈列所的成立
1913年12月,《内务部公布古物陈列所章程》的颁布标志着古物陈列所的建设迈入实质阶段,内务部以“我国地大物博,文化最先,经传图志之所载,山泽陵谷之所蕴,天府旧家之所宝,名流墨客之所藏,珍赍并陈,何可胜纪。顾以时代谢,历劫既多,或委弃于兵戈,或消沉于水火,剥蚀湮没,存者益鲜”,又“默查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馆之先导”[20]。内务部创建博物馆保存古物的努力也得到了民间舆论的赞同,在陈列所开放之前,有市民在《顺天时报》上发文表示:“保存古物一事,欧美文明列邦异常郑重,良以古代遗物非属历史名人所遗,即系昔时美术之特产,诚能加意保守,并公诸社会,任人观览,不独可助科学之进步,致美术之发达,促工艺制造之改良,且可使一般人民目睹本国特别发达之文明及数千年来先民所遗之手泽,其爱国思想自当油然而生。今世谈教育者,莫不首重社会教育,而古物陈列所实社会教育上一最重要之机关也。”[21]当时的舆论环境对于保存古物多持肯定态度,保存古物不仅有益于发扬中华文明,进而还可起到教育国人的作用。
另一方面,古物陈列所的创办也符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潮流,后期的管理者在回忆陈列所创办伊始时的形势时说:“我国为数千年文明古国,历代文物之所萃,品类最宏,举凡金石、书画、陶瓷、珠玉之属,罔不至珍且奇,极美且备。虽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特征,而宇宙神秘磅礴之气,固悉于斯而孕育包涵,此东亚天府之雄,所以早为世所惊羡也。惟数千年来囿于帝制,所有宝器,大都私于一姓,匿不示人。”[22]陈列所将前朝深藏宫内、私于皇室的古物开放展览,将封闭空间改为开放的公共空间,恰好顺应了由帝制向共和时代变革的大势,响应了共和与平等的新观念。
除了有利的舆论、文化环境外,这一时期发生的“热河行宫古物盗案”也促成了古物陈列所的正式对外开放。民国成立后,热河行宫管理逐渐松散,行宫内的古物经常被盗,更有管理人员监守自盗的情况出现,结果古物大量流失,以致北京的古玩市场也有大量的行宫古物出现。热河行宫古物盗案使民国政府认识到了保存古物的迫切,并决定将清朝存放于热河与沈阳清宫的古物都运至北京加以保存。1913年10月至次年10月,共经7次搬运,共从热河向北京搬运了1949箱,约110700余件,另有1877件附件。1914年1月至次年3月底,共经6次共运回古物1201箱计约114600余件[23]。
数量如此庞大的古物运至北京,如何存放旋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原来的古物保存所由于偏居城南的先农坛,位置偏远,影响力不足以辐射全京师,且原有的陈列空间有限,面对如此数量的古物显然已不敷使用。这时,“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明大总统,先后将辽宁、热河行宫所藏各种宝器,陆续辇而致之北京,派护军都统治格兼筹备古物陈列所事。指定就紫禁城外廷武英殿一部,先行修理,辟为陈列室及办公处”[24]。随着古物的陆续抵京,武英殿亦无法完全容纳,遂将陈列所扩至与武英殿相对的文华殿。
朱启钤将古物陈列所的地点选在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与文华殿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虑: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两处宫殿位于故宫内南部,与同期开放的中央公园相邻,都处在京城的核心位置,交通便利,将陈列所设立于此,有利于全城市民前来观览;就文化象征意义而言,武英殿与文华殿在明清两代或作为皇帝召见臣子之处,或作为祭祀之所,都象征着皇权的威严与帝制社会的等级秩序,将这两处作为陈列古物之处并对公众开放,开启了民国开放故宫的序幕,其意义远大于创办博物馆本身。
与中央公园开放时经费紧张相比,古物陈列所在筹办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经费短缺的问题,原因是经朱启钤与外交部协调,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出二十万元作为陈列所的筹办费用。当时的报纸报道了陈列所的创办进度:“工程由德国公司承办,费银六万元,其各殿墙壁梁栋一切照旧,惟窗门改换新式,分成内外两层,外层为菱花式,以绿色铁纱护罩,内层镶嵌玻璃,可以自由开闭;于武英、敬思两殿间加筑过廓一道,顶上□双层玻璃,光线可以从上方射下,非常明亮。”[25]经费充足是古物陈列所能在短期内顺利开放的客观原因之一,由此也可见民国政府对于开放陈列所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创办现代公园。
更重要的是,经过前期的舆论宣传,博物馆的保存古物与补助教育两大功能深入人心,因此,古物陈列所还在筹办过程中即受到市民的欢迎,有人在报上发文表示:“古物陈列所,由本年国庆日开放(即十月十日),听一般人民随意入览,数千年来秘密之宝藏一朝发泄,国民于精神上、实质上所得这利益,定非浅显。故吾人闻此不禁欣忭异常,并望朝野人士皆以国家公益为念,倘有家存古物者,从事取出,寄于陈列所中,则一般人民均受其赐,固不仅发扬国光已也。”[26]在政权更替、国运不稳的朝代背景下,古物陈列所以保存古物为出发点,以开启民智为宏旨,借此以达到培育国人的国家意识,在国势弱小、列强威胁的形势下形成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正是出于这层考虑,民国政府才将古物陈列所的开幕日期定为10月10日国庆日。
1914年10月10日,经过整修布置妥当的武英殿对外开放,标志着古物陈列所的正式成立,“于是我民族数千年文化生活之结晶,数千年精神所系之史料,如得荟萃保存,以公诸国人”[27],也有人称古物陈列所的开放“为我国数千年来开一公共览古之新纪元”[28],肯定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意义与价值。《申报》报道了开幕当天的情形:“昨,古物陈列所开始售入览票,下午二钟,览者纷集,……所列古物之多,美不胜述。然此尚为五分之一余,有每星期一易之说。……计昨售票已达二千有余。”[29]古物陈列所开放后,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文人到此参观,历史学家顾颉刚常常到此赏玩,据他回忆,“陈列所分两部分,文华殿里是书画,武英殿里是古代的彝器和宋以来的各种工艺品。我们进文华殿时,顿使我受一大刺戟。这里边真有许多好东西,尤其是宋代的院体画和明代的文人画,精妍秀逸之气扑人眉宇”[30]。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也常到陈列所观摩,查阅周作人的日记,古物陈列所出现的频率颇高,1917年10月7日“入东华门观文华殿书画,又游承运、体元二殿,出西华门”[31];同年10 月30日,“霞乡亦来,同至东华门观文华、武英两殿陈列,出西华门返寓”[32]。一月之内,周作人就两至陈列所,可见,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古物陈列所的开放,为他们研习古董、赏玩古物提供了新的去处,新辟了一种交往、娱乐空间。
从古物保存所到古物陈列所,回顾民初北京创办公共博物馆的历程可以见出,推动北京近代博物馆创立的力量,除了保存、利用北京既有的历史文物的现实因素外,更重要的动力还是北京当局对于寄希望于博物馆来教化市民、开启民智的推动。有学者就指出,“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国民教育成为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国家往往利用空间对民众进行身体与心灵的塑造”[33]。民国初立,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新的国家认同,培育新的市民阶层与民众精神,这种异于帝制时代等级秩序的新型社会理念,在开放式的公共空间中可以得到有效的培养,特别是经过改造后的北京帝王封闭空间,在开辟为现代公共空间后,在教化市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三 作为一种新型公共空间的意义与局限
开辟古物陈列所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与天安门广场改造、开放皇家禁苑一样,在民国初年的北京践行着开辟现代公共空间的努力。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打破了旧时皇家庙堂广场的封闭模式,变成了群众集会的公共广场。中央公园将清王朝的社稷坛开辟为市民公园,亦是构建公共空间的努力,使原来皇家的祭祀场所转变为市民的公共交往空间,丰富了北京市民的娱乐、生活空间。相比之下,因为紫禁城地位的特殊性,古物陈列所的开放因而具有更加厚重的政治文化意义。台湾学者宋兆霖亦指出:“民国肇兴,清室退位,北洋政府随之将紫禁城前朝开放,使帝王宫禁、私府琳琅终得公诸于世,不仅深具反对封建帝制复辟势力之政治作用,尤富以逊清离宫所藏希代之珍为全民所共有共享之文化意涵。”[34]古物陈列所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像其他博物馆一样,“从早期私人的、受控制的、排外的社会空间中分离出来,经过重新设计,进而成为具有培养人们文明行为功能的组合空间”[35]。古物陈列所之于北京的意义,并不在于保存了多少历史遗产,而在于打破了昔日由皇家所专享的紫禁城的封闭空间,在政治层面消除了因空间管制而形成的社会阶级差异,使共和制度在北京城市空间中有了物质层面的体现,使广大市民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了阶层的平等。
然而,古物陈列所开辟的现代公共空间又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民国政府在当时还不能完全无视清室的影响,而且当时的北京社会仍涌动着一股复辟的风潮,北洋政府为避免刺激仍居宫禁的逊清皇室,在处理古物陈列所开放事宜时比较低调,没有大肆宣传[36]。作为对清室的妥协,北洋政府任命了一位满人担任古物陈列所的首任所长,而这位所长的名字也出现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公布的《引见大臣签》中,并被封为“厢红旗蒙古都统”,因而有学者认为:“古物陈列所的形成并不是革命的直接结果,而是辛亥革命的妥协产物——《清室优待条件》的一个变种。”[37]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古物陈列所从诞生之初就成为多种政治力量交织的场所,使其承载了多重的社会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古物陈列所的运营不得不采取低调进行的策略,无形中限制了陈列所的社会影响力。
与此相关,古物陈列所对外收取高昂的门票费用,“每张售价大洋一元”[38],文华殿开放后,“武英文华两殿游览券各售大洋一元”[39]。顾颉刚对这种高票价就表示不满:“在这生计枯窘的时候,定出这样贵的票价,简直是拒绝人家的进去。”[40]而同期开放的中央公园的门票则为每张一角。据孟天培与甘博对1900年至1925年间北京普通工人家庭收入的调查,一名普通手艺大工的日工资不到四角,而小工则不到三角,收入中仅有5%的杂费用于交通、医疗、教育、娱乐等支出[41]。陶孟和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48户家庭的生活费用调查也证实,被调查的家庭仅有3.1%的支出花费在社交、教育、娱乐等项上[42]。对于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中央公园一角的公园门票他们都难以承担,更何况大洋一元的陈列所门票?从实际生活来看,尽管人们逛公园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参观陈列所的次数,但即便如此,高昂的票价还是严重影响了人们进入紫禁城参观陈列所的意愿。《顺天时报》中的一篇报道证明了这一事实:“救国储金团上次在中央公园开会时,莅会者甚众,故有由该园西北地方新建之桥,径至古物陈列所前,嗣因观览券甚昂,致多扫兴而回,故经陈列所定于今日将展览券减收半价,俾免望洋兴叹之感云。”[43]但门票减价并没有成为常态,即便陈列所的门票按半价收取,普通收入的民众仍不能承受。
因此,除了开放之初几天的热闹之外,古物陈列所在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门庭冷清。尽管陈列所也制定了优惠政策,但也只面向“制服完整之国内军人、国内各学校团体与由外交部专函介绍或经内政部准予优待之外国人士或团体”等特殊人群[44]。而庄士敦也证实,“1916年以后,宫廷博物馆里的贵重物品就一直使成千上万的从世界各地来的参观者感到惊奇和兴奋”[45]。古物陈列所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对吸引外国游客前来猎奇的效果。
自1919年起,除业已开放的武英殿、文华殿外,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开始偶尔接待外宾,有时也举办赈灾会等特殊活动,为三大殿的正式开放做了前期铺垫。1924年,冯玉祥授意其部下鹿钟麟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宫禁,整个紫禁城均归民国政府所有。1925年8月,古物陈列所向内务部申请正式开放三大殿:“查本所存储各项物品,向在文华、武英两殿选择陈列,供人瞻览,酌收券价,藉以补助经费。近因整顿所务,月支日增,开支不敷甚巨,自非另筹办法扩充售券地点殊不足以增收入而资挹注。拟将向来不能陈列之重大物品分别在太和、中和、保和各殿布置陈列。”[46]自此,古物陈列所的范围将三大殿囊括在内并对外正式开放。

图一// 古物陈列所全图(采自北平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专刊》,1934年)
1925年10月10日,民国政府在溥仪原来居住的宫禁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即从乾清门往北至神武门一带区域,开放御花园、后三宫、西六宫、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增辟古物、图书、文献等陈列室任人参观[47]。这样一来,紫禁城内就有了两个博物馆:南部是由东部的文华殿、西部的武英殿与中部的三大殿组成的古物陈列所,北部是由原先的皇宫区域构成的故宫博物院(图一)。自此,整个紫禁城基本全部开放。
古物陈列所的开放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创办博物馆与保存国粹、启蒙民智之间的密切联系,博物馆的倡导者与创办者都寄希望于通过展示中国的历史遗产来达到培育国民爱国精神的目的,这显然比西方博物馆提升“市民的心理与道德健康”[48]的目标更为实际,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中国的第一所官办博物馆以古物陈列所命名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仅收藏古物也有悖“博物”的实质,鲁迅在古物陈列所开放后即前去参观,也认为不过是“殆如骨董店耳”[49]。更有人明确指出,古物陈列所中的物品“无一属于国民之壮史,表尚武之精神者”,而外国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有关于工商实业者,亦有关于军事范围者,如爱国男儿之手迹,敌人炮弹之零星”[50],都未能收藏,这可能是因为,近代中国工商业落后与屡遭列强欺辱的现实使博物馆的主办者不得不从中国古代历史遗产中寻找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慰藉,并以此作为激发市民爱国精神的手段,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公共博物馆“博物”的性质。
无论是古物陈列所还是故宫博物院,这两个从空间上平分了紫禁城的现代公共机构在开放后都收取高昂的门票费用,将广大收入低下的平民挡在紫禁城门外,因而,紫禁城的开放“徒有开放之名,而无开放之实”[51]。如此一来,紫禁城在经过了民国政府的努力之后,实际上只是向那些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上层人民与外籍人士开放,“实违共和原则”[52]。因此,当查尔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尔德(Charles Partrick FitzGerald)回忆其1924年进入紫禁城的情景时就感到了巨大的落差:“我从长安街步行到天安门,然后参观了那些宏伟的宫殿。如果现在参观故宫,你会淹没在中外游客巨大的人流里。可是那一天我只付了微不足道的入场费(大约6个便士),便圆了游览这座心仪已久、金碧辉煌的宫殿的美梦。我发现参观者几乎只有我自己。故宫里既没有导游,也没有外文写的说明,告诉参观者,你是在什么地方,或者看到的是什么。觐见皇帝的宫殿依然挂着小小的牌匾。那些牌匾始终是宫殿的装饰。事实上,一切都没有变,变化的是只是皇帝不在这些宫殿里临朝理政了。故宫的这一部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座博物馆。”[53]
因此,民国政府将紫禁城开辟为现代公共空间之后并未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古物陈列所的创办者对这一新型公共空间寄寓了特殊的政治目的,他们“热切地通过提供公共空间促进新市民的形成,于是城市里出现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厅,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培养新的公共精神和国家意识”[54];同时,他们又通过经济手段将多数平民阻挡在紫禁城的门外,限制了其公共性的生长。结合民初北京政府开放紫禁城的实践来看,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内开办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开辟现代公共空间,而是借开启民智、培育国民爱国精神之名来打破紫禁城的封闭状况,从城市空间结构上改变帝都北京的等级格局,以体现民国政权的优越,这才是开放紫禁城的目的所在。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就抹去创办古物陈列所的历史文化价值,在社会变革、观念更新之际,古物陈列所的创立与运行,虽然承载了特定的国家意志与教化功能,但客观上也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彰显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与国家观念。古物陈列所开辟现代公共空间的努力及其构建公共领域的局限,也折射出近代北京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与曲折。城市空间的变迁表征了社会、文化的变化。
[1][45]〔英〕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23、240页。
[2][36]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3][47]傅连仲:《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
[4]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5][37]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124页。
[6][7]张謇:《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划条议》,《张謇全集》(第四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0、281页。
[8]陈志科:《蔡元培与中国博物馆事业》,《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4期。
[9]秦素银:《蔡元培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4期。
[10][12]《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5、275页。
[11]《教育总长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并大总统批》,《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13]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语丝》1928年1月第4卷第7期。
[14]《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1912年10月1日)》,《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8页。
[15]《先农坛游览十天》,《正宗爱国报》1912年12月27日。[16][49]《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137页。
[17]《存古》,《正宗爱国报》1913年1月6日。
[18][20]《内务部公布古物陈列所章程、保存古物协进会章程令(1913年12月24日)》,《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0、268-269页。
[19]杭春晓:《绘画资源:由“秘藏”走向“开放”——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民国初期中国画》,《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21][26]《保存古物》,《顺天时报》1914年10月3日。
[22][23][24][28]北平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专刊·绪言》,1934年,第1、4-5、3、4页。
[25]《古物陈列所订期开幕及其内容》,《大自由报》1914年9月30日。
[27]原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旧都文物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29]《陈列所与社稷坛游览记》,《申报》1914年10月16日。[30][40]顾颉刚:《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宝权园文存》(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第179、182页。
[31][32]《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699、704页。
[33]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34]宋兆霖:《中国宫廷博物馆之权舆——古物陈列所》,台湾“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71页。
[35][48]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24, 18.
[38]《陈列售票》,《群强报》1914年9月12日。
[39]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游览指南》,1932年。
[41]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第56、87页。
[42]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37页。
[43]《陈列所之减价》,《顺天时报》1915年5月23日。
[44]《修正内政部北平古物陈列所规则(1929年9月)》,北平古物陈列所编《古物陈列所二十周年纪念专刊》,1934年,第108页。
[46]《古物陈列所1914~1927年大事记》,故宫博物院藏《古物陈列所档案·行政类》第39卷,转引自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50]《最古之陈列所》,《群强报》1916年1月4日。
[51]《故宫参观须改善限制》,《顺天时报》1926年2月3日。[52]《故宫博物院索钱》,《顺天时报》1926年2月10日。
[53]〔澳〕C.P.菲茨杰拉尔德著,郇忠、李尧译:《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4-35页。
[54]〔美〕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责任编辑:黄洋;校对:王霞)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and the Opening of Beijing’s Public Space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WANG Q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11)
Abstract: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Guwu Chenlie Suo) in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early time of the Republican Era reflected the social trend prevailing in China at the time that ad⁃vocated reviving China by education and culture. It also reflected the Beijing government’s endeavor to en⁃lighten the public by creating public spaces. The Institute wa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t deconstructed the previously closed space in the Forbidden City, created new type of urban space for the public, and provided the new site and channel of recreations for the citize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charged a high price for the entrance ticket, which restrained the publicity of the Institute.
Key words: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Guwu Chenlie Suo); open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public space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07
作者简介王谦(1982-),男,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文化、城市史。
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般研究项目“近代京津城市空间变迁的比较研究(1860—1928)”(编号:ICS-2016-B-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国家文化中心建设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设计”(编号:12&ZD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