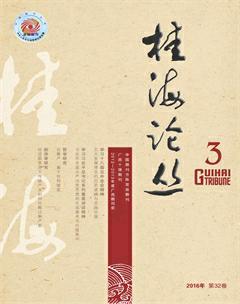感恩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实践的内在驱动力
2016-06-24许建良
许建良
摘 要:如何才能切实有效是对道德建设反思的最重要的问题。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实践也一样,不能再在无效益意识的泥潭里斡旋。人类文明发展实践的历史经验证明:感恩是一个有效的切入口,它连接着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恩是一个链,包括施恩、受恩、知恩、感恩、报恩;这一链本身就内置着能源补充的机制,受恩、知恩、感恩是动力源;这一能源补充机制无疑又为承扬实践的切实运行设置了切实的动力。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徳;施恩;感恩;报恩;恩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3-0041-10
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撞击的同时,我们也无不感到道德危机的冲击,尤其是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著称,由此而来的心理反差自然更为剧烈。就人类文明史而言,道德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必然的联系,换言之,高道德水准必然需要较高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但是,就道德本身而言,它并非是人的天生的产物,而是人类进化的后天成果,即是人的社会化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可以教化的,人是需要道德的。这就给社会倡导一定的道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职责。当然,社会提倡的道德能否变成人的素质,是社会道德建设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实践中,最为重要的不是确立中华传统美德的德目,而是承扬实践的有效性,这是我们在道德危机面前应对危机的最为现实的举措。因此,在道德建设上,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为此,我们的观念需要彻底改变。换言之,就是要创新,不能在习惯的思维框架中徘徊。解决承扬实践内在驱动力的问题,就是如何具体化的问题,答案之一是就是感恩。
一
一般而言,感恩并没有成为我国文化的传统。湖南省醴陵市退休老人陈自绪10年(2000-2010)为154名贫困大学生联系落实资助,他希望受助学子入学后能寄张照片给他,10年中有78人寄来了253封信,这些信件老人保存完好。从时间的维度而言,给他来信的人数越来越少;在总体上,只有40%的学子给他来过信。尽管老人准备好了空信封,以及为人处事的材料,从心底想教他们如何解开心结,知道表达恩情,懂得感恩,学会做人,但无情的现实是,老人的梦无法得圆①。这一现实问题的产生虽然可以归结为不同的原因,诸如道德教育的问题、家教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等等,但这些回答都没有反映这一现实问题的本质,或者说都没有准确地诊断出这一现实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因为教育有许多方面,有许多问题,如果仅仅笼统地用道德教育问题来加以概括的话,无疑是对现实问题的搪塞,缺乏科学的态度和举措,这也正是我们现实道德建设出问题的通病所在。我们如果对这一现实问题稍加仔细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感恩教育的缺失无疑是其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要回答感恩为何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在驱动力这一问题,首先要理清何谓“恩”的问题,离开这一基点,就难于找到正确的答案。
众所周知,在词源的意义上,“恩”字由“因”和“心”组成,是形声词,从心、因,因亦声,本义是好处、恩惠,惠泽、惠和、惠爱、惠握(恩惠深厚)、仁惠、实惠都是基于“好处”而来的词汇,《说文解字》对“恩,惠也”的解释,指的就是好处。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对仁义礼智的理解,虽然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对其的重视却是一切学派表现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仁义礼智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不是孤立分离地存在,而是互相联系的文化因子,在共作中产生最大的效应。诚如《礼记》所说:“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礼记·丧服四制》)[1]1694下这里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仁是恩,道家庄子的“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庄子·天下》)[2]1066的论述,显示的也是相同的特征。二是恩是一种情感。通常所说的“恩情”这个词汇,就是把“恩”作为一种情感来衡量的。法家管子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管子·形势解》)[3]1167里的“无恩”,就是无情的意思;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非常重视恩,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韩非子·用人》)[4]205“上下之恩结”就是在情感的维度加以的立论;另外,他还直接使用“恩爱”,即“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韩非子·六反》)[4]418。这里的恩爱自然是情感的代名词,法家韩非推重对恩爱之度的有效把握,主张不能溺于恩爱的泥潭之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方面②,在下面要分析的“恩义”问题会进一步展开。
从文字的特征上来认识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思想的关键,而以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思想的话,就完全是本末倒置之举了。日本的文字是借鉴中国的,日本人对一些思想问题的认识,其实也是本着中国文字本有特征来进行的。就“恩”而言,日本的思想家也正是从词源的意义上来认识和界定的。丸山敏秋说:“心与因加以组合就成恩。由于‘因在日语里具有寄托、允许寄托的意思,所以,允许把心寄托于他人就是‘恩的字义,并使它具有了恩惠、怜悯、慈悲、慈爱等的意思。‘めぐみ(惠)是从草木发芽而来的概念,意谓冬眠草木的生命力在阳春之晖的照耀下,萌芽并茁长。某物给予他者生命,帮助生命的善行就是恩的施行,从受恩这一方来看,就用感恩之情、报恩之行来表达。反顾我们的生活,‘人在字形上就是两个人互相依凭支持而生的存在,从生到死,即使一日一刻,都无法离开他人和他物的恩惠而存活。”[5]54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知,恩在恩惠、好处的层面,一般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不能机械地偏于一隅。但是,“‘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6]70。在此可以看出,恩一旦成为事实,就说明产生恩的行为已经结束,恩无疑是恩行为带来的自然的果实。在行为链的层面,恩首先在恩行为带来结果的接受者那里得到彰显,在这个意义上,恩就是一种负债,你接受了他人的好处或恩惠,自然也欠下一份情谊。
二
在分析了“恩”以后,再来看感恩就比较容易了。感恩在词义上就是对他人给予的恩惠、好处的感谢、感激。感恩一词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词汇,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成玄英的《老子义疏》,这在马叙伦的《老子覈诂》中可以得到印证。马叙伦说:“各本作‘以战则胜,卷子成疏作‘以陈则胜,旁改‘陈为‘阵。譣弼注上文‘一曰慈曰:‘夫慈,以陈则胜。是王作‘以陈则胜,当从之。成疏曰:‘以大慈之心,临于战陈,士卒感恩,所以胜捷。疑成亦作‘以陈则胜。”显然,感恩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缘由,如“士卒感恩,所以胜捷”。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感恩也非常重视,他说:“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新民说·论公德》)[6]214
上面分析时曾提到,法家韩非强调把恩爱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换言之,恩爱不能任意抒发。对此的辨证,是感恩生发正效率的关键。众所周知,在恩为情感的层面,情感始终存在逾越本有轨道的可能性,一旦逾越轨道,恩就会变成怨或恨。从恩怨这个词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恩怨就是感恩之情与仇怨之情,或恩惠和仇恨。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既同属于人的情感,又是人的情感的不同方面。但怨恨显然不是平常人的正能量,试想,一个内心充满仇怨之情的人,自己与他人始终处在两个相悖的域场,而不是相同的场域。因此,自己与他人是对立的,而不是协调的存在,这在认识上始于自己与他人相分离的基点,而不是相联系的出发点。这一认识无论是在形上学理的层面,还是在形下经验的境遇,都是片面狭隘的,自然无正确性可言。因此,在相互联系的视域里,个人与他人是互为条件的存在体,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人,不能把自己置于与他人相对立的境地,必须与他人协调共作以追求生存的最大空间。在这一前提下,如何抑制或化解、避免仇怨之情的产生,就成为个人实现和谐生活的最大课题,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利益的实现。这就要求对恩怨进行调节,抑制仇怨可以给恩爱腾出最大的生存空间,以满足实现和谐生活的需要。
在现实的生活层面,仁恩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是儒家的特征,《庄子·天下》的运思自然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但在儒家的思想维度,仁昭示的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而首先主要是血缘维度下的人际关系。诚如孟子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27》)[8]183如是,儒家维度的仁义礼智的侧重点就在血缘关系之中,其区别自然也是在这一前提下产物。基于此,“理,义也”的出台才有了现实的基础,用理则来制约义,正是在仁义礼智互作轨道上有效制约“恩”的举措。这一推论为“仁,内也;义,外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六位》)[9]171所证实。仁的内主要就是侧重在血缘关系层面而立论的,义的外则是侧重在外在人际关系视域里的考量,这是对血缘关系狭隘性的突破;在血缘关系里的实际治理中,恩总是占有主要的位置,起主导的作用;外在人际关系里的治理则正好相反,具体秩序的整治必须依归义来进行,恩仅在次要的位置上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运思在后来得到了贯彻,“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1]1695就是佐证。
恩的血缘性的特征,无疑昭示着恩必须在一定的规则的制约下运行,不然容易偏于血缘性的轨道,而血缘性与社会性是相矛盾或存在对立的,这也是道家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13章)[10]22的意义所在。仁是偏于血缘一隅的存在,“不仁”则是逾越血缘一隅而趋于公正无偏的存在。由于恩怨同属人的情感,人作为具有七情六欲的生物性存在,不可能没有仇怨之情。问题是恩怨之间,虽然不是完全用恩情取代仇怨,但以恩情为主轴来调节恩怨,从而给予恩情以最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和谐人生的起码要求。基于这样的理解,就有必要把恩情控制在一定的维度,超过具体的度就势必给仇怨的产生孕育可能的条件。正如庄子所言:“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庄子·秋水》)[2]574大人作为一种道德高尚的人格,其要素之一就是“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这里可以理解为前后互为条件的句子,意思是“不多仁恩”是不害人的具体内容,不害人就要落实在“不多仁恩”上;“不多仁恩”的意思是仁恩不能太多,要恰到好处,不能让恩情任意流淌。
这一运思在法家那里就是要“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韩非子·饰邪》)[4]366由于恩是血缘关系里的情感,属于私的范畴,所以它与法制属于公的域场里的规则是不同的。就一个社会而言,社会事务的有条不紊,在于人们对法度的遵守,也就是法制的落实。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明法制,去私恩”,这是“公私之分”的表现。“去私恩”显然不是去掉“私恩”,韩非重视的是公私之间的分际,而不是以公来取代私,公私是互为条件的存在,因此,“去私恩”的“去”当理解为远离,这显然是制约恩情的一种方法。
其实,在中国思想史上,对恩情的调节是思想家们都重视的,可以以荀子的运思为代表来进行总结:“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11]491-492是如,仁义礼乐的和谐运作才是社会有道的保证。就仁而言,虽然上面提到“恩,仁也”,但这不是必然的关系,其中存在一个如何符合理则的中介环节,“推恩而不理”就无法达到仁。换言之,恩一定要符合理则,这就是对恩情这种最初偏于血缘情怀的情感的一种有效的制约,既在人的情感世界给予了适当的位置,又设置了具体活动的疆界。这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感恩不是绝对个人私情的表现,必须兼顾社会的理则来行为,这无疑为感恩生发积极的正价值设置了最好的境遇考虑。
三
感恩作为对外在他者表达感激、感谢之情的行为,行为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有效性的确定,无疑是感恩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在上面对感恩之恩界定以后,这里要解决的正是恩的基础的问题。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来思考恩产生的基础。
(一)自然
自然是恩产生的第一基础。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价值的基础在自己是宇宙万物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个观点与另一个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是完全相反的,显然,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运思。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中心主义的运思,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的成功,得到畸形的发展,带来的自然结果无疑是人类目前面临的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疏离这三大危机,人类已经进入了与自然互相冲突的境遇。这一境遇要求人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来修补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文明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敲响幸福之门的前奏,离开这个前提,人类无幸福可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天人的关系,虽然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的总体特征,但在不同的思想学派那里,合一的方法论考虑的差异是明显的。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正是在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调的背景下,20世纪末西方学者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道家哲学的世纪”的警世性运思,而这主要就在于道家思想中的宇宙万物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2]79的运思。中国思想中的宇宙这一概念,虽然始于庄子③,但实际在老子思想中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可以在“事实上,道家将‘宇宙(cosmos)理解为‘万物(ten thousand things),这意味着,道家哲学根本就没有‘cosmos这一概念。因为,就‘cosmos这个概念所体现的统一、单一秩序的世界来说,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封闭和限定了的。就此而言,道家哲学家基本上应算是‘非宇宙论思想家”(《哲学引论》)[12]17-18的述论中得到答案。
重视“万物”,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的问题,而是包含着一种价值追求、一种理念。因为,“万物”是道家的标志性概念之一,这在儒家典籍《论语》那里无法找到,《论语》仅仅只有一次提到“百物”④。总之,人类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域场,离开自然人类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从人的基本生活的必需品(诸如空气、水、阳光)到粮食、矿产等等,人类基本完全依赖于自然,这是无法逾越的。虽然人类在有些方面虽然可以依靠理性的发明来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但无法替代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现今回归自然以及自然物含金量的提升的生活现实本身就是无声的回答。所以,自然是人类的最大的恩惠源,感激、感恩自然应是人类的最为基本的诉求和心理欲求,诸如日本的民风中,日常的一日三餐,在吃饭前首先要举行感谢自然给我们带来的恩惠、给我们这样的美餐的简单仪式,然后动筷子用餐,这就是对自然的感恩,获得食品成为自然之恩。
(二)本性
宇宙世界中的万物虽然都有着相同的物质特性,但各自的本性是不同的。不同物类的延伸都有着自己的家族史。在微观的层面,万物都有过从何而来的问题,换言之,万物不是天生的,诸如胚胎生的万物,都是经过母体怀孕而生的,人就是经过母亲10月怀胎而生的,没有父母的养育就不可能有一个新生命的出世和成长,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是儿女的恩人,前面强调的尽孝在这个层面,实际就是一种感恩。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强调的就是对父母的感恩;藏族谚语的“父母之恩,水不能溺,火不能灭”也表达了对父母感恩的重要性。“‘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而且指他对母亲所欠的一切,包括襁褓时期母亲的哺育照顾,孩提时期母亲所做的牺牲以及成年后母亲为他所作的一切,总之,包括母亲在世时对她所负的一切恩情。”[6]70
对父母感恩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行为要求,一个对父母都不存感谢之情的人,不可能指望他对社会他人心存感恩,可以说对父母感恩是人生首要的课题之一。
人与其他动物的本性是相异的,即“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11]164“义”就是外在的规则,即依据外在的规则来确定大家的职责。因此,有规则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在。正如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说:“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人人尽此义务,则子愈多者,父母愈顺,家族愈昌;反是则为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负者,谓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义,尽人能知者也。”(《新民说·论公德》)[7]661
以上主要是血缘之恩。
(三) 社会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生物特性决定人必须过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人都肩负着各自的社会职责,这些社会职责组成一张无形的网络,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就社会关系而言,人无时不在接受着社会的恩惠,诸如接受教育就存在师恩,接受职业训练也有师恩,没有老师、师傅的育养和引导,一个人无法走上人生的征程并创造出人生的社会价值,描绘出最为美丽的人生图画。对老师、师傅的感恩是绝不可少的,每年9月10日教师节的确立,正是在社会的层面为人际之间的连接确立了法定的保证和支持,这不仅我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老师、师傅,也自然有恩惠的存在,由此而来的感恩的必要性也是必然的。对此,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对老师、主人负有特殊之恩。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自己有恩,将来也可能在他们有困难时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恩情越重,形成一种利息。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就象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一个重负,通常认为,‘恩情的力量常常超过受恩者的个人意愿。”[6]71
恩惠渗透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基础。在恩的台阶里,国家之恩居于最高的层次,每个公民都受到其国家的保护,没有国家的保护,个人的一切权力、权利以及福利就无法得到保障,而离开这些,个人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前提条件。在国内是这样,到国外旅游、留学等也是这样。在世界的舞台上,虽然有联合国负责协调所有国家之间的事务,而且也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存在的国际人道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增大而加深,所以一个国家经济能力的强大,并非与其能够无条件履行人道主义义务的行为相统一,这是人类本性的现实存在。而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正义实现的程度远非人自身的情感所能容纳和满足。国际事务的无形规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对自己国家公民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直接左右着其公民在世界上得到的尊敬的程度,以及得到公正待遇的程度。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自己的国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笔者视国家之恩为最高之恩的原因所在。在感恩的事务中,感恩国家自然是我们每个人最为重要的义务,感恩也是爱国行为的具体落实。如果只是单一地提爱国,而不讲爱国的理由——国家的恩惠,不讲感恩国家,那么讲爱国就会成为空虚或无用的口号,很难被民众所认同。对个人而言,听到爱国仍然不知所措,而感恩就非常具体,就是你对国家的感激之恩、感激之情。感激自然也不是抽象的承诺,而是具体的行为,所以,感恩国家必须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落实,诸如不破坏公共财产、每年植一棵树(包括后续的管理)等。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过,“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新民收·论公德》)[1]215显然,感恩社会、感恩国家对个人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公民必须具有的素质。
正如上面所论述的那样,恩产生的基础在自然、本性、社会,这是互相联系的方面,它们既是恩产生的基础,也同时构成恩的种类图谱,这些都是人需要感恩的方面。
四
在回答了恩产生的基础以后,紧接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感恩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驱动力的问题,这是本文现实价值的关键所在。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视角来考察。
(一)“恩”在词义学上所展示的广普性
“恩”字的下面是“心”,而只要是人就在生物的意义上持有心,它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情有义。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恩”的载体,这是词义学上昭示我们的“恩”所具有的广泛性。在内在的意义上,由于恩的上面是“因”,下面是“心”,因此,“恩”因心而生。换言之,“恩”因人而生,这是人恩超越一般其他动物之恩的本质所在。由于“恩”因心而生,“恩”一旦产生,同时成为心之“因”,“心”必须有所依靠,这是“心”的一种具体的落实,如果没有依靠,就无法感到踏实,不踏实就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因此,“恩”就成为人心的依靠,而人之“恩”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心”的功能的内容,孟子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6》)[8]80,不失为一个绝妙的回答。换言之,“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21》)[8]30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人而言,“恒心”(《孟子·梁惠王上7》)[8]17、“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2》)[8]61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仁义的建设上,孟子虽然认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从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31》)[8]337也就是说,人都有不忍心之处,把它推及自己所忍心之处,就是仁;人都有不去做某事的理由,把它推及自己做某事的理由,就是义。人能扩充不想害人之心,仁就用之不尽了:人能扩充不挖洞跳墙即按规矩做事之心,义就用之不尽了。
必须注意的是,“恩”为心的依靠,或者说,“恩”是心得以舒展自己活动领域的生态条件。就个人而言,心的活动不仅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而且也是人健康生活的起码条件。
(二)他人优位性的倾向
众所周知,虽然在词义学的层面,“人”的字形就代表着两个人互相倚靠而成的一种态势,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的互相依存性,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威力,这是在字形上告诉我们的故事。在人类文明史的维度,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出现,表面上显示出对人类事务的关注,但实际上忽视了如何关注才有效于人自身的生活的问题。在最终的意义上,人类无法在自己的领域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必须依赖宇宙的万物世界的存在才能得以衡量。万物在各自的物类世界里无疑运用属于自己的语言来进行沟通,人类虽然无法在非常普遍的程度来精通其他物类的语言,但人类作为灵性的物种,必须明确一个事实,尽管自身具有巨大的能力,但人无法左右宇宙世界,人类只有在与其他万物和谐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自己的和谐的乐园;宇宙是依存性的,是相互依靠的,万物只有在宇宙整体的平衡和谐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确认自己的价值。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的魅力有两个方面,即“中国人是讲求实际的,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意识,他们的所有哲学流派都以某种方式关心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道德标准和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方面。与之互补的,还有带着中国特点的对应于神秘主义的方面,它要求哲学家们超越人间俗事和日常生活,并且以达到更高级的思想意识为最高目标。这就是圣人的思想意识,是达到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的中国贤哲的理想”[13]91。这种神秘主义的魅力,也正是西方人把21世纪看成道家哲学世纪的关键所在,因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主要流派……都认为宇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为基本。因此,任何一个部分的性质都取决于所有其他部分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一个部分都‘含有所有其他部分,对于相互包含的这种想象似乎的确是对于自然界的神秘体验的特点。奥罗宾说:‘对于超思维的意识来说,没有什么真正是有限的,它所依据的是对于每个部分都包含着全体,而又在全体之中的感知。”[13]281
关于部分与全体关系的认识,大乘佛教华严宗的《普贤行愿品》里所讲述的朝山进香者苏达那的故事,最为生动形象。在苏达那看来,“宇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美网络,其中一切事物相互作用的方式都是每一种事物中皆含有其他事物。铃木大拙意译的这部佛经中有一段用一座壮丽的城堡形象来表达苏达那的体验:‘这座城堡像天空一样的宽阔广大……在这座装饰华丽的城堡里还有千百座高楼,每座高楼都像主堡本身一样的装饰华丽,像天空一样的广阔,所有这些数不清的高楼全然不互相妨碍,每座高楼都在与所有其他高楼完美的协调中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存在,这里没有什么妨碍着一座高楼与所有其他高楼单独地或者集体地相融合;存在着一种完美的混合,而又极为有序的状态。年轻的朝山进香者苏达那看见他自己既在整个城堡中,又在每一座高楼中,其中每个部分都包含着全体,而又在全体之中。”[13]281-282人类与宇宙万物是互为依存的,个人与他人也是互为依存的,自己的价值必须在他人那里得到确立,老子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显示的就是一种先有人、后有己的他人优位的价值取向,这也就是我一贯强调的道德的本质在“目中有人、心中有他”,这既是恩产生的起始点,也是感恩的首要环节。其实,这一运思也是中国整个思想的特征之一,诸如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35》)[8]339,体现的也是这种思想倾向;寡欲是人我关系上的一种节俭,实际上我们不能仅仅在自身人格提高的方法上来加以理解,在人际关系的维度,显然自己节俭就包含着对他者的考量,这是必须注意的方面。
总之,从感恩的对象都存在于个人的外在而言,恩本身也是先从他者考虑的结果,感恩可以说是道德本质在实际生活里的体现和贯彻,是使道德产生现实力量的最为关键的方法。
(三)感恩不是孤立的因子,而是一个内在链
把感恩作为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在驱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就是感恩不是一个单一的环节,它本身就有一个环环入口的链,能够自动补充能量。在行为学的层面,感恩则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一般而言,在行为的主客体里,行为主体把自己的“心”寄托给行为客体,对行为主体而言,借助客体可以释放自己的内在能量,这就是施恩的行为;对行为客体而言,则是受恩行为。行为主体的行为能否最终完成,关键取决于行为客体的态度,只有当行为客体允许行为主体把他的“心”寄托给自己时,“恩”才能完成自己的价值实现。因为,一旦接受行为主体的自觉自愿的要求,就意味着行为的主客体之间在道德的世界里,织成了一个特殊境遇里的特殊关系链,关系者也自然地步入了一个恩的世界。此时,任何一方都无法一厢情愿地终止这个关系链,一旦强行终止,乃就是绝恩,势必受到道德的负评价。所以,施恩行为、受恩行为的成立是以人的自觉选择为前提的;在恩的世界里,随着主客体的不同,自然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恩”。
在现实层面,施恩与受恩是在非常自然的条件下进行和完成的,诸如以血缘本性为基础而生发的恩,对父母亲族之间的恩情,往往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当事人而言,无所谓感恩与否。感恩行为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就在于对自己的受恩要有自觉的认知;在血缘关系之外也一样,“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说苑·复恩》)[14]159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施恩虽然不在扬名即“贵不德”,这与老子“上德不德”的运思非常相似,受恩一方最为重要的是考虑回报的具体方法,但是,切实的回报必然要依赖知恩,即对受恩事实的自觉认识。具体而言,就是要知道自然的滋养之恩、父母的养育之恩、社会的哺育之恩、国家的培育之恩,这是总体的认识要求。有了这样的素质,面对外在他者的施恩行为,自然会在受恩的行为实践中,产生知恩的意识。
知恩是感恩的前提,一旦完成知恩,就为感恩奠定了情感的基础。感恩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对施恩者行为表达的感谢、感激之情。这一环节自然也就过渡到了报恩的阶段,因为,感谢就是回报、报答。不过,在此要注意的是,感恩、报恩行为最为重要的支点,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施恩的行为,这无疑可以避免由情感狭隘性带来的短视的局限所发生的几率,实现在最大的程度上对社会行为的正价值的评价。对人而言,报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语言中有“知恩图报”的成语,“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故复于彼,非程婴则赵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说苑·复恩》)[14]179这里的“复于彼”就是报恩的意思,把别人行为给你带来的好处用自己的行为返回给他者,不然就是忘恩。诸如“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制丧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也”(《说苑·修文》)[14]674,说的也是这种情况。当然,“制丧三年”等带有封建时代的浓厚的痕迹,在今天是不可取的,但报父母之恩本身仍然是稳固家庭和社会所必须的。报恩是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如果没有报恩的环节,社会将会走向混乱。“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蟨,前足鼠,后足兔,是兽也,甚矣其爱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必啮以遗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见人将来,必负蟨以走。蟨非性之爱蛩蛩巨虚也,为其假足之故也;二兽者,亦非性之爱蟨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行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源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源基,由不报恩生矣”(《说苑·复恩》)[14]159,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这里说的君臣之间的报恩,在今天就是公民对国家的报恩,这也是必须注意的方面。
在人的恩的世界中,施恩——受恩——知恩——感恩——报恩,成为一个恩链,始点和终点是重合的。静态层面的施恩,实际就是动态层面的报恩。具体而言,在本质的意义上,施恩与报恩是同义反复,是主客体关系转换境遇里的不同说法;报恩是另类的施恩,或者为不同形式的施恩,这是针对施恩者的反向施恩,意在通过这个行为,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释放情感的谢意,达到自己内在情感的平静,同时使人际关系在平和中保持张力,而释放的谢意情感将直接凝聚成张力。受恩虽然需要客体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诸如形式上的认同也是认同,但此时并没有从恩惠的意义上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只有对行为主体的施恩行为产生情感上的理性自觉,才能说是进入了“感恩”阶段,真正感受到来自于他人的恩惠,从而产生情感上的愉悦,达到心理上的享受;同时也感受到自己在人际关系里依存性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对维护这种依存性关系所持有的必然的责任。这就为“报恩”的登场和价值实现完成了事实上的情感准备,一旦与具体的情景实现对接,“报恩”行为就会立即变成现实。恩链中间三个环节则是施恩、报恩的加油站和驱动器,这也正成为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驱动源。总之,“感恩”是“报恩”价值实现的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感恩”是对施恩行为的情感上的理性自觉,或者是对恩的情感上的自觉意识。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是民族的血液,血液的纯洁是民族使命健康的保证,感恩就是保持血液纯净的过滤器。
五
由于中华传统美德之美,不是在道德层次上高位的占有,而是在道德生发价值和意义的范围里的广泛性。故笔者反对把美德定义为居于一般道德之上的存在的运思,美德之所以美在于它的广阔性和广泛性。广阔性是指美德范围的无限广阔,毫无限制地囊括了一切人,只要是人,就有与美德共同生活和实践的权利,美德具有普适性;广泛性是指美德内容的基本生活性,它源于生活,面向生活,而生活是人的营养的源泉,人无法离开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美德是道德的基础,没有美德就不可能有道德,而不是相反。把道德说成美德基础的运思,最大问题就是对道德进行高低的分层,而只要是道德,其价值是同等的,道德没有大小、高低的分别。但是,道德在审美的视域里,不同的道德行为所带来的审美愉悦是不同的。在广普性的层面,感恩可以说是承扬中华传统美德实践工程最好的切入点。
前面提到,施恩、受恩、知恩、感恩、报恩直接成为承扬中华传统美德驱动力,在于它本身就是一条动力链,内置着动力机制,受恩、知恩、感恩就是其动力源。“恩”与人的心相连,这是生物学意义上人的基本器官之一,但是,生物之心只有变成“伦理之心”时,感恩才能可能;同时,这也是文明人的基本条件之一,而整个“恩”链就是从生物之心向伦理之心挺进的实践链。当然,这在学理上是不成问题的,但学理与现实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我们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的那个真正产生效益的动力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的实践来完成。这一实践自然不是依靠感恩教育能够完成的,起码习惯意义上感恩教育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的思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关注的仅仅是做,不注意如何做,因此,做了就可以总结了,至于效果如何自然是无需考虑的事情,这是最为致命的文化杀手因子。恩链还是一条切实的连接个人与社会他者的桥梁,是社会稳定的文化因子,注重恩链的打造是感恩获取活力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中华传统美德文化在现实层面生根的关键。而这一工程的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依靠说教来完成,说教也无法承担这一重任,而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养成。报恩是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其中感恩节就是西方人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报恩行为养成的重要环节。同样,报恩也渗透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中。藏族《礼仪问答写卷》(以下简称《问答》)⑤在第16问中以弟弟向哥哥发问的方式问道:“何为做人之道?何为非做人之道?”兄长的回答是:“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显然,报恩是做人之道的具体内容之一。《问答》第36问中,弟问道:“我有一个干练之仆,若施以财宝,我将变穷;若不大加赏赐,何以报之”?兄答道:“不予权力而令知其礼,乃是最上乘之酬答,财宝亦在其中矣。”把知礼节作为报恩的具体内容,这不失为一种报恩的方法。
显然,从恩的广泛性而言,感恩无疑是编织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纽带,具有纽结人际力量的功能。中国古代具有非常丰富的恩思想,尤其是“恩义”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折射了恩在情感方面的狭隘性,另一方面昭示了恩必须在义的轨道上进行社会生活的演绎。恩义是21世纪现代社会生活所无法离开的因子,如何做好恩义的结合,这是从血缘性恩过渡到普适性恩的关键。感恩实践链的构建,也必须融于现实生活,要在做中育养。具体而言,清明节已经是国家的节假日,可以利用清明节做一件具体的事情来感恩在世的父母亲人。前苏联有一个谚语: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通过做具体的事情来接近高、深,高、深的差距越大,说明做子女的欠父母的恩情越大。通过这种做具体小事的活动来追祭祖先,当然不能只停留在习惯的到祖宗坟墓上烧纸、叩拜,这毕竟不是一种安全而卫生的方法,应该尽快养成献鲜花的习惯,既高雅又安全卫生。每年的3月12日为植树节,这是一个感恩自然世界的最好方式,通过植一棵树的具体行动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恩,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的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9月10日是教师节,可利用这个节日来培养青年学子对老师、社会的感恩之心,自然也是通过做具体的一件事情来切实地落实,而不是提倡和走过场。要通过具体的行动让年轻人认识到没有老师的教育、没有社会的育养,自己就不可能有今天,从而激发思考自己如何来回报老师、社会的育养之恩的现实问题,以在感情上把个人和社会他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其他诸如10月1日的国庆节,从国家层面而言,现在只是放长假,而没有落实到如何通过做一件具体的小事来体现爱国情怀的具体环节上。
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告诫我们,现代文明必须借助古代文明文化的营养来滋润自己的躯体,从而完成净化文明社会环境氛围的重任。中国文化强国的战略也一样,也必须依托古代文化的丰富营养来进行,而在最为切入生活并最能盘活古代文化资源的层面,感恩是最好的选择。迄今我们的道德建设比较重视的是建设本身,而不是如何建设。道德滑坡现象固然有多种根源,但建设无效或无力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不知从如何入手,因而就根本没有效益的考虑和追求,自然也就不过问效果如何的问题。在软文化的领域,追求实效是必须得到切实坚持的,选择感恩为承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驱动力,本身就是对陈式的破除,本身就是从如何层面的切入。因为恩是人在自然、本性、社会层面无法躲避的问题,有着切实而宽广的基础,感恩是连接个人与社会,自己与他人、人与自然的最为切实的切入口。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可以在道德教育的时间,安排“感恩教育”这门课。尽管近些年我们可以不时听到“感恩”的概念,以及“感恩的心”这样的歌曲,但就普遍性而言,目前在学校层面的感恩教育还没有开展起来。这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而且是伴随终生并让人受益终生的。我们应当拓宽既往的教育的视野,拨打学生情感的琴弦,切忌推行千篇一律、泛泛而论的模式,学校学生宿舍可切实实行值班制度,包括教室的卫生间,都应该成为感恩教育的场地。
注释:
①《光明日报·教科新闻》栏目,以“圆助学老人一个梦”为题,从2011年11月9日至11月28日分5次连续报道和讨论了这一现实问题,值得思考。
②参考“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者,积仁也。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说苑·修文》,第559页;[汉]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
③参考“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庄子·知北游》,第758页)
④参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17》)
⑤见诸于敦煌本古藏文文书P.T.1283号卷,该卷与其他流落海外的敦煌本古藏文文书约5000余卷,现分别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国内由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王尧、陈践译为汉语,并加译解,刊载于《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该文献原无标题,书名为译者所加。
参考文献: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郭庆藩辑.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丸山敏秋.纯粹伦理入门[M].日本:新世书房,1987.
[6]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李 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安乐哲(Roger T.Ames),郝大维(David L.Hall).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M].何金俐,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13]F·卡普拉著.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4]盧元骏.说苑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责任编辑 任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