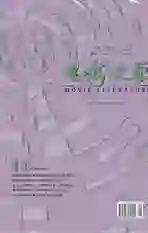刘震云长篇小说的电影改编略论
2016-06-14莫宇芬
莫宇芬
[摘要]刘震云小说叙述的事件和塑造的平民形象,在幽默风趣的个性中富有巨大张力的共性,乃至符号意义,这些是博得导演青睐的重要因子。从改编角度来看,刘震云小说与电影之间有三大变化,分别是:从散乱到集中的结构整合,从个性到共性的形象升华,以及当代生活百态的影像表达。透过小说与电影之间的“离合”,既能把握住刘氏改编的原则,又能审视文本与影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关键词]刘震云;小说;电影;改编
刘震云是一位幽默风趣又饱经沧桑的智者,读他的小说,常让你破涕为笑,笑中又含着辛酸的泪。自1982年执笔创作以来,刘震云已贡献出《故乡天下黄花》《一腔废话》《我不是潘金莲》《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多部长篇小说,后四部作品已先后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刘震云目光敏锐,他注意到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和“单位”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化最犀利、最现实、最广阔的独特视角。[1]几乎社会中的大小事件都离不开官、商的密切联系。但他又不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官场或商业体系,而是透过普通民众、底层人民,或是受害者、压迫者的眼睛,去管窥权力、民生、经济等官商层面的社会问题。因此,小说叙述的事件和塑造的平民形象,就在幽默风趣的个性中富有巨大张力的共性,乃至符号意义。[2]这些是博得导演青睐的重要因子。从改编角度来看,刘震云小说与电影之间有三大变化,分别是:从散乱到集中的结构整合,从个性到共性的形象升华,以及当代生活百态的影像表达。透过小说与电影之间的“离合”,既能把握住刘氏改编的原则,又能审视文本与影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一、从散乱到集中:线索的抽绎与主题的提炼
从体裁来看,刘氏小说是不易改编的类型,形式结构上随意散乱,“貌似”没有紧密的叙述逻辑,整篇小说不像一个安全的堡垒,更像是千疮百孔的“马蜂窝”。将一个完整的故事翻拍成电影,无论是剧本的编排,还是台词的增删调整,普通人都能做到。但若将一个本身就“杂乱无章”的小说用影像表达,那么情节结构、线索发展、主题提炼、人物形象塑造等重大问题可能都要“另起炉灶”。导演们宁愿如此大费周章也不愿放弃的理由,就在于刘震云小说提供的叙事空间确实令人着迷。
第一,线索的抽绎。阅读刘震云的小说,常会有“不知所云”的困惑,一方面由于文本形式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是刘氏特有的“行散神不散”的叙述方式。与天马行空的小说不同,电影需要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再现叙事空间,必须有合情合理的主次线索。如何抽绎出既不偏离小说中心,又便于观众理解接受的故事情节是电影对文本的超越所在。以《一九四二》为例,故事本身是调查体小说,即将那些亲身经历1942年自然灾害的人的回忆口述整理成一部合集,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主要线索,连剧情发展都显得杂乱无章。刘震云在编剧过程中,抽绎出范殿元一家逃荒历程的主线索,再增添辅助性的蒋介石处理河南干旱态度,白修德亲自入豫一查究竟,日军侵华推进路线等次线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四个不同角度考察河南大旱、饿死三百万人、难民逃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影片结构上显得张弛有度,线索鲜明。同样,《我叫刘跃进》也存在类似问题,原著以众多不同人物为视角审视同一社会,从小说角度来看,确实有奇妙之处,但无法用镜像来表达。刘震云巧妙地拈出小人物刘跃进,以他丢了包,又捡了一个新包两件简单事情,将刘氏生活与开发商严格一伙的金融勾当、曹哥等黑社会群体、卧底警察老邢等一干人等全部串联起来。剧本构思之匠心独运让人拍手叫绝。
第二,主题的提炼。电影改编小说,需要将隐于文字之间的主题简明扼要地提炼出来,对于直观的、显性的主题而言,自然容易处理,困难的是那些无法用台词或镜像直接表露的深层命题。刘震云对《温故一九四二》的历史性主题反思堪称完美。曾有学者言及,中国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离我并不遥远的惨痛历史可以被轻易地抛在脑后。或者是政治的导向,或者是传播媒介的桎梏,抑或是中国人的“故意而为”,总之,甲午、庚子、抗战等让人窒息的历史会在轻描淡写中被世人遗忘。如果连作家都不去重塑这些本不应该被尘封的故事的话,那么还有哪些人能够承担起启迪民众的重任呢?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此,他以文献史料和调查记录为基础,以真实性、趣味性为原则,在貌似散乱不堪的叙述中传达出一位作家应有的历史思考。冯小刚正是看重《温故一九四二》透露出的沉重历史,才不惜投入20年的准备去拍摄这部堪称“史诗”的电影。在商业大潮和娱乐至上的冲击下,今天的中国人变得更加务实而又浮躁,电影被理解为消遣放松的重要渠道。在“调侃”层面上,冯小刚是不输于任何人的,但他作为大导演的特质就在于适时地警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遗忘民族之痛。
从散乱的文本叙述方式,到集中的线索抽绎和主题提炼,刘震云实现了小说与电影剧本之间的完美转换,且并没有损伤故事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其改编法则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
二、从个性到共性:人物形象的继承与重塑
阅读刘氏小说,读者经常有抓不到中心人物的感觉。数十万字的《温故一九四二》和《我叫刘跃进》,前后出现的人物足有百余人。每个人在他的笔下都显得生动活泼。电影改编的独特之处即在于放大人物个性,使其上升为共性的“代表”,从而具有符号性意义。
首先,影片对文本形象个性的继承与融合。电影《一九四二》中的范殿元在小说中是没有其人的。若一定要考究,可以算是郭有运和克俭舅老爹的“合体”。鲁迅曾说:小说的主人公未必是生活中的某个人,可能是取多人身上个性的融合。如此塑造的好处是读者都能找到自身的影子,但又与其有一定距离。距离一方面可以制造各种幽默而博得观众一笑,另一方面是扮演镜子的角色照亮自身。范殿元就是河南干旱后逃荒大军中的典型。作为地主,他自私自利又阴险狡诈,多年来没少搜刮穷人的钱财,没少压榨长短工的劳力。作为一家之主,为了全家老小在灾荒之年能够生存下来,他尽心尽力地维系所有人的安全,用星星稳住动摇的栓柱,用小米救助瞎鹿,领养小妮,等等。“穷凶极恶”与人性美的光辉在范殿元身上融合,当他抱着死去的孙子悲叹长吟时,同情已经使人们原谅并忘记他当初犯下的“过错”。如果连这样的人都可以博得世人的怜悯,那些本性善良且从无犯错的人该是怎样的存在?同样,《手机》中的严守一形象也极具个性。他是电台著名主持人,是“正义、正派”的化身;而其背后私生活却一片混乱,在有妻室前提下,他与武月有染、与沈雪“勾搭”。影片通过正反对比,将其丑恶嘴脸描绘得极其深刻。重要的是当代社会中确实有这么一群人生活在周围,其现实批评力度是十分尖锐的。
其次,个性基础上的符号性意义。如果仅仅塑造几个有个性的人物,对小说或电影来说都不是难题。难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升华到具有普遍性的符号。这是刘震云改编影片不可忽视的着力点。《我叫刘跃进》中,刘震云每节都以某个主人公为视角,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展开叙事,整部小说几乎有二十余个人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同一个社会,就在“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影片刘跃进已经不是单指那个工厂厨师,而是一种符号。[3]他代表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国底层的贫苦工人阶层,他们没有多少积蓄,也没有什么文化;家庭经营得一塌糊涂,与妻子离异,对子女缺乏教养;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同类群体。刘跃进形象与鲁迅笔下阿Q有某种共性,阿Q文学成就的取得正因为其独具个性之外又有太多人们不易发掘的共性,如果说阿Q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进程中懵懂的底层人民,那么刘跃进代表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仍然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刘震云敏锐地注意到刘跃进身上具有的特殊符号意义,于是在他的笔下,本是一个不小心卷进社会洪流的小人物,却牵连出足以反映整个阶层和社会百态的核心。于此,足以窥见在改编电影中继承与重塑人物形象的重要意义。
三、影像对文本的超越
影像表达有文本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随时调度时空场景的变换。给人视觉冲击的同时,瞬间将观众的视野导入想要表达的主题中。
第一,蒙太奇转换中营造紧张气氛。《我叫刘跃进》中,当青面兽杨志被张端端哄骗入室后,镜头一面是他俩行苟且之事,一面是三位大汉破门而入,诬告其强奸。镜头在二者之间切换,伴随着锣鼓声音节奏的加快,紧张气氛逐步加强。类似画面还有很多,如杨志在公交车上欲对张端端报复;刘跃进追踪杨志进入贝多芬公寓;严格与瞿莉电梯相遇等场景,多次使用蒙太奇转换来制造不同氛围。另外,闪回的镜头还可以产生别样的寓意。刘跃进找地头蛇曹哥询问钱包被偷事宜,对他来说关乎一生的大事在本就一身黑的曹、崔眼中是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饶有趣味的是镜头在刘跃进从高空被扔出与瞿莉将糖块“跌入”咖啡之间转换,一动一静之间有某种契合,上层社会的资产转移与刘跃进的寻包过程实现暗示性链接,为下文做好铺垫,堪称神来之笔。
第二,远近视角彰显视听空间。面对1942年河南大旱这样殃及全国的大事,缺少了远视角的宏观镜头是不能彰显灾难严重性的。当数百万的难民“大军”在迁徙路上蹒跚而行时,透过高空视角,犹如一条受伤的长龙在哀吟,天灾已经让人手足无措,更何况国民政府的漠视和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饿死三百万人并不是危言耸听。为了制造刻骨铭心的伤痛,少不了近距离的微观透视。尽管刘震云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如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但面对影片中花枝抛下儿子时的黯然神伤,其冷峻的严肃是比撕心裂肺的哀吼更可怕的,感情烈度堪比“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的《悲愤诗》。而当花枝与栓柱交换棉裤的“戏剧性”情节出现时,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笑得出来。微观聚焦何止一处,儿媳饿死细节、火车顶上紧抱孙儿的范殿元、片尾孤苦伶仃的小妮等,都成为“饿死三百万”的有力注脚。远近视角的搭配在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对比中深化人性美丑的差异。如果说《一九四二》是启迪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之痛,《我是刘跃进》是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百态,那么《手机》就是走进人性深处,反思婚姻道德的伦理命题。[4]主持人严守一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声音沙哑,失去主持人的明星地位;与妻子离异,失去本该完美和谐的家庭;失去朋友,费墨出国,沈雪、武月相继离开。他将结局的罪魁祸首归于“手机”,殊不知此举只是自欺欺人的无奈。刘震云真正诉诸的是严守一无法控制的内心欲望和道德沦丧。在现实与节目之间存在如此差异的“有一说一”主持人,是如何违背良心做到“严”“守”“一”的。台前幕后的鲜明对比直接撕下其人性的丑恶嘴脸。包括貌似“循循善诱”的费墨也逃不过与女研究生之间的暧昧。与其说严守一不敢再触碰手机,倒不如说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嘴巴和内心。对比中深化人性美丑还不止体现在《手机》中,代表工人阶层的刘跃进与资本家严格、瞿莉的不同下场;地主“老东家”与花枝、瞎鹿、栓柱、星星、儿媳等人的不同遭遇等,既在比较中张扬个性,也在对比中体现人性。
以上分别从线索结构、人物形象、拍摄手法等角度分析刘震云长篇小说的电影改编策略,可以说,影视与文本取得的双向成功是二者实现完美转换的必然结果。刘震云在历史的反思、人性的挖掘、形象的刻画、语言的锤炼等层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
[参考文献]
[1] 秦剑英.权力文化的解读与批判[D].郑州:郑州大学,2003.
[2] 曾军.拧巴式幽默——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刘震云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
[3] 黄轶.在“华丽”与“转身”之间——评刘震云《我叫刘跃进》[J].扬子江评论,2008(01).
[4] 周霞.《手机》:都市生活的后现代寓言[J].当代电影,2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