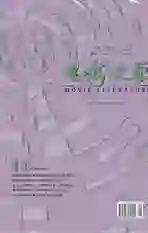《老炮儿》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2016-06-14杨继祥
杨继祥
[摘要]管虎的《老炮儿》以北京市井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老混混”为表现对象,通过主人公六爷的视角,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社会的变化、观念的流转与个体的惶惑不安。影片人物轮廓清晰、性格鲜明,不同人物之间相互投射映照,与影片这一核心冲突契合良好。这对影片审美效果的实现与提升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其中,主人公六爷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本文从市井英雄、父权与父爱以及时代的“他者”三方面,分析了《老炮儿》中六爷这一男性形象。
[关键词]《老炮儿》;人物塑造;男性形象
管虎的《老炮儿》以北京市井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老混混”为表现对象,通过主人公六爷的视角,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社会的变化、观念的流转与个体的惶惑不安。曾经在老北京风光一时的六爷,为救儿子,走出自己的小胡同。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让六爷看到,其一直坚守的规矩与道理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于是,倔强的六爷用自己的原则去救儿子的过程,便成了他一个人与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对抗。影片人物轮廓清晰、性格鲜明,不同人物之间相互投射映照,与影片这一核心冲突契合良好。这对影片审美效果的实现与提升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本文从市井英雄、父爱与父权以及时代的“他者”三方面,分析了《老炮儿》中六爷这一男性形象。
一、市井英雄
人物形象是《老炮儿》这部影片饱受赞誉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冯小刚塑造的老北京混混六爷。六爷重情重义,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江湖原则。六爷这一人物不但具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又不乏仗义豪迈的英雄情怀。这是人物具有吸引力,能够引起观众观影热情的主要原因。
首先,六爷出身于市井,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片开始捕捉了许多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一方面,这些细节勾勒出六爷生活的全部背景。人物生存的空间虽然狭小,却不乏浓郁的生活气息,带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六爷开一间小店,生意不温不火,没事跟邻居闲聊几句,逗逗鸟,管管闲事,日子过得分外悠闲。影片中的北京老胡同、特有的方言俚语和粗口、路边小摊贩端上的热面,城管与小贩的争吵,装盲人拉二胡的街头艺人,以及熙熙攘攘的人声与车声,都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质感和活力。另一方面,影片也通过这些日常琐事,从不同角度将人物的个性刻画得鲜明而清晰。六爷有自己的原则,偷钱不管,但小偷得把证件给失主邮回去;问路没礼貌要教育,道歉了还是得给指路。影片中,城管跟小贩的冲突这一情节,六爷鲜明的人物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烘托。灯罩儿砸城管的车灯、阻碍城管执法,理应被没收出摊的车;但城管打了人,六爷也巧妙地用巴掌给予回敬,帮灯罩儿要回了面子。这样,一个传统、倔强、强势又好打抱不平的男性形象,便生动自然地建立起来了。
影片以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来展现出人物的性格,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评价立场。就人物的言行来说,观众对人物的感知也必然是褒贬不一的。他的固执、强势和对某些不道德事物的包容,显然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同,但六爷虽然是胡同里人人都畏惧三分的老混混,却又不是整天游手好闲,做些鸡鸣狗盗之事的大无赖。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六爷这样的人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表征。这种力量存在于市井社会,存在于社会法规之外,是一种良性的秩序力量。因此,六爷身上又有着超越普通小老百姓的质素。
其次,当六爷走出自己的小胡同,遇到乖张跋扈的官二代小飞及其伙伴后,他的权威遭遇到巨大挑战。他的倔强、担当与侠义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市井老混混身上仗义豪迈的英雄情怀。影片前段的诸多细节,都是为了六爷随后与官二代小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铺设的。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观众对人物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发生了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对人物的情感,也从最初的不置可否,转变为钦佩与敬重。对于儿子的事情,他认错认赔;他宁可“憋屈”,也不让下手没有轻重的“生瓜蛋子”插手;话匣子借钱给他,他用房产证做抵押;特别是在影片结尾,六爷明知必败,仍豁出性命,以一己之力进行抗争。这种慷慨赴死的姿态,成为人物最后的定格。没钱没权的市井小人物,在强大的环境压力面前,仍坚持自己的个性和道德原则,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人物值得书写的意义所在。同时,这种英雄情怀并非讲人物有什么超越常人的善举大义,而是为了救孩子,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尊严和原则遭受挑战时迸发出来的。因此,人物没有无限地偏离现实生活,不是一个被抽象化的英雄符号。
可见,六爷这一男性形象,是在市井小人物与侠义英雄之间取得平衡的。他既渺小,又高大;既狭隘,又宽宏;既刚强,又脆弱。这是人物塑造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父权与父爱
从《老炮儿》中的六爷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社会浓重的父权制观念:对父辈要有礼数;作为子女要对父亲无条件遵从;在女性面前表现出大男子主义等,这些在六爷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铁律。同时,六爷除了是老北京胡同里的老混混,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父亲。而六爷晚年不得已再次踏入年轻人的江湖,也正是源于父亲的责任所在。因此,从这一角度审视影片的主人公,同样是瑕瑜互见、颇令人玩味的。
一方面,六爷年轻时靠着勇武之力和仗义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其身上的父权观念,决定了他在情感和家庭生活中必然是一个失败者。父权思想在中国曾经根深蒂固。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观念也呈现多元发展,但长辈,特别是父亲在整个家庭关系中仍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六爷是这类男性的代表。对于六爷来说,长幼尊卑,无论对于家庭还是江湖,都是其规矩和道理的重要部分。而在家庭和江湖的两相比较中,男人更是应该以江湖为重。当妻子和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六爷在监狱;当六爷对儿子说“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亲的人”时,儿子反问“霞姨呢?”六爷却只摇头说“女人……”可见,六爷的江湖是把家庭、女性排除在外的,是大男子主义式的。这也决定了六爷在情感和家庭生活中的失败。
影片通过主人公对兄弟和晚辈的不同态度,进一步揭示了人物的传统父权思想,表明了主人公这一思想并不仅局限于家庭和江湖,而是指向广泛的社会。六爷对兄弟以仁义与平等为核心。不管谁遇到什么难事,他出钱出力,鼎力相助。但对年轻的问路人、对儿子的朋友、对小飞和阿彪、对儿子,六爷都会高高在上,强调一个礼数。甚至在与儿子喝酒时,举酒杯谁高谁低得有规矩。实际上,六爷思想中的父权观念和行为准则,不能完全从表面意义上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态度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回应。在朋友间不讲义气、男人没有个男人样、只图自己乐不管别人苦、金钱和权力至上的现代社会,六爷通过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传统,以表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
另一方面,影片通过六爷和晓波之间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作为一名父亲,他对孩子的爱和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担当。影片中父子之间情感的弥合是一条隐线,是亲情缺失与弥补的过程。在六爷最应承担起家庭责任的时候,却因为犯事进了监狱,这本已在晓波的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加之六爷在儿子面前不是靠关怀与呵护,而是不断地重提自己过往的辉煌来建立父亲权威。这样不但无法填补晓波缺失的父爱,反而引起后者更多的反感与抗拒。儿子认为他除了打架斗殴外,一无是处。当两人发生争吵时,更是对父亲直言不讳:“打啊,反正你是我爹,反正你爱打人,反正你现在也打不了别人。”由此可见,六爷与晓波的矛盾冲突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却为父子关系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六爷为晓波奔走和抵挡伤害的行为,表现出一个父亲的担当和对儿子的深爱。这才是晓波一直以来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期待。并且,六爷在保护儿子的过程中,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道理和规矩,使得晓波对父亲嘴里的江湖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这样,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与冲突,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包容和谅解。
可见,六爷的父权,既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和对抗的一种表现。晓波的事件使得六爷的父爱找到了落脚点,同时也加剧了六爷与时代之间的隔膜与冲突。他的行为也从一个父亲的担当,转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立场。人物也因此逐渐被观众所接受与认可。
三、时代的“他者”
影片一直在表现六爷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在大部分时间里,六爷始终作为一名时代的“他者”存在着。他看不惯年轻人的轻浮和自私,看不惯现代人的冷漠,也看不惯权钱当道的世俗。人物与环境的冲突自始至终都在,并且这种冲突是难以调和的。时代与个体没有任何一方选择妥协,两者之间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影片是具有悲剧精神的。正因为这种悲剧精神,才使人物获得了一种美感和崇高感。
六爷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电影创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传统美德的怀念。因此,虽然六爷身上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有着诸多的不完美,但随着情节的发展,电影创作者不断地将人物推向新的高度。在六爷的不变与时代的变之间,矛盾冲突愈发激烈和不可调和。影片中的六爷也在这个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从一个市井小人物,转变为一个为了尊严和信仰而战的英雄。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是很巧妙的。影片开始,在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内,六爷对很多事情,仅停留在作为局外人的看不惯和极其有限的介入上。他平日里管管闲事,逗逗鸟,发发牢骚,喝喝酒,平淡地过活。这些铺陈使人物显得分外真实,为影片的后半程人物形象的升华做了极好的铺垫。正因为六爷的真实,当他被推到超越现实生活的,被抽象的理想化人物高度时,也才最具撼动人心的力量。
此外,影片将六爷从一个真实的人变为一个超越现实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成了时代的“他者”。电影创作者正是利用六爷的这一“他者”身份,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以局外人的立场去审视现代社会的视角。影片中涉及的诸多细节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社会问题。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街头小混混毫无顾忌地斗殴,诸人对轻生者的冷漠和嘲笑,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嚣张跋扈,政府官员的腐败等,这些问题与现实生活距离如此之近,与普通人的利益多有相关。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对这些现实问题是保持缄默的,抑或仅仅是将其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六爷不是时代的“他者”,而是生活的参与者,他抱持着生命的主体性,不为金钱、权力和各种暴力所左右。而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冷漠看待他人疾苦,甚至是社会暴力的帮凶者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真正的“他者”。无疑,六爷这一人物不仅提供给观众一个审视社会的“他者”角度,也激发了观众对自身的反思。
综上所述,影片《老炮儿》中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塑造是较成功的。瑕瑜互见的人物性格、精神世界的理想主义以及作为反观现实生活之“眼”,这一男性形象不仅真实,而且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影片审美力度的实现和提升上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 管虎,赵斌.一部电影的诞生——管虎《老炮儿》创作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6).
[2] 赵斌.迷图——影片《老炮儿》的叙事困局解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6).
[3] 李涛.游走在艺术“叛逆”与生存“胁从”之间——试析管虎电影风格[J].艺术教育,2013(10).
[4] “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张元、管虎创作比较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5] 陈旭光.抒情的诗意、解构的意向与感性主体性的崛起——试论第六代导演的“现代性”问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