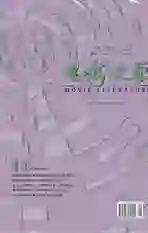精神分析视域下大卫?芬奇的电影作品
2016-06-14杨跃珍
杨跃珍
[摘要]有着“电影鬼才”美誉的大卫·芬奇,其电影的叙事无不充满了荒谬、暴力、怪诞的元素,甚至直指人类在社会制度与道德伦理上的弱点。相较于传统学院派的故事片导演们,大卫·芬奇更为深谙画面细节与人类心理,他将自己娴熟的拍摄、镜头切换和场面调度技巧在影片中展示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在电影之中融入了深层的哲学和心理学意义。文章从大卫·芬奇电影中的童年创伤、恋母情结、自我欲望宣泄三方面,以精神分析视域观照芬奇的电影。
[关键词]大卫·芬奇;电影;精神分析;弗洛伊德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就引发了心理学界的强烈震动,其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的影响最终超出了心理学界而被文学、影视艺术学乃至宗教学等用来对人的心理进行解析。纵观当前影坛,能够在票房以及电影批评圈内能取得一定佳绩的导演们,都有一个较为有趣的共通之处,那便是其电影带有一定的精神指向性,这就使电影因为带有导演对于人性、社会、宗教等复杂问题的阐释而具备了一定的深度,并且与弗洛伊德类似的,这些导演能使电影在视听语言艺术之外的社会学科,如心理学等,能够进入到对影片的解读之中,使电影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开采价值的富矿。美国著名导演,有着“电影鬼才”美誉的大卫·芬奇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电影的叙事无不充满了荒谬、暴力、怪诞的元素,甚至直指人类在社会制度与道德伦理上的弱点,能够给观众带来心灵的震撼。这位出身于音乐MV导演的影坛怪人相较于传统学院派的故事片导演显得更为深谙画面细节与人类心理,他将自己娴熟的拍摄、镜头切换和场面调度技巧在影片中展示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在电影之中融入了深层的哲学和心理学意义。[1]如拉沃热·齐泽克、安东尼奥·梅内盖蒂、维基·勒伯等学者就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如后现代主义等,来阐释芬奇的电影,但至今从精神分析领域对芬奇电影进行观照的研究还为数不多。事实上,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一、大卫·芬奇电影中的童年创伤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可以分为自我、本我与超我三种人格,而这三种人格之间往往是互相抵牾的。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术语为防御(Defense),其指的是人们的本我会产生冲动,这些冲动与人的性欲望有关,它有可能造成人极大的焦虑,但是人的自我却会对这些冲动进行觉察与抵制,将不良的情绪和冲动转移到其他事物身上,这一过程便可称之为自我防御。[2]并且人本身是不会意识到这一防御过程的。良好的防御机制能够帮助人降低精神压力,实现心理的平衡,但是防御机制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奏效。精神分析理论中极为重视人的童年创伤,认为童年是人情感、意识以及思维等还未成熟、未定型的阶段,而这一时期的不愉快经历将给人造成深重的童年创伤,这种创伤一般被压抑于个体的潜意识深层之中,扭曲着人们的心智,在童年结束之后,童年创伤仍然有可能会被不同程度地激发,这也就是为何弗洛伊德指出童年创伤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童年早期经历事件的记忆,青春期后经历事件的记忆及后期经历事件触发对早年事件的记忆。”[3]一旦防御机制崩溃,那么童年创伤将有可能影响作为成人的个体的行为与生活。
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便是《心理游戏》(The Game,1997),这部电影充满了悬疑感,整个叙事之中的音效等全部服务于悬疑的氛围,芬奇直到影片的最后才揭开谜底,而谜底尽管出人意料但又完全可以用常理来解释。电影中的主人公尼古拉斯作为一名亿万富翁,可谓是俗世意义上的成功者,但是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的弟弟交给他一张卡片,使他卷入了一场神秘的心理游戏之中。尼古拉斯先是去某个奇怪的公司里填了大量的表格,并做了身体测验,被弄得筋疲力尽。他误以为一切只不过是恶作剧,但很快,尼古拉斯便发现自己处处受到捉弄,被人追杀,有家难回,且弟弟也误解了自己,几次死里逃生的尼古拉斯发现自己还是被逼到了绝境,即在大厦顶上因为极端的恐惧而开枪杀死了弟弟。最后,万念俱灰的尼古拉斯选择了从大厦上一跃而下,却发现自己落在了一个巨大的气垫上,而弟弟也好端端地活着。原来一切都是弟弟为解开他的心结而安排的“游戏”。而尼古拉斯的心结早已在心理测试的表格中暴露了,即他有着深重的童年创伤。因为在他小时候的一次生日聚会上,他的父亲,跳楼自杀了,这给尼古拉斯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包括这次在顶楼的“谋杀”也是算准了尼古拉斯会效仿父亲跳楼)。以至于他长大以后对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十分冷漠,婚姻也并不幸福。
电影在表现了金钱与权力在命运面前的虚无缥缈的同时,也表现出了童年创伤对人的影响,这一影响同样没有因为主人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社会能量而消失,主人公依然深陷在恐惧的海洋中。在游戏尚未开始时,尼古拉斯为自己对他人的苛待的自我安慰是他并不需要爱,而这个游戏却教会他要从父亲自杀的痛苦回忆中走出来,珍惜自己的身边人,好好经营自己现在的生活。与之类似的还有《龙文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2011)等。
二、大卫·芬奇电影中的恋母情结
弗洛伊德是最早使用古希腊神话之中的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以“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词语来形容恋母心理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的发展有不同的阶段,而第三阶段则是“生殖器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儿童会滋长一种恋母(父)的情愫,这种情愫会促使儿童厌憎自己的同性家长而爱恋异性家长,即对于儿子来说,会不自觉地爱恋母亲,将母亲当成是自己第一个产生性冲动的对象,而讨厌父亲,将父亲视作自己的情敌,对父亲有与暴力相关的念头,女儿则反之(恋父情结则被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这种心态正好与俄狄浦斯王故事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大悲剧相对应。但是与俄狄浦斯故事之中主人公饱受命运的困扰,是个别的例子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其实是普遍、原始存在的,甚至可以视作是人诸多行为发生的出发点:“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4]只不过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在成长后意识到这一行为对伦理的违背,尽其所能地压抑之。在对《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蒙娜丽莎》等文学美术作品进行分析后,弗洛伊德宣称恋母情结已经成为审美表现的主题,艺术家只不过是把人们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杀父娶母)表现出来,从而激发观众或读者的共鸣。
大卫·芬奇踏上影坛的电影处女作《异形3》(Alien 3,1992)中,就有较为隐晦的恋母情结。单纯就《异形》的前两部来看,电影的主旨带有某种冷战背景,只不过把背景设置在外太空而已。但是芬奇本人却无意表现单纯的科幻题材或嗜血的恐怖片,而是希望创造一个人战胜自己内心恐惧,坦然面对生死的故事。在《异形3》中,长相令人作呕的外星生物异形有着对于生育与繁殖的狂热,它们需要吸附在人类的脸上,往人类的口中植入卵,而卵就此寄生在母体身上,待异形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冲破宿主的胸部摆脱宿主的控制。此处体现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之中的某种对父母的仇视。而女主人公蕾普利因为是低温休眠仓之中的唯一生还者,她成为161星球上异形寄宿的唯一母亲,岛上的异形开始为了有更多的异形能够生下来而开始保护蕾普利。这让蕾普利痛苦万分,因为她孕育的是人类的敌人。这种行为也是“公司”所不能容忍的。就像俄狄浦斯王故事之中,俄狄浦斯王的母亲伊俄卡斯忒在生下俄狄浦斯王之前就已经知晓了神谕,于是并不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在最后知道真相以后,这个母亲在羞愧之中自尽而死,而蕾普利也因为自己要生下祸害而选择了自杀。尽管异形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的是恐怖感,但是芬奇却运用主观镜头来赋予异形人文性,让观众站在异形的视角上思考它的命运。
又如在《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1999)中,芬奇则将恋母情结表现得更加明显。饱受失眠症困扰主人公杰克加入了睾丸癌患者互助会,在互助会里认识了鲍勃,因为切除睾丸并且服用了类固醇药物,鲍勃开始出现了女性特征,而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与母亲意象紧密相连的胸部的膨胀。杰克则有意与鲍勃拥抱,将自己哭泣的脸埋在鲍勃的胸前,此后一直生活极为苦闷的杰克竟战胜了失眠症。这实际上暗示的便是杰克的心病只能在母亲的关爱之中才能得到治愈,他显然是把母亲当成了欲望的客体。与之类似的还有《七宗罪》(Se7en,1995)、《战栗空间》(Panic Room,2002)等。
三、大卫·芬奇电影中的自我欲望宣泄
弗洛伊德理论严格来说属于前精神分析学派,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后精神分析学派中荣格等人的纠正或补充。而荣格等人在反对弗洛伊德时最为强烈的一点,就是认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有抹杀人社会性本质的一面。电影所关注的对象,往往不是观众所熟悉的芸芸众生,而恰恰是要选取或塑造极端的、突出的形象,从而给观众造成视觉与心灵上的刺激。作为一名极富个性的导演,大卫·芬奇的电影中就擅长表现在长期自我压制之下,最后实现自我欲望的宣泄的角色。可以说,芬奇在保证电影戏剧性的同时,又对现实社会进行了一定的妥协,其电影走的是对前后精神分析学派进行中和的道路。
以《搏击俱乐部》为例,主人公杰克是一个汽车事故调查员,他在平淡的岁月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迷失了自我,开始长期失眠,也正是失眠造成的精神分裂使他认识了另一个自己,即他当成好友的泰勒。两人一起创办了“搏击俱乐部”,让像自己一样苦闷的人在其中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宣泄不快的情绪,在徒手搏击、聚众斗殴、爆炸等行为之中获得片刻的快感。观众眼前出现的杰克可以说是一个一直对自己的冲动进行抑制的人,这种抑制使得他不得不通过合法但是诡异的方式来寻找抚慰(如加入绝症患者的互助团)甚至上了瘾。而泰勒则是杰克内心深处想成为的那个自己,这个人是欲望可以随心所欲宣泄的杰克,他浑身充满了叛逆、残酷的力量,并且对于其他人有着神一样的号召力。最后他带领着成员们到处砸车放火,甚至成立了一支“军队”准备将城市里的几座大楼炸毁,这一切让杰克感到非常不安,却没有想到自己实际上就是泰勒。芬奇借助这部电影来表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两面,一面是会自我抑制,具有社会性的杰克,而另一面则是受动物欲望驱使的,反社会的泰勒。与之类似的还有《七宗罪》,电影中的主人公米尔斯心高气傲,作为警察又是正义的化身,他一心想追缉到凶手约翰,然而他也在约翰的设计之下,因为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杀死了约翰,成为被“七宗罪”惩罚的七个人之一。
由弗洛伊德创建,荣格等人发展的精神分析理论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后世诸多艺术创作与美学批评,并且在美国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通过对大卫·芬奇电影作品的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芬奇并没有对外宣称其将《梦的解析》视为“圣经”,但他确实对精神分析理论极为熟悉。在提及电影的娱乐性时,芬奇坦承自己想要拍摄的与其说是娱乐观众的电影,不如说是令观众印象深刻的电影,而他所举的例子便是《大白鲨》让其再也不敢在大海里游泳。这便是芬奇清楚电影与观众心理之间联系的一个例证。在芬奇的电影中,他无情地暴露着人们的潜意识场景,用影像语言揭示着人性的薄弱与不稳定之处,将人们的行为归因到人们的意识层面,给观众带来了极为难忘的观影体验。
[参考文献]
[1] 张巍然.通俗的哲学家——大卫·芬奇[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03).
[2] 赵丽琴,石勤.精神分析的焦虑理论述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S1).
[3] 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
[4]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