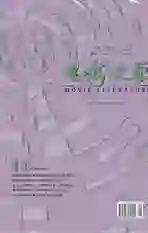第六代导演文化乡愁的影像美学表达
2016-06-14刘瑞红
刘瑞红
[摘要]乡愁是中国文学艺术里很重要的一个母题,乡愁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审美文化。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六代导演把电影创作的主要目光锁定在了失乡的流浪儿和都市外乡人等都市边缘人物身上,在对小人物进行边缘性书写时使作品具有深深的文化乡愁意蕴,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本文从第六代导演对文化乡愁表达手法的运用上来分析他们作品具有的 “不虚美不隐恶”的纪实美学风格、强烈的家国情怀等美学特点。
[关键词]第六代导演;文化乡愁;影像美学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经济方式的影响,数千年来国人一直具有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因生计、求学、为官等原因漂泊在外的游子往往将自己的思乡之情、羁旅之愁诉诸笔端,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被大家吟诵玩味,乡愁文学成为中国文学里一个永恒的母题。乡愁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审美文化,其浸润到中国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作品里——包括电影,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被归纳为“叛逆与反思”的一代的第六代导演偏爱以手中的镜头来寄一己之乡愁,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第五代导演的影像美学风格。现以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王小帅、张扬、管虎等的电影作品为例进行解读。
一、第六代导演的文化乡愁
第六代导演大多属于60后、7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等重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市场经济进一步繁荣,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上各种新事物、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南北差异也渐趋突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开始不断发生变化,农民工、移民、北漂等流动群体日益壮大。远离故乡和旧土的游子们在漂泊中渴望回归,但思乡、失乡的游子就像被剪断了脐带的婴儿,总也回归不到母体当中,这种欲回母体而不能的苦苦追寻演变成了现代乡愁。作为新世纪电影创作生力军的第六代导演或来自于农村、小城镇,或来自于皇城脚下,或因上学离开故土,或因城市改造搬离旧居,成人后都以大都市为阵地开始新的生活,因家庭、事业已无法回到故土,但对家乡、故土从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已经无法割舍,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回忆,对故土、旧家园的留恋则不时出现在他们的电影作品里,成为心头抹不去的文化乡愁。
二、第六代导演文化乡愁的表达手法
第六代导演对故乡、对乡愁的表达虽然具有各自的风味,但面对同一种情绪,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表达手法。
(一)故事发生地的选择
他们大致以四种方式来进行文化乡愁的表达:一是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自己出生的地方或成长的故乡,完成对故乡的观照和反思,如贾樟柯的《站台》《小武》《山河故人》均设定在他的出生地——山西汾阳,王小帅的《青红》设定在他儿时成长的地方——贵阳;二是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对国家、老百姓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张扬的《落叶归根》、章明的《巫山云雨》都不约而同地设定在了三峡库区;三是以目前生活的大都市为立脚点,以“都市外乡人”的身份表现离乡人群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状态,如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贾樟柯的《世界》等;还有一种就是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但面临城市建设,老房子、旧街景即将不复存在,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即将终结,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房子、旧秩序的留恋和致敬,如张扬的《洗澡》、管虎的《老炮儿》等。
(二)故事母体的叙述
第六代导演在故事的选择上普遍采用了流浪的母体。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国家、社会变革浪潮中,为了生存、生活或者为了梦想外出流浪、漂泊。流浪在外的游子经历了事业、亲情、友情、爱情、婚姻等挫败后,要么选择回归,如《小山回家》中被城市所不容的小山,《站台》中四处碰壁的文艺青年崔明亮,《洗澡》中痛失父亲和旧家园的大明,《山河故人》中发誓永不回乡但在外乡得了重病即将离世又重返故乡的梁子;要么为了梦想执著地选择继续流浪,如《十七岁的单车》中不向命运低头、一条道走到黑的小贵;还有一些却因失乡被迫继续流浪,如《落叶归根》中因建三峡大坝故乡已成为废墟的老刘灵魂无处安葬,被迫在路上,《小武》中回乡却因拿不出父亲提出的金钱诉求被赶走,不让其归家的“手艺人”小武。
(三)文化乡愁意象的设立
中国人在艺术创作上特别注重意境,组成这种意境的景和物我们称之为“意象”。第六代导演大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高校,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和文化熏陶,对意象的使用和设立独具匠心,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山河故人》中的千年古塔、黄河水、麦穗饺子、钥匙,《山峡好人》中不断出现的三峡美景,《站台》中的汾阳城墙,《洗澡》中的北京胡同里的老式澡堂、斗蛐蛐,《老炮儿》中的北京胡同、鸟笼、鸽哨声,既构建出了一幅幅具有地域色彩的风景画、风俗画,也营造出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化乡愁意味。而《青红》《站台》《老炮儿》《山河故人》里不断回荡的港台歌曲更是平添了浓浓的怀旧、感伤情绪。
(四)叙事方式的选择
第六代导演在文化乡愁的叙事上没有采用疾风骤雨式与当代社会飞速发展相适应的矛盾感、节奏感极强的情节,采用的恰恰是松散的叙事方式、缓慢的叙事节奏,甚至让剧情相对弱化,把主人公的命运和小人物、边缘人物的喜怒哀乐如涓涓细流缓缓地、细致入微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导演没有把个人的主观情感强行介入到影片里,只是让摄影机以一个个长镜头客观地展现给大家,这种具有东方内敛型的舒缓又略显压抑的情调既富有表现力,又具有戏剧张力,这在《三峡好人》《站台》等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第六代导演作品呈现出的乡愁美学风格
通过以上相同或相似文化乡愁表达手法的运用,第六代导演的影像作品也呈现出特有的美学风格。
(一)冷峻的画面风格
与“第五代半”导演霍建起构建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影像美学风格不同,第六代导演的乡愁影像镜头里大多是破败的、杂乱的、灰暗的画面,整体上呈现出冷峻的风格,如《青红》里贵阳氤氲的天,泛着冷光的潮湿的路以及逼仄的居所;《十七岁的单车》里主人公小贵的工作服和背包都是土黄色的,小坚的居住空间是杂乱的、灰暗的,胡同是斑驳的灰黄色,放学后娱乐的场所也是一些在建的工地里、脏乱的铁路旁;《站台》《小武》里的汾阳街景更是如此,城市建设把街道一条条“开膛破肚”。这些作品里即便出现了一些温馨、美丽的场景,也是以美景、乐景衬托哀景,如《落叶归根》中虽然老赵所经之路一直都是青山绿水,但却让观众无法内心舒畅、大口呼吸,因为背着好友尸体的他总是遇到恶棍式的饭馆老板、不讲信用的小货车司机,还有孤苦无依、提前花钱为自己办葬礼的老人;《三峡好人》中著名的三峡美景也因三峡大坝水位线不断升高,迤逦的风光和家园被江水一点点淹没。这些影像画面里也会出现被中国人崇尚的红色,但这些红色也跟施了魔咒似的不但没给主人公带来幸运和幸福,甚至还把主人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如在《十七岁的单车》中偷穿主人红裙、红高跟鞋,偷抹红嘴唇的保姆红琴,《青红》中接受农村恋人小根送的红色高跟鞋的青红,《站台》中崔明亮、尹瑞娟在城墙下燃烧的火苗,《山河故人》中涛不断变化的红色上衣等,导演们的文化乡愁以亮丽的景色为依托,采用反衬的修辞手法,给人以阴冷、凄婉的感觉,使作品构成了冷峻的审美基调。
(二)浓郁的草根情结
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农民工”群体,他们离开家乡和故土来到城市打工,大部分活跃在建筑工地、保姆市场、保安市场等,因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做一些脏、苦、累的活儿,有的被生活所迫做起了按摩女、小偷等,流浪在城市边缘成为都市外乡人。而在城市里也有一部分被称为下岗工人的群体,他们早年在工厂内做工,因工厂改制等原因下岗、失业,也与农民工一起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既为城市服务又被城市边缘化,这些都市外乡人和都市草根被来自外乡或同样来自草根的第六代导演一一吸纳到自己的影像作品里。《世界》里的主人公均来自农村或外乡,有的被灯红酒绿所迷惑出卖身体,有的保持纯真本性却被生活所欺骗,有的为了多挣几块钱晚上加班殒命在工地;《老炮儿》中六爷、灯罩儿等这些在北京狭窄的胡同里讨生活的老百姓,在遇到“新秩序”的挑战时为了“祖辈儿留下的规矩”和自身的尊严不惜豁出性命;《小武》中小武虽是个三只手,但却是“侠盗”,总是把失主的身份证偷偷塞到邮筒,好朋友小勇结婚时为了履行当初的誓言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依然送去礼金,却被小勇以来路不明退回,最后友情、爱情甚至亲情、人身自由也一并丧失。这些主人公不是英雄,不是社会主流,甚至身上具备不少被主流社会所诟病的缺点,但导演们没有去谴责、批判这个群体,而是真实记录他们的生存状况,在完成对边缘人物、草根人物的边缘性书写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流浪者、失乡人的人文书写。
(三)“不虚美不隐恶”的纪实美学风格
第六代导演在文化乡愁的表达上往往都采用纪实拍摄手法,将镜头对准离我们最近也最为实际的生活进行客观记录。他们镜头下的文化乡愁以真实场景、自然声音、自然光线、长镜头甚至非职业演员的方式出现,对普通老百姓的人生冷暖,小人物的内心情感,对城市建设中环境的破坏和重建不刻意去丑化和美化,只是用镜头冷静地、冷眼地看着和记录着。但作为观众却分明从《青红》《站台》《洗澡》《老炮儿》等作品里读到了导演自己的过往和生活经历,他们以司马迁做《史记》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来将普通小人物当成了重要历史进行展现,讲述他们这一代人对时代的感知和思考。如在《三峡好人》《世界》《站台》中反复出现的说着满口山西话的韩三明,既是生活中的具有乡土气息的韩三明,也是艺术里具有乡愁意味的韩三明,生活与艺术相互依托,既完成了现实主义的表达,也具有明显的纪实美学风格。
(四)强烈的家国情怀
被贴上“叛逆与反思”标签的第六代导演把目光投向在时代变迁中小人物命运沉浮的故事时,也不断对时代变迁下大社会与小人物的关系进行反思,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发生碰撞之时,也就到了价值观进行重构之日。这些远离故土流浪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望乡人和城市底层的小人物们虽然经历着西方文明、都市文明的冲击,但内心对故土、家园的守望,对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一直根植于内心。《洗澡》中,被深圳等沿海城市先进文明洗礼过的大明连洗澡都跟北京胡同里的老百姓们不一样——站着淋浴,深圳文化与澡堂文化相互碰撞,父子关系拧巴,但在中国意象里最富有乡愁意味的“水”的调和下,父子冰释前嫌,完成了浪子到孝子的回归。在北京城市化建设中,大明虽然与二明、街坊邻居一样对纯净、美好的家园充满不舍,但还是深明大义地配合代表国家身份的居委会进行搬迁。《老炮儿》里爱打抱不平的六爷虽然年轻时曾因“茬架”蹲过监狱,但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道义、规矩深植于其内心,在与新一代老炮儿的冲突中宁可“茬架”殒命,也要“一码归一码”地以布衣之身向中央纪委举报违法犯罪之徒,体现出了深深的家国情怀。
(五)无法去圆的悲剧美
第六代导演影像中的失乡流浪者的文化乡愁之所以总是萦绕心间无法忘怀,是因为故土的人和事随着历史大潮一路向前、无法挽回,如《洗澡》中的大明因父亲突然离世再也无法为代表故土和家园的父亲搓背;《落叶归根》中的老刘因三峡工程建设再也无法在故园安放灵魂;《青红》中父亲不计一切代价回归上海老家前夕青红却被小根强暴,为上海梦的实现蒙上惨烈的阴影;《山河故人》中到乐虽然脖子上还挂着象征家的钥匙,但这个“无父无母”的弃儿只能在异国风尘的畸恋中以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来为思乡情怀寻找突破口,体现出了深深的悲剧意蕴。
[参考文献]
[1] 第六代导演[OL].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177651-187662.html,2016-04-06.
[2] 孟君.“小城之子”的乡愁抒写——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的一种空间叙事[J].文艺研究,2013(11).
[3] 郭春燕.贾樟柯与第六代导演的“平民化”审美风格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