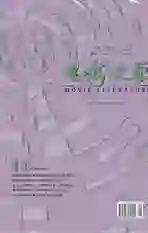当代生态纪录电影的镜头语言解析
2016-06-14刘丹
刘丹
[摘要]镜头语言是电影提供信息、与观众达成心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电影中每一帧画面呈现的形式。当代生态纪录电影为了让观众领悟到自然的神奇与美丽,更需要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努力营造出某种令观众心生向往的祥和、唯美意境,从而使观众对自然产生由衷的喜爱之情和保护欲望,达到影片传播生态责任,进行文明批判的目的。文章从画面布局的丰富性、光影运用的抒情性、色彩的协调性三方面出发,解析当代生态纪录电影的镜头语言。
[关键词]当代生态纪录电影;镜头语言;光影;画面布局
镜头语言是电影之所以能提供信息、与观众达成心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电影中每一帧画面呈现的形式。[1]一部电影中导演选择怎样的拍摄角度、机位、造型元素和剪辑手法等都将直接关系到观众是否能与影像融为一体,享受电影的魅力。一般情况下,与故事片之中导演可以大胆地使用夸张的色彩、大量的长镜头或短镜头蒙太奇甚至是分割画面不同,通常在强调真实性,所拍摄的对象全部取材于真实情境的纪录片中,导演往往会选择较为保守的镜头语言,从而令观众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影片的内容而不是某种气氛、风格和情绪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纪录电影不需要运用丰富的、具有技巧的镜头语言。以当代纪录片之中较为引人关注的生态纪录电影为例,影片为了让观众领悟到自然的神奇与美丽,更需要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努力营造出某种令观众心生向往的祥和、唯美意境,从而使观众体会到自然界之中各类生物的生存境遇,对自然产生由衷的喜爱之情和保护欲望,达到影片传播生态责任,进行文明批判的目的。
一、画面布局的丰富性
从电影本身的角度来说,生态纪录电影是对真实情境的再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镜头语言只是呆板的对生态环境、生态景观的摄录。摄影机在电影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只是记录,而是取代人们的眼睛进行观察,它本身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有着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热爱之情的。从电影摄制目的角度来说,生态纪录电影所关注的对象是生态圈,它所要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狭隘的生态观,电影要达到教化、宣传和批判的目的,这也就导致了电影中出现的景物往往是大多数观众所陌生的。[2]但是电影的价值又必须建立在观众的理解之上,只有观众对影片的内容与情节喜闻乐见,甚至耳熟能详,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解决,生态系统的最终和谐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对于被观察、被表现的对象,导演往往会对其赋予人性化的情感,这除了体现在拍摄动植物生长等方面的顺序、角度等具有拟人化的倾向外,还体现在运用多样化的画面布局来对观众视觉进行安抚。
在一部电影中,如果画面布局相宜得当,各有讲究,那么不仅从美学的角度观众能获取视觉上的享受,从教育性的角度来说,单幅画面之中蕴含的信息量也将得到扩展。比如,在生态纪录电影之中往往会运用长焦距、大特写拍摄,将被表现物置于画面之中的构图,这样一来主体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突出,二来背景尽管被虚化,但是依然能够对画面主体所生存的环境做出必要的交代同时还不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除此之外,在单部生态纪录电影中,甚至是在对单一对象的表现中,要运用到的构图手法还必须是多样的,如此才能避免观众的审美疲劳,并促使观众从尽量多的角度来观察对象。
例如,在被公认为不仅将鸟拍摄成极为美好的生物,且赋予了山、水、沙漠、绿洲等自然景观灵魂的《迁徙的鸟》(2001)中,导演雅克·贝汉从头到尾只是给观众叙述了一个鹏程千万里,鸟儿用双翼来实现回归的承诺的故事,但是这部仅有9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却耗费了摄制团队三年多时间和四千余万美元的投入。影片不仅跨越地域广,选择的鸟种类多,且在表现“飞行”这一行为本身时也针对不同的环境做出不同的画面布局,电影在开头简单介绍之后便停止了旁白,这在纪录片之中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贝汉用大量美不胜收、具有特定意味的构图取代了旁白。如在表现天鹅群以滑翔的方式飞越红海海面时,导演采用一个俯拍的大全景,天鹅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位于画面的中间偏右下方,其背景为整个红色的海面,白色的鸟展开双翼,身后则是它们脚蹼拍打起的白色浪花,其队形和留下的痕迹犹如人类所熟悉的飞机,也只有俯拍的镜头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天鹅伸直的脖颈和起伏的肩胛骨;而在表现大雁的起飞时,导演则采用平行水平线的视角,收录镜头之中的不仅有大雁群,还有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荒野之上奔腾的野马,雁群瞬间被惊起,占据画幅中下方大部分的黑色、褐色野马群和飞扬的黄色尘土赋予了整个画面某种厚重感,而大雁则在蔚蓝的天空中远去,让观众瞬间感受到同样是在迁徙活动中,自然展现出来的沉重与轻盈的鲜明对比。更为微妙的是,这种视角正好捕捉到了野马走后一只掉队的大雁,此刻的它显得极为孤独和脆弱,在前面万马奔腾的气势给观众造成震撼后,观众很难不为这只掉队的大雁而感到担忧。如若导演依然采用俯拍视角来表现大雁的飞行,那么一来观众的注意力将很快集中在地面上狂奔的马群,二来也很难看清落单的大雁。
除此之外,《迁徙的鸟》在表现白天鹅飞行的气势时借助覆盖白雪的树让天鹅迎面飞来,使天鹅似乎有着一种从仙境中出来的美感,在表现一只死于沙漠中的鸟时,则让沙漠占据了画面80%的空间,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沙漠之中寸草不生,毫无人迹,在这一背景下鸟干枯的尸体显得触目惊心,此时没有解说,它的遭遇也让人揣测有可能是在迁徙中脱水造成的。
二、光影运用的抒情性
在生态圈中,光被认为是生命之源,而对于人类的感知来说,只有光传播的存在人类才能够依靠眼睛来感受到物体的形态。在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艺术之中,光照也成为表现任何事物的先决条件,而光线所无法到达的区域则形成影,光与影不仅能够共同让人们掌握被表现物的存在,也能够在电影的叙事之中表现叙事者的情感、气氛甚至剧情。生态纪录电影与普通故事片一样,会在拍摄中使用自然光与人造光,而相比起通过人造仪器与设备制造的光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态纪录电影更倾向于选用由太阳产生的光线。使用自然光一是能够保证电影的真实感,让观众能够更好地产生作为第三者的旁观感,二是能够不影响或破坏动植物所栖息的环境,不干扰对方的作息规律,如在拍摄夜间出没的动物时,都采用夜视镜头而非采用人造光进行照明,让动物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处于“被看”的状态中,捕捉到动物最真实自然的一面。但是追求真实感也不意味着要付出牺牲审美体验的代价,相反,即使是对日光的运用,导演所选择的时间和角度也完全能够使被拍摄物呈现出醇厚的质感,贯注着导演本人的形象、情绪以及感觉,正如维·图斯拉鲁所指出的:“电影摄影就是在胶片上用光写作。”[3]
例如,在克劳德·纽利迪萨尼和玛丽·佩莱诺的《微观世界》(1996)中,导演运用不凡的光影技巧带领观众进入了昆虫生活的世界。在《微观世界》中,导演不但要保证观众将被拍摄物看得一清二楚,各种平时被人类忽视的虫子此刻都纤毫毕现,让观众得以大开眼界,还要保证光影具有某种美感,让观众意识到昆虫的“渺小”实际上也是大自然的伟大、神秘之处,昆虫是不可轻视和凌虐的。相比起《迁徙的鸟》,《微观世界》更加惜字如金,良好的光影运用也同样能代替旁白来对人类诉说道理。影片先使用逆光来拍摄树木,这是观众所熟悉的自然界之中的景象。在逆光中,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树木的轮廓和坚实有力的质感,然而当电影将镜头对准昆虫生活环境中的小草时,依然使用了逆光,并且有意使用了仰拍,大部分的阳光都被挡在了被拍摄物之外。在逆光之中,草和树木本身的颜色并不清晰,此时观众可以震撼地发现,他们在平日里觉得弱不禁风的小草身上看到了和树木几乎一样的轮廓和质感,也就是说,尽管对于人类来说草似乎可以随意地践踏或插拔,但是对于昆虫来说,它们就跟树木一样坚韧、笔直、挺拔,这就是“微观世界”的准则,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也就从宏观世界正式踏入了微观世界。
又如在拍摄雨珠时,《微观世界》也大量使用了逆光,与草、木不同,水珠不会呈现黑黢黢的轮廓,而是会将光线反射回来,并且雨珠是呈运动状态的,于是在镜头中倾泻而下的雨水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清晰、透明,具有迷人的动感。《微观世界》同样在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观众,这些有可能令人类厌烦的雨水对于昆虫来说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就像钻石、珍珠在人类眼里一样,是晶莹剔透、弥足珍贵的。
三、色彩的协调性
电影之中的色彩可以分为主观色彩与客观色彩,在常规故事片之中,导演可以大量运用主观色彩,来表达剧中人物的情绪或所面临的某种状态,如红色与凶险、欲望有关,黑色与压抑、悲哀有关,等等。而在生态纪录电影之中,导演一般只能如实表现被拍摄对象本身的固有颜色,包括对方的色相、明度以及饱和度。但一来,大自然本身就具有和谐的色彩美,大自然是人类最早的色彩美学导师;二来,导演依然能够在色彩的运用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首先,导演在选材上可以从内容出发,研究在表现对象的选择上以及在拍摄过程之中的时间变更与空间跨度等,进而确定整部影片之中的色彩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整体色彩风格。例如,在《微观世界》之中,整部电影的色彩基调就必须为鲜明的绿色。由于拍摄对象为栖居于草木或生长于草木的泥土之中的昆虫,电影中充斥着大量墨绿、深绿、翠绿、浅绿等颜色,绿色是整部电影的大背景,而其他与之搭配的颜色则或鲜明,或淡雅。前者如红黑相间的瓢虫,后者如淡紫色的薰衣草、蓝紫色的牵牛花、白色的蒲公英等。绿色背景既不会压住这些动植物的原本色彩,包括草绿色的蟋蟀,也会因为绿色背景的层次感而能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又不会在搭配中影响观众的观感,让观众感到突兀,因为在人类的潜意识之中,绿色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旺盛、蓬勃的生命力,这恰是与电影所要表现的生死轮回、忙忙碌碌的小昆虫们的生活是相契合的。从电影协调的色彩中也可以发现自然界本身万物繁茂或凋零时所产生的各种色彩造就了人类面对色彩时的生理、心理感受,而电影人则能反过来利用这种心理联结来对大自然进行刻画。
其次,导演尽管无法对自然物进行打乱、重组等,却可以通过对镜头角度的选取来制造纳入框内的色彩种类,从而创造出能给予人们舒适愉悦的视觉感受的协调的色彩。例如,在埃里克·瓦力执导的《喜马拉雅》(1999)中,导演所拍摄的藏人的衣服、帽子、围巾等往往是深红色或金黄色的,给人以一种低沉、温暖感,而导演在拍摄人物时往往会有意将人物身后的皑皑雪山和湛蓝的碧空收入画面中,从而使得浅蓝、白恰到好处地突出了皮肤黝黑、黑发并身穿红、黄衣物的藏民。背景颜色体现出了喜马拉雅山脉高远、缥缈的美感,而人物身上的颜色既是当地人的民族喜好,在影片的审美语言中也象征了某种热烈、坚强、淳朴感,这也是藏人在当地恶劣的条件下依然能够生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从这样的颜色对比之中,观众可以微妙地感应到藏人与当地环境的关系,即以一种原始而有力的态度生活,既不屈从于自然,也不凌驾于自然之上。
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保护地球上广阔的生态景观,让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互利共生关系的必要,而在“读图时代”[4],生态纪录电影无疑在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家园意识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当整个当代电影的影像在数字技术与多媒体发展的作用下取得惊人的成就时,生态纪录电影也同样要在形式与内容上不断地推陈出新,在生态美学的指导下将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镜头语言,如光影分配、色彩的运用上精雕细琢,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受众群,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从而代替沉默的大自然发声,将原本单调、枯燥的生态知识以美轮美奂、真实鲜活的画面呈现给更多的人。
[参考文献]
[1] 傅晓姣.当代影像镜头语言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2] 万修芬.雅克·贝汉生态纪录电影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3] 潘秀通,万丽玲.电影艺术新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 汤天明.读图时代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