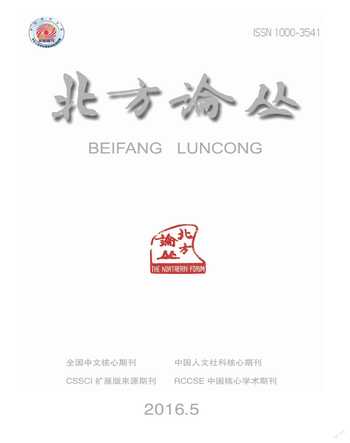指称问题:抽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难题
2016-06-09孙杨
孙杨
[摘 要]指称问题研究之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既有的分析范式——主要是就“语言”来看问题——中并未穷尽,“指称何以可能”的问题还有待于进入哲学探究的视野。澄清指称问题的发生机制,即指称问题缘于由语词与所指构成的指称之抽象二元对立结构,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层面上重新审视指称问题,也能在相当程度上使人们得以避免在生存实践领域囿于指称的抽象二元對立结构而可能导致的一系列后果。
[关键词]指称问题;语词;所指;抽象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59-07
Abstract: The referent of a word is uncertain even without referent that is reference problem, and it obsesses human beings intelligence. However,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probably one can only base on reality to regulate language, or make the meaning of word get rid of reality and to be independent. But the core question of “how word to refer” is ignored by reference theory. This paper conclude that reference problem derives from the referential dualistic abstract structure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word and its referent, and referential structure lies in linguistic abstract of speech in existence practice. That is, reference problem is an abstract problem of language per se, and which is possible only in the abstract language.
Key words:reference problem; word; reference; abstract
一
指称(reference),通常被视为语言(language)与实在(reality)相联系的基本方式。它作为哲学的一个主题是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事情,这与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是紧密相关的。指称的主题化,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或人类知识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所涉及的是哲学史上很古老、很难解的“两个世界”的问题。指称概念作为反思人类知识并寻求真理的有效审查工具,力图将人类知识实证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无所指的语词和由之构成的语句从已有的知识中排除掉。在这方面,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哲学家所处理的“无所指的语词和由之构成的语句”的问题,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指称问题。
指称问题一般是指语词的所指不确定的问题。例如,一个人说:“我的电脑出问题了。”其中“电脑”指称什么呢?可能是说电脑外壳摔破,也可能是硬件破损,还有可能是系统与软件出了问题,如果这个人有两台或是几台电脑,那么也可能是这一台或是那一台甚或所有电脑都出现故障……外壳、硬件、软件等,所有这些可能的对象都可以是“电脑”的所指。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觉得句中的“电脑”一词在使用上有什么问题,因为生活中的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所谓的所指不确定是由于用词不准确造成的,如果能够明确地指出“这台电脑的风扇出现故障”,应该就可以避免语词的所指不确定的问题。只是这种解决方案的可操作范围事实上是有限的,或许对这一事例来说是合适的,但对于更为复杂的情况来说,则无异于“鸡肋”。
语词相比世界中的事物而言,无疑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语词指称无限的事物,就必然要求语词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用范围,而这种灵活性和更大的适用范围就造成了语言的模糊性。关于语言的模糊性,张乔在《模糊语义学》一书中说,模糊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征,也是思维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且“模糊词语,如同其他类型的词语一样,在自然语言中客观地存在,并且在语言交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p.197)。如果从语言的模糊性来看待指称的话,那么所指不确定的问题可谓在所难免。如果无视语言的模糊性,一味去追求精确的指称从而进行长篇累牍的赘述,那么语言反倒会成为生活中不堪重负的累赘。这样的话,倒不如像《格列佛游记》中飞岛国的学者那样,干脆每个人都背着装满实物的袋子以代替语言。
所指不确定的问题的极端形式是无所指的指称问题,这是困扰语言哲学家们的一个理论难题。如果说,上文中的方案被弃之不用是由于得不偿失,但总归可以给人以慰藉。因为这至少在可能性上许诺了语词的所指是确定的。无所指的指称问题则不是这般好相与的,这一问题的出现可能会导致语词和所指之间的联结的破裂,给人类理智造成巨大的困扰。看一看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称,如“女娲”“孙悟空”“哈利·波特”“四不象”“金山”“飞马”等,这些语词指称什么呢?人们没办法为这些语词指出对应的实在,那么按照指称论指称论是从属于意义理论的其中一种类型,它以语词的所指作为其意义的承载者。的原则,这些语词就应该是无意义的。令人为难的是,说这些语词没有意义恐怕并不合适,因为在面对这些语词时人们仿佛能够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还可能会联想起某些形象来。这种情形无疑动摇了指称本身的合法性。
二
如果在应对无所指的指称问题时,采取坚守指称论的做法,那么现有的语言必然会被大大缩减,因为语言中所有无所指的语词都应被消除。换言之,语言只能单纯地作为自然实在的镜像存在。这不但禁锢语言形式化发展的可能,而且如果人们当真采取这种极端的指称论的话,也在很大程度上撤除人类生存实践通向自由的阶梯。因为人类的生存实践一旦没有语言的指引,就只能在一片昏暗中摸索前行,文明的发展也只能寄希望于某种机缘巧合。这对所有人来说,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彻底的绝望。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是人们难以接受的。
在坚守严格的指称论之外,应对指称问题的方案还有两个:一是扩大对实在的理解,将观念和概念均视为是语词的所指,以化解无所指的指称问题所造成的困难,此种方案可称为“广义所指”“指称”(reference)总是与“意义”(meaning)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对指称的研究从属于语义学研究范围,而且“所指”也是意义理论的诸种类型之一。观念论和概念论同样是意义理论的类型之一。明确且集中论述意义的观念论的哲学家当属洛克。与指称论不同,意义的观念论主张语词的意义就在于它所代表的观念(idea)。概念论则专指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是音响形象和概念联结在一起的两面一体的心理实体,音响形象和概念是语言实体本身的内在规定并且是语言内在的不可分离的构成要素。上述三种意义理论都在语言——语音及其衍生出的文字——与意义之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特征在指称论和观念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是在语言外部寻求意义的承载物,“语词—所指”和“语词—观念”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至于概念论所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特征,单从语言实体的“能指”—“所指”这一成对术语的使用中就可看出些许端倪。只是概念论与前两种理论略有不同,这种结构性是在语言实体内部要素的对立中体现出来的。在笔者看来,上述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关系”完全可以用“指称”来表示。当然,这种说法只能是基于对“指称”做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解。;二是以语言为模型或目标,通过生存实践创造出现实的所指以维护指称论。从反对指称论以实在去规范语言的角度看,这两种方案的思路是一致的。它们不是以实在为基准来审视语言;相反,是以语言为基准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实现语言的指称。只不过,这两种方案对所指的具体规定有所差别而已。这两种方案的确是有的放矢,看起来也似乎让人信心满满,但无奈事与愿违,这些方案可能导致的困难,并不亚于坚守狭义指称论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影响。
在指称关系中,从语词出发去寻找所指会遭遇所指不确定的问题;反之,从所指出发去寻找语词,则会遭遇语言的限度问题。语言的限度问题只能通过语言的形式化发展予以缓解,而且语言的形式化必须受生存实践的制约,否则,语言就成为空中楼阁。在语词和所指二者之间,语词有明显的主动性优势,这种优势得自于语言自身的形式化特征。语言可以暂时脱离具体的生活情境,获得相对独立的形态,并进行形式化的组合和繁衍。可是,以“广义所指”的方式去消解指称问题,无疑会进一步肯定并发挥语言的形式化特点,这也就意味着语言的形式化获得无限制的通行证。倘若以“广义所指”修改对指称论的理解,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语词指称什么——具体事物、观念、概念——都可以。这的确能够有效消除无所指的指称问题所加诸理智上的困扰,但是,这也会造成在指称关系中语词一方独大的局面。形式化一旦获得这种权限,语言就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自行繁衍,而语言与生存实践之间的间接性关联,也必将消失殆尽。当所指可以被任意规定时,实在就失去了单纯作为所指的确定性,语词反倒成为唯一可以被人牢牢抓住的东西。如果借用索绪尔的术语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分别是指音响形象与概念。本文在此处使用这一对术语的方式(在指称关系中“能指”表示语词,“所指”则表示被指称的对象)同它们的原意有所差别,这种使用可以视为对索绪尔术语的引申。来说,就是“能指”得以摆脱“所指”的约束,“所指”完全成为“能指”建构的产物。
事实上,语言相较于实在的优先性早在指称未被主题化讨论之前就已然如此了,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姑且不论语言对实在的优先地位在采用“广义所指”的方案之后会在程度上有多大改变,语言能指的优先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的生存实践造成了影响。对这一影响的考察是衡量这种方案是否可取的重要依据。
在把握能指优先性对人类生存实践的影响方面,拉康和鲍德里亚都做过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作分别以个体和社会角度为侧重对语言能指的优先性问题所做的批判性表达。
拉康吸收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形成了其独特的人学理论。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能指与所指是构成语言符号整体的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与索绪尔不同,拉康认为,能指与所指是互不重叠的两个网络,并且能指相对所指来说具有优先性,而且“单单能指就足够保证了整体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一贯性”[2](p.398)。拉康的人学理论认为,个体在降生之初就通过语言的询唤(interrogation)认同于语言,个体在被命名的同时,被建构成一个主体。这个用来命名的语词,在拉康看来,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它是内在的空无,并意味着主体的死亡。也就是说,个体在被命名为主体的时刻起,主体就被语言能指所取代了,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是不可能的无。能指对主体的建构还不仅限于最初的命名,当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介入到语言中时,语言更是作为“他者”时刻统制着人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身份往往被粘上各式各樣的能指标签,在拉康看来,正是这些能指标签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所谓主体间的交往不过是能指间的交往,至于所指并不为人所关心。
拉康的理论,无疑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别样的人生图景。透过这一图景,个体的生存完全成为一场骗局,而且根本无法说是谁精心编织了这样一场骗局,因为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不仅引人猜想,人在面对语言时,究竟可不可能做些什么以避免能指在本体论上的篡位呢?换言之,主体是否真的就如拉康所言是为语言所掩盖的空无吗?在拉康的理论中,这种猜想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在拉康看来,个体面对语言根本无力反抗,而且所有人自以为是的反抗,只不过是落入又一个新的——或许是略有差别的——能指牢笼中。
不论人们接受与否,拉康的理论都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由于语言能指优先于所指而在个体层面所引发的后果,尽管这一理论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事实上,能指优先于所指对人类生存实践的影响并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人们在社会生活层面同样会遭遇这个“能指的牢笼”。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着社会生活层面中的能指牢笼。
鲍德里亚指明,现代社会中的消费品已然是一个有序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物品丧失了其客观目标、其功能,变成了一个广泛得多的物品总体组合的词汇,其中它的价值在于关系”[3](p.104)。这也就是说,消费品不再是以满足具体的生存需要为人所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符号被消费。消费品作为符号的意义,完全是以能指为中心的,至于符号所指的对象则微不足道。人们在遭遇消费品时面对的不再是某一具体的物,而是整个物的系统,物只能凭借在系统内与他物所形成的关系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消费品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而是作为符号被消费。现代社会的符号性消费,消费者丝毫没有可选择的余地。因为消费不再是消费者的享受,而是具有生产性的、可进行符号化操作的社会功能,消费者只能在作为符号的消费品系统中进行选择。
应当说,鲍德里亚阐释现代消费社会的论述不似拉康的理论那般令人绝望。这可能是由于在鲍德里亚理论中的能指对所指的优先性,并不如拉康的理论表现得那么彻底。尽管商品的符号系统对消费者实行了某种统治,但人们在被迫进行符号性消费的同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费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便如此,鲍德里亚的理论还是为人们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相当严肃的生活场景。
拉康与鲍德里亚的理论分别呈现的在个体生成过程中,作为他者的“能指”和现代消费中作为商品系统的“能指”都明显盖过“所指”,并对所指发挥着建构性甚至强制性的作用。因此为能指对所指的优先性冠以“能指的牢笼”这样的说法似乎也不为过。用“能指的牢笼”去评判“广义所指”方案会发现,语言与其所指间本就是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本身就需要人们费尽心思地去应对。如果在此基础上,仍然以“广义所指”的方式,试图应对所指不确定甚至无所指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问题的进一步加剧,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做法。基于这种考虑,“广义所指”方案似乎并不可取。
应对指称问题的另一种方案是力图为语词创造出现实的所指以维护指称论。为表明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只需回顾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就能给人足够的信心。因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绝大部分事物,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造出一座金山、一匹飞马来。
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相当程度上都受益于语言的指引和生存实践的创造。但受语言指引的生存实践在为人类生存境况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的生存境况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因为语词没有所指,也就意味着,由语言所塑造的目的与现实的生存实践之间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这很可能会导致受这些没有所指的语词所塑造的目的所指引的生存实践难以确保实践的成功。人们可能会在现实的生存实践过程中,遭遇诸多语言并未关涉到或言之不详的具体情况,这就为生存实践带来难以预计的风险。并且如果无视这种风险,坚持以语言的所指作为实践的最终目的,就可能会对人们的生存境况造成破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人们曾一度受“金丹”的指引而进行生存实践,炼制和服食金丹的结果却是人们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人们沉溺于一个无所指的语词所构建的目的,并努力为之奋斗期望使之成为现实时,就可能会面临这种风险。
对此,人们倒不必过分苛责语言,只能是保持警醒并尽可能使语言的指引相对完备,避免失利的情况出现。可是,如果将语言的“指引”功能代之以“指称”的话,情况就会有所变化,人们很可能会遭遇到“所指的统制”问题。所指的统制,指的是语言对生存实践的导向演变成一种强制的硬性规定。在这种统制之下,生存实践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沦为语言“现实化”的工具。反倒是语言——或者说语词的所指——成为生存实践的最终目的,这无疑是语言异化的一种表现。
一般来说,语词的所指不确定甚至无所指的指称问题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难题。但是,应对这一问题的结果,却把指称问题从理论层面延展到实践层面。这种延展是通过语言对生存实践发挥指引作用实现的。以此来说,指称问题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难题。而且为应对理论层面的指称问题所采取的方案,无论是坚守严格指称论所造成的语言指引对生存实践的禁锢,还是“广义所指”所造成的能指统治的加剧,抑或是“所指的统制”在生存实践中可能导致的后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境况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些生存实践层面的指称问题,比之理论层面上的指称问题对人类理智所造成的困扰来说,是更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
三
在应对指称问题时遭遇的困难,必然会促使人们对指称本身加以研究。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的研讨,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指称理论重点讨论了语词如何指称的 “机制问题”(mechanism question)[4](p.1),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由弗雷格开创的语义指称理论,即语词的所指需要凭借意义进行确定;二是克里普克(Saul Kripke)提出的因果指称理论,即人们通过最初的命名仪式和历史因果链来确定语词的所指;三是塞尔(J. R. Searle)提出的意向性指称理论,即语词的所指由意向内容所确定。
关于指称的研究一般追溯到弗雷格的“论意义和所指”德文“ Sinn”一词,英文一般译为“ sense”或“meaning”,中文译为“涵义”或“意义”。在中文译本《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1994年版和2006年版中,王路先后使用“意义”和“涵义”两种译法,对此,他做出的说明是国内文献中人们惯常使用“涵义”一词。在他看来,“意义”和“涵义”,这两个词的差异不会给理解弗雷格的思想造成问题(详见《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2006年第1版“再版译者序” )。江怡在《分析哲学教程》一书中和陈嘉映在《语言哲学》一书中对“Sinn”也使用了“意义”的译法。出于术语协调性的考虑,本文采用“意义”的译法,并在必要时对相关引文进行局部改写。德文“ Bedeutung” 一词,英文常译为“ reference”与“referent”(Max Black,参见“ Introductory Note” of “ A Translation of FregesUber Sinn und Bedeutung”,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ume 57, Issue 3 ( May, 1948), p.208.)、“ meaning”( C. K. Ogden,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New York: Barnes&Noble Books, 2003, pp. 24-25.)或“ denotation”(参见Bertrand Russell: “ On Denoting”, Mind, New Series, Vol. 14, No. 56(Oct., 1905), p. 483.)等。从“Bedeutung”的术语使用情况来看,大致可以推論,英语学界就该术语并未达成明显的共识。在Michael Beaney所编辑的The Frege Reader中,对“Bedeutung”一词并没有做英文翻译(参见The Frege Reader, edited by Michael Beaney, Oxford: Blackwell, 1997, p. 151.)。中文一般把“Bedeutung”译为“意谓”(王路)、“所指”或“指称”(肖阳、涂纪亮)。韩林合在《〈逻辑哲学论〉研究》一书中对“Bedeutung”和“bedeuten”分别使用了“所指”和“指称”的译法(参见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为将“Bedeutung”或“reference”与从中引申出的“bedeuten”和“refer”相区别,也为了突显本文所关注的联结语词与其所指的结构性联系,本文对“Bedeutung”采用“所指”译法,同时用“指称”标示语词和所指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及指称行为。指称理论中的“所指”与索绪尔的“所指”(signifié, signified)不同,但“所指”在指称理论中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索绪尔理论的引申性使用,特此说明。(Uber Sinn und Bedeutung)一文。该文使指称逐渐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专门问题,开创语义分析研究的先河。不仅是对指称的讨论,整个分析哲学运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经典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弗雷格著作的影响。
按照弗雷格的观点,语词弗雷格的“语词”包括专名与概念词。在“论意义和所指”一文中,弗雷格是针对专名做出的意义和所指的区分。但是,在“对意义和所指的解释”(Comments on Sinn and Bedeutung)一文中,弗雷格还说道:“我在一篇论文(《论意义和所指》)中首先只对专名(或者,如果人们愿意,单称的名)区别了意义和所指。对概念词同样也可以做出这种区别。[中略]原则上说,相应每个概念词或专名都有我所使用的那样的意义和所指。”(《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20页,文字略有改动。另见The Frege Reader, edited by Michael Beaney, Oxford: Blackwell, 1997, pp. 172-173.)基于弗雷格的这段话,除了特别涉及专名与概念词的区别,本文对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的讨论不对二者进行区分,一律使用“语词”进行表述。有意义也有所指,并且语词的所指需要借助意义来确定,因为从语词进到意义并从意义进到所指的步骤受逻辑的要求,否则人们便无法谈论所指。在弗雷格看来,意义与所指之间的地位并不对等,即便确认了语词的意义,所指是否存在也是不确定的。用弗雷格的话说:“人们理解一种意义,但由此并不能肯定也有一个所指。”[5](p.97)文字略有改动,笔者把“涵义”“意谓”改为“意义”“所指”。英译本内容如下: “ In grasping a sense, one is not certainly assured of a reference.”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的一系列演讲中就指称 “提出一个比业已接受的观点所谓“业已接受的观点”主要指摹状词理论,克里普克并不赞同摹状词理论,以及簇摹状词理论。所作的解释更好的解释”[7](p.95)。国内学者将其概括为:“名称是通过一个最初的命名式和一条历史因果链指称对象的。”[8](p.3)这就是说,语词在传播中形成了信息传递的历史链条,因此,所指的确认需要回溯到最初的“命名仪式”(baptism)。克里普克认为,命名仪式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或者是通过摹状词确定所指,或者通过实指(ostension)来确定。对克里普克来说,命名方式并不是确定语词所指的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那根实际的传递信息链条”[7](p.94)。克里普克对指称所提供的这种历史性的解释被称为历史因果指称理论。
意义与指称是语义学的主要概念,但语用学也对指称做了很多说明。塞尔的意向指称理论就是在语用学层面对指称机制做出的阐释,并使对指称的研究深入到人的心理层面。因此,塞尔指出:“指称是一个言语行为。”[9](p.28)言语行为是意向性的表现。在他看来,说话者指称的对象与意向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所有的所指都来自(宽泛解释的)意向内容的功效,不论该所指是经由名称、摹状词、索引词、标签、标示、图画还是其他获得的”[9](p.265)文字略有改动,笔者将“指称”改为“所指”。原文如下:“ All reference is a virtue of Intentional content (broadly construed), whether the reference is by way of names, descriptions, indexicals, tags, labels, pictures, or whatever.” 。
经过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的精细研讨,指称问题日益成为现代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毫无疑问,现代哲学研究所积累下来的相关理论财富已经很丰富,其中不少学说深刻地更新了人们对传统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上述三种典型的指称理论是就“语词如何指称”的问题做出的解释和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化解理论层面的指称问题提供帮助,只是它们对前文所述的延展至生存实践层面的指称问题来说,其效用却有限。这是因为指称理论并不是把指称本身作为其研究的對象,而是将其作为探究语词及其所指如何进行关联的前提。指称理论以“语词如何指称”为其核心问题,而更具前提性的“指称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不为指称理论所重点关注。在指称理论中,问题的焦点是语词如何指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语言与实在的联系尚能确定。一旦出现无所指的指称问题时,且人们又难以决断语词如何指称的争议,指称本身就会成为难以决断的问题,进而人们也就可能面临在语言与实在二者间的抉择问题。这已然超出指称理论的研究范围。这种局面,不应当简单地归咎于指称理论自身还不够完美,而应理解为研究范式中问题意识、理论前提,以及研究范围的差别。这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在继承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理论财富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其他范式深化并扩展对指称问题的研究。
四
指称问题研究之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既有的分析范式——主要是就“语言”来看问题——中似乎并未穷尽,某些方面的重要议题,甚至还有待于进入哲学探究的视野。指称问题的发生根源就是指称理论尚未涵盖的问题之一。
“指称”作为一个二元性的关系,联结着语言与所指,以语音和文字形态出现的语言是指称的一极,所指则是与语言相对应的指称的另一极。指称得以可能,需要满足两个最起码的条件,即指称关系的两端——语言及其所指——都是可能的。
关于语言,目前尚没有绝对权威的定义。潘文国在《语言的定义》一文中,收集整理了19—20世纪中外关于语言的68种定义;于全有在其《语言本质理论的哲学重建》一书的附录部分列出了“语言定义百态”,涉及国内外有关著作和工具书中关于语言的122种定义。单从所搜集到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对语言下定义包含多么复杂的情况。在百余种定义中,人们实难选出一个关于语言最权威的定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定义能够涵盖语言的全部。奥格登和理查兹认为:“一切定义实质上都是特定的;它们仅与某种目的或情境有关,因此仅适用于某个限定的领域或‘论域” [12](p.101)。所以,本文在提出对语言采取何种规定之前,先对这些定义做一番梳理,看看这些定义都是就什么来定义语言的。
这些定义大致上可以被概括为四类:交际工具、音义系统、存在形态和活动方式笔者以于全有的“语言定义百态”为材料,对这四类关键词做了计数,每一条定义种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只计为1,122条定义中体系或系统出现了66次,工具或手段出现了49次,存在形态相关的出现了10次,活动方式相关的出现了16次。在诸定义中,有些条目是仅就一个关键词下的定义,但不乏做综合定义的条目,特别是从工具与系统两方面来综合定义语言。。在此分别各举一例。斯大林:“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13](p.561)索绪尔:“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4](p.37)吕叔湘:“语言就是人们说的话(用文字把话写下来,当然还是语言)。”[15](p.7)钱伟量:“语言是人们借助于特定的意指符号系统进行社会交往的活动。”[16](p.266)在笔者看来,这四类定义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类,即言语定义与语言定义,其中,交际工具和活动方式是就言语所下的定义,而存在形态和音义系统则是就语言所下的定义。
言语与语言,这两个概念通常来说并没有得到足够严格的区分,而常以“语言”统称两者。所以,这就造成“语言”有时指语音或文字,例如,帕默尔所说的:“语言是为了影响听者的行为这一特殊目的而发出的声音”[17](p.16);有时又指活动,例如,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 [18](p.56),或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语言仅以实践性的状态而存在”[19](p.20)。言语与语言,实乃两个不同抽象层次的概念,不可统而论之。换言之,如果不厘清言语与语言之间的抽象层次的差异,就难以准确把握言语或语言对人类生存实践的意义。为此,本文自觉地对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别使用,并力图从二者的抽象关系入手来阐释言语的主题化实质与语言的形式化特征。
就语言来说,它是在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不论人们对语言的起源问题存在多么大的争议,语言都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先于我们这些对之进行反思的每一个个体。语言的事实性存在是对之进行反思首先要面对的境况。不过若只停留在此处,就很可能会错失掉理解指称的关键。因为一旦继续深入探究语言的本质就会发现,语言乃是对言语进行抽象的结果。语言实质上是从言语与非言语的实践活动之间的“程式化规约”所谓程式化规约,指的是言语与非言语的生存实践之间形成的约定性的稳定配合。可参见钱冠连的《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书中作者对言语的程式化做了集中阐释。中脱离出来的抽象物。当人们面对语言时,不同于言语所展现出来的生存实践的场景,语言世界乃是抽象的景观。脱离了言语的实践基础,语言就只是空洞的声音和符号。这样的声音和符号既无法解释,也无法参与言语与生存实践之间所形成的程式化规约。意义或指称的必要性是由语言的抽象所导致的,意义是人们在面对从言语中抽象出的语言的人为设定。换言之,语言与意义都是抽象的结果。语言的本质就是抽象的,如果说语言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那么也只能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来说才是如此。意义的问题由此发生,指称也随之一道登场。
语言需要意义,这实际上就体现着指称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指称是随着语言从言语中抽象出来一道产生的结构性的抽象关系。要求必须有一个与语言相对应的所指,这是由指称的抽象结构所决定的,指称问题缘于由语词与所指构成的指称之抽象二元对立结构,这一结构出自对生存实践中的言语所进行的语言抽象。也就是说,指称问题乃是一个抽象性的语言问题,它只有在抽象语言层面上才是可能的。
抽象是语言的本质所在,对所指来说也是如此。指称论中的指称或是命名,都只有在语言的层面上才是可能的。因为不论是言语,还是生存实践,均不涉及指称的问题。在生存实践中人直接与世界中的事物相关联,实践是主客统一的现实活动。对言语来说,它所面向的是非言语的生存实践,而不是作为语言所指的实在,更不是观念或概念。只有在抽象的语言的层面上,由于脱离了浑然一体的生存实践以及言語,才可能生发出语词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的指称关系。
指称问题的生发源于对言语的抽象结果,即语言所做的再抽象,再抽象的结果是与实在相对立的语言,以及与语言相对立的实在,它们都是言语同生存实践相脱节的结果,是某种异化的产物。由此,指称便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人们所遭遇的指称问题,都是囿于指称的抽象二元对立结构所导致的,其抽象性质就决定了仅在语言层面不可能真正化解这一难题。
结语
囿于指称的抽象二元对立结构,人们很可能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都遭遇到指称问题。理论层面的指称问题是指语词的所指不确定甚至无所指的问题。在指称结构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在语言和所指两端进行抉择:要么以语言为基准为语词创造所指,要么以所指为基准重新厘定语言范围。这两种解决办法,都把理论层面的指称问题延展至人类的生存实践层面。前者直接把指称问题引向生存实践层面,后者也通过语言与生存实践之间的关联对人类生存实践造成了并不可喜的影响。不论是出于化解理论层面上的指称问题的需要,还是出于对语言同人类生存实践之间关联的考量,指称问题都不单纯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且实践层面的指称问题是更关乎人类生存的难题。
指称问题,只是在语言层面才得以发生。指称问题在本质上是对生存实践进行主题化,并进一步做语言抽象所导致的抽象问题。在明确指称的抽象结构与发生根源的基础上,对语言做言语和生存实践的反向还原就能够化解指称问题。也就是说,将所指不确定或是无所指的语词放置到言语中,进而放置到生存实践中,考察它究竟是对哪一部分生存实践的主题化,以及它意图指引或指向哪一种具体的生存实践,这样,理论层面的指称问题便无从发生。
对指称问题的化解,并不意味着指称概念就会彻底被消除。本文对指称问题所做的生存实践还原只是为了化解成问题的指称并使之祛魅。但生存实践中的指称概念或指称行为,不会仅仅因为一篇论文就被彻底消解,事实上,任何论文都不会实现这一目的。对言语做语言抽象所生发出的指称概念,其发生历程呈现出一种必然性,换言之,指称概念仍依托语言而存留。
生存实践中的指称概念不但可能为生存实践提供某種目标以发挥指引作用,而且会造成语言对人类生存实践的异化统制,进而对人类的生存境况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生存实践层面的指称问题远比理论层面上的要严肃和复杂得多。人们的生存实践受语言的指引,因此,实践层面指称问题的化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理论层面上对语言指称结构的反思与批判。对指称抽象结构的批判,可以为人们在生存实践中应对语言的指引或是异化统制树立指称概念的非强制性原则。如果在生存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保持这种自觉,就能够使人们的生存实践不为语言的指称结构所挟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语言统制生存实践而可能导致的后果。
[参 考 文 献]
[1]张乔.模糊语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法]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Reference and Referring[M].edited by William P. Kabasenche, Michael ORourke, and Matthew H. Slater. London: The MIT Press, 2012.
[5][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M]. edited by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7][美]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梅文译.涂纪亮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8]郭贵春,刘高岑.指称理论的演变及其语境重建[J].山西大学学报,2003(3).
[9]J. R. Searle,Speech Ac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0][美]约翰·R·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M].刘叶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John R. Searle, 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美]C.K.奥格登,I.A.理查兹.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学的研究[M].白人立,国庆祝译.林书武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3]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4][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法]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吕叔湘全集:第6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6]钱伟量.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英]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李荣,等,译.吕叔湘,原校.周流溪,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8][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M].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作者系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陈 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