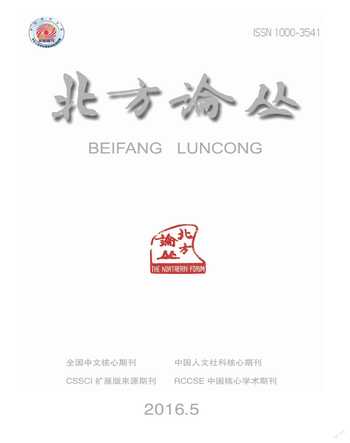中国文学对日本平安时期物语文学的影响
2016-06-09王洋
王洋
[摘 要]《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分别是日本最早的虚构物语及和歌物语,这类单纯描写私人感情的浪漫文学似乎颇受日本读者喜爱。不但作品本身超越时空流传至今,而且这种文学样式亦影响后世,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并确立了日本文学无政治性的传统。然而,作家创作之时,为了顺应汉学风潮,也为了使物语内容更为丰富、情节更为生动,除了在作品里融入大量与该物语主题有关的,具有传奇性、浪漫性的小说、汉诗文外,还撷取具有讽喻性、教育性之汉诗文里的各种语汇及知识,使得两部作品都洋溢着浓郁的汉文学风味。
[关键词]平安时代;白氏文集;神仙传;竹取物语;伊势物语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48-05
日本从平安时代初期开始全面推行唐风运动,即对唐文化的消化理解,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下汉诗文成为朝廷的正式文学。嵯峨天皇及淳和天皇相继令官方编撰《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及《经国集》等汉文诗集。当时,日本以官员、僧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但大量阅读中国典籍,同时以汉文创作诗歌也成了时代的风尚,《都氏文集》《菅家文草》等汉诗文集相继问世。然而,平安中叶后,随着遣唐使的废止及假名文字的出现和推广,日本文学家们开始运用假名撰写和歌、日记、物语等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当时就很受欢迎,并且影响后世,成为日本所谓“国文学”的源头。这些作品尽管是用日文撰写而成的,却有浓厚的中国文学风格,于物语文学上体现尤为明显。究竟中国文学给予日本文学重要源头之一的物语文学何种影响,这一问题正是本文关注焦点所在。
一、《竹取物语》与唐传奇中的神仙思想
《竹取物语》在日本平安时代就被称为是物语的肇始,但其确切的成立年代却不甚清楚,只能大致推测在9世纪后半段至10世纪前半期这一时间范围内。至于作者,也是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但可以推测其内容应与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关联。中日多位学者认为,《竹取物语》是受到了中国民间故事“斑竹姑娘”的影响[1](pp22-31);甚至有的学者论证《竹取物语》简直就是中国传说“斑竹姑娘”的日本翻版。斑竹姑娘这一民间故事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晚,最早见于20世纪60年代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金色凤凰》一书,该书由田海燕搜集大量的中国汉地及西藏地区的民间传说故事编纂而成。而此前,中日典籍都没有“斑竹姑娘”这一故事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明确记载,因此,也就无法断言二者之间有影响关系。所以,日本学者日三谷荣一荒唐的认为,“斑竹姑娘”是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入侵西藏时,由《竹取物语》或是类似的日本口传求婚难题故事,传入中国后而本土化的结果[2](p76)。
《竹取物语》的“升天谭”部分,亦即沦落于人间的神仙赫夜姬拒绝他人求婚,而回到月宫那一段的构想及描述,与中国神仙类小说有诸多类似之处。《太平广记》卷六十二所收一篇名为《杜兰香》的传奇[3](p387),与《竹取物语》之间有下列几点相似之处:首先,两作品都喜欢用的“三”这个数字,如《杜兰香》中主人公被渔夫发现时仅“三岁”,杜兰香升天后降修道者张硕之家也是“三年”。《竹取物语》中,竹取翁于竹子里发现赫夜姬时,她只有“三寸”,带回家养育“三月许”,便已长大成人。向五个求婚者开出完成难题期限也是“三年”,与天皇书札往来也是“三年”。其次,两作品之主人翁杜兰香、赫夜姬,本来皆属天仙,因犯过而谪于人间,一旦期满,便升天而去。再次,所列举之物品极相似,如《杜兰香》中的“火浣布”与《竹取物语》中的“火鼠皮衣”,还有《杜兰香》中的“羽帔”“氅”与《竹取物语》中的“羽衣”。“火浣布”本由火鼠毛皮织成,二者实为同一事物。但这种物品本来就不是凡人易得之物,《竹取物语》里出现此类描述,除了道出赫夜姬所出的难题非凡人轻易可完成,多少也暗示赫夜姬与神仙界有关,又羽衣和羽帔、氅等一样,本来就是神仙传里常出现之服饰。《竹取物语》受中国文学之影响,似乎非“杜兰香”故事所能包括,据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古代中国之神仙类故事,如《汉武内传》《漢武故事》《神仙传》《列仙传》《搜神记》《搜神后记》《抱朴子》[4](p112)都曾传入日本,日本知识分子接触此类故事几率极大。而《竹取物语》恰恰与这些中国古代的神仙传说很相似,与其说《竹取物语》仅受到某一神仙传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广存于中国典籍里之神仙思想的影响更为贴切。
首先,中国神仙传说中的谪仙思想对《竹取物语》的影响深远。赫夜姬由仙界被贬谪至人间,但到八月十五日时,刑期已满,所以,天人之王亲自将其接回。这一情节,折口信夫认为,是对日本“贵种流离谭”故事母题的继承[5](p244)。日本的“贵种流离谭”可分为两大类:其一,出身高贵的人因获罪而被流放至远处;其二,神仙因某种因缘而来到人间。第二类似乎与《竹取物语》相似,但其中还是有差异的。日本这类神仙下凡人间的故事最早应推《古事记》里少名毗古那的传说。少名毗古那本是高天源之神,因长得特别小巧,某日不小心从其母神神产钦日神手指缝滑落下来流落人间,并非犯过被贬下凡。但他帮助大国主命共同建造好日本国后,又自己渡海返回仙界去了。另外,日本较为古老的传说《奈具社》里的天女虽因羽衣被偷,暂住老夫妇处,并帮他们致富,但却非被贬谪下凡。由上两例可知,日本本土传说中造访人间的神仙,常为人类带来财富或幸福,却没有一例是因获罪而被谪放至人间,倒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汉文中有诸移描述谪仙的故事,《汉武故事》便是一例。故事里记载,西王母下凡造访汉武帝“谈语世事之事的”,东方朔于外偷窥,王母察觉到了遂告诉武帝说:“此儿好作罪过,疏妄无赖,久被斥退,不得还天。然原心无恶,寻当得还。”[6](p151)历来中国民间也有东方朔是谪仙的种种传说,诗人李白也在《玉壶吟》里写道:“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与谪仙有关的传说屡屡出现于中国诗或小说,精通汉诗文的《竹取物语》作者自然也有可能对此有所了解。因此,赫夜姬因在天上获罪而谪于人间,罪满之后,又得予遣还天廷的这段情节,应是受到中国神仙思想中谪仙观念的影响。
其次,《竹取物语》中升天的道具及方法来自中国神仙传说。赫夜姬是在满月的八月十五夜尝“不死药”,穿上“羽衣”之后,乘坐“飞车”升天的。八月十五夜吃下长生不老的仙药,飞奔月宫的铺陈,立即令人联想到“嫦娥奔月”的传说。至于“羽衣”一词,年代早于《竹取物语》的日本典籍《古事记》及《万叶集》里没有出现过,在日本最早出现的例子,存于《近江风土记》里的佚文“伊香小江”及《骏河风土记》里的佚文“神女羽衣”。二者都是叙述天女因“羽衣”被偷,无法升天,只好委身下嫁偷“羽衣”的男子,某日找到“羽衣”后便立刻穿上升天而去的故事,其情节和《搜神记》卷十四的“毛衣女”极相似。虽然世界各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日本《风土记》里的这两则故事原文皆用汉文写成,因此,“羽衣”两字应是借用中国语词。
“羽衣”与月宫之关联,应是与《长恨歌》及唐玄宗的故事有关。《乐府诗集》所引用的“唐逸史”一段,曾记载罗公远于八月十五日凭借仙术带唐玄宗游月宫,但见“仙女数百人、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遂上前问道:“此何曲也?”答曰:“霓裳羽衣也。”玄宗深爱其曲,回来后,便作成“霓裳羽衣曲”[7](p816)。《乐府诗集》成书于北宋,年代虽比《竹取物语》略晚,但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开元天宝遗事》里,很可能此类传说,早已出现,所以,《长恨歌》里才会出现“霓裳羽衣曲”一词。而这类故事又随“长恨歌”或者其他中国民间传说,一齐传至日本亦未可知。“羽衣”固然是代表天上或是月宫的神仙界才配享有的服饰,却未必具有飞行功能,这点也与《竹取物语》里的情节极为相似。赫夜姬也是穿上“羽衣”后,再乘坐“飞车”升天。而“飞车”则是神仙思想的产物,《倭名类聚抄》记载:“《兼名苑注》云:奇肱国人,能作飞车,从风飞行,故曰飞车。”[8](p167)而奇肱国则出典于《山海经·海外西经》,因此,可以由这些飞行道具判断《竹取物语》确实受到中国神仙思想的影响。
最后,承袭中国神仙传说中仙人不具凡人情感的思想。在《竹取物语》里,赫夜姬一穿上“羽衣”后,便对养育自己多年的竹取翁夫妇不再有不舍之心,完全超越凡人情感接受的底线,冷漠地离开竹取翁。与其说是羽衣具有如此神奇之力,倒不如说是仙界的仙人本来就不能具有凡人的情感。平安时代,广受日本人喜爱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长恨歌传》里,记述“蓬壶”仙山的玉妃在方士来访时,忆起与玄宗的往日旧情,不胜唏嘘,旋即自悲道:“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后堕下界。”唐传奇中仙人如果具备凡人的情感便不得为仙,这点亦可由传奇小说《杜子春》看出一斑。杜子春在道士指导之下,欲修炼成仙,却在最后的试炼——亲子之爱那关失败。道士对他说道:“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人世间最难割舍者莫过于亲情。对亲情的眷恋也会是文学家们讴歌的恒久主题。而神仙却无情,恢复了神仙身份的赫夜姬完全不再具有七情六欲等情节,可说是与中国的神仙思想完全符合。《竹取物语》虽非以汉文撰写而成的,但精通汉诗文的作者为了顺应当时的唐风风气及读者喜爱新奇事物之势潮,充分展现了汉文素养,大量撷取与神仙思想相关的汉文知识及典故,终于成功的描写出一部内容充实生动、富有传奇性的物语,其中中国文学所居之功实不可埋没。
二、《伊势物语》中歌物语与《白氏文集》中的诗歌主题
《伊势物语》是平安时代第一部和歌物语,问世于公元10世纪初,主人公为“某男子”。作品虽未明言这位“某男子”是谁,但作品当中收录了不少在原业平的和歌。主人公风流多情,善作和歌,其风貌、作风颇似在原业平,自然让人联想及在原业平。而该部作品也与中国文学有很深的关联,中日两国早已有诸位学者指出其受《本事诗》《游仙窟》《白氏文集》《韩诗外传》《柳氏传》《莺莺传》敦煌本《韩朋赋》,以及《楚辞》等影响[9](pp361-364)。两部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间是否相互影响,常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证实。但由于日本本来没有文字,在平安时代末期假名文字产生之前,全是借用中国的汉字进行书写,因此,在探讨日本古代文学是否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时,常可由语词的借用而加以证实,这是一个虽不免有些零散却行之有效的方法。
《白氏文集》早在平安时代便已传至日本,这一点可由藤原佐世撰的日本最早的汉籍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出现“白氏文集七十卷”“白氏长庆集二十九卷”等条获得证实。而《伊势物语》受到《白氏文集》影响一事,也可从《伊势物语》里的词句及歌语借用白居易诗语一事获得证实。早在江户时代,日本国学大师契冲便曾于《势语臆断》里指出《伊势物語》第九十六段蹈袭《白氏文集》中《李夫人》一诗中的词句。第九十六段是说从前有“某男子”热心追求一女子,历经多年,“是女子既非木石,遂觉不忍,渐萌情意”,是受到《白氏文集》卷四“李夫人”之人非木石皆有情之句影响。此外上野理等人亦指出《伊势物语》第二段亦有借用白居易诗词之痕迹[10](pp73-79)。《伊势物语》第二段里,某男子与西京一位人品、教养均极佳的某女子一夜缠绵后,写给该女子一首和歌:“一夜诉衷情,非寝亦非起,恍惚至天明,已入春物季,终日空眺之,竟至日落矣。”(《伊势物语》汉文翻译皆依照译林出版社的林文月汉译版)当中的“春物”被认为是翻译自《白氏文集》卷第六之“坐怜春物尽,起入东园行”中的“春物”。《古今和歌集》卷第十三里,亦有收录该首和歌,咏者便是在原业平,这里的“春物”是指春雨。在原业平之前日本并未有人以“春物”来形容春雨,比《古今和歌集》问世略早的日本第一部诗集《万叶集》里,亦未出现“春物”一词,因此,“春物”两字应是出自白诗之译语。
日本文学中平安时代的惜春之歌中有很多是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收录甚多惜春诗而且在平安时代就已传至日本的《白氏文集》的影响。另外,《古今和歌集》中收录部分和歌与《伊势物语》中出现的和歌完全一致,而这些和歌也都具有浓厚白诗的影子。首先先看以惜春为主题的九十一段的和歌:“虽然惋惜之,今日春已尽,春归留不得,况又渐黄昏。”这首和歌早有日本学者上野理氏指出,其受到《白氏文集》“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一诗的影响[11](pp73-79)。除了上述这首诗,惋惜春已尽,又渐黄昏的歌意亦有《白氏文集》卷第十《送春》:“三月三十日,春归日复暮,惆怅问春风,明朝应不住。”及第十二卷《送春归》:“送春归,三月尽日日暮时”的惜春情趣。又和歌前言哀叹岁月匆匆流逝之部分,亦具有白诗惜春之诗里常吟咏的叹光阴似飞、岁月催人老的母题。如卷九《春暮寄元九》里的“但觉日月促”、卷十《送春》之“人生似行客,两足无停步。日月进前程,前程几多路……唯有老到来,人间无避处”、卷第三十五《送春》之“送春兼送老”及卷三十三《闲居春尽》里“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阴似飞”等皆是。无法断言其仅受到某首白诗影响。
《伊势物语》中题名为“渚院”的第八十二段同样与白诗有着密切的关联,“渚院”位于今天日本大阪府枚方市附近,是嵯峨天皇时的离宫,同样也是贵族文人进行文学活动、文化交往的場所。而离宫被称为“渚院”应是受到《白氏文集》中《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一诗里“渚宫”称谓的影响。仿白诗“渚宫”之名,称“交野离宫”为“渚院”的,应是惟乔亲王、在原业平或是其周围的贵族文人。但同时亦可看出白诗在当时的日本,尤其是在原业平之文学世界里,确实具举足轻重之地位。而八十二段既命名为“渚院”,当然更与白诗有密切的关联。《伊势物语》八十二段所载的这两首和歌:
那位马头者所咏之歌为:倘我人间世,无此樱树时,自无花凋谢,观赏春光时,无须怜花散,春心多闲适。而另一人则歌咏:正因花易散,才更值人怜,忧烦人间世,何事能不变,花期既短暂,更须及时看。
文中两首和歌皆在歌咏作为日本春天代表景物的樱花,虽然两者皆有惜樱之意,想法却相迥异。前者认为,与其担心美丽的樱花随时会散落,而惶惶不安,不如一开始就没有樱花树,那么欣赏春天景色时,心情将可更悠闲。只是现实的世界,若真的没有樱花,日本的春天的景色大概会逊色不少了。后者则认为,人世本无常,美丽的事物正因其必然消逝,所以,才更值得珍惜。而这首和歌的歌意应受《白氏文集》卷十四《惜牡丹花》二首中之前一首及卷十三《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之影响。《惜牡丹花》云:“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是指灿烂盛开的牡丹禁不住强风的侵袭,到夜晚只剩两枝,可能明朝风一起便全部被吹落,因此,趁着牡丹尚未凋零之前,在夜里挑灯看个够。在当今的日本,人们也有观赏夜樱的习惯,可看作是这一诗歌在现实世界中的佐证。《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诗云:“华阳观里仙桃发,把酒看花心自知,争忍看时不同醉,明朝后日即空枝。”也一样是说要趁着花尚未凋谢前,把握时间,及时欣赏之意。这两首吟咏要在花盛开之时尽情欣赏的诗,想必能引起“渚院”风雅之士们的深刻共鸣,所以他们才会在歌咏樱花时吟出“花期既短暂,更须及时看”的歌句。
此外,《伊势物语》第九十段的和歌亦具有同样情趣。第九十段题为“樱花”,是说一位男子想尽办法追求一位冷漠女子,女子终于受到感动答应与其幽会,该男子虽欣喜欲狂,却又有些疑虑,遂于盛开的樱花上系一首和歌。歌曰:“今日樱盛开,灿烂如此花,未知明日夜,能否无变化。”这首和歌虽是借用樱花来比喻女心,道出男子担心女子明夜又反悔的心情,但是和歌里吟咏出盛开的樱花可能在一日一夕之间产生变化而凋谢零落的歌词,则具有《惜牡丹花》《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两首诗的影子。
《伊势物语》第八十段有和歌云:“暮春三月末,日值雨纷纷,折得紫藤花,雨濡不恤身,可知今年内,复余几日春。”依歌词意境应是把握暮春最后时光,趁藤花未谢之际,折摘下来献给某人。福井贞助认为,从“藤花”及用“献”字来看,这里的“人”应是指藤原氏。而金子彦二郎则认为,这段用藤花来代表春天的花是受到了《白氏文集》卷十三的《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里的“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句的影响[12](p203)。但上野理则认为,雨中折花部分的构想是受《白氏文集》卷二十二《和雨中花》中之“何异花开旦瞑间,未落仍遭风雨横,草得经年菜连月,唯花不与多时节,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几日供攀折”的影响[11](pp73-79)。两人所言虽不无道理,但该和歌具有《惜牡丹花》里“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的惜花之情,亦是不争之事实。这首和歌实际上亦受白居易惜春之诗感叹光阴飞逝、人生易老的诗意影响。卷八《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中“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及卷九《春暮寄元九》“但觉日月促”、卷十《送春》“唯有老到来,人间无避处”、卷二十五《送春》“送春兼送老”等亦皆富有此种情趣。
同样以惟乔亲王及马头为主人翁,被称为八十二段续卷之八十三段,《小野》前半部也是以惜春为主题的故事。
从前,往来于水无濑离宫之惟乔亲王,前去猎鹰时,又如往常以马头翁为随从。经数日后,又回到京城宫殿,马头送亲王回殿后,原想早些告退,未料,亲王竟赐酒,又云欲赏禄,未允其告退。马头不免心急,遂咏道:莫援草为枕,今夜是春夜,不似秋夜长,瞬间天即明,时值三月末,亲王彻夜未眠,与之欢谈达旦。
关于这首和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马头表示春夜苦短,转眼即天明,愿彻夜不睡陪亲王,请亲王也不要睡。做这种解释的代表人物是室町时代连歌大师宗祇。上野理曾在《伊势物语与汉文学》里,引用汇集宗祇相关注释之书籍《肖闻抄》《宗长闻书》加以详细说明。另一种则认为,马头向亲王表示春夜短,转眼即天明,所以,要早点回家休息。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藤井高尚,之后,许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说法。因此,福井贞助才会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里作如是解释。虽然无法立刻论断哪一种才是正确的,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因为这首和歌本身含有感叹春宵易逝,转眼天即明,故应把握时光、珍惜最后春夜之意而来。而这种歌意除了与贾岛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诗意相通,还富有《白氏文集》卷二十四《城上夜宴》中“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将秉烛游”之情趣。由上可知,《伊势物语》与白诗中之惜春诗有密切关联。但与其说受到某一两首惜春诗的影响,不如说受到惜春类诗中几个主要母题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融合了白居易在不同时地,不同情境的各种咏叹,其主要母题大致可归类为:其一,思友;其二,叹时光流逝、逐渐老去;其三,珍惜时光、及时行乐等三大类。若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八十段、八十二段、八十三段、九十段、九十一段等具惜春情趣,或与赏吟樱花有关的段落,则可发现这几段除了摄取《惜牡丹花》《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等惜花之诗意,还受到白居易惜春类诗里常见的叹时光流逝、逐渐老去,及认为应珍惜时光、及时行乐等母题的影响。至于描写思友者,不只未出现于上述之惜春诸段中,在整部作品里亦只有四十六段一例。倒是有不少描写“某男子”向各种不同女子示爱,或交往之和歌或小故事。这当然是因为恋爱本来就是《伊势物语》里重要母题之一的缘故。但也可视为作者在摄取白居易惜春类诗时的偏好。《白氏文集》里常出现吟咏饮酒乐趣的诗也影响了《伊势物语》。八十二段便有一例:
一行人离开樱树下,返回离宫。走到途中,天色已暗,忽见同行伴侣令侍从持酒,来到野中。众人想找个饮酒的好处所,遂来到一名为“天河”之處。马头敬酒于亲王,亲王说:先以“狩猎交野至天河畔”为题吟首和歌后,再递酒杯过来。马头遂咏出:狩猎至日暮,忽至天河处,愿得织女顾,今宵可借宿。
这部分除了蹈循《荆楚岁时记》里张骞至河原遇织女的典故,无论是和歌前面之情境说明,或是马头巧妙地运用地名“天河”一词将在此喝酒之喜悦吟咏成和歌的各种铺写,都具有《白氏文集》第三十二卷《晓上天津阁间望,偶逢卢郎中张员外携酒同倾》的情趣:“上阳宫里晓钟后,天津桥头残月前。空阔境疑非下界,飘飘身似在寥天。星河隐映初生日,楼阁葱茏半出烟。此处相逢倾一醆,始知地上有神仙。”
除了上述诸段,《伊势物语》里尚有不少富白诗情趣者,足见作者对白诗之偏爱。然而,据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白诗可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种。而白居易最重视者则是可遂行其道的讽谕诗。这一点《伊势物语》的作者当然知道。但《伊势物语》里被认为最具暗讽意味者,却只有101段业平以藤花为题吟咏和歌那一例:
某日,业平之兄行平于府邸宴客时,特别邀请藤原良近为主客。并在花瓶插上藤花,业平拗不过众人的要求,遂以藤花为题吟了首和歌:盛开紫藤花,其下隐多人,遂使藤花荫,更显气势凛。
这里的藤花是象征当时权门藤原氏,第二句的隐是指隐在花下。因此,这句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多人受其庇荫之意,而另一种则是说有多人在其权势下销声匿迹之意[2](p231)。若采第二种解释,可认为在原业平意欲借此和歌暗讽藤原氏专权。而该首和歌则有可能是受《白氏文集》卷一《紫藤》之影响。除此之外,《伊势物语》并未有明显讽谕政治之例,即便是摄取《李夫人》诗句的第九十六段也不具任何讽谕之意,纯粹只是叙述男女之情。这主要是因为在平安时代,日本文学仅用于抒情,而不兼备讽喻时政的功能。由上述诸例可以得知《伊势物语》受《白氏文集》影响极深。亦因作者大量撷取《白氏文集》各卷诗的诗语,表现手法、审美意识,而使《伊势物语》的内容更丰富、表现方式亦更趋多样化,当中有些思考模式甚至影响日本后世甚巨。又因本作品主要是在描述某风流男子私人的感情世界,所以,偏重风雅情事,作者在摄取白诗时亦多择取具感伤情趣的诗,即便是摄取讽谕诗类诗句时,也都是用来叙述男女感情之事,较少具讽谕性。创作时作者刻意营造风雅氛围,遂将本作品撰写成一部唯美的、浪漫的和歌物语。
三、小结
《竹取物语》与《伊势物语》分别是日本最早的虚构物语及和歌物语。这两部作品亦是物语文学的源头,日本文学重要源头之一的《源氏物语》便是依据这两大源流撰写而成的。只是由于当时是以汉文学为正式场合之文学,假名多是女子在使用,假名文学亦是属于私下场合之文学。作者自然亦遵循这种默契,以假名撰写物语时,亦与以文章经国的理念为主的中国士大夫文学有所区别,不具政治性、社会性,纯粹只是在撰写适合私下场合阅读,具娱乐性、消遣性的物语文学。又因作者个人的际遇及喜好,遂分别将《竹取物语》及《伊势物语》撰写成一富传奇性之虚构物语,或富浪漫性之恋爱物语。而这种描写私人感情世界的浪漫性文学似乎颇受日本读者喜爱,不但作品本身超越时空流传至今,这种文学样式亦影响后世,成为日本文学主流,确立了日本文学不具政治性的传统。然而,汉文学根基深厚的两位物语作家于创作之时,为顺应当时的汉学风潮,也为了使物语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生动感人,以便吸引更多读者,积极的摄取了汉诗文及其思想。作者在作品里除了融入大量与该物语主题有关之具有传奇性、浪漫性的小说与汉诗文,还撷取了具讽谕性、教训性之汉诗文里的各种语汇及知识,使得作品里洋溢着浓郁的汉文学味。平安朝物语之创作确实与汉文学具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也可以说,汉文学不只是平安时代的正式文学,更在日本和文文学形成之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参 考 文 献]
[1][日]冈村繁. 中国文学与王朝物语[J].中古文学与汉文学,1987(2).
[2][日]三谷荣一.竹取物语[M].东京:角川书店,1981.
[3]李昉,等.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4]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录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日]折口信夫.折口信夫全集:第7卷[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
[6]萧统.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郭茂倩.乐府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8][日]源顺. 倭名类聚抄[M].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68.
[9][日]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全集:第2卷[M].东京:春秋社,1985.
[10]上野理. 伊势物语与海彼之文学[J]. 国文学,1999(3).
[11][日]金子彦二郎. 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M]. 东京:培风馆,2003.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