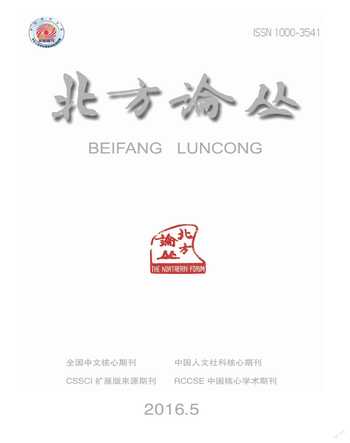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周易》对苏轼文艺创作观的影响
2016-06-09徐建芳
[摘 要]在《周易》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以虚受人”的感应观念等思想启示下,苏轼主张:一是文艺创作应“有意于济世之用”,不可空口大言;二是文艺创作要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必须不断创新求变;三是作家在感受外物、进行文艺创作时,必须保持空明虚静的心态。
[关键词]苏轼;《周易》;文艺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21-05
Abstract: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of statecraft, the change thought of “the end will change, change is smooth, smooth is long”, the concept of induction of feel the person with the empty state of mind of Zhou-Yi, Su Shi claims: firstly,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should be for the purpose of statecraft, not utter lack of substance. Secondly, only changing and innovating constantly, the author can create unique works through the ages. Thirdly, only in the empty and quiet mind, the writer can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nd then create the wonderful works.
Key words:Su Shi; Zhou-Yi; literary creation
一直以来,大都认为苏轼的文艺创作观主要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但笔者研读苏轼作品发现,除了道家思想外,《周易》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①。本文拟从《周易》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创作目的、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以虚受人”的感应观等角度探讨易学对苏轼文艺创作观的影响。
一、“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有意于济世之用”的创作目的
作为中国一切文化源头的《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本在“推天道以明人事”,[1](p.50)这一创作目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中国一切文化创造大都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优良传统。这一创作目的在《周易》中有明确表述,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系辞下》)高亨注曰:“精义,精于事物之义理。入神,进入神妙之境地。精义入神,学也。致用,用也。此句言学中有用。”[2](p.428)这句话其实就是《周易》一书创作宗旨的精要概括。《系辞上》对《周易》这一创作宗旨做了更明确揭示:“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还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可见,圣人们的一切创制都是为了天下之用。刘纲纪对《周易》的这一创作宗旨做了更详尽的阐发:
《易传》讲“形而上”的“道”,但目的仍是为了“形而下”的“器”,为了行动,为了天下的大业。……整个《易传》都充满着诉之行动的“致用”精神。刘勰也很明确地抓住了这种精神。他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宗经》)这是对《易》的精神的简明而深刻地概括。[3](p.384)
又说:
《易传》十分关心“天下”,“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举而错之天下之民”,“鼓天下之动”(《系辞上》)。[3](p.362)
综上可见,经世致用的确是《周易》一书创作的根本目的。
自幼研讀《周易》的苏轼不可能不受《周易》这一创作观念的影响,如其《东坡易传》解“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曰:
精义者,穷理也;入神者,尽性以至于命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岂徒然哉?将以致用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尽水之变而皆有以应之,精义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与之为一,不知其为水,入神者也。与水为一,不知其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谓致用也。[4](p.138)
“精义入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这其实正是苏轼一生治学的指导方针。如其《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曰:“始臣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乃者屡请治郡,兼乞守边。欲及残年,少施实效。”一切学术应有益于现实人生之用,不可空口大言。这一治学宗旨其实也是苏轼一切文艺创作的指针。如苏轼年轻时写的《策总序》曰: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三代之衰,学校废缺,圣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犹贤于后世者,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故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尽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务为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常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于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于极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绳之以法度,考之于有司,臣愚不肖,诚恐天下之士,不获自尽,故尝深思极虑,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曰略、曰别、曰断,虽无足取者,而臣之区区,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
言语文章应有益于现实之用,不可为了某些功利目的而“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苏轼一生的创作切实奉守了这一宗旨,如苏辙说:“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5](pp.1120-1126)明代焦竑也充分肯定了苏轼为文的这一良苦用心:“至于忠国惠民,凿凿可见之实用,绝非词人哆口无当者之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当与韩、范诸公相竞美。”[6](p.2388)
正因持这种文艺创作主张,所以,苏轼平生最推崇的就是那些文章于世有实际功用的作家。如其《答虔倅俞括奉议书》说:
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王,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陆贽(即陆宣公)之所以成为苏轼唯一敬慕的对象,关键在于他的奏议就像能医治世人疾病的良药妙方一样,有益于现实政治人生。“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这种“有意于济世之用”的文章,正是苏轼期望朋友及仁人君子们作的。苏轼评判他人文章的价值就常以此为尺度,如他评价司马光文章说:“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司马温公行状》)评张方平文章曰:“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乐全先生文集叙》)评颜太初诗文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凫绎先生诗集叙》)等等。这些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到苏轼的充分肯定,就在于他们都是秉着“有适于用”的目的“有为而作”的。
苏轼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及观察认识到,儒者之文的主要弊病就在于“多空文而少实用”;以此,他谆谆告诫子弟们应继承、发扬贾谊、陆贽等人的那种实用之学:“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与王庠书》)。临终之前,苏轼唯一想告诫子弟们的,就是希望他们多做实用之文。又如他劝告侄孙及弟子秦观说:“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三)“太虚未免求禄仕……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当卓然有可用之实者”(《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可以想见,这一创作宗旨在苏轼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创新意识
《周易》的核心思想是变易,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共同存在法则。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只有随时变化才能亨通、长久。所谓“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恒·彖》)、“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功业见乎变”(《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等。《周易》中这些本是阐述宇宙发展规律的哲学思想,其实都可通用于文艺创作。如刘纲纪说:“《周易》提出的‘日新、‘通变的思想并不是专门针对美与文艺而发的,但又无不可以适用于美与文艺。”[7](p.292)敏泽说:“从文艺上集中而深刻地论述了‘通变的,首推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刘勰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这看来是直接套用《周易》‘通变、‘日新的思想,但完全符合文艺史的事实,没有‘通变、‘日新,就没有文艺的发展。”[8](p.294)任何文艺形式只有不断变化创新才能蓬勃繁荣的发展,否则,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遗弃。
对变易思想深有体悟[9](pp.72-76),且文艺创作经验极其丰富的苏轼也认识到,文艺创作只有不断地创新求变,才能创作出独步千古的作品,才能“自成一家”。在苏轼看来,颜真卿等人的书法之所以冠绝古今,就在于他们能“变法出新意”,如其《书唐氏六家书后》:“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難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等等。《书黄子思诗集后》:“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划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书苑菁华》对变化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作了更加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凡书,通则变者,则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永禅师、禇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是书中得仙手,皆得法后自变其体,以传后世,故俱得其名也。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奴书。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10](p.21)可见,凡是能在书法史上自立一体、自成一家者,必是在得到前人笔法的基础上,又能自变其体而成;若执泥于旧法而不知变通,便只能成为前人的奴仆。正如黄庭坚所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11](p.712)
正因苏轼洞烛到创新对文艺创作的至关重要性,所以苏轼平生的文艺创作就能够自觉地追求变化创新。如其《评草书》自述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不步古人后尘,应该是成就苏轼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地位的根本因素之一。苏轼之所以在中国词史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代表性作家,应该也得力于他的创新之功,如其《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颇壮观”的小词,就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在苏轼生活的时代,词坛上盛行的是以柳永为代表的以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为主要内容的婉约词。苏轼第一个突破这种传统,把诗的题材、境界引入词中,把词从“艳科”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词从此变成一种真正独立的抒情文体;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词史上“自是一家”的地位。正如王灼《碧鸡漫志》所评:“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12](p.235)可见,苏轼的豪放词创作的确得益于他的创新之功。苏轼在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独树一帜,与他这种创新求变的自觉追求应有直接关系。《后山诗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13](p.306)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推崇变化创新的同时,曾多次强调对基本技法的掌握。他认为,只有在熟练掌握基本技法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求变,才能达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境界。如他评论吴道子: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书吴道子画后》)
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跋吴道子地获变相》)
吴道子之所以能成为“古今一人”的画圣,另一方面,在于他毕尽“天下之能事”;一方面在于他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反之,若技法不熟,则即使成竹在胸,也创作不出作品。苏轼对此深有体会,如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曰:“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可见,技法精熟的确是文艺创作,尤其是创新的基本前提。
正因有这种认识、体验,所以,文艺创作向来追求随兴所致的苏轼,其实并不忽视对基本法度的掌握,如其《跋山谷草书》:“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论书》:“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与东坡相上下耳。”《书所作字后》:“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等等。从这些论述可见,曾自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和子由论书》)的苏轼在看似无法的创作中其实是遵守一定法度的,而且还颇以自己的法度自负、自豪。在苏轼看来,蔡襄的书法之所以在当时能独占鳌头,就在于他洞悉书体之间的本末,基本笔法精熟所致:“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跋君谟书赋》)
依苏轼之见,只要掌握了基本法度,既使技巧上有所欠缺,也远胜于没有法度之作;而若没有掌握基本法度,则即使弊精疲神地强力学习,也终究达不到最高水平。如其《书诸葛笔》曰:“宣州诸葛氏笔,擅天下久矣。纵其间不甚佳者,终有家法。如北苑茶、内库酒、教坊乐,虽弊精疲神,欲强学之,而草野气终不可脱。”《书诸葛散卓笔》:“散卓笔,惟诸葛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以此,苏轼特别重视基本技法的勤学苦练。如其《记与君谟论书》曰:“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题二王书》曰:“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答刘元忠四首》之一曰:“诗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制尤佳也。为之不已,何所不至。”这些话应该是夫子自道。苏轼的诗文成就就是通过日积月累地勤苦练习获得的,并非天赋神授,如其《监试呈诸试官》说:“我本山中人,寒苦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廪。”《书赠徐信》曰:“大抵作诗当日煅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事。”
三、“君子以虚受人”:“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的创作心态
一个作家在创作时能否有敏锐独到的感悟,能否进入最佳创作状态,与创作时的心态有密切关系。而关于主体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与外物相感这一问题早在《周易》中就已有所论述。
《周易》在论述君子的修养时提出了“君子以虚受人”的原则,所谓“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咸·象》)孔颖达疏曰:“‘山上有泽,咸,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君子以虚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泽,故能空虚其怀,不自有实,受纳于物,无所弃遗,以此感人,莫不皆应。”[14](p.140)高亨释曰:“山上有泽,则山感其泽,泽感其山,山泽相感,是以卦名曰《咸》。山上有泽,乃崇高之山上有洼空之处,以容纳水、鱼、蛙、蚌、萍、藻等物。此象人有崇高之德或爵位,而内心谦虚,能容人也。君子观此卦象及卦名,从而以谦虚之心,接受他人之教益,以此与人相感。”[2](p.219)概言之,咸卦象辞旨在强调,君子应以虚怀若谷的胸怀,受纳万物,以此与人相感,则莫不皆应。这里的“人”实包含万物在内,如王弼曰:“以虚受人,物乃感应。”[14](p.140)这一感应规律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中作家与外物之间的感应关系。
苏轼在解《易》过程中对“以虚受人”这一感应原理深所认同。如其《东坡易传》解咸卦象辞时发挥说:“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将遗其心,而况于身乎?身忘而后神存,心不遗则身不忘,身不忘则神忘。故神与身,非两存也,必有一忘。”[4](p.58)感应主要是通过精神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而要想保持精神的存在就必须遗忘身、心。所谓“忘”其实就是使身、心“空”、“虚”,只有身、心“空”“虚”,才能容纳精神的存在。又如,其解《系辞下》说:“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其心至静而清明,故不善触之,未尝不知;知之,故未尝复行。知之而复行者,非真知也。”[4](p.139)颜回之所以能够做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关键在于他“心至静而清眀”,心灵保持虚静清明的狀态,与外物相触相感时,就能得到真切的认识;识得透,就能行得当。这些体悟不可能不被善于触类旁通的苏轼贯彻到文艺创作中去。
从苏轼诗文中可以看出,这种“以虚受人”的观念,的确对苏轼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依苏轼体验,一方面作家只有在空明虚静的心态下,才能接纳宇宙万物,与万物发生交互感应,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如其《送参寥师》: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15](pp.410-411)在韩愈看来,张旭的草书之所以能达到变化莫测、出神入化的境界,是因为他把“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所致;而高闲上人作为佛教徒,本已“颓然寄淡泊”,他的草书之所以也能呈现出张旭草书那种豪放勇猛的风格,大概是由于佛教徒的幻影所致。苏轼则认为,这是高闲上人的真正技巧使然,并非幻影所致。因為依苏轼的体验,作家要想创作出绝妙的诗歌,必须耐得住“空”“静”之境,所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而作诗的思维过程与参悟佛法的过程本是相通的,高闲上人与参寥之所以身为佛教徒,而能创作出与世人风貌相类的文艺作品,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悟法的同时参透了文艺创作的三昧。类似观念苏轼在《仲殊》中也表达过:“苏州仲殊师利和尚,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予曰:‘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在苏轼看来,“胸中无一毫发事”是仲殊取得各种文艺成就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作家只有在空明虚静的心态下,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文艺创作中去,从而才能创作出精微绝妙的作品。如其《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文与可画竹时,遗忘了周围的一切,身心与所画对象完全融为一体,在这种专一凝静的心态下,才能创作出无穷无尽清新怡人的佳作。又如其《题鲁公书草》:“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颜真卿之所以在无意于创作的情况下反能创作出更加奇特、自然、姿态横生的作品,主要就在于心灵轻松、精神专一。所谓“心闲诗自放”(《广倅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二首》之二),“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评草书》)。
[参 考 文 献]
[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
[3]刘纲纪. 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新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苏轼.东坡易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刘纲纪.周易美学:新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8]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1卷[M].济南:齐鲁书社,1987.
[9]徐建芳.《周易》“变易”思想与苏轼的处世哲学[J].贵州社会科,2008(5).
[10]陈思.书苑菁华:卷2[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1]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2]王灼著;李孝中,侯柯芳辑注.王灼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5.
[13]陈师道.后山诗话[C]//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韩愈著,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