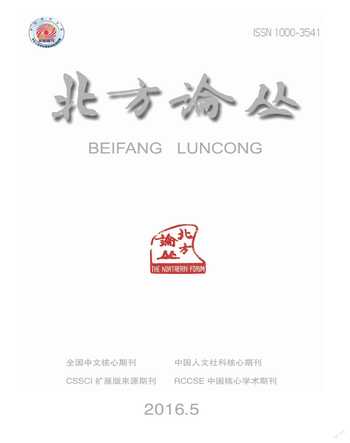中唐宦官专权及对文学的影响
2016-06-09徐海容
徐海容
[摘 要]中唐宦官专权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面对时局,文人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或参与政治改革,或发起文体革新运动,弘扬孔孟儒学,维护王政一统,借以振兴士风,挽救时弊。也有部分文人背道而驰,以致在诗文创作中逢迎谄谀宦官。中唐宦官专权使得文人的创作心理、文学发展潮流及文学作品的体制和形态都发生变化。
[关键词]中唐;宦官专权;唐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16-05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eunuch authoritarian is long in Tang Dynasty, It put wide influence on social life,especially literature. Scholars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struggle to against eunuch authoritarian in different ways. They had carried forward Confucianism, so as to save the malpractices. In addition some scholars,had flattered eunuch in the poetry. The authoritarian of eunuch mad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Tang Dynasty;The eunuch authoritarian;Tang Dynasty literature
安史之亂后,唐代开始出现宦官专权,而自代宗大历至文宗大和之间的中唐时期,宦官专权尤为突出,其掌控军政大权,左右皇帝废立,对社会政治风气有着深刻影响,这期间文人活动、文体运动,文坛风气也不断发生变化,可以说,中唐宦官专权的八十多年,恰恰是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本文也就此探究,从中唐士人与宦官的关系、宦官当权下的文学创作及文体革新活动等方面出发,阐述中唐宦官专权对文学的影响,以期从不同角度对中唐文学求得更全面的认识。
一
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古者,阉官擅权专制多矣……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 [1](p.53)唐代宦官专权始于安史之乱,李辅国因拥立肃宗即位有功,倍受重用,拉开唐代宦官专权的大幕。此后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时期,持续八九十年,在此期间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窦文玚、霍仙鸣、王守澄、刘克明、仇士良、鱼弘志等轮番掌权,废立君主、杀戮朝臣,给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造成了极大影响,正如赵翼所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2](p.383) 宦官专权从中唐到晚唐,持续一百多年,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唐王朝的毁灭。当然,这当中从皇帝到群臣也对宦官进行过斗争,但多以失败告终。原因何在?固然是唐代后期君主无能,臣子不力,但长期以来的历史环境则是更为深层的因素。
据《贞观政要》所载:“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征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 [3](p.141)可见在唐初,对于宦官有着严格的提防与限制。“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 [4](p.4473),初唐宦官仅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等事务,远离政治,官阶低微,尚无干涉政权的基础。故高祖至太宗年间,“自七十年,权未假于内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5](p.3235)。但此后这一禁令被打破,“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朱紫者尚少” [4](p.4473),至玄宗时,开始突破祖制,重用宦官,比如,杨思勖,“少给事内侍省,从玄宗讨内难,擢左监门卫将军,帝倚为爪牙” [4](p.4473)。开元初期,玄宗“诏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赴安南平叛,最终,杨思勖“以功进辅国大将军,给禄俸、防阁。从封泰山,进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4](p.4473),这就从官制上打破了太宗以来对于宦官“不任以事”“阶第四”的禁令。
在玄宗时期,“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监军持权,节度返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 [4](p.4473),而尤以对高力士的任用最为典型。据史载:“玄宗在藩,力士倾心附结,已平韦氏,乃启属内坊,擢内给事。先天中,以诛萧、岑等功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于是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虽洗沐未尝出,眠息殿帷中,徼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帝曰:‘力士当上,我寝乃安。” [4](p.4475)高力士备受重用,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着朝廷的用人大权,“当是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自余承风附会不可计,皆得所欲……然悉借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 [4](p.4475)。就连太子也对其敬畏异常:“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将军。” [4](p.4475)这一时期,宦官开始取代近臣,进入权力中枢,不仅决定百官晋升,还参与军国大事,决定皇帝的废立,如高力士就曾帮助玄宗决断太子的确立。《新唐书》载:“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帝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 [4](p.4476)
自古宦官政治是王朝腐败的产物,秦汉时的赵高、十常侍专政就说明了这一点,而玄宗为何还要突破祖制、重用宦官呢?纵观初唐以来帝王的政权交替,多是在政治斗争中进行的。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武则天篡位,中宗时韦后、上官婉儿的乱政到李隆基、肃宗的即位,无一不伴随着阴谋和厮杀。此间,外戚篡权,女祸频仍,朝臣摇摆不定,使得皇帝几无依靠,而其最亲近的人,只剩下宦官,“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善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迁之忠,使令则有称惬之效”[6](p.8595)。在皇帝看来,宦官是被阉割过的闺阁之臣,是家奴,不可能有异心,由其分担权力以保卫自己和聚敛财富。总比让外戚和将相体系独揽放心,正如任爽所云:“宦官是君主的家奴,完全附属于皇权,既无室家妻小之类,又无君临天下之机,即使权势膨胀到极点,也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皇权。这是宦官最受信任而难以铲除的根本原因。”[7](p.49)事实上,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的中国,宦官一直存在,任何皇帝可以限制宦官,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宦官制度。正如刘昫所论:“自书契以来,不无宦寺。况垂之天象,备见职官。” [5](p.4755)司马光也說:“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6](p.8596)在《周礼》《仪礼》《礼记》中,都有宦官、名号、地位及职责的详细且明确的规定。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种族最早沟通天(神)人关系,并代表前者行使人间统治权,且赋予统治权合法性的人,都是祭师及后来的巫觋,而要在人间宣谕天神的旨意,祭师必须使自己半人半神化,这就是阉割,阉割使得祭师在生理上无性化,并成为双性合一的有神性的人,也使阉割行为成为一种崇高的道德献祭。阉割造成半人半神的身份,再由半人半神的身份代表神意,取得对王位授予权和人间教育权的主宰,成为祭师拥有王权确认权(意识形态阐释权)、历史记载者和社会施教者等多种职责与多重功能的基础,而这正是自诩“君权神授”的帝皇们所需要的。根据日本学者山田村泰助的研究,中国至迟在商朝武丁年间,阉割者的地位已下降为天子近侍及宦官[8](p.49)。而唐代开元之前的皇室政治、帝位更替,基本上都是由阴谋、斗争、倾轧、暴力血拼等非正义因素组成,不具有传统文化思想所强调的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政治背景。一个充满着阴谋变数、动荡不安的政权难以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所以,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李唐皇室日益巩固发展,自然要对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加强建设,以消弭那些政权更替中的不光明因素,而宦官所传承的祭师与巫觋文化,宣传皇朝的应天合命、君权神授,多少能为李唐政权的繁荣稳定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话语,这就为玄宗朝的重用宦官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文化依据,故胡三省云:“唐制,宦官不得过三品;置内侍四人,从四品上。中官之贵,极于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杨思勖以军功,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9](p.6928)
纵观玄宗以后的王朝,相比外戚和朝臣,宦官也确实对皇帝忠心耿耿。安史之乱后,文臣陈希烈等袖手无策、左右摇摆,最后竟至投敌,而边将诸如玄宗曾倚重的哥舒翰之类,或反或降。更有甚者,德宗建中四年(738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发动兵变,德宗遂“诏集六军”平叛,而由宰相调度的六军竟“无至者”[5](p.6443),此后德宗逃往奉天,追随者只有妃嫔儿女及宦官“百余人”[5](p.6443),满朝文武竟无一个,这就更为皇帝重用宦官提供了现实需要,所以,自玄宗以后,对宦官信任有加,将军政大权一概与之,最终造成了宦官专权,而宦官专权又引发了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唐代宦官专权的危害是巨大的,正如《新唐书》所论:
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籓,则争出我门。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偾,至昭而天下亡矣。祸始开元,极于天祐。[4](pp.4473-4474)
二
中唐宦官专权百余年,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史上的影响,历代史家已有详细论列,不赘。其对于文学的影响,可从宦官专权后中唐科举、吏治状况、宦官集团与文人的关系及文人的创作心态等考察。
范文澜说,儒家文官体系是士族的代表而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10](p.208),将双方均视作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中唐宦官专权左右皇帝废立,贪揽军政大权,导致王政腐败,这就引发了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双方为争夺政治权利而势不两立。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指斥宦官“总天下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11] (p.7720),请求朝廷“黜左右之奸佞,进股肱之大臣”[11](p.7720),陆贽在《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中,也提出选拔人才,应该“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12](p.155),要像武则天时“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 [13](p.158),而帝皇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有意识地加大文官的培养,以求权力分享、制衡宦官。唐德宗时期先后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及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贞元八年(792年),陆贽奉命主持进士科试,韩愈﹑欧阳詹﹑李观等8人登第,时称“龙虎榜”,誉为“天下第一”, 这种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政策大大激发了广大文人的从政热情,刺激了寒士的进取热情和报国意识,在其诗文中多有表露,例如,孟郊《百忧》:“朝思除国雠,慕思除国雠。”[13](p.4190)韩愈《龌龊》:“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执澜。”[13](p.3784)元稹《说剑》以剑自喻,立志“剑隳妖蛇腹,剑拂佞臣首”[13](p.4460),都反映了士人阶层在现实面前,自觉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体现出对宦官专权的反对。而皇帝喜好文学,也促使了文士的创作及仕途晋升,如“文宗尚贤乐善罕比。每宰臣学士论政,必称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多以文进。上每视事后,即阅群书,至乱世之君,则必扼腕嗟叹;读尧、舜、禹、汤事,即灌手敛衽……试进士,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试,览之终日忘倦。尝召学士于内庭论经,较量文章”[14](pp.148-149),当时儒学风气浓厚,文人治经史者多注重经世致用,“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吝《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庭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里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纯,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14](p.180),这都促进了文士对时局的认识,对改革政治的热情。
中唐通过科举选拔文官的力度是大的。以宰相为例,太宗时宰相26人中科举出身者仅4人,高宗时宰相中进士出身者占1/4,武则天时宰相明经、科举出身者占1/2。此后逐次提升,中唐德宗朝宰相进士出身者占343%,顺宗朝714%,宪宗朝586%,穆宗朝643%,敬宗时宰相全为进士出身,文宗时占792%,武宗时占80%,宣宗时873%,懿宗时占813%[15]。可见,加大科举取士,壮大儒家文官体系,通过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的博弈,来制衡群臣、掌控政权是帝皇的一贯策略。而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集团的斗争,终于在永贞革新和甘露事变中达到高潮。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这些人才,在政治、操守、文学方面都很突出,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士跻身政权,把握舆论话语,成为政坛和文坛的中坚,他们影响着中唐的仕宦风气和文学发展,如参加永贞革新集团的人物,大多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刘禹锡、柳宗元堪称中唐后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吕温、李景俭、程谏等也都有文集传世。永贞革新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命运,还决定了其一生的文学命运。而更重要的是,自永贞革新后,创新精神成为中唐后期文学的主题精神。正如罗宗强所论,这种革新精神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一方面功利主义文学观得到充分发展,从初唐开始的散文改革,自此成熟,诗歌方面,讽喻说在创作上的付诸实际和理论上的积极提倡,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革新精神也反映在作家们对于独特的审美理想、鲜明的创作个性的自觉追求上[16](pp.114-191)。不仅出现了创作个性鲜明的诸多作家,还出现了不同的文学流派,这是文学思想潮流充满革新精神的结果。这种关注现实政治、追求文学革新的思想,促进了中唐文学的繁荣。如白居易与永贞革新中的关键人物韦执谊、柳宗元、李谅、严绶及裴均熟识,先后作有《上宰相书》《上太原事状》等文论及时政,其与元稹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17](p.962)的主张,而早在元和初年所作《策林》六八六九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17](p.1368),要求“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17](p.1370)。白居易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秦中吟》《新乐府》的不少诗篇如《卖炭翁》《道州民》《陵园妾》《太行路》《上阳白发人》等都论及宦官专权和朝政風云,“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其二),“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陈寅恪评价《陵园妾》说:“此篇以幽闭之宫女喻窜逐之朝臣,乐天此篇所寄慨者,其永贞元年窜逐之八司马乎?”[18](pp.266-269)韩愈、柳宗元针对中唐宦官专权以来的乱局,弘扬儒道思想,发起文体革新运动,力求以文学革新推动政治革新,挽救时弊。《新唐书》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有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4](p.5265),像孟郊、李翱、皇甫湜、张籍、贾岛、沈亚之等都因其培植,享有文名。对于中唐文体革新思潮下的创作繁盛,《唐语林》卷二《文学》说道:
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权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长庆以来,李封州甘为文至精,奖拔公心,亦类数公。甘出于李相国宗闵下,时以为得人,然终不显。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试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学继业。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凤、堂弟尚书涤,诸家无比,而皆以清望为后来所重。景凤登第,与堂兄特并时,世以为美。[14](pp.146-147)
三
中唐宦官专权,使得文学在题材、体制和表现艺术等方面也发生变化,对中唐文学的思想内容有着重要影响。
宫市是宦官专权的一个产物,陈寅恪说:“自天宝历大历至贞元末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18](p.251)对于这一弊政,中唐诗文多有反映,如白居易的组诗《秦中吟》和《新乐府》,都涉及宦官专权下的种种腐败,直斥宫市害民,尤以《卖炭翁》《轻肥》闻名,其余如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的《聚蚊谣》《百舌吟》《昏镜词》也论及宫市,就连一贯政治态度较为保守的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对宫市也多不满之辞,《顺宗实录二》云:“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未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19](p.5)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也终于在永贞年间达到高潮,典型如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呼吁政治改革,这在其诗文中多有表露,罗宗强说:“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出现了一种改革朝政、渴望中兴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了唐代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文坛充满革新精神。”[16](p.2)但政变失败,诸多参与其中的文人或被贬或被杀,使得贬谪文学盛行一时,成为文学中的重要题材,这在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的诗文中多有体现,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不赘。
除了题材方面,中唐宦官专权对文人的创作心态、文学作品的体制和形态等也多有影响。永贞革新后的宪宗虽受制于宦官,但颇为振作,特别是在平定藩镇叛乱上取得了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们的士气。而宦官专权下的宪宗中兴造成社会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这也使得文人心理处于分裂状态。一部分文士重新思考与宦官的关系,改变以往与宦官的对立态度,走向缓和,如元稹在江陵结交监军崔潭峻,步步依附宦官,官至相位,复杂矛盾的思想行为导致元稹这一时期的诗作多写身边琐事,很少论及军国大政,缺乏实质性的内容。韩愈怀着同样的复杂心理,写下《永贞行》《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等诗,讥讽王叔文等人,颂美宦官,刘禹锡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 [20](p.161)句,流露出对永贞革新的复杂感受。柳宗元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言“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21](p.1159),表达参加政变的悔恨。王建则直接和宦官头目王守澄交往,写下《赠枢密》一诗,以示友谊。典型如活跃于文宗、宣宗时期的郑薰,出于政权变化及个人功利需要,在《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一文中,对墓主仇士良阿谀至极,赞其治国为政:“举策画若应神明,阅簿书无逃心目。而又精鉴,冠绝当时。门馆宾僚,荐延功行,必求明德,用辅圣朝。则有秉忠正之心,荷匡赞之任,才表正佐,出为国桢,康济群生,辉华四海者矣。”[11](p.8273)美化臭名昭著的大宦官仇士良,贬低发起政变的郑注、李训等,行文以恶为美,肉麻吹捧,谀墓极为明显。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22](p.214)强调碑志文写作的以史为据,追求记人写事的真实准确,而郑薰作文,违背事实,虚美妄赞,浮夸粉饰,体现出中唐碑志文创作的不良风气。
中唐宦官专权影响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中唐后期宦官专权日益稳固,而王政一蹶不振,中兴之梦破灭,儒学衰朽,士人也开始面对社会现实,以适应求生存,他们用现实的眼光审视世界,开始关注个体化的生活,进行个性化的创作。这个时期的审美时尚和文学思潮是一致的,“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23](p.60)。这就使文学呈现出世俗化、多元化等倾向,“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24](p.1330),李肇《唐国史补》云:“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 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 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 元和之风尚怪也。” [23](p.55)都指出这一时期文坛尚奇尚怪的俗化倾向。当然,元和文风转变的原因很多,但宦官专权下社会政局的混乱,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参 考 文 献]
[1]孙光宪. 北梦琐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赵翼. 廿二史札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任爽.唐代典章制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8]李珺平.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J].社会科学论坛,2012(1).
[9]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0]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陆贽.翰苑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吴经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16]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7]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陈寅恪.元白詩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韩愈.顺宗实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0]刘禹锡.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3]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作者系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