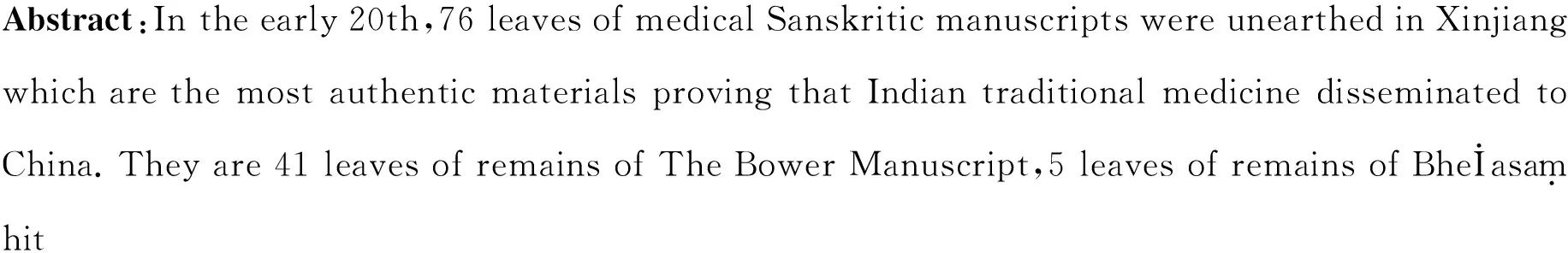新疆出土隋唐梵文医学写本述要*
2016-06-05王兴伊
王兴伊
新疆出土隋唐梵文医学写本述要*
王兴伊
二十世纪初,从新疆出土的隋唐梵文医学写本包括41叶《鲍威尔写本》残卷、5叶《毗卢本集》残片、3叶《医理精华》残片、11叶不知名医书残片、12叶不知名药方残片、3叶《八支心要方本集》等残片、1叶不知名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共计76叶写本文书,是印度传统医学传入中国的真实写本材料,对此本文做了系统梳理,概述其主要内容。
新疆出土 梵文医学写本
梵语原本是印欧语系的古代印度语族的一种语言,属于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使用的文字即为梵文。正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梵语为古代印度常用的一种语言,不但在印度通行,还传播至中亚、西域等地。 二十世纪初,新疆出土的隋唐写本中就包含有76叶梵文医学写本:41叶《鲍威尔写本》残卷、5叶《毗卢本集》残片、3叶《医理精华》残片、11叶不知名医书残片、12叶不知名药方残片、3叶《八支心要方本集》等残片、1叶不知名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其中《鲍威尔写本》属于英藏“霍恩雷收集品”,即1893年至1899年由英属印度政府授权德裔英国籍梵文专家霍恩雷(A.F.Rudolf Hoemle)(1841-1918)收集的西域文献和文物,1901-1902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Oxford)购存*J.D.Pearson,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A Survey,Bibliotheca Asiatica 7,Switzerland: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1971,p.376-377.。而《毗卢本集》残片、《医理精华》残片、不知名医书残片、不知名药方残片等,则属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得梵文文书,收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分别载录于由瓦尔德施密特(Emst Waldschmidt)、贝歇特(Heinz Bechert)、桑德尔(Lore Sander)等从1965年至2000年整理研究出版的《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Sanskrithandschrifen aus den Turfanfunden)*Emst Waldschmidt et al.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VOHD.X.Teil 1-10(Wiesbaden:F.Steiner,1965-2000).(1-10册)中。《八支心要方本集》等残片,则由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但具体收藏地不详。不知名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也是由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收藏于德国美因茨(Mainz)科学与文学院。
1.《鲍威尔写本》(The Bower Manuscript,简称Bo.)梵文残卷一、二、三(41叶)
《鲍威尔写本》出土于新疆库车的库木吐喇(Kumtura)石窟前的佛寺。
1889年6月,英属印度陆军第17孟加拉国骑兵团中尉哈密尔顿·鲍威尔(H.Bower)(1858-1940)去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探险打猎,在途中接到英国驻拉达克列城的兰赛上尉的密令,令其追捕杀害英国商人的凶犯。鲍威尔来库车,约于1890年3月2日或3日,有阿富汗商人拜见鲍威尔,将一包夹封在两片木板间的古代桦皮梵文写本卖给鲍威尔,同时还带鲍威尔去出土处实地考察。其间凶犯已自杀,鲍威尔便于1890年8月16日回到英属印度的西姆拉。随后他给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会长华特豪斯(J.Waterhouse)上校写信,称自己在中国新疆获得桦皮写本,希望有人释读。华特豪斯回信,让其寄至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并要求详记获取经过和出土地址。9月30日鲍威尔将写本及札记寄给华特豪斯,其中描述了写本出土于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附近一座佛塔中*1890年9月30日鲍威尔致华特豪斯札记,英文手写原件藏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霍恩雷文库第439号12张信纸第7、9、10张(Hr/439/12-7 9 10)。。随后华特豪斯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月度总会展示了写本,以及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纪要》上发表鲍威尔的札记和写本的两张页子的照片,虽然有人尝试,但还是无人释读。
霍恩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考古学的奠基人*王冀青:《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在鲍威尔发现写本时是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语言学研究干事,之前成功解读过出土的桦皮写本。但当时他正在欧洲度假,直至1891年3月霍恩雷才接触到鲍威尔所获的桦皮写本,并开始释读,很快就有成果展示,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纪要》1891年4月号刊登了《喀什噶里亚出土古代桦皮写本》*A. F. Rudolf Hoernle,‘The Old Birch MS. from Kashgaria’,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for April, 1891,pp.54-65.文章,是霍恩雷释读《鲍威尔写本》的第一篇文章。随后又在《孟加拉国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0卷第2期发表了《论鲍威尔写本的断代》*A. F. Rudolf Hoenle,‘On the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Vol. 60, for 1891,No. 2, pp. 79-96.专题研究论文,第一次将写本定名为《鲍威尔写本》,因中尉鲍威尔最早发现而得名。后来霍恩雷就专心研究《鲍威尔写本》,进行整理、释读、英译、刊布等工作,在1891年至1892年,刊布了《鲍威尔写本》的第五、第二、第三部分。虽然尚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干扰,但他始终关注研究刊布《鲍威尔写本》,1893年至1897年,将《鲍威尔写本》7部分校注部分和英译部分分册排印。但直至1908年才排印完《鲍威尔写本》的全部梵文索引,而1909年又将医书部分(第一、二、三部分)英译修订本重新排印。1910年,撰写全书的“导论”,至1912年完成。这部书集名为《鲍威尔写本(影印图版·那迦梨字母释录·罗马字母转写·附注英译)》*A.F. Rudolf Hoernle (,Ed.),The Bower Manuscript: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鲍威尔写本(影印图版·那迦梨字母释录·罗马字母转写·附注英译)》),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Vol.22,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93-1912.,由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印刷厂印刷出版。从1891年至1912年,用了21年时间进行研究、释读、刊布《鲍威尔写本》,其用功之精令人称赞,这部《鲍威尔写本》至今为止是研究梵文本《鲍威尔写本》的唯一专著。
《鲍威尔写本》全部抄写在桦皮上,由大小相同的桦皮叶子组成,每叶中穿一孔或两孔,用绳子穿孔固定,然后夹在两个木板中间。《鲍威尔写本》由51张桦皮组成,内容主要有七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医书,第四、第五部分是关于骰子占卜书,第六、第七部分是关于咒语书。研究该写本的意义,陈明引述文献评价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本身提供了一份印度古代医学成就的实证资料,更在于引发了东西方大规模的西域考察、探险以及搜集文物的高潮,并最终使敦煌学、吐鲁番学成为20世纪的国际显学之一。”*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鲍威尔写本》最早的研究者当推霍恩雷,他推断其抄写时间为350~475年之间。但1986年,德国著名印度字体学家、文献学家桑德尔发表了《〈鲍威尔写本〉的来源与时代新考》*Lore Sander,“Origin and Date of the Bower Manuscript,a New Approach”,Investigating Indian Art: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Buddhism and Hindu Iconography,held at the Museum of India Art in May 1986 ,1988,pp.313-323.,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应该抄写于500~550年,而且出自罽宾。目前史学界还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国外的一些学者在涉及中亚佛教史、印度医学史都会提到或介绍《鲍威尔写本》。国内最早涉及研究《鲍威尔写本》的是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原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季先生指出:“1890年,在中国新疆发现了一些梵文文献残卷,从字体上看属于公元后四世纪后半的。其中有三个医学残卷,里面讲到大蒜的医疗效果,还开了不少的药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医学在中亚西亚一带传播的情况。”,后来荣新江也介绍过它的来历*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荣先生指出:“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amilton Bower)在库车买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送到时任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总干事的霍恩雷手中。霍恩雷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这是现存最早的梵文写本。”,另外王冀青通过日本大谷大学所藏的“霍恩雷文库”,详细揭示了霍恩雷对释读、研究、刊布《鲍威尔写本》的贡献*王冀青:《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第134~157页。。但目前国内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当属陈明,成果集中展示在其专著《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尤其是将《鲍威尔写本》前三卷医学部分全文翻译成汉文作为附录*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310页。,则是其最显著的贡献。
《鲍威尔写本》卷一,5叶,132颂,包括38个药方。首先讲大蒜,大蒜的起源故事、大蒜性质、大蒜节日仪式、大蒜与其它药物的配方及其功效等,共计43颂。44-51颂讲消化能力。52-54颂讲获取良好记忆的方法。55-59颂讲有关制药学。60-67颂讲各种药方。68-86颂讲各种眼病的疗法。87-105颂讲膏药贴敷法。106-120颂讲眼药水及头发病变的疗法。121-132颂讲咳嗽及其它病症的疗法。
《鲍威尔写本》卷二,32叶,1119颂,包括392个药方,名《精髓集》。其内容相对完整,分十六大章。一开始就说它是古代诸位大仙创造出的最好的药方,以《精髓集》为名的手册,对患病男女有益,也受医生喜爱,更受大家欢迎。第一章讲“达子香叶散”、“苦药散”、“石墨根散”等散剂药方。第二章讲“甘露食酥”、“大苦酥”、“‘牛五浄’酥”等各种药用酥。第三章讲“心叶黄花稔油”、“甘露油”、“萝卜油”等药用油剂。第四章讲治疗各种杂病的杂药方,有治疗麻疯病、恶臭腹泻、大出血、痢疾、打嗝、热病、心臓病、头痛、牙痛、耳病、各种皮肤病、白色皮肤病、淋症、鼻衄、炎症、呕吐、丹毒、黄疸等病症的药方。第五章讲双马童的阿输干陀灌肠剂、万带兰灌肠剂、木棉灌肠剂等灌肠剂。第六章讲“‘长胡椒渐增’长年方”、龙葵方等长年方。第七章讲毗卢粥、善妙粥等药粥方。第八章讲各种春药方。第九章讲各种洗眼剂。第十章讲各种乌发方。第十一章讲诃黎勒的药理。第十二章讲五灵脂的药理。第十三章讲白花丹的药理。第十四章讲各种童子方。至此卷二整个篇章结束,但前10颂还讲到第十五章涉及怀孕妇女,第十六章关于[生孩子而]高兴的妇女。因此该卷残缺了十五、十六这两章。
《鲍威尔写本》卷三,4叶,72颂,14个药方。内容较为混乱,讲了油剂、散剂、糖浆剂、酥剂、涂抹剂、丸剂等剂型药。
故《鲍威尔写本》医学部分共计41叶,1323颂,444个药方。内容分别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男性等科的病症,包括了散剂、油剂、酥药、丸剂、糖浆剂、酒剂、膏药、含漱剂、汤剂、栓剂、灌肠剂、洗眼剂、乌发剂、药粥等剂型,并且深入探讨了大蒜、诃子、五灵脂、白花丹的药理及应用等,可知《鲍威尔写本》医学部分当为一部医方选集。
考察其理论渊源,古印度有三部医典《妙闻集》、《阇罗迦集》、《毗卢本集》,霍恩雷研究指出,《鲍威尔写本》的药方源于《阇罗迦集》、《毗卢本集》、《妙闻集》等*A. F. Rudolf Hoernle (,Ed.), The Bower Manuscript: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ni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鲍威尔写本(影印图版·那迦梨字母释录·罗马字母转写·附注英译)》)[M].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893-1912:57.。陈明经比较认为,《鲍威尔写本》是“生命吠陀”的系列医著,带有医方精华选集的特点*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26页。。“生命吠陀”的音译就是“阿输吠陀”,“阿输吠陀”的疾病观,主张“三体液”或“三液”说,即“风、胆、痰”,也即三种体液在身体中不平衡,从而导致身体疾病。甚至也有将血液也列入,“三液”变“四液”的,《妙闻集》中就有。《鲍威尔写本》分析疾病发生皆以“三体液”说,如:“在雨季它们据就能治愈那些[由被搅乱的]风所引起的疾病;在秋季它们能用来治疗那些[由被搅乱的]胆汁所引起的疾病:在夏季它们能治愈由[被搅乱的]血液所引起的疾病:在春季它们据说能治愈那些[由被搅乱的]痰所引起的疾病。”*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247页。证明《鲍威尔写本》理论源于古印度传统医学阿输吠陀。
2.《医理精华》(Siddhasāra,简称Si.)梵文残片(Vorl.Nr.X 398、Vorl.Nr.X1182、Bleistift-Nr.663)(3叶)
德国西域探险考察队在吐鲁番所获,具体出土地点不详。
(1)编号为Vorl.Nr.X 398的1叶,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8册(86~87页),内容为《医理精华》第4章第20颂(Si.4.20)、第21颂(Si.4.21),主要讲述解梦、疾病的预后等。可参陈明汉译*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3~244页。。
(2)编号为Vorl.Nr.X1182的1叶,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0册(71~72页),内容为《医理精华》第30章第53颂至第31章第7颂(Si.30.53-31.7),主要讲述泻药的基本疗法及具体泻药的药方、大蒜的用法等,可参陈明汉译*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第347~348页。。
(3)编号为Bleistift-Nr.663的1叶,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0册(393-394页),内容为《医理精华》第26章第36至50颂(Si.26.36-50),主要讲述各种治疗眼病的药方,可参陈明汉译*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第323~324页。。

陈明指出:“根据恩默瑞克教授的梵文精校本所加的脚注,可以发现其中有5条药方来自《妙闻本集》。1条与《遮罗迦本集》相同,2条与《青苗本集》(Hārīta-samhitā)相同。笔者还对出其中有3条与《鲍威尔写本》十分相似。同时,《医理精华》中的不少药方(或诗颂)为后世医籍所引用,除了《八支心要方本集》(3条)和《耆婆书》(17条)外,主要的医籍还有《孟迦斯那》(Vangasena)、《持弓本集》、《轮授集》(Cakradatta)和《明解集》等。”*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28页。其成书大约于七世纪中期,但并未出版过,而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于世,影响很大,经常被印度后世医家所引用。它甚至流传至中亚、西域、阿拉伯等地域,在我国流传有于阗文写本、藏文写本、回鹘文写本、梵文写本,其中藏文写本非常完整,保存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Tanjur)。恩默瑞克于1980年出版了《医理精华》梵文精校本*R.E.Emmerick,Siddhasāra of Ravigupta,vol.1:The Sanskrit text.Wiesbaden 1980.,1982年将藏文本翻译成英文*R.E.Emmerick,Siddhasāra of Ravigupta,vol.2:The Tibeten version with facing English translation.Wiesbaden 1982.。
对《医理精华》的研究成果,陈明在《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综述*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第14~19页。,揭示了国外学者Palmyr Cordier、G.R.Rachmati、贝利(H.W.Bailey)、恩默瑞克(R.E.Emmerick)、D.Wujastyk、Jinadasa Liyanaratne,等,自1899年至1990年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学者也只有陈明本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探讨,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殊方异药 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中,尤其在《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一书中,陈明依据恩默瑞克整理的《医理精华》梵文精校本,并参考了恩默瑞克的英译本,将《医理精华》全文翻译成汉语*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第217~351页。,此为《医理精华》的汉文译本。
德国西域探险考察队在新疆考察过四次,其中第二次从1904年9月至1905年12月,由勒柯克(A·von Le Coq)负责,其在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发现的梵语《毗卢本集》残片4叶:病理胚胎部残片、T1653(T II T44)、T1654(T II T16)、T1658(T II T12)。另外还有情况不详的梵语《毗卢本集》残片1叶:S1600。
(1)病理部(Nidānasthāna)和胚胎部(Vimānasthāna)残片:1叶,内容是《毗卢本集》的病理部第八章的最后部分,和胚胎部第一章的开始部分*Heinrich Lüders,“Medizinische Sanskrit-Texte aus Turkestan”,in:Aus Indiens Kultur.Festgabe Richard von Garbe,Erlangen1927,pp.148-162. Heinrich Lüders,Philogica Indica,Ausge-wahlte kleine Schrigten.Festgabe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e am 25.Juni1939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Freunden und Schulern,Gotti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40,pp.579-591.。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册。
(2)T1653(TII T44):1叶,正背书写,每面10行,内容为《毗卢本集》的残片。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册(第287页)。
(3)T1654(TII T16):残叶,正背书写,每面4行,内容为《毗卢本集》的残片。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册(第288页)。
(4)T1658(TII T12):1叶,正背书写,每面6行,内容为《毗卢本集》的残片。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册(第288页)。
(5)S1600:出土地点不详,1叶,正背书写,各7行。内容为《毗卢本集》的残片。载于《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8册。
《毗卢本集》是印度生命吠陀早期的一部医籍,在印度有传世本,从霍恩雷对《鲍威尔写本》的研究文献可知,《毗卢本集》与《妙闻集》相当,同为印度早期医典,《鲍威尔写本》传承了其中部分药方。因无汉文译本,其具体内容提要无法揭示。
4.不知名医书梵文残片(K1650(TIII MQ 49)、K1651(TIII 49)、K1663(MQ 152)、Vorl.Nr.k 401 (T III MQR))、Vorl.Nr.X 945、Vorl.Nr.X 956、Vorl.Nr.X 1200、Vorl.Nr.X 1761)(11叶)
德国西域探险考察队在新疆第三次考察于1905年12月,格伦威德尔在喀什与勒柯克会合,然后去了图木舒克(Tumshuk)、库木吐喇、克孜尔(Kizil)、硕尔楚克(Shorchuk)、吐鲁番、哈密等地,一直到1907年4月,获得大批梵文、龟兹文、回鹘文等文献资料,其中就包括以下不知名医书的梵文残片。参见《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
(1)K1650(TIII MQ 49) :存同一叶的左右2叶,及另一残叶的中间部分。前者每面7行,正背书写,书叶装。a面高6.5 cm、宽5cm;b面高6.5 cm 、宽8cm,内容为有关护胎法之序言。后者残叶4行,高3.5 cm 、宽4.5cm。《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3册(第47~49页)著录、转写、注释。
陈明译为汉文并指出:“虽然文字残缺很厉害,但仍然能看明白这份残卷与童子方中的护胎的内容相关。与许多生命吠陀典籍一样,此卷的开篇介绍了各路神灵的名称,然后是以‘先问后答’的方式来引出具体的护胎方法。”*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104~105页。
(2)K1651(TIII 49) :2叶,正背书写,每面3行。《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1册(第11页)著录。
(3)K1663(MQ 152):1叶,AB两处各3行,出土于克孜尔,不知名医书残片。《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7册著录。
(4)Vorl.Nr.k 401 (T III MQR)):1叶,正背书写,正面6行,前3行为不知名医书,出土于克孜尔。《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7册著录。
(5)Vorl.Nr.X 945:1叶,正背书写,各7行。为不知名医书残片。《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8册著录。
(6)Vorl.Nr.X 956:1叶,正背书写,各6行。为不知名医书残片。《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8册著录。
(7)Vorl.Nr.X 1200:1叶,AB两处各5行。为不知名医书残片。《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8册著录。
(8)Vorl.Nr.X 1761:硕尔楚克出土,1叶,正背书写,各7行。为不知名医书残片。《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8册著录。
以上为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8件不知名梵文医书残片,具体内容不详。
5.不知名药方梵文残片(K1655(TIII MQR,MQ 46)、K1656(T III MQR)、K1657(T III MQ41)、K1659(T III MQ49)、K1437(T III MQR))(12叶)
德国西域探险考察队在新疆第三次考察所获的不知名梵文药方残片,具体内容不详。
(1)K1655(TIII MQR,MQ 46):5叶残片,书叶装。第1叶3行,其它为正背双面各3行。药方。《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3册(第49~51页)著录、转写、注释。
(2)K1656(T III MQR):4叶残片,书叶装。第1叶为双面各4行,其它为单面3、4行。药方。《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3册(第52页)著录、转写、注释。
(3)K1657(T III MQ41) :1叶,正背书写,每面4行。药方。《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3册(第53页)著录、转写、注释。
(4)K1659(T III MQ49):1叶,正背书写,每面7行。药方。《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3册(第53~54页)著录、转写、注释。
(5)K1437(T III MQR):1叶,正背书写,正面5行,背面4行。背面第1行呪语之后为一个药方。《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第3册(第52页)著录、转写、注释。
6.《八支心要方本集》等梵文残片(3叶)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中亚、西域等地收集的三种晚期印度梵文医学文书抄本,《八支心要方本集》、《病决定》、《成就瑜伽》残片*真田有美:《大谷探险队将来梵文佛典资料》,《西域文化研究第四·中央アヅア古代语文献》,法藏馆,1961年,第51~118页。。具体收藏地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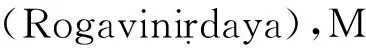

7.不知名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Mz639)(1叶)
德国西域探险考察队在吐鲁番所获,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正背面书写,各7行,粟特文与梵文隔行书写。Von Dieter Maue、Nicholas Sims-Williams对其转写和翻译*Von Dieter Maue & Nicholas Sims-Williams,“Eine Sanskrit Rit-Sogdische Bilingue in Brāhmī”,BSOAS,54:3,1991,pp.486-495.。收藏于德国美因茨(Mainz)科学与文学院。陈明根据Von Dieter和Nicholas Sims-Williams的转写及翻译译为汉语*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77页。,并认为该残片应是治疗眼病的,正面1-4行是1个药方,方中用了一种尿(牛尿?),此剂药或者此疗法七天一个疗程;正面5-7行是一个药方,药物有胆矾、三果药、珠仔树、汁安膳那、铜粉等,主治眼睛发痒等眼病;背面可能是一个药方,使用了白花丹、诃黎勒、姜黄、小檗等,主治一切眼病*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78页。。我们知道粟特文原本属于古代伊朗语族中一种东部语支粟特语的文字,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为窣利,后来随着粟特人活动范围的扩大,粟特文一度成为中亚、北亚的一种通用文字。粟特文用3种字母书写,一是粟特字母,后来又形成佛经体;二是摩尼字母,也用来书写巴列维语、回鹘语;三是叙利亚字母,也用来书写巴列维语、叙利亚语、突厥语。它们都是来自阿拉米字母的各种变体,一般自右至左横书,也有少数铭文自上而下竖书。既然出现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也表明吐鲁番地区在当时已有粟特人聚居或受到其文化影响。
以上我们梳理、概述了76叶出土于新疆的梵文医学写本,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相当于我国中古时期的隋唐。其中45叶可参考陈明的汉译版,尚有31叶未翻译成汉文,其中包含《毗卢本集》、《八支心要方本集》、不知名医书、不知名药方等。我们期待懂梵文的专家予以翻译,以利中印传统医学交流研究,也可对《隋书·经籍志》所载西域所传医籍进行溯源研究,更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The Summary of Medical SanskriticManuscripts Unearthed in Xinjiang
Wang Xingyi
Unearthed in Xinjiang; Medical Sanskritic Manuscripts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疆出土医药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4BZS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