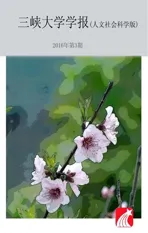声符多义成因及声符义关系探寻
2016-05-31王勇
王 勇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声符多义成因及声符义关系探寻
王勇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词语滋生的多向性、层次性和声符假借共同造成了声符义的多元性,同一声符的多个声符义之间可能存在相反、因果、平行、变易、感性等关系。从词源研究的角度赞同“声符假借”这一说法,并建议将发生变易的词源意义指派给声符,亦称之为声符义。如此更有利于声符示源研究和词族构建。探明声符多义的成因、理清多个声符义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祛迷除惑,而且有利于在据声系联时展现各谐声字组的亲疏源流和历史层次。
关键词:词源;声符多义;成因;声符义之关系
形声字的声符具有指示语源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这一观点心存疑虑[1]9-11,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为许多声符义因历时久远而隐奥难晓;二为声符义的多元性,即同一声符蕴含多个声符义。
本文欲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说明声符多义的成因,并梳理、揭示同一声符多个声符义之间的关系,借以发掘声符义发展的内在规律。
同声符的谐声字组往往衍变多途,分化为若干个簇,各簇之间意义相关,也有些之间意义歧别较大,从而使得它们的声符具有了多个声符义。这一问题,据笔者所见,主要有沈兼士、黄永武两位学者论及。
黄永武在《形声多兼会意考》中说:“陈氏(堟)虽未能说明同从‘尊’得声而义有不同之故,究为一义之引申,抑或相反之引申,抑或为字根假借,亦或无声字多音致使多义,然其较之动辄谓字从某声皆有某义,而不加博证者精审多矣。”[2]37黄氏见识卓越,对声符多义的成因及各义之间的关系已有所认识,即一为引申,一为假借,一为无声字(独体象形字)多音。沈兼士的观点亦为声符多义由声符义之引申所致,其《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推阐》一文总结焦循考求“让”字语源的材料,认为:“绎原文所叙各字意义引申之次第,先考与让同声系之瓤釀镶囊等字均有在内或缊入之义,因以定让字之亦有包裹容入之义。引申之而有‘禳’‘攘’除谢推却之义。又引申之而有‘穰’‘瀼’众盛之义,及儴因之义。又引申而有曩久之义。”[3]98
两家所言均为确论,然惜其语焉未详,故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一、声符多义的成因
我们认为,声符义之多元性由词语滋生的多向性(包括反向)、层次性和声符假借等因素共同促成。
1.词语滋生的多向性
词语主要循着相似类比、相关联想、引申分化、语音变易[4]63-83等方式滋生、发展。相似类比滋生以词语所指的事物或概念在形象状貌、情态特征、功能作用、性质事理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为契机滋生新词。其关键为语言群体所把握的事物或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如《蜾蠃转语记》所涉诸动植物、器物、形体、地貌、食品、建筑、自然现象等名物均有“圆形”这一特征。
相似类比滋生的情况很复杂,因为滋生词总是以源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的某一特征为理据而滋生,而任何事物或概念的特征都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特征都能成为滋生的契机,一个词语的意义要素(即该词所指的事物或概念的特征)有多少,其滋生新词的方向便有多少,从而形成词语滋生的多向性。
事物特征的多元性在古人命名造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实异名现象充分显现了这一点。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把握其特征,从而命以不同的名称。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诗·卫风·芄兰》:“童子佩韘。”传:“韘,决也。”笺:“韘之言沓也,所以彄沓手指。”马瑞辰云:“决也,韘也,沓也,异名而同实。以其用以闿弦,谓之决;以其用韦为藉,谓之韘;以其用以韬指,谓之彄沓。”马瑞辰抓住材料和功用两方面的特征解释了异名之由。
文字孳乳在词语滋生的推动下以增加或改换义符的方式进行,字的孳乳和词的滋生之间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源词朝不同方向滋生新词,就会在形声孳乳中以声符义的形式留下痕迹。
例如:包,《说文·包部》:“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包,胞之初文。胎胞有包裹、圆、突出等特征,所以“包”朝着这三个方向滋生新词,继而孳乳新字,从而“包”声就有了“包裹”、“圆”、“突出”诸义。
——(2)[圆义]饱雹泡
——(3)[突出]龅皰


(2)包为胎胞,形圆,故“包”声有“圆”义。沿该义滋生“饱、雹”等。
饱,《说文·食部》:“猒也。”即吃饱,餍足。饱足则腹鼓,饱含“圆”义。雹,《说文·雨部》:“雨冰也。”雹形圆,故由包滋生。
(3)胎胞又有突出的特征,圆,高起、突出有内在的联系,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曰:“又物之突出者,其形常圆,故又有圆义。”所以“包”声有“突出”之义,沿此义滋生出“龅、皰”等词。
龅,《玉篇·齿部》:“露齿。”皰,《说文·皮部》:“面生气也。”《集韵·效韵》:“皰……或作疱。”《正字通·皮部》:“疱,凡手足臂肘暴起如小泡者谓之疱。”
通过此例,我们可以看出,词语滋生的多向性直接导致声符义的多元性。
2.词语滋生的层次性
新事物的出现与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都会导致新词的滋生。创制新词的需要使一些滋生词又作为源词继续滋生新词,再度滋生使词语滋生表现出层次性。再度滋生的层数与因此而产生的声符义的个数相当。
1.巠声含“长直”义,又含“颈”义
巠——(1)[长直]径经胫茎牼桱痉泾娙①颈
颈——(2)[颈]经刭
颈,《说文·页部》:“头胫也。”其得名之由与胫同,皆为“长直”。上述各字声符“巠”皆含“长直”义,为相似类比滋生之结果。经、刭之声符“巠”无“长直”义而含“颈”义,我们认为是以“颈”为源词相关联想滋生而成。
经,《广雅·释诂四》:“经,绞也。”《字汇·纟部》:“经,缢也。”“经”义为缢为绞,绞需以绳索勒人颈部,故由“颈”滋生出“经”。文字分化词语的主要方式为在初文上缀加义符或改换原形声字的义符。“颈”为形声字,故需改换其义符为“纟”,而又得“经”。此“经”非经纬之“经”,形同而非一词②。刭,《说文·刀部》:“刑也。”段注:“刭谓断头也。”“颈”为刭之对象,与“经”得名之由同。同理,改换“颈”之义符,得“刭”。
2.重声蕴含“厚重”、“聚”二义
重——(1)[厚重]湩踵
踵——(2)[钟聚]瘇肿堹钟
重,《说文·重部》:“厚也。”沿“厚重”义滋生“湩、踵”。
湩,《说文·水部》:“乳汁也。”湩为乳汁,从重得声,正言其浓厚③。
踵,王卫峰云:
《释名·释形体》:“足后曰跟……又谓之踵。踵,钟也。钟,聚也。体之所钟聚也。”又《释疾病》:“肿,钟也,寒热气所钟聚也。”实际上,它们本来与“重”有关。踵,承负身体重量的部位,故以重为声;足跟又是体重聚集之所,重声又获得聚会、集中之义。踵疾曰“瘇”,《说文》特列“瘇”字,义即脚肿。《疒部》:“瘇,胫气肿。”“瘇”的义域括及其他部位,则有“肿”,体气郁聚则成肿[4]7-8。
《国语·周语》:“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钟正为“聚集”义。因踵为体重聚集之所,故以“踵”为源词沿“聚集”义滋生出“瘇、肿、堹、钟”。
瘇、肿已见前说。堹,《集韵·用韵》:“池塘塍埂也。”塍,《说文·土部》:“稻中畦也。”堹为防水之堤,当聚土而成,故含“钟聚”义。钟,《说文·金部》:“酒器也。”酒器以储酒,亦有“钟聚”义。
词语滋生的脉络和层次是较为复杂的,多向滋生与多层滋生往往参差互见。
3.声符假借
声符假借即章太炎所谓“取义于彼,见形于此”之类,杨树达、沈兼士对此着力颇多。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各篇多为寻本字求语源而作,又撰《造字时有通借证》,专文阐述该问题。沈兼士序《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云:“撮其要旨,约具三纲:形声字声中有义,一也。声母通假,二也。字义同缘于受名之义同,三也。”[5]“声母通假”为声符义研究的重点之一,前人治理颇多,成果丰赡,毋庸赘述。
关于“声符通假”,有一点需要说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形声字声符标音即可,所以从文字记录词语的角度讲,声符无所谓假借。但是,从词源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提法极具意义。因为它以词源研究为旨归而提出,假借意味着有“假”有“本”,我们在寻“本字”的时候并非为了寻出文字学意义上的本字,而是词源学意义上的源词。当然,音同之字往往通用,其数目不止一二。有时两个或更多声符常常通用,它们本身就是同源关系。此时我们探寻所得到的“本字”并非该词的语根,而是该词所属词族中的一个滋生词。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探寻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所探寻到的“本字”可以使我们所研究的词语理据更显豁,同时使我们知道它的族属。
如“辟”,《说文·辟部》:“法也。从卩,从辛,节制其辠也。”声符为“辟”的“劈、擘、闢、糪”皆含“判分”义。
劈,《说文·刀部》:“破也。”擘,《说文·手部》:“撝也。”段注:“《礼记》:‘燔黍捭豚。’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擘豚,谓手裂豚肉也。”闢,《说文·门部》:“开也。”糪,《说文·米部》:“炊米者谓之糪。”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炊米半生半熟也。”

二、声符义关系探寻
同一声符往往有多个声符义,这些声符义之间的关系是本节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王云路云:“一个词有诸多义项,这些义项绝大部分受着深层辩证关系的支配,表面看来杂乱无章,其实都有着相互依赖的脉络联系,清晰而深刻。”[7]同一声符的多个声符义亦如此。声符多义的成因与声符义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滋生的多向性而形成的同一声符的多个声符义往往是平行关系,由滋生的层次性形成的同一声符的多个声符义往往是相反、因果、变易或感性关系,由声符假借形成的声符义与该声符的其他意义无关。
1.相反关系
相反关系指同一声符同时具有表示相对意义的两个声符义。词义与经验密切相关,相反相成的经验必然在语言中有所体现。如“面”由“面向”义引申为“背向”义便是反向的引申。《广雅·释诂四》:“面,向也。”《广雅·释诂二》:“偭,偝也。”“偭”为后出分化字,专表“背向”义。相反相成的道理在声符义之间的关系中亦有所体现。同一声符蕴含相反或相对的两个意义的情况已为很多研究者所重视。
徐朝东撰有《同一声符的反义同族词》[8]一文,列举了部分有相反关系的声符义,如“尧”有“高大义”、“短小义”;“介”有“大义”、“小义”;“党”有“明、解悟义”、“昏昧、不明义”等。曾昭聪撰有《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综述》[9]一文,对前修时彦的相关研究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2.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极为普遍,多个声符义之间往往表现为因果关系。
声符“奄、弇”声义皆同,都有“覆盖、昏暗”二义,昏暗不明为覆冒的结果。
[覆盖]:罨、裺、女奄、渰、揜、鞥
[昏暗、黑]:晻、黤、黭
晻,《说文·日部》:“不明也。”段注:“凡言晻蔼,谓阴翳也。”“阴翳”即覆盖之义,正见覆盖与昏暗的因果关系。黤,《说文·黑部》:“青黑也。”段注:“谓青色之黑也。”黭,《说文·黑部》:“果实黭黯黑也。”
同一声符的若干个声符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事物的联系、发展的规律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反映。但是有些因果关系并不存在普遍联系,而只是事物或现象客观的非必然联系的反映。
如:“高”义与“明”义相关,日高则明,日低则暗。《六书故》:“亮,从儿从高省。”戴侗认为“亮”从“高”省,可见他认为“亮”与“高”有关。
声符“尧”既寓“高”义又含“明”义。
[高]:峣、顤、翘
峣,《说文·山部》:“焦峣,山高貌。”顤,《说文·页部》:“高长头。”翘,《说文·羽部》:“尾长毛也。”段注:“尾长毛必高举,故凡高举曰翘。《诗曰》:‘翘翘错薪。’”
[明]:晓、皢
晓,《说文·日部》:“明也。”段注:“此亦谓旦也,俗云天晓是也。引伸为凡明之偁。”皢,《说文·白部》:“日之白也。”
声符为“高”之“缟、翯、暠”等均有“明”义。
缟,《说文·糸部》:“鲜色也。”《诗·郑风·出其东门》:“縞衣綦巾。”毛传:“缟衣,白色男服也。”翯,《说文·羽部》:“鸟白肥泽貌。”暠,司马相如《大人赋》:“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
章太炎《文始》卷九“高”下云:“高、明本一义之变。”杲,明也;晧,日出貌;皎,月之白也;皦,玉石之白也;颢,白首也;白隺,鸟之白也。并与高声近,均有明、白义。张舜徽《演释名》:“杲,高也,谓日高在木上,其明四照也。”
高、明相因建立在日光的基础上,光明来自太阳,正午的太阳比朝夕之时高,光照强,这是人们的生活经验,“高”义与“明”义的相关是人们生活经验在语言中的反映。并非任何情况下“高”义都能引申出“明”义,因此,“高”义与“明”义的联系既有客观基础又不必然发生。
又如“长”义与“臭”义发生关系。《广雅·释器》:“潲、濯,滫也。”王念孙《疏证》:“长谓之修,亦谓之梢,亦谓之擢;臭汁谓之滫,亦谓之潲,亦谓之濯。事虽不同,而声之相转则同也。”王念孙证明了“臭”义与“长”义相因,泔水(汁)存放时间长则变溲,所以臭、长相因,然而这一关系只发生在泔水或其他可致腐败的事物之上,不具普遍性。
声符义的这种关系说明,词语滋生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两意义之间的联系往往并不普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在探求词源意义的引申运动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考察、求证。
3.平行关系
事物或概念的特征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体悟便会获得不同的感受和经验,这些感受和经验作为词语滋生的理据蕴含于滋生词的意义之中。正如词义的辐射引申所产生的各义项处于同一层次一样,这些声符义反映了事物或概念的不同特征,它们是处于同一层次的。
如声符“夗”(宛)有“弯曲、微小、婉顺”等义。“微小、婉顺”等义处于同一层,均由“弯曲”义引申而来。夗,段注:“凡夗声、宛声字,皆取委曲意。”
“夗(宛)”声诸字按其声符义分列如下,同时阐明各声符义的由来。
[弯曲]:眢、琬
眢,《说文·目部》:“目无明也。读若委。”戴侗《六书故·人三》:“眢,眸子枯臽也。”眸子枯臽亦含坳曲意。琬,《说文·玉部》:“圭有琬者。”段注:“后郑云:‘琬犹圜也……’玉裁谓:‘圜剡之,故曰圭首宛宛者。’”圆、曲义近。
“微小”义由“弯曲”义引申,曲则短小。张舜徽《郑雅》云:“曲,犹小小之事也。”《广雅疏证·卷四上》“诎也”条王念孙云:“凡物申则长,诎则短。”④
[婉顺]:婉
婉,《说文·女部》:“顺也。”段注:“《郑风》传曰:‘婉然美也。’《齐风》传曰:‘婉,好眉目也。’”
“弯曲”义引申而有“婉顺”义。眢,读若委。夗、委声义皆近。“委”有“弯曲”义,从“委”得声之“覣、倭”有“婉顺”义。覣,《说文·见部》:“好视也。”段注:“和好之视也。取委顺之意。”倭,《说文·人部》:“顺貌。”⑤
4.变易关系
由滋生的层次性形成的同一声符的多个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可能是变易关系。变易是指声符义不沿着原声符义(源词之源义素)继续引申,而是以其他语义特征为新的起点继续滋生新词。如“巠”声有“长直”义,又有“颈”义;“重”声有“厚重”义,又有“聚集”义;“悤”声有“中空”义,又有“青色”义。声符义之所以发生变易,是因为在词语滋生过程中,以某一滋生词为源词,以滋生词的非词源意义的义素为契机滋生新词,从而产生了新的词源意义。如滋生词“葱”得义于“悤”,其词源意义为“中空”,又以“葱”为源词,滋生出“璁、骢”,词源意义为“青色”。“中空”与“青色”并无直接联系,只因“葱”具有这两种特征而偶然地发生了关系,并且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

比较上图所示声符为“皮”、“悤”的形声字之滋生脉络,不难看出,“青色”显然不是“悤”的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同意“悤声含青色义”的说法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滋生词由源词滋生出来的依据是它们所指的事物或现象的相似性、相关性,所以各滋生词的意义必相同或相近。所谓“相同或相近”不过是沿袭传统说法,表现在词义上,就是有相同义素。如《说文·马部》:“馬隺,马白頟。”段注云:“鸟之白曰白隺,白牛曰牛隺。”《说文·牛部》:“牛隺,白牛也。”段注云:“白部曰:白隺,鸟之白也。此同声同义。”馬隺、白隺、牛隺都具有“白”这一特征,段氏所谓同义只是特征的同、义素的同,即具有相同的词源意义。黄易青说:“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常说的‘凡某声多有某义’,当代杨树达说的‘形声中有义’‘字义同缘于语源同’,其中的‘义’都与词源意义相应。”[10]105
第二,形声字的特殊结构。形声字由可表范畴义的形符和可标音的声符构成。
第三,传统释义一般采取“属性+类别”的方式。黄易青认为:“古代训诂对词义结构的两分,跟汉语词汇义的结构、词义运动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10]137“从古代训诂来看,词源学上的词义结构是两分的。古代训诂有很大部分是从意义结构分析的角度而做出的。如《释畜》:‘四胶皆白,驓;四蹄皆白,騚;前足皆白,騱;后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启’。”[10]132
《说文》的训释也多用两分的形式,如“狡,小犬也”、“豭,牡豕也”、“驯,马顺也”等。
这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声符的“义”。同谐声字组所记录的同源词有共同义素(词源意义),经过二分分析,范畴义由各自意符承担,而他们所共有的词源意义便自然地由它们所共有的声符承担。王宁所使用的义素分析法便能说明我们的观点。所谓义素分析法,即“把词的用来判定同源关系的义位切分为两部分——词义特征和概念所表事物类别,从而得到同一组同源词的相同的意义即意义特征的方法。”[10]127王宁所举的例子正是一组同谐声字记录的同源词。虽然她所举的一组形声字的声符确实“兼义”,但是这个方法也用在了改换形符而成的同谐声字组上。如“葱、璁、繱、骢”都有青色的特征,都有声符“悤”,从而得出“悤”声含“青色”义的结论。
虽然这种声符义是人们分析出来的意义,但这并不影响声符的示源功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将同源词的词源意义赋予记录它们的形声字的声符,并视为声符所蕴含的意义,这有利于同源词研究。故而,我们对这类“声符义”不持否定的态度,反而把它作为研究手段,来观察声符义的运动脉络和规律,从而反映词语滋生的历史层次。
5.感性关系
以上所论,是基于理性的关系,下面讨论基于感性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语的滋生理据反映了古人对事物或现象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感性关系是说,声符的多个意义之间的联系以心理感受为基础而发生,而并非基于客观规律。如前面所说“诎曲”义引申出“委顺、美好”义,这体现了古人面对客观事物时的心理感受。房德里耶斯对文化心理现象有比较透彻的论述,他说:“痛苦的观念很容易和巨大的观念发生联系,又如强暴的观念容易和力量的观念发生联系。……怜悯的观念很容易转变为柔情的观念。人们想到不幸总会掺杂着同情。怜和爱在人们的心田里是很接近的。可怜的观念和小的观念都跟软弱同义,它们会立刻钩起柔情和怜悯。”[11]230-232

又如,古人既以大为美,又以小为美,以整齐、鲜洁、纯一、柔顺为美,这些虽然在事理上显得扞格难通,但却是汉民族审美心理的流露。
“大”与“美”义相通⑥。《广雅疏证·卷一上》:“皇、翼、蒸、将,美也。”王念孙云:“大亦美也。美从大,与大同义。”
又如“我”声有“高大”、“美好”义。
[高大]:峨
峨,《说文·山部》:“嵯峨也。”峨义为山势高峻,宋玉《女神赋》:“其状峩峩,何可极言。”
[美好]:誐、娥
誐,《说文·言部》:“嘉善也。”嘉,《说文·壴部》:“美也。”娥,《说文·女部》:“帝尧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晋谓好曰娙娥。”《方言》卷一:“娥、女嬴,好也。秦曰娥,秦晋之闲凡好而轻者谓之娥。”
“微小”义与“美好”义通。《诗·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毛传:“婉娈,小好貌。”《方言》卷十三:“纯、毣,好也。”郭注:“毣毣,小好貌也。”《广雅疏证·释诂一》:“凡小与好义相通,故孟喜注《中孚卦》云:‘好,小也。’”
声符“兆”含“微小”、“美好”义。


[美好]:姚
姚,《说文·女部》:“娆也。”《方言》卷十三:“姚,美也。”
“肖”声有“小”义,从“肖”得声的“俏”有“美好”义。《广韵·笑韵》:“俏,俏醋,好貌。”《集韵·笑韵》:“俏,好貌。”“微小、美好”义通同样反映了人类的审美心理。孙雍长对小、好的义通关系作了很深入的阐释,他说:“所谓‘小与好义相近’,就其义通这一语义现象之缘由来说,主要还是一种功利观念的反映。因为小的东西一般都比较精细,故‘小’与‘精’同义。《书·君奭》篇‘文王蔑得’,郑注:‘蔑,小也’,正义:‘小谓精也’。以‘小’为‘好’,即是以精妙为良善。”[12]
盛林说:“‘小’之所以与‘好’义相近,恐怕缘于‘小’的事物常常给人柔弱的、可爱的感觉,这是一种好的情感联想,所以说‘小与好义相近’。”[13]68
从以上义通关系中,我们窥见了古人的审美观,即以宏大、精小的事物为美,这就是语言蕴含文化的表现之一。
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其中的文化蕴含值得大力挖掘。
三、结论
本文主要探明,词语滋生的多向性、层次性和声符假借等共同造成了声符义的多元性,同一声符的多个声符义之间可能存在相反、因果、平行、变易、感性等关系。同时从词源研究的角度赞同“声符假借”这一说法,并建议将发生变易的词源意义指派给声符,亦称之为声符义,如此更有利于声符示源研究和词族构建。探明成因、理清关系不仅有利于祛除迷惑,而且有利于在据声系联时展现各谐声字组的亲疏源流和历史层次。当然,有些声符义与该声符的本义、引申义、变易义均无关,这一现象我们将另文阐述。
注释:
①“径经胫茎牼桱痉泾娙”等含“长直”义,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之《释经》,中国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杨树达认为:“经字从巠声,巠实假为颈。”他的意思为“经”由“颈”滋生而来。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0页。
③章太炎认为浓之声符借为乳而得浓厚之义,沈兼士从其说。参见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页。
④又从“句”得声之字多有“弯曲”义,而“驹、狗、鼩”均有“微小”义。
⑤又卷,义为“弯曲”,而从“卷”得声之“婘、鬈”皆有“美好”义。婘,《广雅·释诂》:“婘、孉,好也。”王念孙《疏证》云:“婘与下孉字同。《玉篇》:‘婘,好貌。或作孉。’”鬈,《说文》:“髪好也。《诗》曰:‘其人美且鬈’。”
⑥《诗·邶风·简兮》:“硕人俣俣”,传云:“俣俣,容貌大也。”《释文》:“《韩诗》作扈扈,云:美也。”马瑞辰云:“俣与扈音近,美与大亦同义,故扈扈训美,又训大。《檀弓》:‘尔毋扈扈尔’,郑《注》:‘扈扈谓大’是也。”
参考文献:
[1]曾昭聪.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M].合肥:黄山书社,2002.
[2]黄永武.形声多兼会意考[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3]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推阐[M]//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王卫峰.上古汉词语汇派生研究[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5]沈兼士.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7]王云路.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M]//中古汉语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徐朝东.同一声符的反义同族词[J].古汉语研究,2001(1).
[9]曾昭聪.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综述[J].古汉语研究,2003(1).
[10] 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 房德里耶斯.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2] 孙雍长.王念孙“义通”说笺释[M]//管窥蠡测集.长沙:岳麓书社,1994.
[13] 盛林.《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杨勇]
中图分类号:H 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3-0047-06
收稿日期:2015-10-10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周祈《名义考》校注与研究”(1251)。
作者简介:王勇,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