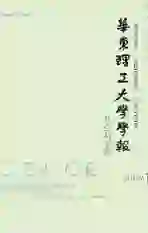重新检验推拉理论:来自夜间灯光数据的证据
2016-05-30刘林平蒋和超李潇晓赵丽芬
刘林平 蒋和超 李潇晓 赵丽芬



[摘要]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推拉力作用的结果。本文利用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PS)收集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对推拉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力资本、土地、住房、迁移距离和家庭等因素的条件下,经济目的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驱动力,农村老家的普遍贫困是农民工外出的推力,农民工迁移的方向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迁往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此外,农民工1年内和3年内的返乡意愿受到家乡经济发展状况的显著影响。
[关 键 词]推拉理论 灯光数据 事件史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户籍限制放开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研究”(批准号:13JZD018)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和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李潇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赵丽芬,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1-0010-09
一、 引言
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7 395万人,①农民的跨地域流动成为了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有关农民工迁移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常年外出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②③④但农民工“候鸟式”迁移、“钟摆式”流动的解释却一直存在着理论争议,更有待经验研究的证实。
根据Chiswick与Jessica等学者的归纳,⑤⑥有关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一直存在多种竞争性理论视角:一是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托达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决策范式,它们强调劳动力的供需不平衡、迁移成本、工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因素,视迁移为个体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二是以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为代表的家庭决策范式,强调迁移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家庭的集体决策,不只是为了实现预期收益的最大化,更是为了降低家庭风险;三是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历史-结构主义方法的迁移范式,它们强调迁移决策的宏观结构,前者强调现代工业制度的结构性需要,后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市场的跨国界渗透。
上述理论从迁移决策的个人、家庭、国家和国际四个层面揭示了劳动力迁移的个体动机和结构性因素,但是人们的迁移行为并非个体动机与结构决定非此即彼的结果,劳动力的迁移完全可以是个体或家庭基于迁移成本和预期收益的理性决策,同时又受到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的限制,忽视劳动力迁移的内生性因素或者外生性因素都不能全面理解人们的迁移行为。
由Lee发展和完善的推拉理论将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归纳为四种: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①将结构性和个人因素同时纳入了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迁移的动因,是对中国农民工研究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框架。但Lee的推拉理论几乎只是一个理论,它阐述了影响迁移的一系列因素,却并未检验实际的因果机制。②本研究借助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收集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来验证推拉理论,回答推拉理论在农民工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文沿用Lee对迁移的定义,③将农民工流动视为迁移行为,因为就农民工流动这一行为而言,它与西方国家的劳动力迁移并无实质差异。根据笔者的研究,农民工迁移会经历外出务工、地区流动(或职业流动)、永久迁移(或返回农村老家)等三个阶段。
(一) 农民工的首次迁移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地方都存在引发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当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大于迁移的阻力时,迁移就会发生,④诸如气候、经济等是导致迁移的常见推拉力。中国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就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迁移浪潮。李强指出,无论是来自城市的拉力——“城市收入高”,还是来自农村的推力——“农村收入水平太低”,经济目的是农民工外出的首要驱动力。⑤但有学者注意到,虽然经济目的是农民工外出的首要驱动力,但是农民工外出的推拉力作用程度是不一致的。⑥孙立平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来自农村的推力是农民工外出的首要驱动力;⑦而程名望等人在福建、河南、山东、四川和湖北等地进行的两次问卷调查却发现,2000年至2004年间,中国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工进城的第一动因由农村推力变成了城镇的拉力。⑧笔者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济目的是农民工迁移的首要驱动力,家乡与外出务工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越大,农民工就越可能离开家乡外出务工;
假设2:较早外出农民工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农村老家的推力;
假设3:较晚外出农民工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城镇地区的拉力。
(二) 农民工二次迁移与返乡意愿
王子成等人指出,农民工流动与国外移民的最大不同点是西方国家的移民是永久性的迁徙,而农民工流动是循环迁移或重复迁移。①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高流动性的解释强调人力资本、②工资收入和制度条件③以及城乡身份分割,④认为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和户籍限制,农民工只能进入以高流动性为特征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次级劳动力市场低廉的工资收入会进一步导致农民工的高流动,因此,农民工二次流动实际上还是受经济目的驱动。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地区流动或职业流动放入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一定是首次迁移不能给农民工提供稳定的就业预期和就业现实所致,二次迁移是为了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我们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农民工二次迁移受经济目的驱动,首次迁移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预期,首次迁移迁入地的经济发展越好,农民工就越容易停留,反之则迁移;
假设5:农民工二次迁移的迁移方向是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迁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永久迁移或返乡是农民工流动的第三个阶段,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尤其关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市民化,⑤⑥⑦而对农民工返乡关注较少。Lee认为,每个主要的迁移浪潮都伴随着一个反向的迁移流,促使迁移者反向迁移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迁出地与迁入地推拉力得到消失或者消减;二是迁移者受生命周期影响而回流。笔者认为,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同样会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老年农民工更趋向于返回农村老家,而家乡与打工地之间推拉力的消减则会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农民工的迁移决策。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受家乡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家乡与打工地的经济水平差距越小,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越强。
三、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是微观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和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PS)收集的夜间灯光数据。
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来自笔者于2014年6-8月在山东泰安、肥城,陕西咸阳、兴平,江苏常州、武进,浙江金华、义乌,湖南岳阳、汨罗,贵州遵义、凯里和广东广州等7个省13个市(区)进行的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含被访者详细的工作史信息,为探讨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提供了依据。
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 心,⑧它是DMSP卫星搭载线性扫描系统(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OLS)收集的世界各地夜间——当地时间20:00—21:30之间——室外灯光、火光、油气光线和渔船灯光的图像,分为三种类型:平均可见灯光数据、稳定灯光数据和云层覆盖数据。本文使用稳定灯光数据作为社会经济参数,⑨参照Doll、①②Chen③与Michalopoulos④等学者的方法提取灯光数据。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在特定年份的迁移行为与返乡意愿。对应农民工迁移的三个阶段:首次迁移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在1992年至2014年间是否有外出务工;二次迁移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在1992年至2014年间是否有跨地区的工作流动或职业流动;而返乡意愿则根据农民工对回流意向的回答处理为:根本不会、回流意愿较弱、回流意愿较高和肯定会四个次序,在问卷中该变量的设置是:“在以下时间(1年内、3年内、5年内和最终),您会回流家乡,并留在家乡的可能性是多大?”采用0-9的数值来代表回流可能性的大小,0表示根本不会,9表示肯定会。因此,农民工回流的四个次序取值为:0=根本不会、1-4=回流意愿较弱、5-8=回流意愿较高、9=肯定会。
2. 自变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夜间灯光密度,并派生出灯光密度差值、灯光密度均值和灯光密度的预测值。⑤
灯光密度:灯光密度是指当地当年的平均灯光强度,用来表示农民工迁移时家乡和打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灯光密度差值:灯光密度差值是指农民工迁移时迁出地与迁入地灯光密度的差值,用来表示农民工迁移两地间的经济差异程度。
灯光密度均值:灯光密度均值是指农民工迁移前迁出地与迁入地各年灯光密度的平均值,用来表示农民工迁移时迁出地与迁入地历年经济的发展状况,因为灯光密度差值只是单一时点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经济参数,不能很好地代表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使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灯光密度均值作为两地历年经济发展状况。
灯光密度预测值:为了探讨农民工回流意愿,还预测了农民工家乡与现打工地2014年、2017年、2019年和2020年的灯光密度,并计算了农民工返乡时家乡的灯光密度与现打工地的灯光密度差值、返乡时家乡的灯光密度与首次外出时家乡的灯光密度差值、返乡时现打工地的灯光密度与迁入时的灯光密度差值。
3. 控制变量
在建立模型时,本文还考虑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健康状况、人均土地面积、务农经历、住房、65岁以上老人数量、16岁以下孩子数量、父母的迁移经历、迁移前后收入差、打工年限、目的地和迁移距离等。
(三) 模型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来分析农民工首次迁移和二次迁移的概率,因为农民工迁移可以视为是在一定时间内对原生活状态的一次改变,满足事件史分析的基本要求,其基本模型是:⑥
h(tij)=ho(tj)exp(xi′β)
它可以转化为常见的对数形式:
logh(tij)=logho(tj)+xi′β
logh(tij)是个体农民工i在时间t迁移的风险概率的对数,logho(tj)是基准风险函数的对数,它代表对时间的依赖。xi′β是一系列预测变量,预测农民工迁移的概率,它包括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变量、经济社会参数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在中国,年满16周岁才是适龄劳动力,因而在农民工迁移的比例风险模型中,个体只有年满16周岁才进入分析样本,并将农民工迁移的最高年限设定为70周岁,如果个体年满70周岁则被排除在分析样本之外。
事件史分析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可以比较不同时期农民工迁移影响因素的变迁,为此,笔者将农民工从1992—2014年间的迁移划分为两个时期:1992—2002年和2003—2014年。1992年—2002年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头十年,是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2003年—2014年间的十余年作为第二个时期,用来比较两个时期农民工迁移因素的变迁。
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使用次序probit模型,模型除了人力资本变量、经济社会参数变量,还增加了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因素,包括家乡的住房状况、人均土地面积、配偶所在地以及农民工务工的权益保障情况等。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首次迁移
表1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对农民工首次迁移的检验,表中给出的回归系数是指数模型的系数,取自然指数e即是风险比率,若回归系数为正,表示生存时间越短,即农民工迁移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迁移可能性就越低。考虑到农民工迁移不只是个人决策,本文控制了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积、65岁以上老人数量、16岁以下孩子数量和父母的迁移经历等家庭层面的因素。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家乡与首次迁移迁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具体而言,农民工首次迁移时,家乡与迁入地的灯光密度差值越大,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的,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系数表明,家乡与迁入地间的经济差距在1992—2002年、2003—2014年两个时期对农民工迁移决策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
为了检验推力和拉力的作用程度,笔者将农民工外出前家乡的灯光密度均值作为农村老家的推力,将外出前迁入地的灯光密度均值作为城市地区的拉力。由模型1可知,农村老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低;而首次迁移迁入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越高,农村老家的推力和城市地区的拉力对农民工迁移都有显著的影响。在模型2中,由于家乡灯光密度均值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大于迁入地的灯光密度均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来自农村老家的推力显著大于城市地区的拉力,这表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农村老家的推力。在模型3中,城市地区的拉力对农民工迁移的作用消失,这表明1992年至2014年间农民工外出的动力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来自农村老家的推力仍然是农民工外出的首要驱动力,假设2得到数据支持,假设3没有得到支持。
(二) 二次迁移
在二次迁移的Cox比例风险模型中,排除了来自农村老家的影响因素,在控制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情况下,集中探讨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参数对农民工二次迁移的影响。
假设4、假设5关注的是农民工二次迁移的经济驱动力:首先,首次迁移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对再次流动的影响。在模型4中,使用首次迁移迁入地迁出时与迁入时灯光密度差值和首次迁移迁入地灯光密度均值来表示二次迁移迁出地的经济社会参数,回归结果显示,首次迁移迁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民工二次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次,二次迁移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对再次流动的影响,在模型4中,使用二次迁移时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灯光密度差值来表示再次迁移时迁移两地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用二次迁移迁入地灯光密度均值来表示二次迁移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结果显示,二次迁移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民工二次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模型5、模型6可知,二次迁移迁出地与迁入地经济发展程度对农民工再次迁移的作用在两个时期具有持续影响,无论是1992—2002年间还是2003—2014年间,首次迁移迁入地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民工再次流动都具有负向影响,二次迁移迁入地经济发展程度对农民工再次流动都具有正向作用,假设4、假设5都得到支持。
(三) 返乡意愿
在农民工返乡意愿的次序probit模型中,笔者把人力资本、土地、住房、家庭因素和权益保障等社会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使用农民工返乡时家乡与打工地的灯光密度差值来衡量家乡与打工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用外出时与返乡时家乡灯光密度的差值和迁入时与返乡时打工地灯光密度的差值来衡量家乡和打工地在农民工迁移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家乡与打工地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仅对农民工1年内的返乡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乡与打工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农民工1年内返乡的可能性就越小。
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返乡与否不仅会横向比较打工地与家乡的经济发展程度,还会纵向比较外出务工期间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打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这种纵向比较会显著影响到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在模型7中,农民工1年内返乡的可能性会受到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显著影响,外出打工期间,家乡的经济发展程度越好,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就越高;在模型8中,农民工3年内返乡的可能性同样会受到家乡经济发展程度的正向影响,家乡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农民工返乡具有拉力作用。而在模型9中,家乡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作用消失,农民工5年内返乡的可能性受到打工地经济发展状况的显著影响,迁移期间,打工地经济发展程度越好,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模型10中,打工地的经济状况、家乡的经济状况以及家乡与打工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工在1年内、3年内返乡与否会考虑经济因素,尤其是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但打工地和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民工最终返乡意愿无显著影响,假设6得到部分支持。
五、 结论
本文运用美国国防气象卫星收集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重新检验了推拉理论。在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内,本文着重关注的是迁出地与迁入地间的经济社会参数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目的是农民工迁移的重要驱动力,农民工迁移的方向是从经济发展状况较差的地区迁往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过去三十几年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其实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如果城乡间、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平衡,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将会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
虽然农民工流动是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来自农村老家的推力和来自城市地区的拉力的作用程度是不一样的。根据笔者的研究,1992年至2014年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首要驱动力是来自农村老家的推力,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主要是因为农村老家的普遍贫困。此外,农村老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外出务工期间,农民工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改善越大,其在1年内、3年内返乡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农民工研究仍然有待深化,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必须拓展研究主题,值得期待的是,根据笔者对夜间灯光数据的分析,发现了部分区县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的痕迹,这些城市扩张现象有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生活际遇的研究。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