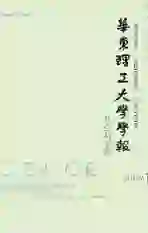矛盾的“城市性”与近代上海棚户区的污名
2016-05-30吴俊范
[摘要]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扩展,棚户区从城乡交错带日益向城市肌体内侵入,最终成为令城市管理者头疼而又无法排拒的贫困社区。城市社会主要以规范的城市社区景观和主流城市文化为模版,来诟病棚户区的种种弊端,使棚户区的污名逐渐加积。尽管如此,棚户区仍然长期作为城市社区的重要部分而存在,并在城市政府的推动下逐渐向规范的城市社区转化。近代上海棚户区污名的形成和延续,与其矛盾的“城市性”以及城市社会对待城市贫困社区问题的矛盾心态密切相关。
[关 键 词]棚户区 城市性 贫困社区 污名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和芝加哥城市贫困群体文化融入过程的比较研究》(吴俊范主持,编号为14PJC08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俊范(1971-),女,河南荥阳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人文地理、城市社区史。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1-0019-12
一、 污名:城市贫困文化的观察角度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一系列有关贫民窟和城市贫困家庭的著述,逐渐建构起社会学意义上的“贫困文化”概念。这一概念并非泛指各种贫困群体的文化,而着重是指工业化以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贫困移民文化,他在《以拉维达为例的贫民窟文化研究》一书中将其表述为:“最典型的具有贫困文化的人群,是那些来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并且已经部分地与主流社会疏离的下层人群,因此,失去土地的乡村劳动者迁移到城市后更容易生发出贫困文化。”①可见,城市贫困移民及其居住生活的社区可作为讨论现代城市贫困文化发生与表现的重要切入点。基于这一理解,本文以近代以来上海城市长期存在的贫困移民社区——棚户区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为对象,以其污名的塑造与内涵变化为主线,对中国城市制度环境下贫困文化的发生机制与存在状态进行讨论。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贫困移民群体作为被主流文化边缘化、承受着各种偏见和歧视的人群,成为重要的一类“被污名者”。从乡村初来城市而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的新移民群体,其文化特征中“乡村性”的延续与“城市性”的薄弱,与城市主流文化阶层所寄予的期望值反差较大,可谓是其污名产生的原动力。城市贫困群体的污名产生机制应受到研究者的更多关注,但作为西方社会学领域污名理论的开创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三种形式的污名,即各种身体残疾的污名、个人性格缺点的污名、种族民族和宗教有关的集团性污名,却未将现代社会中更为广泛存在的贫困群体的污名涵盖在内,①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贫困人群在文化特征上的边界与可识别性不如种族、宗教群体那样明显,很难精确地加以描述,其次是贫困文化缺乏独立性,只能与主流文化相对而存在,充其量是一种城市文化中的亚文化。正因如此,城市贫困群体污名的建构过程必然是一个社会生态过程,非贫困阶层与贫困阶层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对立、磨合乃至同化过程,都深刻地反映在贫困污名的构建之中,因此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相对更大。然而,随着西方大城市贫困问题的凸显,西方学界对于城市贫困污名的研究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盛起来,彻姆·维克斯曼(Chaim L. Waxman)的著作《贫困的污名:贫困理论和政策的批判》,②即是从生态视角对当时的贫困污名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主张研究者应该通过解读“穷人在社会结构框架之内如何理解自己的地位,非穷人如何对待穷人的态度和行为,其他群体的方式在穷人身上产生了什么效应”,来互动式地理解贫困污名的内涵。
总之,污名已成为一种广为认可的城市贫困文化的研究视角,西方贫困文化研究范式十分注重从社会生态角度揭示城市贫困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的明显对峙与磨合,而贫困污名的塑造过程恰恰体现了贫困文化的生态特征,各种城市人群的价值观和态度均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反映。本文对上海棚户区污名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城市管理者和媒体对待棚户区的心态和所采取的立场,但最终落脚点仍然是讨论城市贫困文化的特定内涵。
二、 徘徊的乡村性:棚户区融入城市的先天不足
棚户区是近代以来上海城市最典型的贫困社区,缘起于19世纪中期租界城区形成之后的城乡交错带,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外来贫困人口聚居区。至1949年建国前夕,上海约有1/4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棚户区,以来自灾荒频仍、经济落后的苏北地区的移民为人口主体。建国初期由于城市户籍的紧缩,棚户区的扩张得到了遏制,其空间位置由城市边缘进一步向中心城区位移。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再次活跃,棚户区人口成分更为复杂,除已获得上海户籍的原有居民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的比例逐渐增加。政府改造棚户区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改造力度最大的是1990年迄今的20余年,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中心城区内的棚户区大部分完成拆迁改造,其原有居民通过原地回迁等方式搬入新房,或集中迁往中心城区边缘的新建住宅区,这种曾经长期位居内城区的贫困群体的聚居模式才基本走向解体。从景观存续的角度,上海棚户区基本已成为一个历史现象,但从贫困文化的机理来看,原有棚户区景观的拆迁与改造并不等于贫困文化土壤的消失,今天中心城区边缘大量存在的“城中村”依然具有容纳外来贫困人口的基本功能,仍然具有孕育贫困文化的基础。
棚户区的污名与棚户区景观的变迁相伴发生,一直以来,棚户区及其居住群体的污名是上海城市文化生态中的典型现象。追溯其早期的发生过程,棚户区长期依存的乡村环境,以及棚户区人群的生计与乡村资源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其污名的构建中均起着基础作用。
首先,早期棚户区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具有显著的乡村特征,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属于一种“非城非乡”的过渡性聚落。在城市空间扩张之下,周边乡村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城市化转型,但这种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一般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较长时间地徘徊,这便为棚户区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一,农业用地被城市地产商收购,转向商业化开发,但未及转让的农地开始疏于管理,外来人口可容易地从本地人手中租到一些便宜的农地,搭建简易的房屋。在20世纪30年代的沪西,初来乍到的外地人“联合向地主立约租赁,或由地主允其结庐,随便纳若干之租费”;①在小沙渡一带乡村落脚的外地人,每月付1元左右的地租,即可租得1方丈的地皮,来搭建自己的棚屋,②这比起在市区租房几乎接近零成本,但其地理位置又贴近市区,便于在城市中寻求就业机会,由此吸引了众多的贫困人口在此集中居住。人力车夫通常几家合租一块地皮,每月只需付几角钱的地租。③有些疏于管理的农地甚至直接被占用,而业主则懒得去讨回。
其二,江南水乡河道密布,大大小小的河浜构成一批可观的潜在性土地资源。在乡村向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原来对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十分重要的河道丧失了原有的价值,由于疏于维护而渐趋淤塞,转化成一批产权不明的土地,进而被外来人口占用搭建,形成随处分布的棚屋区。许多苏北来的穷人先是以船只作为安身之所,栖息在河道上,河道淤塞之后,再转到岸上搭建简屋。1926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经公布东区租界线一带(位于城乡交界带)河浜上船户人口的变化,其结果是:1900年有11331人,1905年有12358人,1910年有12604人,1915年有11246人,1920年有10612人,1925年有14082人。④可见多年来仅仅在这一块位于城乡交界处的狭小区片内,船户人口就一直稳定在万人以上的水平。当初以船为家的贫民手头有一些积蓄之后,就会设法在河岸上搭建草棚、简屋,或者在浜上搭建水阁,使自己的住所稍稍安稳一些。“用船上的芦席、毛竹在河边搭个滚地龙”,⑤或者买一些便宜的毛毡、木头、稻草,盖一座简易的小屋,是许多人定居下来的开端。大量淤塞的河道成为棚户区产生的地基,体现了上海所处的江南水乡特征。
其三,在传统江南乡村,坟地随处可见,坟地周围的祭田则属于乡村家族的公益性土地,其地租主要用于家族坟地的维护和祭祀费用,而在乡村转型时期也逐渐成了族人觊觎出租的对象。传统上大家族的族人总以捐助祭田或祠田为公德之事,“族人皆量力来助,以其租供祭享外,则以为修葺之需,并体恤族之无告者”。⑥一些有实力的家族拥有几百亩祭田是司空见惯的事,中等之家也常有几十亩或十数亩。这些祭田是族中的公产,一般委托给有能力的族人经营租佃之事,但遇到私心严重或行为不端的“不屑子孙”,也常常出现经营不善,田产被变卖的结局,“非特田不可问,即祠宇亦变迁,仅余颓垣芜壤”。当时在城市空间扩张的步步进逼之下,风水形势发生变化,祭田的管理日渐松懈。一部分直接被城市建设所征用,例如曹氏家族的南山、北山田产,于民国四年被工巡捐局征用数块用以修筑打浦路、斜土路,在族谱中均有所记载。⑦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族中贪利之人往往变卖或低价出租祭田以获利。由于祭田本属族中公地,又不便大张旗鼓地变卖或出租,“租额大都较轻”,正常年份也就“三至五斗”粮食或折合成相应的金钱,⑧这也给棚户区的扩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除了上述地理环境方面的特征外,早期棚户区的部分居住群体长期保持着农民身份,其职业与生计的城市性比较模糊,同样也为这种居住区贴上了“非城非乡”的标签。当然这与本地乡村人逐渐转向城市谋生、将本地乡村的生计资源空出给外来人口很有关系。
城市周边的乡村人享有靠近城市的便利,许多人在城市找到了新的赚钱方式,至少其生活方式受城市的影响较大。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许多本地的农村人在城市的工厂中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周边)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已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苦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和杨树浦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①最初,本地人虽然在市区的工厂劳动,但仍然还居住在村庄内自家的房屋,土地也只是出租给他人。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曾经记载:“这里很多年前建起的工厂,从就近的农村吸纳了大批劳动力,这些工人不仅拥有自己的房屋,还拥有自己的土地。现在租界周围仍然有不少这样的村庄。”②但后来周边聚落的本地人中从事传统农业的逐渐减少,其居住地也移向城市社区。1951年对漕河泾镇三联行政村31户本地家庭户主的职业和居住地进行调查,发现工商户有8户,工人户有18户,仍然从事农业的只有5户。其中18户工人家庭的实际居住地均不在村庄内,地址分别是:天钥桥路赵巷14号、西康路697弄、虹桥路254号、肇周路平江里1号、永嘉路371号、常熟路38号、漕泾镇44号、小南门南仓街、浦东白莲泾50号、文庙路260弄、武康路38弄、合肥路148弄、永寿路60弄、徐家汇路、宁武路73弄等。③对漕河泾镇甲申、胜利等行政村以及姜家堰、沈家宅自然村本地人的居住地统计,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
本地人转为城里人,空出的土地在转化为商业用地之前,给外来人口提供了暂时赖以立足的生计资源。以苏北人为例,他们中许多人在家乡就以种田为生,来沪后没有别的技能,租田来种倒是较好的生路。在1951年龙华镇的土地调查中,大部分租种土地的佃户为外来户,租种的土地面积一般都在5亩以下。④有时较大规模的土地也租给有实力的“二地主、三地主”,由他们再分租给外来人。不过,这时传统的种植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租佃人根据变化了的水环境,为了适应城市的需求,不再沿袭以水稻、棉花为主的传统种植结构,而是以种植城市人需要的花卉、蔬菜为主,以此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据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是在上海近郊。”⑤这里的“上海近郊”,不仅包括离城较远尚未解体的乡村聚落,也包括紧贴城市边缘其内在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更易的城周乡村。据1949年10月份上海市政府对8239户棚户区居民的职业调查,在市区附近村庄种田的共有2291户,占总户数的1/4强。⑥21世纪初还有一些棚户区居民在回忆当初来上海谋生的门道时说,“刚来上海时是租种菜田赖以谋生”。⑦
总之,早期棚户区虽然在地理位置上贴近城市,但距离其变为城市社区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其乡村性长期存在,首先是因为棚户区的产生得益于传统乡村向城市过渡时期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所提供的契机,由于城周乡村土地的农业价值正在减小,而城市化的利用方式尚未建立,这一过渡期为棚户区的规模化发生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和发育时间。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上海棚户区,显著地体现了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特征,例如:上海地区河道密布,故而依河道形成的棚户区则随处分布,缺少空间规律,致使在其转为城市社区之后仍然显得杂乱无章,遍布残浜断河,加大了公共卫生管理的难度;坟地由于风水的关系与河道相互依存,数量众多且分布亦无规律,进一步加剧了棚户区的扩散和零星杂乱;河道淤塞促使农地价值相应减小,本地人放弃农业,更进一步助长了棚户区的蔓延。如此甚至可以说,早期上海棚户区的产生是江南水乡传统的农业生态链发生瓦解的一个结果,一开始就具有规模化扩展的有利条件,所以才造成后来其侵入城市的强势。当然,棚户区乡村性的长期保持,与其人口群体缺少城市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在城市谋求稳定职业比较困难也是对应的,棚户区人群的职业在城市社会生态中具有边缘性和不稳定性,早期人力车夫、临时雇工、打零工者一般占有较大比例,其次是小商小贩、小手艺人,还有部分无业游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在城市周边的乡村租地来从事农业和种植业,确为一种不错的生计门路。
然而从现代城市规划科学的角度来看,早期棚户区的产生折射出转型期城乡社会管理的失控,处于变动中的乡村地理环境与混乱失范的土地利用秩序,同规范的城市景观和有序的城市土地规划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成为棚户区后来向城市社区融入的先天不足,也成为棚户区污名的开始。
三、 乡村性与城市性的碰撞:棚户区污名的初塑
在第二阶段的发展中,棚户区从城市外围日益向城市肌体内侵入,其乡村性与城市性不断发生碰撞;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展,日益将棚户区包容进来。在这一阶段,棚户区在空间上更加靠近市区,其人口群体与城市人群的接触日趋密切,棚户区的环境、景观与种种弊病被城市人看的更加清楚,于是,由城市人所施与的棚户区污名传播开来。
毋庸置疑,棚户区的污名是城市人根据城市景观与社会秩序的标准来审视棚户区所施与的,污名的主要内容,除了棚户区景观的不入眼,就是其人口群体的声名狼藉,前者使整个城市有碍观瞻,后者则使城市人的生活秩序受到扰乱。
棚户区污名内涵之一:污秽的环境与边缘的位置
乡村向城市转型中失序的水环境变化,是造成近代上海城乡交错带污秽环境长期存在的根源。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的水网地带,在传统农业时代,纵横交织的水道是其最主要的地理景观,但是19世纪中叶突如其来的城市化对传统水乡的河道体系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至20世纪初,租界中心城区内的河浜已基本消失,越界筑路区(即当时的城市扩展区)内的河道系统处于紊乱状态,因水质下降而变得污秽不堪,乡村河浜淤塞严重,成为棚户区的滋生地。同时,由于工厂区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边缘,工厂可为外来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因此成为棚户区就近滋生的又一动力。于是在当时棚户区集中分布的城市边缘区,正在崩解的传统乡村聚落、密密麻麻的棚户区、星罗棋布的工厂或作坊、工厂排放的污水、以及淤塞污秽的河浜、星星点点的臭水塘,低洼泥泞的空地,构成了一种与传统水乡迥然相异的不和谐画面。①
棚户区所依赖的污秽环境,并非外来移民之过,他们只是本能地选择可资落脚的空间来搭屋居住,而城市管理者对转型期的水乡地理环境缺乏认识、缺乏前瞻性的规划,才是当时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例如大量的填浜筑路、越界筑路阻断了水流与潮汐,造成了随处可见的残浜断河,致使水体变质发臭等。但是,城市管理者与其他话语权阶层却有足够的能力,将环境的污秽与棚户区、工厂区、城乡交错带的存在联系起来,他们通过官方文件的定调、媒体等的反复宣传,有意无意地树立了棚户区的污秽与混乱名声,使棚户区的空间位置和环境特征尽人所知。例如1926年4月22日《北华捷报》的报道:“关于棚户难民的分布,以极司非而德地区和杨树浦地区最为声名狼藉,在闸北附近的城市边缘地区也有大量分布。”①1926年11月21日的工部局报告强调说:“租界之外有大量污秽的棚户区,但是在西区的租界线附近,紧靠小沙渡路西边的苏州河一带,也有不少贫民,他们主要依靠在租界内外的工厂里做工维持生活。”②上述提到的区域和马路距离当时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尚有较远的距离,但毕竟已经在城市管理可及的范围内,棚户区的种种问题引起城市当局者的不安,城市社会的关注意味着棚户区的城市性逐渐显露,但这却是一种受到社会各界的排拒、被边缘化的城市性。
至1930年代中期,租界边缘及其外围的棚户区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其环境污名在各界的排拒与诋毁中也变得日趋明确。尤其是日据期间,租界边缘一带小型工厂大量增建,甚至侵入了租界以内的居民区,一度使城市边界变得模糊。1937年后的租界边缘及外围的乡村地区,工厂、棚户与污秽河浜交错分布的景观进一步扩散,尤以苏州河以南的郊区地带最为严重。据1937年11月20日卫生视察员的调查报告:“在租界以外地区,完全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棚户到处搭建,却没有任何市政部门的许可证;棚户被用于各种生活用途,却没有任何防火及卫生设施;丝毫没有考虑邻近居民的文明需求。”③而棚户区的增建,又使河浜卫生陷入更加不良的境地。正如卫生处官员给工部局总办的汇报中所总结的那样:“棚户区的混乱状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河浜污秽淤塞。租界外河浜的糟糕状况,一定程度上对界内尚存河浜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外,租界对河浜周期清理不力,资金短缺、劳动力缺乏也是重要原因。”④1939年6月西区卫生官的报告也说:“整个大西路的卫生都很差,尤其是忆定盘路以西的区域。分布着污秽的河浜、难民棚户、棺材、以及小型缫丝厂。”⑤
棚户区污名内涵之二:庞大的底层人口
棚户区人口的底层特征也是备受诟病的因素,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棚户区人口持续增长,庞大的底层人口与潜在的社会问题,比起环境的污秽更加引人注目。中日战事发生后,由于租界区的相对安全性,上海城区内及边缘区的人口曾出现大幅度增长,1939年曾出现超500万的峰值,达到550余万。虽然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人口总量时有浮动,但总体保持在400万人上下。⑥人口密集、外来人口比重大、生活贫困、就业机会稀缺与廉价住房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使得城市周围乡村地带(包括小市镇)正处于乡城转型期的河浜、河岸、荒地、抛荒农田等低价值土地,一时间成为抢手的资源,依托廉价土地、以简陋材料搭建而成的不规范居住区逐渐形成并扩大规模,这虽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新移民的居住困难,但也造就了庞大的底层人口群体。例如沪西有500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法华镇,⑦在1941年时已变成以外来人口为主、棚户区为主要景观的格局,“(法华镇)陆家路口一带板木平房,鳞次栉比,达数百间之多,居民大都为苦力”,①曾经繁华一时的市河两岸更是棚户区最为密集的地方。
随着棚户区向城市内部的浸入,更多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找到谋生的门路,棚户区的城市性逐渐强化,城市当局试图对棚户区加强管理,但被迫和不情愿的意味十分明显,其对棚户区底层人群的排斥态度和管理上的被动性实际上起着塑造棚户区污名的重要作用。到了1920年代,闸北火车站周围、虹口中虹桥一带、南市董家渡附近、沪西曹家渡等大区片已成为“江北”人(或称苏北人)居住的集中区域,形成了规模化的棚户区。虽然这种社区具有城市社区的基本属性,例如人口密集、建筑呈现集聚式或联排式、居民职业以非农产业为主、依靠城市讨生活等,但又未完全脱离乡村人群的某些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市政部门的官方档案,还是媒体在报道发生于棚户区的新闻事件时,其心态上的排斥倾向和对底层人群的俯视态度清晰可见,这等于是加积了棚户区的污名。例如1926年4月15日《申报》的一则报道称:“住居闸北之江淮客民,每届阴历三月,举行都天神会,会中除执事旗伞之外,加入龙灯及香阴皂隶等,兴高采烈,如醉如狂,以迎神消灾为由。严厅长以现值戒严期内,此种劳民伤财之举动,严令禁止。而司令部因该商民等一再环请,已姑予照准,该会已于昨日举行矣。”②首先,该报道将这些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只不过是居住在棚户区集中地带——“闸北”的人们,直呼为“江淮客民”,暗示城市主流文化对于这类人的不接纳与不认同,“江淮客民”之于上海,似乎只是短暂逗留的过客,他们不具备在这个城市正常生活的能力;其次,连这些人从家乡继承而来的传统的“都天神会”仪式,也被认为只是愚昧无知,劳民伤财的行为。通过当时各种媒体对“江北”一词的反复使用,江北人逐渐成为上海城市社会底层群体的代名词,其居住、职业以及生活习俗等亦被贴上“底层”的标签。反过来讲,媒体通过对江北人生活状况和文化特征的的反复渲染,使棚户区群体的污名逐渐传播开来。
概而言之,由于棚户区在整个城市空间区位中的边缘性、卫生环境的污秽、底层人口的大量集聚等特征,又因为城乡交界带向规范城市区域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棚户区的污名由此产生并长期持续。在这一时期,棚户区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之间的差距,其乡村性与城市性的碰撞,棚户区人群与其他城市人群的近距离接触等,是其污名不断加积的主要动因。
四、 嵌入城市:棚户区污名的深化
在第三阶段的发展中,棚户区在空间上日益嵌入城市内部,成为城市居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污名的内涵也进一步丰富与深化。1920年代上海的房荒问题已日趋严重,闸北、南市及虹口等城市设施相对薄弱的区域,此时成为棚户区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这种社区的快速扩展与无孔不入,使相邻社区的人们倍感警惕,也引起媒体的更多关注。其中《申报》对棚户区火灾的大量报道,颇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社会对棚户区危险性的认知,他们对于棚户区城市性的认同,充满着无奈、犹疑与矛盾,但却不得不与这种社区比邻而处。
由于建筑材料简陋,房屋间距极小,河流又多淤塞缺水,城市给排水系统并未覆盖到此,因而棚户区成为火灾高发的区域,威胁着城市日常生活的安全。这一时期《申报》对棚户区火灾火警的大量报道,逐步构建起棚户区作为“危险社区”的形象,其不堪一击、脆弱、临时性的景观特征,以及其居住者甚至是邻居的生命随时会被大火吞噬的可怕,一时间得到强有力地渲染。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棚户区作为城市社区的性质似乎已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承认。
例如1930年7月29日《申报》载:“沪北临平路底胡家木桥路南首太平桥路间之平房草屋,昨日下午二时五十分左右,忽生火警,被火焚毁者约三十余间,并有八十岁高邮老人吴万兴周身灼伤。火场地盘略作方形,四周均系瓦屋楼房,遭殃之草屋及平房,均围于中央者也,被灾之区,以祥安里为通路,实则狭窄异常,为一小弄耳。出祥安里北行,即为胡家木桥路。越桥为庙东路,与庙东路相对者为临平路,两路之间,隔以小河,灌救时即取水于是,其地并无自来水或自流井,居民饮水咸多仰给于此河,火场四周,被屋包围,是以出路甚少。有之,惟接通胡家木桥路之祥安里。”① 这则新闻首先是将发生火灾的棚户区作为城市社区来看待,其地理位置值得注意:该棚户区位于城市马路纵横交错(胡家木桥路、太平桥路、庙东路、临平路)的虹镇附近,与一般市民居住的石库门里弄房屋错杂分布,被祥安里等石库门里弄所包围,这说明它已完成了由乡村区位向城市区位的过渡,成为嵌入城市内部的社区。换言之,是城市的扩张将该棚户区包围在内。其次,该报道又着意勾勒出一幅不同于一般城市社区的景观画面,凸显出棚户区在规范城市空间中的异质性:狭窄、拥挤、简陋、草屋、苏北人(高邮老人)、无自来水、饮用肮脏河水、缺防火能力、缺消防用水、缺灭火通道,总之这种社区不堪一击,在城市中立足不稳,甚至保留着几分乡土气。
在很长时间内,对各处不断发生的棚户区火灾之报道,都持续着上述腔调:犹疑、矛盾而又无奈。上海老城厢及城外沿黄浦江的南市码头区,原是传统市镇与乡村交融的鱼龙混杂之地,但近代以来在严重的人口压力下,也滋生了大片棚户区,改变了原有的景观面貌,形成码头、货栈、商铺、摊位与棚户区错杂相处的格局。1947年6月8日的《申报》报道了这里发生的火灾,火灾烧毁的棚户区为“南市小南门外南仓弄马当弄一带,有草棚四十余间,住户大部分为三轮车及人力车夫”,且火灾发生后,因“地处狭窄,水源缺少”,致使“全部草棚变为焦土一片”;②1949年1月8日火灾涉及的棚户区,地处“南市薛家浜路新街”, 被焚棚户达三百余家,其中人口大多为来自苏北的苦力。③
《申报》某些报道还反映了城市当局在对待棚户区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因其建筑违规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而排拒之,又因其容纳贫困人口的巨大能力而承认之,无奈之下只有力争改善其现有条件,以确保一时的相安无事。棚户区房屋一般属于违规建筑,缺乏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建筑手续,加之污秽的卫生环境和犯罪等治安问题,城市政府本能的反应是遏制其扩张,对其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但由于住房紧张、贫困人口大量存在等问题,当局对于已经成型的棚户区,又往往采取妥协措施,尽力将其纳入常规市政管理的范围。从下引这段新闻稿中大体可窥见城市当局对待棚户区的姿态:“市政当局已决定于明日起开始取缔在禁建区内建造新棚户,但旧有棚户则仍准予继续。惟如有妨碍交通,或架跨河浜等情,非拆除不可者,将尽量予以出路使之迁移。明日起,市工务局将会同警察局组织一巡回队,由该两局有关人率领工匠等至各处巡逻。如遇在禁建区内已搭未成之棚屋,则令工匠协助拆除,交还材料,令其在非禁建区内盖造。”④当时上海正处于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复原时期,由于难民流入、时局动荡等综合原因,棚户在上海城市边缘区甚至城区内部的扩展十分迅速。市政当局为解决“房荒及军民经济问题”,曾采取鼓励搭建临时房屋的举措,专门划分了许可建造棚屋的区域;对于即已形成的棚户区,则采取了软性管理的手段,尽量将其纳入规范化管理。这标志着城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棚户区的合法性,但对其未来的发展却缺乏长远规划。
市政当局对棚户区的统一管理主要体现在清洁、防疫、卫生设施等方面,试图先在环境上缩小其与一般城市社区的差距,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方便操作的路径。在日伪时期(1938-1945年)已经建立比较系统的公共卫生管理办法,例如在其美路、天同路、邢家宅路等草棚相对密集的区域设立施疗所,进行霍乱预防措施,预防的办法包括:清洁检查、健康检查、防疫注射、采便检验等。由虹镇施疗所的主任医师率领全体员工前往各草棚对户口进行逐一健康检查,同时对各棚户进行清洁检查。若是发现有病态者咨其到所治疗,如有疫病之嫌,则立即采便送往同仁会进行检验。发现棚户内有污秽不洁者,则令其改善,并且要对其宣讲卫生条例。①卫生局还对各地草棚住民实行强化预防性注射。鉴于棚户区居民大多属于苦力,早出晚归,卫生局特别规定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为注射时间,为的就是使每一位棚户居民都能够接受霍乱防疫注射。②
虽然在各方努力之下,棚户区逐渐进入城市规范管理的范围,但在整体城市居住生态中,棚户区毫无疑问处于最低级的档次上,有了其他“高级”的城市社区作为参照,棚户区的底层污名反而愈加凸显。在1934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对工人生活程度所进行的一项专门调查中,关于住的方面,将棚户区列入了工人居住房屋类型的最末等。其他两等分别是:(一)优等住屋,大都是楼房,有石库门式(有天井)和东洋式(无天井)两种;(二)次等住屋,大都是旧平房,质料较差。而棚户区则是处于荒僻之区或设施不完善区,环境污浊、租金最便宜的一种临时住屋。③1947年《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虽然承认城市中到处分布着棚户区,但却将其视为城市中的“另外一个国度”:“你走到棚户区去一看,密密麻麻一片黑海和神经不健全的人,臭气可以使你昏倒。妇女孩子不停的吵嚷和打架也可以使你昏倒,那似乎是另外一个国度。土地、二郎神和火神,统治着人们的灵魂,胖胖的绅士,地产的主权人统治着他们的肉体。另外,还有一批年青力壮、用拳头打出天下来的人,他们的语言就是法律,三句不对,就可以把你‘做了……”④尽管言辞有偏激之嫌,但至少代表城市人群对棚户区异质性的一种认知。
由上述分析可见,城市社会在棚户区的社区性质与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存在显著的矛盾心态,因此也不断调整着对它的应对措施。棚户区嵌入城市肌体内,棚户区人群成为城市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这是棚户区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其受到的诟病也进一步多样化,其污名的内涵也进一步清晰化,并不断累积和加重。
五、 讨论:棚户区污名的发生机制与改善前景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上海棚户区在融入城市空间与社会的前期所承受的污名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其污名的发生机制,既体现了传统江南水乡环境在城市化驱动下发生无序变化的地域性特征,也体现了外来贫困人口在城市社会生态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以及融入困难的共性特征。概而言之,这种污名是城市化过程中一种典型的人地关系矛盾和土地利用矛盾在文化上的体现。
首先,上海城市空间的扩张对区域水环境造成改变,河浜体系的瓦解引起乡村地理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农业经济的式微,这为棚户区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条件。早期棚户区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城市,但其环境生态和人群生计的乡村性长期存在,乡村土地利用方式向城市的过渡期为棚户区的规模化产生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和发育时间。所以可以说早期上海棚户区的产生是江南水乡传统的农业生态链发生瓦解的一个结果,一开始就具有规模化扩展的有利条件,所以才造成后来其侵入城市的强势。
其次,棚户区污名的确立与加积,则主要由掌握着舆论控制权和主导权的城市管理者和主流文化阶层来推动。对于同美好城市生活“背道而驰”的棚户区,他们本能地采取了排斥、贬抑的态度,而对于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劳力阶层在社会经济、服务链条中所扮演的必不可少的角色等,却未做出足够的正面理解和评价,贫困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对政府的期望等看似微小但意义深远的社会问题,在主流文献中更是少有记录,政策上的引导更为缺乏,这导致棚户区的负面文化形象不断地被构建、宣扬、扩散和传递。
经过长期的累积,上海棚户区的污名也发生了模式化,并且具有景观与社会方面的丰富内涵。棚户区污名在国家政治局势十分动荡的20世纪40年代达到高峰,这从当时报纸媒体对棚户区问题高频度的报道中可以证明。戈夫曼曾指出人际关系中的施污现象在污名模式化之后是很容易发生的,类似于对号入座的意味:“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马上就有迹象表明他具有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使他可能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成为一种不大值得羡慕的人——总而言之,一种坏透了的,或一种非常危险的人,或一种非常懦弱的人。他就是这样在我们心目中从一个没有缺陷的、正常的人贬低为一个有污点、被轻视的人。这样一种属性就是污名。”①随着棚户区污名的持续和内涵的加积,淡化污名的难度也相应增加。
1949年前的城市当局对于已经成型的棚户区,也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尽力将其纳入常规市政管理的范围,例如专门划分了许可建造棚屋的区域,帮助棚户区居民防治疫病和改善卫生环境,但这些措施毕竟缺乏主动的谋划和建设性的眼光,具有较强的权宜性,所以对于淡化棚户区的污名收效甚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政府对棚户区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措施有助于推动棚户区融入城市的进程,对于淡化棚户区的污名起到了实际作用,例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清洁棚户区卫生环境,设立识字班,提高棚户区人口文化素质,安排棚户区人口进工厂就业,解决其生活困难,财政拨款帮助改良棚户区住房条件等,就是对已经固化的棚户区污名的试图扭转。建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正是围绕着加强棚户区的城市性,减少其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距离来进行。
“贫困文化”是西方贫民窟文化研究者惯常采取的归结点,污名则是贫困文化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本文认为,无论早期棚户区污名的内涵与程度如何,上海城市的棚户区污名及其社会效应在1949年后的演变中并不构成一种贫困文化。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棚户区人口虽然在居住条件、教育状况和职业身份等方面仍然偏向低端,在城市整体社会生态中处于底层的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自卑感,能够比较明确地感受到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歧视,但其文化心态的积极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在社会调查中了解到:今天棚户区的老居民们对过去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过于深刻的记忆,对自己的上海人身份有深刻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足,对未来生活的提升有明确的期待等,这种心态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棚户区改善措施有直接关系,也明显有别于刘易斯根据西方城市贫民窟文化状况所定义的贫困文化。
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无疑应当存在于城市贫困社区,而这种社区的居民有着明确的社区和领土意识,他们有着明确的贫穷身份感、对未来的绝望感以及与周边社区的隔离感。以美国许多城市的黑人社区为例,居住其中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人,具有单一的族群性,在物质空间方面他们是被隔离的,受到中产阶级、白人和新教徒的歧视,在居住、读书、工作、教堂、娱乐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是被隔离的状态。这些因素加深了他们的自卑感,某种程度上也加深了他们对权威阶层和主流社会的敌意。②上海棚户区的文化与此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社会分层、贫富差距的极化效应相对较弱时,棚户区群体能够较为平和地认识自身的生活状况,并具有城市文化的归属感和安居乐业的安全感。建国初期政府提倡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大力改善棚户区的卫生环境和基础设施,提高棚户区人口的就业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棚户区人口迈出了“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关键一步。整体看来,他们与整个上海城市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奋斗历程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普通人在城市化大潮中的人生选择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说,改善人生境遇,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正是他们当初涌向大都市的初衷。这一心态情境的形成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在我国,“没有贫民窟”一直以来受到舆论的正面宣传,这种宣传是有其合理性的。虽然贫民窟与棚户区在概念上常被混用,但从制度层面和发生机制来看,二者确实存在区别。我们确实无法否认城市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贫民”群体,今天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确实居无定所,居住条件达不到城市规范社区的标准,但政府对此问题的正面应对态度也是不可否认的,每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题目即可说明问题,政府支持学者进行大量的外来贫困群体融入城市的研究。在现代时期国家政策的调控下,棚户区持续地得到改造,棚户区居民的城市融入也一直在推进,甚至是中心城区的退化社区也在不断更新,也就是说,底层社区景观的不断解体,大规模的贫民聚居模式难以形成,起码动摇了贫困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
再从土地管理制度来看,中国实行土地国有制和城市发展用地的统一规划,政府主导各类土地的调配和使用,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印度孟买、巴西里约热内卢那样大型的贫民窟。在缺乏贫困人口大规模集聚效应的条件下,消极颓废的贫困文化是难以形成的。
在西方早期的移民史著作中,“适应”这个词指的是“移民根据目的地的状况调整自己的过程”,该过程有几种分类:“在社会结构的平等上逐渐同化进入,逐渐适应目的地的文化,适应目的地人群的习俗和价值观”;①荷兰移民文化研究学者比杰尔(Beijer)也指出:从乡下来的移民首先从精神上对新的生活做出反应,人人都有自己的性情和自己的反应方式,②因此,城市新移民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中,更需要的是精神和人格的平等与尊重,这是政府层面和主流文化层面可以努力的方向。但从本文研究来看,在上海棚户区形成和扩散的前期,贫困群体在精神和人格上与城市人的平等无从谈起,其文化上的城市性十分薄弱,所以导致棚户区污名的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