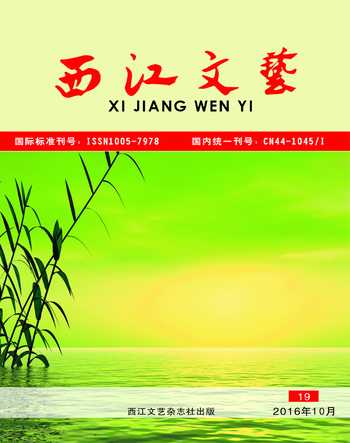哈尼族民间象征性交换研究文献综述
2016-05-30王亚宁
王亚宁
【摘要】: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墨江哈尼族地区存在的民间象征性交换进行梳理,从象征性交换的理论研究、哈尼族民间宗教仪式研究两方面进行概述,总结关于哈尼族象征性交换研究成果以及结合目前田野实际丰富哈尼族研究中的个案。
【关键词】:哈尼族;象征性交换;传承;文献综述
一、关于象征性交换的研究
1、象征性交换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从民族志的角度对礼物交换的研究由来已久,从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到莫斯的《礼物》再到马歇尔·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西方人类学家对礼物交换基本确定了互惠原则。与此相对,中国学者对礼物的研究起步较晚,最系统的是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既是对互惠原则的回应也是对于中国礼物交换现象中“面子”、“沾光”等本土概念的分析。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经济角度的交换原则有别于中国人际关系的礼物研究。在夏莹《象征性交换:鲍德里亚思想的阿基米德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一文中,概括的分析介绍了经济交换与象征性交换,在阐述过程中也提到象征性交换不受任何价值规律的影响和约束,作为一种交往方式,象征性交换必然要受到某种强制性因素的制约,以保证交换的持续进行,只不过这种强制性约束不再局限于价值,而是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也就是莫斯礼物交换中所包含的“交互性”。并指出在原始社会中,象征性交换作为特有的交换方式,是对本真的交换模式的一种理想构想,经济性交换作为一种异化形式游离出象征性交换,却不得不以其为复归理想而回到象征性交换。
2、象征性交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呈现
郑宇《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献祭礼物的象征性交换》(《民族研究》,2009年)中提到哈尼族丧礼中出现了即赠即还的献祭牲畜礼物,通过象征性交换不仅完成了经济层面的作用,还充满了社会功能乃至宗教方面的意义。郑宇、谭本玲《经济消耗与社会构建——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的经济人类学阐释》(《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中通过哈尼族私人生活领域仪式中经济耗费最大的葬礼来解释象征性交换,指出象征性交换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它精巧的运作过程、复杂的交换流程、层次分明的结构特征,多样化的功能和意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适应当地现实状况的合理安排。郑宇《箐口村哈尼族社会生活中的仪式与交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针对象征性交换,很明确的指出在元阳箐口村私人仪式交换中,摩批主持私人祭祀仪式后,会获得一定的“报酬”。
二、哈尼族宗教文化及其仪式研究
哈尼族的研究作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笔者在参阅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对于哈尼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族源研究、哲学与原始宗教研究、文化研究、民族习俗研究等方面。
1、哈尼族宗教文化研究
白玉宝《哈尼族哲学思想探索》(《民族学与博物馆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肖万源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伍雄武《哈尼族哲学思想的萌芽》(《思想战线》1993年,5)中都介绍了哈尼族《奥色密色》、《哈尼阿培聪坡坡》和《雅尼雅嘎赞嘎》中所涉及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与神灵观念;李国文《论哈尼族社会中的原始宗教》(《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1)一文将哈尼族原始宗教信仰总结概括为四个方面:(1)灵魂观念和古传葬仪、祖先崇拜;(2)与氏族祖先崇拜相关联的村社神崇拜;(3)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与相关的农业祭祀;(4)原始占卜与巫术。毛佑全《滇南哀牢山区哈尼族占卜、招魂述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4)介绍了哈尼族占卜招魂的宗教性习俗;《哈尼族祖先崇拜文化内涵》(《云南社会科学》(1993,6)中则提出哈尼族庞杂的祖先崇拜都与血亲家族观念有关联;李学良《关于昂玛神的性质》(《云南社会科学》1994,3)中认为,哈尼族“昂玛”神是一个几经变化了的复杂的神灵实体。其中毛佑全《略论哈尼族馈赠礼俗及其社会功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2)中哈尼族民间馈赠习俗是一种有形的文化传统现象,是物质文化、行为传承文化以及民俗行为的观点给后来笔者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2、哈尼族摩批研究
哈尼族“摩批”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在哈尼语中,意为“有智慧的长者”,其具有的职能及内涵都超过了汉译的“巫师”。在传说中,摩批和“首领”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无论是个别家庭的婚丧嫁娶、村寨中的集体社会活动,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摩批至高无上的地位依旧不能取代。因此,研究哈尼族的文化传承,研究民间象征性交换对文化传承的影响,研究哈尼族摩批是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摩批的产生:在王清华《哈尼族社会中摩批》一文中,王清华从哈尼族《三个神蛋》的传说讲起,论述了摩批的历史地位及其社会功能,并引出哈尼族摩批的现实社会职能——文化的保存与传播、主持宗教活动、指导农业生产、主持人生礼仪、行医治病。其中,在主持宗教活动部分中,提出摩批作为神、人、鬼三个世界相互沟通的媒介是哈尼族宗教活动中的主持人,并在参与集体性祭祀活动中,摩批主持活动和仪式的能力得到淋漓精致的发挥,并有着十分显耀的地位,然而本文只是对了解哈尼族摩批的概况具有指导意义,却并未涉及与论文写作相关的交换与传承。
摩批的社会功能:黄绍文《哈尼族村社祭司——咪谷》一文則从咪谷的产生、咪谷与摩批的关系、咪谷精神的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入手介绍哈尼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咪谷。在咪谷产生的论述中,咪谷的产生方式、组成人员、被选举条件、选举条件等都给后来笔者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二手田野资料。郑宇《哈尼族宗教组织与双重性社会结构——以菁口村“摩批——咪谷”为例》一文,从《哈尼族宗教组织中的“摩批——咪谷”、哈尼族双重性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成与演变、哈尼族宗教组织与双重性社会结构的互动三个方面介绍了哈尼族摩批并在论述中涉及了哈尼族传统的祭祀仪式,提及“咪谷的主要任務是每年重复性的主持生祭、熟祭,然后代表全体村民向神灵祈福”。毛佑全《哈尼族的“摩批”和原始宗教残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3)一文介绍了哈尼族的“摩批”驱邪除害,祈福的社会功用。
摩批的传承:哈尼族地区由于没有文字,所以其文化传承就不能依托社会教育系统、通讯设施、大众传媒、文化交流,主要依靠哈尼族的原始宗教。哈尼族的宗教职业者摩批的传承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哈尼族文化的传承。李宣林《哈尼族的原始宗教与民族文化传承》中就哈尼族的原始宗教在哈尼族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进行论述,并同时肯定了摩批在哈尼族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就其传承模式也指出了自然神授和人为、师承两种。张金文《摩批——哈尼族文化传承者》中提到摩批在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职能,并提出了关于抢救和保护的工作思路。潘立勤《哈尼族咪谷、摩批宗教文化保护研究》中着重分析了咪谷、摩批对于文化保护传承的意义。李泽然《论哈尼族的摩批教育》中提到了摩批的教育传承形势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