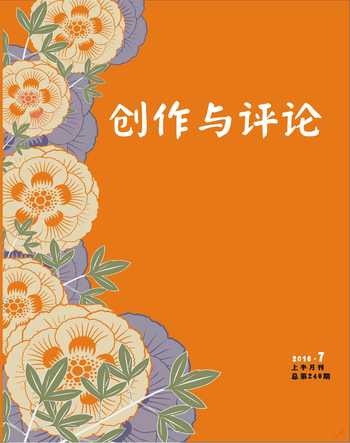“食”文解字
2016-05-30陈绍龙
羹
“喝吧。”
冬燥,口干,唇上起了层“锅巴翘”。我不时地用舌头舔,把唇润湿,这样舒服些。不过两日,唇上的“锅巴翘”倒了落了不少,哪知,患处却布满了血印,像涂了口红似的。多有不适,感到很是难受。爱人见状,说上火了,忙着买了莲子、白木耳、枸杞、冰糖熬了半锅的羹。一大早,她便把莲子木耳羹端到了桌上。
熬煮过的银耳粉嘟嘟的,与白瓷碗浑然一体,浓稠而有质感,素雅清淡,绵糯玉润。莲子已花,瓷白的莲子仁混搭其间,嫩绿的莲心和褚红的枸杞成了点缀,纵使色彩对比鲜明,却也不闹不喧。玲珑剔透,透着高雅和静气。汤匙在碗边划拉,一时都不忍搅动。
“自此长裙当垆笑,为君洗手做羹汤”。配料,清洗,厨间忙碌,洗手更衣,小火慢炖,静心地守候,小心地观照,耐心地等待,氤氲的雾气里,笼罩着羹的味道,家的味道,爱的味道。我不比司马相如的才气,爱人也没有卓文君的财产,共有的却是彼此真实的生活,相濡以沫日子都叫一杯羹吐露着浓浓有的热气。
在古代,羊乃食中至尊。在古人们朴素的意识里,拥有一只“大羊”才是“美”的。中原农牧民族羊为鲜。“羹”中有两只“羊”。“羹”之美自然不容怀疑。“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岑参见花思羹,不怀疑他对羹的钟爱;“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杜甫在胡饭里嗅到了羹的美味;“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花羹”,韦庄说的更是直接,江上好的时光里,食紫花羹那是一定的喽。猜想也罢,推测也罢,思念也罢,羹如诗美,在诗人的脑子里,在食客的心中,早已扎下了根。
隔壁一张姓邻居,叫张家根。而他偏偏好吃螃蟹羹。自己也会做。他开了一家小餐馆,螃蟹羹成了他家的招牌菜。螃蟹羹鲜香滑腻,营养好。他说螃蟹羹是羹中的佳品。每年秋季螃蟹上市的时候,他都会买好些螃蟹回来煮熟。去壳,敲开螯,用牙签把里面的蟹肉细剔出。然后把蟹肉、蟹黄、蟹膏打包放在冰箱里,留日后做螃蟹羹,差不多能吃上一年的时间。更有意思的是,他的餐馆的名字就叫“张家羹”。好些吃客到他小餐馆吃饭,也都是冲着螃蟹羹去的。
早年家贫,奶奶却能给全家做出一锅鲜美的豆腐羹来。说是豆腐羹,其实,也不过半块豆腐。葱、姜煽出香味,把胡萝卜切成丁,将海带切成发菜般的细丝,豆腐切成豆粒大的方块,半锅的汤里仅有的豆腐和海带们依然显得料少。奶奶毕竟是做羹的好手,她把一只鸡蛋打成花,放在沸水里搅动,说也怪了,蛋絮细若游丝,仿佛满锅都是,最后,加上山芋粉的勾芡,整个一锅羹变得内容丰富起来。豆腐白,蛋花黄,辣椒红,海带褐,色汁好看,亦菜亦汤。要是在豆腐羹上淋几滴麻油,或是再放些炒香碾碎的花生米,那简直是羹中的极品了。这是我奶奶说的。我在奶奶的描述中有过好多美好的想象。其实,奶奶做的豆腐羹已经很好吃了,那淋过麻油、加了碾碎炒香的花生米的羹是什么味呢。羹如诗,奶奶对羹的描述也就这样搁在了我的心里,使对羹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成了憾事,自小,我就没吃到那淋过麻油、加了碾碎炒香的花生米的羹。好多年过去了,如今,吃上那淋过麻油、加了碾碎炒香的花生米的羹也决不是难事,奶奶早已离开了我们,这,又成了我心中更大的憾事。
鲜
“鲜”是一道菜。鱼羊鲜。
那天到饭馆“小菜香”吃饭,老板娘亲自端上来一碗汤并没有立时离开,望着我。她间或余光飘过汤碗。我猜出了她的心思。小菜香门脸不大,老板娘也兼做厨师。我是熟客,有什么拿出手的菜品她会让我给她“提提意见”。
我舀了半勺入口,象是认真地在品尝。
“鲜!”
听到我的评价,老板娘紧张的脸片刻放松了下来。笑意散开,象是有一串小鱼忽儿兴奋地在眼角四下逃窜,进而泛起了水花。
在老板娘转身的当儿,我又不禁把勺子伸进汤碗。汤,乳白醇厚,散开的热气也变得绵柔细软,丝丝缕缕,一时间,屋子里满是香气。什么汤?同桌的几个朋友自然难敌我“嘶嘶啦啦”喝汤声的诱惑,跟着拿起了勺子。只是一会儿,几只勺子在碗边划过细响之后,汤穷鱼现,碗底还有细碎的肉丁。是羊肉。
“鲜!”
“鲜!”
朋友跟着呼应起来,夸说菜的好。哪想,我不经意说出的一个字,却叫我言中了菜名。
中国字表意。中国字有味道。望文生义,望字生义,生出一道菜谱来。有人打起了“鲜”的主意,做出了这道菜。
“鲜”成了一道菜。叫我想不到的是,这道菜还曾是宫廷菜。在南宋称它“鳖蒸羊”,口味与“鱼咬羊”相类。小菜香的老板娘称这道菜叫“鱼羊鲜”。
北方人以羊为鲜。南方人以鱼为鲜。北方多山。南方多水。盱眙原属安徽,上世纪50年代划归江苏,地处淮河岸边。淮河秦岭一线是南北的分界线。鱼羊同蒸,聚南北两鲜于一盘,能做出一道“鱼腹藏羊”的鲜羊鲜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鱼羊鲜骨酥肉烂,不腥不膻。后来我才知道,鱼羊鲜是微菜中的名品,想来自然不怪。
做鱼羊鲜用鲜腮鱼,鲫鱼居多。鱼取下头尾,不宜过大,不出一斤为佳。带皮羊肉好,切成方块。鱼煎至皮黄,佐以姜、葱煽出香味,放入肉丁,小火烧煮,大火收汤,绍酒去腥,胡椒去膻,白糖提鲜,酱油着色,菜心添彩。
传说有个农民带着羊过河,羊不慎落水,鱼争而食之。有渔民轻舟荡过,撒了一网,捕上来的都是肚子里装满羊肉的鱼。渔夫不舍羊肉,于是连鱼一块蒸煮,出锅的鱼奇香无比。继而名声大响,多有仿效,“鱼羊鲜”便在江淮一带流传开来。
传说罢了,我不信。鱼能撕开羊皮?做鱼羊鲜的多为鲫鱼、草鱼,它们哪有“食人鱼”锋利的牙齿,水虎鱼们在南美亚马孙河呢。生拉硬扯把“羊”与“鱼”搁一块了。传说自然无须考证,也没法考证。这也无妨。鱼羊鲜倒是真的。其菜是鲜美无比。纵使你没有太好的厨艺,把鱼和羊肉一块儿随意煮了,鱼汤鲜,羊汤鲜,鱼羊混煮,哪有不鲜之疑。难怪那天朋友喝过汤之后私下调侃,哇噻!怎么感到胸前发胀,莫不它鲜得能给男人催奶。莫非鲜汤比酒烈,说了醉话。笑煞。
糟
糟是酒渣,能食,也指用酒或酒糟腌制食物。
“糟糠不饱”,《盐铁论》里提及的糟就是吃的。酒之余,粮之余,糟糠终究是酒和粮食的下脚料,营养不多,口感不好,“吃糠腌菜”自然不是好生活,吃起来还没面子。
《笑林广记》里有一则笑话。一人家贫,喝不起酒,每次吃两个糟饼就有醉意。有朋友问,你早上喝酒了?他如实答,我吃的是糟饼。回家告诉妻子。妻子不比丈夫那么愚钝,说你就告诉朋友说喝酒了,这样有面子。又遇友,他按照妻子的意思回答。朋友问,酒是烫着喝还是凉着喝的。他每答,是油煎的。此公又回家告诉妻子。妻有愠色,又教他说,是烫着喝的。复遇友,如是答。哪知朋友又逗他,你喝了多少?他伸出两手指:两个。还是糟饼呀。
虽是笑话,但也可以看出,旧时,吃糟在平民穷人中也很常见。糟是粗劣食物。糟糠之妻,说的就是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
糟货却是好东西。
腌糟货是中国美食的一绝。几经沉积,几经发酵,食物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公不见肉糟淹更堪久邪”。《晋书》里话也告诉我们,糟过的东西保存也久。这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消受糟货。
南方的黄梅雨季度,妈妈每年都会想着为我们做糟豆腐。老豆腐,切成方块,在锅上蒸过,晾干,码在大大小小的广口玻璃瓶中,加上糟卤、盐,密封。一周后,糟豆腐柔糯可口,香气扑鼻,是早晚佐餐的佳品。妈妈会把这大大小小的瓶子让我们拿回家去。吃完了,妈妈又会把塞满糟豆腐的瓶子给我们。糟豆腐细腻鲜香的口感里,让我们品出了妈妈菜的味道。
家乡人有酿米酒的习惯,酒多了,酒糟也就多了,制作的糟货也便多了。家乡人除了糟豆腐之外,可糟之菜异常丰富,有糟鸡、糟鹅、糟鸡爪甚至糟毛豆等,似乎是入口之物,皆可糟之。
糟货的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的《楚辞》便有记载,南宋之后吃糟成风,什么糟鲍鱼、糟羊蹄、糟猪头肉的应有尽有,到了元、明、清,除了市上供应糟制品外,已发展到家庭自制了。
“旧交髯簿久相忘,公子相从独味长。醉死糟丘终不悔,看来端的是无肠。”陆游写的《糟蟹》今天仍很普遍,超市里便能买到。我爱人不习惯吃糟蟹,嫌它生,有点腥味。这倒好,每次从超市里买回糟蟹,我都是独自消受。
“鳊、鲌、鲤、鲫”,都是上等河鲜,淮河鲌鱼曾是贡品,受到皇上的垂青。“寒潭缩浅濑,空潭多鲌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梅尧臣的《糟淮鲌》为我们家乡的糟鱼扬了名。“楚人怀沙死,葬腹千岁余。今兹有遗意,敢共杯盘疏”。只是他心不在鱼,吃着吃着,想起他的政治偶像屈原来了,睹物言志,这样的糟鲌鱼,吃出了另一种的滋味。
因糟而成的小吃更具风味。糟田螺肉质鲜嫩,汁卤醇厚,入口鲜美,成了上海的著名小吃;糟辣椒不则是云南贵州的调味品,又因其香、辣、酸、脆的独特风味,成了不少人喜好的佐餐小菜;醪糟这道家家喜爱的四川小吃,又哪里只是四川人喜欢呢。每每看到电视上那则雨巷里挑着木桶、戴着篾笠的妇女唤“黑芝麻糊”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卖醪糟的场景来。醪糟不只是市民百姓的最爱,它也成了高档宴会上的一道甜食。
糟糟鲜,朝朝美,所有的日子,有了糟的存在,仿佛更有滋味。
脯
脯,从月,从甫,月是肉;甫,亦声亦形,也是肉。《说文解字》里说,脯,干肉也。这个拥有“两块肉”的“脯”,从造字本意来我们能揣摩出它的意思,一是古人加工佐餐的干肉是如何烦复精心,再者,这干肉是有何等的美味。
梅尧臣在《腊脯》里说它“考之新目录,美脆胜庖牛”。“巡檐攫脯脩,入舍掠脍炙”,陆游说的“脯脩”、“脍炙”都是肉。
干肉香。我们叫它腊肉。入冬以后,冬至起,日渐长,阳光足,家乡人便开始腌腊货了。不只是腌肉,也腌鸡,腌鸭,腌鱼,还有野兔什么的。十天半个月之后,肉出卤,洗净,挂在檐下,借着阳光的力,其色渐次沉稳,其香渐次溢出。年渐近,看到这一排在在小小的腊货,过年的滋味你有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便会觉得日子有滋有味,殷实而富足。
汲取流岚风雨,汲取阳光的汁儿,几多沉积,几多吐纳,腊肉的味道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其散发出来的陈香非一般食物可比。无须添加任何佐料,切几片腊肉放碗里,碗放在煮饭的米上,饭菜同出。不只饭有了股淡淡的腊香味,揭开锅盖,满屋生香。路过的村民两三天都会记着问你:你家蒸腊肉了?
腊肉中的金华火腿算是有名响的了。它给腊肉扬了名。如何烹饪如何好吃哪要我饶舌。
陆游说的“脯脩”都是干肉。《周礼》云,脩,脯也。唐贾公彦疏:“谓加姜桂锻治者谓之脩,不加姜桂以盐干之者谓之脯。”也有说脯是初作成的干肉,脩是做成时间比较长的干肉。我国制作脯的历史悠久。《礼记》有“牛脩鹿脯”,《论语》有“沽酒市脯不食”。什么五味肉脯、白脯法在南北朝时已多有提及,唐代“赤明香脯”,元明之际的“千里脯”,皆脯之有名者。我国古代还有“束脩”之说,十条干肉为“束脩”,是学生向老师送的礼物,也指酬金,学费。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一所乡间学校教书。学校没有食堂,客籍老师就我一人。学校采用的便是“代饭制”,就是到学生家轮流吃饭,吃百家饭。早年家贫,村民们会把珍藏的干肉留着给老师吃。“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尝无诲焉。”这让我心生感动,我自然无怨无悔。《论语》有言,虽为自愿,只是你孔子一定要收了人家的十条肉么。试想,如若没有十条肉,或者家长是不自行不自愿呢,是不是你教他了呢。我稍加妄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若非,孔子是个大美食家,他有私心,喜脯,他是为干肉所惑的呀。
现在我们说的脯多脂胸脯中的肉,比如粤菜的干煎鸡脯就很有名。人们腌渍干肉、腊肉也多喜欢胸脯中的肋条肉为最佳。
脯,“肉食者谋之”,作为美食平民的果脯也一样叫得响。我国用蜂蜜腌制水果早在春秋时就有文字记载。果脯是新鲜水果经过去皮、取核、糖水煮制、烘干和整理包装等主要工序制成的食品。果脯种类繁多,苹果脯、杏脯、梨脯、桃脯多的是,老北京的“北京果脯”就很有名,据说,其独特的其制作技艺正在申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说来,脯,这一荤一素的“两块肉”,都一样讨喜。
韭
“吃早韭,不松口”。别说话,不张嘴,细啖轻品,满口香。
“三月韭芽芽,羡杀佛爷爷”,又有民谚为证。这么好吃,难怪叫沾不得荤的出家人也齿颊生津了呢。早韭晚菘,说的是时令菜蔬的好。《南史》“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颙是素食主义者,他如此推崇早韭,出家人却把韭当作荤菜,这么好的蔬菜不上口,可惜了。汪曾祺说写作行文亦当如 “早韭晚菘”,想想也是。
雪化,阳光渐暖。茄苗才育,豆还没点呢,从菜畦里最先拱出地面的就是韭了。纤细柔弱,含露负霜,在最严肃的日子里蕴积向往,在最踏实的依托中寻找归宿,你得佩服韭的勇气。早韭并不全是绿,是一茎茎的红,有点血的颜色,是生命红。
有风,雨总是这么没缘由地下着。韭呢,依着风,依着雨,依着地,撒娇样的,站也站不稳,纷披而下;总有两茎立着,细细端详这个“韭”字你就知道了。《说文》说“韭”字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中国字就是这么有味道。
不只有风,不只有雨,在叶上沾着的,还有是一串晶莹的露点点,难怪韭会撒娇,作醉态。
其实,“韭”“久”谐音,《尔雅》说“一种久而生者,故谓之韭,韭者懒人菜”。在乡下没有人说“懒人菜”,说韭是“当家菜”。菜地总有一墒韭。去年我家房屋拆迁,新建的房子在一块坡地上,屋后有一片空地。妈妈见了,无比的喜,她买来韭菜籽,种了一墒韭。庄户人知道,有了韭,日子便踏实了许多。
韭“春食则香”,知百草的李时珍当然晓得。扬州八怪们还会在早韭上市时相邀开“party”。他们一边吟诗,一边饮酒,一边食早韭,何等惬意。郑板桥说“春韭满园随时剪”,韭已“满园”了还不剪呀。妈妈是等不及了。韭长三叶,不出五叶,妈妈便去割“头刀韭”了。“头刀韭”便是早韭。
坐门前,妈妈掐去韭叶上的黄尖死叶。她如此小心,我猜是不愿多掐一丝粘在韭叶上的绿茎。燕在低飞,竹篱上的霉干菜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开犁了,一年中柔美的时光仿佛都罩在了妈妈纤巧的指间了。
早韭包饺子当然好。费时费事的,春已至,忙着呢,没那闲功夫。村民们只是将早韭炒着吃,放些千张也行,放些鸡蛋也行,放些肉丝一块炒更好。更多的时候只是单炒韭菜。只是这一盘早菜,一家人围着。记得父亲从不动一筷韭,他只是端盘子向碗里泡点韭菜汁。起先我也相信“韭汁味好”。后来知,是父亲舍不得吃。饥春荒年,村民们也会调侃:咱吃了一千零九道菜。其实人人都知道,他家中午只是一道菜:韭菜炒千张。要是家里的人口多,单炒早韭也变得奢侈了,他们只是用韭菜烧汤。韭也真给面子,只是一小把,一锅汤便墨绿的很,且清香无比。
“夜雨剪春韭”,春了,能把菜蔬吃出诗意的,怕只有早韭了。
姜
姜是美女,真的很漂亮。宋代诗人刘子晏《咏姜诗》云“新芽肌理细,映日莹如空;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美吧。苏东坡也说“后春莼茁滑如酥,先社姜芽肥胜肉”,肉美?我猜宋还留有唐的审美遗韵,以肥为美,单是“滑如酥”还不就让你有了些许的联想;秀色可餐,苏东坡讲的倒是实在,姜,毕竟讨的是口饴之福。
选块向阳的坡地,挖窖。窖如井状。井有水,窖不同,它是万万容不得水的。窖在高地。在我的记忆中,窖里一般有两样东西,一是山芋,一是姜。饥岁荒年,山芋是村民的主食,姜呢,哪能当饭吃,调味品而也。江山美人,有时你很难说清孰轻谁重,就像姜有如此礼遇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滋味生活寄托着人们多么美好的期盼,束之高阁,我愿意费时费力养着,怎么了。姜之于生活,不也类爱情之于婚姻。待字闺中,经不得风霜,姜娇气。
天暖,渐热,姜也不是随便就打发下地的。种姜的地年前就深挖冻着,负霜,含露,经风,历雨,土细熟,乖的很。然后踩实,做成埂状,埂间挖沟。每年春上,父亲做姜沟时我便跟着踩埂,细细密密的,一寸寸挪步,如此反复,要四五个来回才能将一墒埂的土踩实。姜沟与埂等距,也如摁下的琴键。
其实,在父亲做姜沟的当儿,熏房里早就忙活开了。熏房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小房子。种姜人把姜装在纸箱里在熏房码好,用毛笔在纸箱上写上各自家人的名字。文火,熏烤,烟雾缭绕。刚出窖的姜似醒非醒,不多日,满腹的心思吐露,是芽,瓷白,嫩红,玉指有甲,啄梦如喙。“四月取母姜种之。”出过芽之后的姜李时珍称它“母姜”。其实这当儿姜依旧挺美。色汁圆润,纤指如玉,十足的美少妇。
窖藏,熏芽,这等繁烦的农事看不出村民们有半句的怨言,种姜能看出村民们的精致和细腻,其实,姜招人烦的事多着呢。单是浇水就让你天天牵挂。沟里的土不能裂一条缝儿,小嘴唇天天湿,滋润,好看。种姜有机肥才好,村民们便把黄豆煮了,做肥。豁出去了。姜叶如竹,“村峦当户茑萝暗,桑柘绕村姜芋肥”,田园美,姜芋熟,盼丰年。春种,夏实,秋收,冬藏,姜历四季,能让村民们如此心仪的,怕只有姜这情种了。
姜辛温,民间称“姜佐百味”,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故谓之姜”,我猜他有点武断。姜还壮阳,中医素有“男子不可百日无姜”之说,苏轼在《东坡杂记》中记述杭州钱塘净慈寺80多岁老和尚,面色童相,“自言服生姜40年,故不老云”。姜为男人生。姜是美女,本来就是嘛。
粉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刘三姐》的歌里“青藤”有股情色的味道。我猜“青藤”便是葛藤。有传说为证。东晋道学家、医学家、养生学家葛洪带弟子云游炼丹。哪知弟子修行不深,毒火攻心。有人向葛洪指点迷津:山上有青藤可医。一试果然。自此,青藤取了葛姓,叫葛藤。
葛藤疯的很。20世纪70年代,葛藤曾占领了美国佐治亚、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等州的万顷土地。肆意忘为,不具节制,狂野不羁,哪知它会如此淫荡。
葛粉取之葛藤的根块,岂不是“一路货色”。
紫花含羞,绿叶青艳。葛根发达,去泥削皮,柔滑细腻,玉脂纤嫩,泡在水里,十足的睡美人。将葛根磨碎,滤去茎渣,白色的葛浆在水里沉淀下来的便是葛粉了。
每年秋后,村民们便会上山采葛挖根做葛粉。匾里晒的是粉,竹笆上晾着的是粉。有的村民将粉从缸里盆里倒出,整个儿将“粉坨”风干撂在家里。粉坨有十多斤甚或几十斤重。有大粉坨撂着,日子也仿佛踏实了许多。
葛粉圆子是徽州一带叫得响的名点。将猪肥膘、白糖等做成圆球状馅心,反复滚上葛粉,然后上笼蒸。蒸至外皮呈黑色发亮并有小泡即成。葛粉圆质地柔韧有劲,味香甜,只是吃多了会腻。
“十碗大菜九碗粉,搛块肥肉捞捞本”。葛粉是席间的主角,村民家的红白喜事都靠它了。葛粉是“大众情人”,跟哪道菜都合得上。葛粉在锅里熬过,切成细碎的块。说是“大菜”,其实村民们知道,这碗底垫的都是葛粉细块。鸡,只是在高汤烩过的粉块上撒点鸡丝。烧三鲜,只是在粉块上撒上金针菜、蘑菇、山药罢了。头道“大菜”当然是肉。肉只是薄薄的几片覆在粉上。厨师好象算好了的,一人一块,可又往往不够数。常是人多肉少。村民顾不得吃相,还不待端菜的将碗在桌上放稳,有人已伸过筷子来搛肉了。虽说端菜的大声吆喝“油——着——嘞——”,没人买帐。那年听父亲说他去邻庄喝喜酒,肉刚端上桌灯叫风吹灭。主家急找蜡烛点上。一分钟的功夫,再一看那碗上的肉一片也没有了,只剩下细碎的粉块。好些人懊悔自己没有“先下手”。饥岁荒年,毕竟是出了礼舍了份子的,“捞捞本”也没错。
野葛藤渐少,葛粉现在没人舍得这等海吃了。烧菜作勾芡,平日多作饮品。杯盏冲饮佐以白糖、蜂蜜或酸奶什么的。盏中把玩,怜惜有加,啜饮在口,回味不尽,却也增添了不少情趣,不改情色本质。
据说泰国有“红葛根”和“白葛根”。“红葛根”用于女性丰胸,“白葛根”用于男性壮阳。这等“色”全“色”美,是因为葛根里含有异黄酮诱导素成分,有人称它为植物性激素。葛粉解酒那是真的,《医林纂要》说它“除烦、解热、醒酒”,有人称葛粉汤“千杯不醉”。
酒后归来,递过一杯冲好的葛粉,色汁清纯,绵糯可口,知寒知暖,红袖添香,举案齐眉,酒醉人酣,这等情境让葛粉调剂的恰到好处。色食性也。本来就是。
酱
发酵酿制的东西味浓,酒是,醋是,老酱也是。
家乡人将做酱叫“下酱”。下酱的主要原料是豆,黄豆居多,也有用豌豆的。将豆煮烂摊放在匾里发酵,焐。匾入厢房,关好窗,放下门帘,妈妈小心看守,防猫,也不许我们走近。近乎神秘。后来我明白了,豆发酵怕脏。不多日,匾出,一层霉衣,豆也成黄褐色饼状。“铜绿”厚是好色相,妈妈喜,这豆饼下到缸腿的盐水里定能成好酱。
缸是重要的家什。“缸腿”是小缸。缸盛水的多,小缸见大缸,差不多在水缸的腿部,村上人叫便叫小缸“缸腿”。缸腿下酱的多,有人也将缸腿叫酱缸。
晒酱是要些时日的。夏天日头好,晒一天,原本有水气洇润的酱面,便起了层红褐色的硬壳。妈妈早起,用搁在缸里的筷子将壳搅了,酱香已出。要是将这一缸乳黄色的酱都晒成红褐色,差不多要一个夏天。这时,这缸酱也便能称之为“老酱”了。
酱香难敌,瓜妞好时,我会偷摘几条塞酱缸里。隔数日,瓜妞色黄,软,捞出埋在碗里便能吃了。瓜妞是嫩黄瓜,或是嫩菜瓜。端碗离桌,鬼鬼祟祟,逃不过妈妈的眼,她举筷便打。妈妈是怕有不洁的东西坏了酱。她哪里打得着。事也败露,索性将碗里的酱瓜用筷搛起,有时故意将酱瓜在家人面有个亮相,送入口中,将酱瓜夸张地吃出声响来。酱瓜脆,满口香。
我还在酱缸里酱过豆角,茄子,辣椒。
酱生吃的不多。妈妈会把新摘的豆角茄子等切碎放碗里,再放上葱、椒、姜等佐料,放一两勺酱,煮饭时把碗放锅里蒸。饭菜一锅出,不费事。出锅时要是在酱上撒层蒜花,或是芫荽,浇上麻油,一搅更香。酱单蒸的也有,放上佐料,放虾米当然好。一样好吃。
家家门前一缸酱,大户人家一年要下两缸或是三缸酱的。夜露,或是雨日,只消将缸旁的荷叶盖在酱缸上,将叶周边用细麻绳扎好便行。为防冻裂,这酱缸到了冬天上冻的时候才收回。把吃了一夏一秋的酱舀出,包在荷叶里。这老酱要吃一个冬天。这之后用不了多少时日,翻过年,春种不久,妈妈便又会下新酱了。
家家有了这一缸酱,日子像踏实了许多。
“老酱还有幺”。妈妈常打电话要我回家拿酱。妈妈每年还想着下一缸酱的。
饭局多了,却是酱香难忘。周日的时候,我常会想着熬老酱。熬老酱的配料要多,毛豆米,干子,小米虾,豆角也行,茄丝也行,老酱兼容性极好,好像没有不能容纳的菜蔬。葱、椒、姜要猛放。所有的菜蔬炒过之后加水加酱,文火,熬。一边不停地用锅铲搅动,一边闻着那缕缕的酱香,你便会觉得,这滋味生活,哪里离得开老酱。
蒜
佛言,人有三生。蒜也是。
想想蒜叶蒜茎是蒜的今生才是。着如许清水,放碟里或是碗里,有芽无根,有根无土,天渐冷,水蒜已出落的亭亭玉立。灶台边,也有放阳台上的,洁白的触须水中如玉。水蒜你是不指望它会长出苔来,长出瓣来。你在意的是叶,以叶当花,是蒜花。各式菜肴出锅,切好细碎的叶撒在上面,青艳好看,扑鼻香。蒜花是点晴之笔,一如画师书家最后的那枚红印。蒜在地里的多,虽说离灶远点,但无论是做菜还是炒饭,人们是不会忘了掐几根蒜叶做蒜花的了。从中秋始,蒜要待在地里至端午前。
如果说叶只能当佐料切蒜花那你便“小看”它了。叶炒千张一清二白的,素净,好看,炒肉丝炒青椒当然更好,叶稍老时烧豆腐、烧肉更是讨食客们的青睐。蒜如韭,割了的茎用不了多少日子便又会长出来的。因蒜叶青香味美,好些人专打叶的主意,不分季节,在大棚里培育蒜叶,做起了蒜黄的营生。
叶似乎揣摩透了食客喜好的心理,赖在地上似乎是让人们尽情享用似的。这一待,就是二百多天。想想,还没有一样菜蔬有如此衷情的呢。天渐热,小南风一吹,不多天的功夫,蒜便脱胎换骨似的变了样儿了。用不了几天,蒜苔便抽出来了。蒜苔才不会那么低调,趾高气扬的样子。这时候,无论如何你得高看它一眼的了。
蒜苔是蒜的来生幺。
白嫩,浅绿,墨绿,干净,高雅,质感丰富,蒜苔不矫情很有征服感。端午前后,餐桌上是要有蒜苔的了。蒜苔炒菜、烧菜都好。只是“来生”无常,能享用蒜苔的时日太短。小城人聪明,家家腌蒜苔。腌过的蒜苔鲜嫩微黄,清脆可口,滴上麻油,是佐餐极好的小菜。那天我去一文友家串门,看见他家柜子上的饰物很另类,是一排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文友看我疑惑,笑:哪里,这些瓶是留着日后腌蒜苔的。我们家好这口。
嘿嘿。都好。都好。
蒜花如花,那果呢。蒜头如果算果,那得隆重推出才是。这是蒜的第三条命。
椒辣嘴,蒜辣心。生吃蒜瓣生猛且夸张了点,吃相不好,有胡吃海塞的感觉,更主要的是辣的你受不了。三瓣下肚,不吃出心绞痛才怪。要是做成蒜泥,再调些许味精、麻油那味就文多了。不过,蒜瓣狡猾的很,它很难就范,对付它得有一套家什才是。自小我看父亲捣蒜用的是擀面杖。将剥去蒜皮的蒜瓣放碗里,左手覆上且拇指和食指处留出空隙放杖,右手持杖将蒜捣碎。妈妈喜欢在蒜泥里放上煮过捣碎的鸡蛋,蒜泥拌在手擀面上吃,那味,啧啧,啧啧!现在好了,木质的蒜臼好些超市里都有卖的,样式也好看,只是还有谁会自己持杖擀一桌手擀面呢。
来生有土。蒜恋土。也就两三个月的功夫,你无论如何是断不了它怀春的念想的。这当儿你再吃蒜,便没有了先前的水分,再一看,芽已渐次长了出来。沾土就出苗,放水里是水蒜,纵是无土,这芽,也是一定要发出来的。
蒜叶,蒜苔,苔尽有瓣,一年之中,一生之中,蒜就没有闲的时候。蒜有三生,之于食客呢,沾着这美味,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绍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失眠的星空》、散文集《悟人子弟》《你是哪棵树》《何处留白能涂鸦》《我的乡村“稻”路》。淮安市文联签约作家,《文苑》《读者》杂志社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 谢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