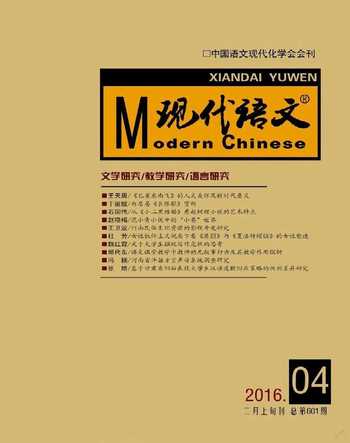命运的轮回
2016-05-30沈鹏
摘 要:叶炜的长篇小说《富矿》以矿区历史兴衰巨变的书写,通过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及影响。其创作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对自然、人性进行了深入反省。论文在分析《富矿》女性形象的基础上,指出了叶炜《富矿》创作的精神指向。
关键词:叶炜 《富矿》 乡村现代化 女性形象 命运书写
引言
长篇小说《富矿》[1]是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开篇之作。这部作品作者首次将目光转向苏北鲁南这片广袤的土地,开始了其乡土小说的创作征程。同时,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全方位地展示了他所熟知的苏北农村风俗人情,塑造了以麻姑、笨妮等为代表的众多人物形象,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及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宏大议题。当然,叶炜书写《富矿》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揭露,更在于引起人们对乡村社会发展模式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
小说《富矿》围绕麻庄矿的发展变迁展开叙述。麻庄位于苏鲁大平原的腹地,是苏北鲁南乡村的缩影,这个原本寂寞的小村庄因发现丰富煤炭资源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也是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麻庄的历史和洋务派、国民党、日本人联系了起来。改革开放后,沉寂一个时期的麻庄又迎来了煤矿开采的春天。麻庄的故事便在新时期社会转型背景下展开的。小说着力刻画了麻姑和笨妮两个人物的命运,麻姑和笨妮都是麻庄普通的农村姑娘,随着麻庄矿的开发,二人先后进入矿区,在见识到矿区表面下的丑恶后,二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麻姑选择了继续留守,而笨妮选择了逃离。麻姑、笨妮只是乡村世界众多女性之一,她们的命运折射出乡村底层女性的命运。叶炜通过乡村女性命运的书写,思考着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经过发展变迁,开采完毕的麻庄矿又恢复到了从前,麻姑嫁给老来,笨妮和六小重归于好,无论大地还是生活其上的人们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
一、命运中的挣扎
《富矿》不仅展现了麻庄矿区的变迁,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煤矿开采对麻庄人心理、生存状况的冲击。麻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小小的麻庄矿所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在整个中国随处可见。文学是人学,人的故事是小说叙述的重点。《富矿》正是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沉浮去表现创作主题的。在《富矿》中,叶炜鲜明地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
一是以麻姑、笨妮为代表的麻庄新女性形象。麻庄矿的重新开发建设打破了麻庄多年的平静,麻庄村民的命运也在轰隆的机器轰鸣声中开始了改变,麻姑正是其中之一。单纯的麻姑本与同村的六小青梅竹马,随着煤矿的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命运的安排下,麻姑嫁给了矿工蒋飞通。可是麻姑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丈夫与医生肖芳有了婚外情,自己与六小旧情未断。当蒋飞通撞破麻姑与六小偷情之后,一切矛盾终于爆发了,可怜的丈夫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丈夫的死让麻姑背上了恶名,她无法选择“回去”,只能在矿区里煎熬地活下去。矿区的生活是属于男性的,这是一个属于男性的世界。就像紫秀所说:“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尤其是失去男人的女人。”[2]一个背负恶名的女人如何在矿区生活?麻姑选择了向现实妥协,依靠一个个男人,从害死丈夫的胡列到矿长陈尔多,麻姑如行尸走肉般出卖着自己的肉体。当所有靠山失去以后,现实逼迫她放弃最后一丝尊严,她彻底沉沦,成了矿区有名的“大洋马”。经历了这些波折之后,命运之神终于眷顾了她,让不起眼的老来进入了麻姑的生活,这个平凡的男人并不计较麻姑的过去,用爱情温暖和感化麻姑,麻姑最终找到了归宿,生活也从此走向安定,一切又回到幸福的原点。
笨妮的命运与麻姑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她是较早进入矿区的乡村女性之一。矿区的生活让生活在农村的她很向往,但是她也因此早早地见识到矿区繁华生活背后的污浊与丑恶,尤其是在遭到胡列的强暴之后,她对矿区生活产生了厌倦,她选择了“离去”。她主动追求六小,甘愿回到麻庄与六小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随着丈夫六小的入狱,笨妮终究不得不走上出賣肉体的道路。在这时期,她发现了强暴她并因此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胡列,她以伤害自我的极端方式阉割了胡列,残酷的报复让笨妮身陷囹圄。然而命运并没有让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女人绝望,最终她和六小重归于好。
麻姑与笨妮都出身农村,她们是麻庄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她们虽然出身农村却向往城市生活,希望融入城市,过上拿工资的日子。煤矿符合她们的期待,也最容易实现她们的这一梦想。她们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矿区,但煤矿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不尽如意的现实,让融入矿区的她们付出种种惨痛的代价。她们的“离去”与“归来”,折射了社会转型期乡村青年女性的命运。
二是以肖芳、阿细为代表的城市女性形象。小说在塑造一批农村女性的同时,还塑造了一批城市女性群体形象。她们或者在麻庄有着正式的工作,如肖芳是卫生室医生;或者有着地位,如矿长陈尔多的老婆阿细。与麻姑、笨妮等农村女性不同,她们衣食无忧,渴望爱情,追求情欲的满足。来自上海的肖芳有着城市女性的知性温柔,一直暗恋着蒋飞通,深藏着自己的爱意。在得知蒋飞通即将与麻姑结婚的消息后,惊慌失措的她主动坦露了心意,却无力改变即将发生的事实。蒋飞通结婚后,肖芳并未放弃蒋飞通,虽然明知无法改变现实,却努力地与他保持情人关系。在蒋飞通不堪受辱自杀以后,肖芳却意外怀孕了,然而孩子并不是情人蒋飞通的,而是风流成性的矿工胡列的。或许是对情人的愧疚,或许无法面对流言蜚语,肖芳最后选择了自杀。肖芳的命运是悲惨的,明明深爱着蒋飞通,却因为害羞错失了机会。在蒋婚后,却又不顾名分地与他保持情人的关系,这种为爱牺牲的精神,在女人如玩物的麻庄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可是麻庄矿这片诅咒之地却没有放过这个勇敢的女性,她也没有逃离被强奸的诅咒。刚烈的她选择了与蒋飞通同样的不归路。
阿细在小说里出场不多,显得有些神秘,而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更是匪夷所思。阿细是矿长陈尔多的老婆,在矿区有着极高的地位。她美丽善良,过着贵妇的生活。可是平静的生活终究因被黑衣人强奸而被打破,她成了矿区里明争暗斗的牺牲品。被强奸的她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情安慰,反而遭到丈夫的抛弃和责骂。经历重重打击的阿细竟与村长喜贵走到了一起。来自大城市的阿细美丽高贵,来自麻庄的喜贵年老貌丑,这两人的结合既有人的情欲也有人性的黑暗。矿里的工人们玩弄了农村的姑娘,而村长喜贵对阿细的占有,不仅因为阿细是女人,更重要的是城里的女人,是矿长的老婆。
肖芳、阿细们来自大城市,在情感上都表现地极为勇敢,一个不顾名分,一个不顾地位,大胆热烈的追求情爱。然而在充满欲望的麻庄矿,即使高贵如矿长夫人也无法摆脱被强奸的厄运。她们的结局也是悲惨的,一个自杀而另一个沦为交易的砝码。作者塑造的这群城市女性形象大胆追求爱情,突破世俗伦常,在黑暗的麻庄世界里显得尤为光彩。
三是以紫秀、花鼓和春天为代表的其他女性形象。小说除了塑造以上两类女性形象外,还有一些女性人物,她们不是主要人物,游离于两大群体之外,却与两者密不可分,她们的存在丰富了小说人物的群体形象。
紫秀来自温州,既不属于矿区家属又不是麻庄村民,在矿区里依靠皮肉生意生活。她们作为特殊的一类群体表现的是矿区女性中自甘堕落的形象。花鼓本是知青,为了能早日回到城里找公社书记理论,不幸被强奸,回城的事却仍没有解决,花鼓大受刺激变得疯疯癫癫。文革以后,又遭受种种折磨最后彻底疯了。在花鼓去世之后,善良的麻庄村民接受了她,将她埋在麻庄,她成为第一个埋在麻庄的异乡人。花鼓是麻庄年老女性的代表,她的回城与麻姑的进矿遥相呼应,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麻庄最早的融入城市的尝试,然而结果却是失败的。春天是六小捡来的小姑娘,聪明可爱,也不幸被矿工诱奸。麻庄似乎是片诅咒之地,所有的女性都逃不出被强奸的厄运。她是麻庄小一辈的代表,她的经历表明,在这片诅咒之地上似乎所有女性都逃不出这样的厄运,即使还是年幼的姑娘。年轻一代的女性正重复着上一辈的厄运,黑暗的现实已经在侵蚀麻庄的年幼一代。
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从年幼的春天到年长的花鼓,从麻庄的笨妮到上海的阿细,都遭到同样的厄运——强奸。她们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其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性格原因。小说的背景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正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先后经历了农村土地改革,城市企业改革,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目標提出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发展。在如此背景下,全国各地都在经历着企业股份制改革,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为潮流。小小的麻庄也在经历着这一变革,传统封闭的麻庄随着煤矿的到来开始了城镇化进程。矿区的扩大给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矿工的娱乐需要推动了麻庄第三产业的发展,麻庄的一切就像中国大地上各处发生的一样经历着冲突与融合。麻庄是封闭保守的传统乡村文明,矿区是先进的工业文明,二者相遇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与交融。麻庄要发展必须吸收工业文明的成果,矿区要扩大也必须依赖麻庄。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与冲击,传统的乡村文明面临着严峻挑战。在乡村文明中成长的麻庄村民们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考验。工业文明在麻庄村民眼里意味着财富,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人们往往把持不住心中的道德,向现实屈从。麻姑和笨妮先后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正是屈从现实的压迫。
性格决定命运,现实的逼迫是催化剂,而性格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麻姑的性格是懦弱犹豫的,与六小青梅竹马却不能坚持到底,嫁给蒋飞通后又不能断绝关系,在得知丈夫婚外情后隐忍不发,最终造成丈夫自杀的悲剧,这都是性格的懦弱犹豫造成的。肖芳的性格则刚烈勇敢,不顾名分与蒋飞通保持情人关系。情人死后,她却遭到强奸而怀孕,羞愧难当,选择了自杀。这样的命运抉择也是与她性格刚强有关的。小说中没有完美的人物形象,她们或多或少都有着性格的缺陷,这也是最真实的状态,她们的命运也因为性格悄然改变。
小说中麻姑与笨妮都爱着六小,可是青梅竹马的麻姑却嫁给了蒋飞通,六小也最终娶了笨妮,乍一看似乎是一个三角恋的爱情故事,其实作者这样的安排是深有寓意的。麻庄新女性群体突破了传统麻庄女性依赖男人的生活的桎梏,她们向往矿区,希望过上拿工资的生活。她们象征着传统的乡村文明被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主动融合的尝试。麻姑笨妮是麻庄新女性的代表,麻姑经历千辛万苦终于融入矿区,她象征着乡村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融合虽然困难重重,却最终成功的尝试。笨妮在见识到矿区光鲜外表下的丑恶后选择了逃离,这意味着乡村文明与工业文明融合中存在着退缩、失败的现象。麻姑和笨妮都爱恋着六小,她们三人都出身在麻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都相同,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这表明虽然在工业文明的吸引下,传统的乡村文明依然眷恋着它的过去,传统的力量很难改变,在融合的过程遭到挫折后,部分人往往选择回归。肖芳阿细代表的城市群体女性,她们有着光鲜的外表,体面的身份,她们不用为生活打拼。小说里着重刻画她们的精神追求,她们的存在表明工业文明下的人们物质上虽然充裕,精神上却存在着道德缺失、情欲放纵的现象。
二、命运轮回的精神指向
轮回是佛教用语,是流转之意。轮回,有循环、如轮转动、周而复始、无有穷尽之意。《富矿》总共有71章节,然而在目录上,它的标明章节是0,1,2,,,,69,0.第一章跟最后一章都是“0”。如此极为独特的安排,显然是作者故意设置。“0”是一个圆,从0上任意一点转动最终都回到原点。小说在经历了69个章节的发展之后,一切又回到原点。而最后一章却鲜明地以“轮回”为题,而“0”正是寓意着“轮回”。原始佛教采用业感缘起的学说解释轮回之道,认为众生今世不同的业力在来世可以获得不同的果报,贪嗔痴等烦恼可造成恶业,由恶业招感苦报。苦报之果,果上又起惑造新业,再感未来果报,往复流转,轮回不止[3]。作者以“轮回”为题,并不是宣扬佛家的因果循环的报应,而是着力宣扬命运轮回的主题。小说的“轮回”不仅指向大地,也指向生活其上的人。麻庄的煤矿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这个轮回暗示着八九十年代社会的转型。麻姑嫁给老来,六小、笨妮出狱重归于好,她们由迷失沉沦到灵魂的净化实现了命运的轮回,这个轮回喻意着人的命运轮回。
煤矿的发展变迁既展现了大地的轮回,同时也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线索。麻庄矿古已有之,历史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起到巨大作用。改革开放后,麻庄矿面临新的生机。麻庄矿的新建需要从麻庄招工,这次招工笨妮、福妮等进入矿区,成为矿上工作人员,而麻姑在这次招工中落选。随着麻庄矿的扩大,矿工的增多,解决矿工婚姻问题成为留住矿工的关键。在这一前提下,麻姑以家属的身份进入矿区。为了满足矿工的各项需求,麻庄矿相继新建了发廊,菜市场,影院等等,麻庄的城镇化道路自此开启,封闭的乡村文明开始了它的转变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提出后,麻庄矿成为自负盈亏的试点,必须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福妮、宝妮等人相继下岗,麻姑在这样的背景下,走投无路只能走上出卖肉体的道路。麻庄出现大规模的坍塌之后,国家缩小麻庄矿的规模,并对坍塌区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把麻庄矿塌陷地改造成鱼塘和风景区。麻庄矿的规模又缩小到从前。麻庄矿的兴衰既是我国煤矿行业的缩影,也是国家曲折的发展道路的例证。改革开放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煤矿行业不断扩大规模,一味地追求效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生态坏境严重破坏的恶果。市场经济目标提出后,国企相继改革,精简人员提高效率,改变吃大锅饭的局面在麻庄矿中也有所体现。随着发展认识的深化,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要求体现在麻庄矿就是对坍塌区进行农业开发。小小的麻庄矿正是时代的缩影。 麻庄矿由小到大再有大到小,这样一个轮回象征的正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展的曲折道路。
女性的回归,既显示了人的命运轮回,也成为推动小说的发展的另一条线索。麻姑笨妮是不幸的,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下,她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融入矿区的过程中,二人都经历了重重挫折,所不同的是麻姑选择了坚守,笨妮选择了逃离。坚守的代价是惨痛的,失去丈夫后的麻姑只能出卖身体,依靠一个个男人生存,在失去所有靠山后,不可避免地沦为“大洋马”。或许之前的麻姑还能让人原谅,毕竟一个没有工作的农村妇女在矿区生活很艰难,在沦为“大洋马”之后,麻姑彻底放弃了最后一丝尊严。此时麻姑的灵魂是堕落的、沉沦的。然而幸运的是老来不计较她的过去,真诚地接纳使麻姑走出厄运的泥淖,过上了平静的生活。逃离的笨妮并不幸福,婚后的生活充斥着背叛与不幸,随着丈夫的入狱,走投无路的她开始了“回归”矿区,这种“回归”却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实现的。在经历了报复与入狱之后,笨妮的灵魂也随着丈夫迟来的“专一”而净化。麻姑嫁给老来,六小、笨妮出狱后重归于好,她们由迷失沉沦到灵魂的净化实现了命运的轮回。这个轮回象征的是人们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下,往往沉沦于物欲的泥淖中,只有实现灵魂的净化才能回归人性。
三、命运轮回的艺术表达
叶炜的《富矿》展现矿区生活形态和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给了人们很大的反思,这种反思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下,人们如何坚守道德准则。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是人类肩负着的重大使命与职责。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相互促进发展、相互扶持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4]。不顾一切的追求效益,导致麻庄矿发生矿难,麻庄大规模的坍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终于迎来了恶果——自然的报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往往导致人们沉沦于物欲的追求,忽视道德的坚守。麻姑和笨妮不是特殊的存在,她们是底层劳动人民的代表。她们的经历展现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她们的沉沦堕落展现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展现的既是一部矿山的兴衰史,更是底层劳动者命运的沉浮史。
《富矿》是一部极富地方特色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叶炜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他所熟知的乡土世界。他在吸收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造了文学史上新的“地标”——位于苏北鲁南的麻庄。新“地标”的建立奠定了叶炜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寄托了其艺术追求。他的追求在于利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乡土情怀。
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改革的时代,二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农村在变革,城市在变革,土地在变革,企业在变革,人心在变革,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狭隘的发展理念给我们社会带来种种苦果。国家开始修正发展观念,提出注重让群众有尊严的生活。这段歷史也体现在《富矿》这部小说里,叶炜用一个充满佛家智慧的词——轮回,来归结这段历史。命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小说里既指大地的命运,也指生活其上的人的命运。叶炜尤其注重人的命运,表现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运用了独特的艺术手法,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命运轮回这一深刻主题。
叶炜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运用到魔幻现实的手法。一般来说,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容易就把人物和故事写实了。当然写得太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能把农村和农民的基本现状和精神面貌艺术性地表现出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往往还不够有味,不够过瘾,不够灵动,不够飘逸。[5]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炜巧妙地运用魔幻现实的手法,赋予了小说“神性特征”,使得小说在精神层次上兼具魔幻和现实的双重性。小说最大特色就在于魔幻现实手法的运用。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现实的政治社会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从而创造出一种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魔幻”而不失其真实的独特风格。这种手法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6]小说里对魔幻现实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尤其是主人公之一的麻姑。麻姑身上既具有“魔幻性”——神性的特征,又具有“现实性”——人性的特征。
麻姑的神性体现在她的出生和使命。魔幻性常常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小说里的本土色彩即是指盛行于苏北鲁南农村中的巫神信仰、土地信仰。巫神信仰几千年来一直盛行于民间,尤其是封闭落后的农村仍然保留着这一习俗。在过去的农村,巫婆神汉往往被视为神灵的使者,在农村有着极高的地位。小说里对麻姑的身份也有这样的设定。麻姑并不是常人,小说的开篇讲述了一个有关黑雪的传说,传说的主人公官婆即麻姑的前世,作为庇佑麻庄的大仙,她在一场祈求降雪中牺牲了自己。几十年之后,作为官婆的转世,麻姑被当做再次拯救麻庄的“救世主”。
前世的官婆为救麻庄而死,今生的麻姑仍然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她的使命在于为新时期麻庄村民的生存探索出路。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麻庄的生存已经不止是一场降雪那么简单,麻庄要生存必须吸收工业文明的成果——依靠麻庄矿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一要求下,麻姑进入矿区,作为第一批进入矿区的女性,麻姑承担了为麻庄村民的未来开路的使命。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结局却是幸运的。麻姑被老来的爱情感化,并最终与麻庄矿的新矿长老来结合。麻姑的经历给麻庄村民做了很好的示范,她与老来的结合也预示着麻庄村民未来的命运必将是与矿区紧密相连,麻庄未来的出路也在于与矿区的紧密结合。
麻姑的使命还在于对灾难的预警。小说除了开头的传说还有两处极重要的梦境描写。小说第64章节花大半章节的篇幅写了两个梦。一个是官婆的托梦,一个是二老爷的托梦。托梦的主旨都是讲麻庄即将有灭顶之灾,麻庄村民必须开展自救。可是现实中,麻姑将梦境告诉他人却遭到众人的嘲笑,她也慢慢放弃了这种在别人看来无谓的劝说。[7]最后一章节也写了这样一场梦,梦中的场面是海水吞没了整个矿区和麻庄,萨满预言的灾难终于成真。小说最后一章节已经写道国家开始重视保护矿区,麻庄矿已经收缩,塌陷区也进行了农业开发,麻庄沉陷的可能已经不大。麻姑的这场梦预示着灾难本将发生,幸亏国家及时的保护才得以避免发生。两处梦境的描写意在表现过度开发造成的灾难后果,警醒世人注重生态保护。这种生态保护意识,又蕴含了另一层信仰——土地信仰。中国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土地信仰一直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信仰。面对工业文明的诱惑,麻庄村民并没有坚持自己的信仰,土地信仰已被现实的麻庄村民抛弃。这种信仰的缺失给麻庄带来深重的灾难,麻庄的塌陷根源上源于信仰的缺失。梦境的警示也意在重新唤起人们对土地的认识,重塑土地信仰。
麻姑的人性则体现在她的悲惨经历与灵魂的沉沦。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最根本的核心是“真实”二字,所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以此作为基本立足点。[8]小说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因为麻姑“大仙转世”的身份而给予特殊的待遇,在麻庄这个大染坊中,所有的女性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同样的厄运。这种现实性的描写,真实的展现了底层女性在转型大潮中的痛苦地经历与悲惨的命运。
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使得小说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既充满了宿命论中命运轮回的意味,又体现了时代的特征——社会转型时期底层女性的普遍悲惨的命运。同时,叶炜的艺术追求、创作动机也在此体现,他希望自己的家乡也有类似麻姑的“救世主”出现,为自己的家乡探索出路,带领乡亲们走出贫穷的困境。总之,这种亦真亦假,亦实亦虚的手法使得小说既有反映农村真实状态的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色彩。
《富矿》总体给人一种沉重感。掩卷长叹,在这个不算幸福的故事里,两位女主人公都有了相对圆满的结局。因为对土地和人们的关怀,叶炜给了圆满的结局。但刻意追求圆满的结局也会降低小说的深刻内涵,影响对小说主题进一步深化。叶炜眷恋着苏北鲁南这片生养他的土地,这种乡土之爱迫使他为自己的家乡寻找出路。或许他不能改变现实状况,于是他用一支笔尽情的在麻庄的世界里抒写自己的愿望。他希望自己的家乡山清水秀,于是黝黑的煤矿开始了生态保护,他希望乡亲们都生活的好,于是迷途的人们实现了灵魂的升华。我们仿佛看到一双饱含深情的眼睛注视着这片广袤的大地,让我们在反思中重拾淡忘已久的乡情。
注释:
[1]葉炜:《富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初版,青岛出版社,2015年6月再版。
[2]叶炜:《富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3]百度百科词条,更新日期:2013年8月6日。
[4]牛心宇:《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6期。
[6]刘爽:《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书汇网,2013年1月28日。
[7]叶炜:《富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
[8]刘爽:《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书汇网,2013年1月28日。
参考文献:
[1]叶炜.《富矿》和《后土》里的苏北鲁南[N].徐州矿工报,2014-1-17.
[2]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J].扬子江评论,2013,(6).
[3]叶炜.在艰难中寻找尊严[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3-11-13.
[4]朱云霞.被表述的“她”,解读煤矿书写中的女性形象[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3,(2).
[5]刘新生.《后土》:真实的再现与深情的阐述[N].文艺报,2014-5-5.
[6]王丽.道教和佛教关于死后归宿轮的异同,新浪博客,2011-9-1.
[7]王志彬.反思中国乡土文明的《后土》[N].文艺报,2013-11-25.
[8]葛红兵.乡土中国的发现与重构[Z].青年作家叶炜作品上海研讨会,2013-12-4.
[9]涂桂林.叶炜:十年完成精神还乡[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11-5.
[10]郝敬波.乡土中国的形象艺术建构[J].南方文坛,2014,(3).
(沈鹏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