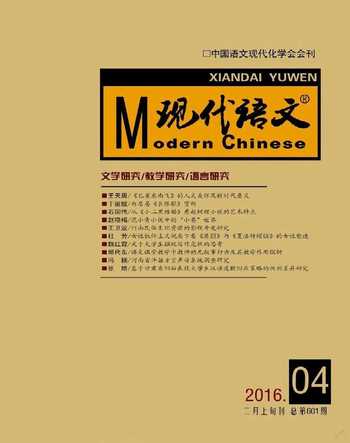意境之我见
2016-05-30李忠
摘 要:王国维的“意境说”作为其文学理论的重要学说,由于词话体的限制,所以对其定义和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阐释空间,而对于意境分类的划分标准也需要从科学意义上进行界说,同时对文学境界和人生境界的复杂关系上则还有进一步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意境 定义 人生
一、意境的定义和缘起
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意境说”作为王氏文学理论的重要学说一直受到推崇,我们需要从词源学角度对其原始定义和后来的演变做一番细致的考察。在作品中,当谈到严羽评价盛唐诗歌时,提出兴趣说,而清初的王渔洋提出神韵说,王评价到“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这里牵扯出文学审美本质的特征或者说要素的研究,从前人的论述中,王感觉到没有道其本,故自己提出意境二字作为文学性审美本质的主要元素和特点,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成为判定作品质量的一个标准。
这里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严沧浪的“兴趣说”,“兴”字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手法本来指《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方式,后来生发出感兴、感发的含义,也就是审美主体在面对外物时内心所引发的情感和想法;由对于外物的感发产生出创作的文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和作者的深层次审美情感产生共鸣。而“趣”则是指诗歌本身的味道,“滋味”“味外之旨”“味外之味”“旨外之旨”,类似于中国画作中的留白艺术,言有尽而意无穷,作品中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独特的审美空间,产生了文字之外的想象和感受,对于作品的意蕴有更加深邃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很明显对于“趣”的具体内容的探讨和“兴”之间的关系还在印象式的平淡和顿悟之中,并没有清楚地阐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具体内容。
而王渔洋的“神韵说”则是在吸收前人关于神韵的学说基础上,把它提升到关乎诗歌创作的根本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上,例如,对于严羽的“以禅入诗”和“兴趣说”有所借鉴,而在现实层面则是对于明代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抄袭之风的纠正,也是对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浅率之风的超越,正是在对于上述两者的发展基础上,提出了“神韵说”,提倡一种空寂超脱的风格,同时具备含蓄蕴藉的诗歌写作手法,则他的诗歌理论倾向日益走向空蹈和虚无,对于广大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反映的不多,对艺术的雕琢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在总结前人的美学思想成果的前提下,对于西方理论包括印度的佛教思想批判性的吸收,使得王国维相比较古人来讲,视野大为开阔,西方现代的分析、归纳、下定义的科学方法的借鉴上提出“意境说”,意境一词本来源自于佛教中的梵文,原意是指六根所能感知的世界范围,这六根也就是六种佛教认为的六种感觉器官,从眼睛、鼻子、耳朵到舌头、身体和心灵,而心灵则构成意根,等同于英文中的“mind”这个概念,由六根产生出六视,也就是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心视,由此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构成六尘,色尘、香尘、触尘、声尘、味尘、法尘,而由上述三者观照的世界就是境界。这里面牵扯出佛教和我们世俗对于世界的看法是大为不同的问题。“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在吾人感受之所在。”[1]
在佛教看来,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六根的意识和感官所投射的世界所达到的范围,与我们通常的唯物主义世界不同。在我们看来,事物客观存在于现象世界,并不因为审美主体的存在与否而发生改变,它是实在地存在着,和主体的主观意识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佛教定义的世界和我们所定义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两者在范围、主客体关系、主体的地位和客体的地位等方面是存在巨大差異的。在佛教的世界本义已经有现实的有为世界、大乘佛教中的绝对世界和无为世界之间的区别,比之我们古代的天下观念大大拓展了生存的空间和时间。除了现世,还有前世和来世;在空间上除了东西南北、上下十方之外还有六道的轮回。换言之,在佛教看来,如果没有主体的情感投射,客观世界的存在性便没有意义,也就不再是世界的本义。而由此构成的境界成为王国维论说境界说的依据和前提。
在现实社会层面,词体作为自从唐代开始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体,一直到王国维的年代地位仍然不及诗文显赫,诗歌和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把它作为治国理政,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重要文学体裁而发展的,对于文以载道有着极为深重的责任感和优越感。相比于诗歌来说,词体只能作为诗余的面目出之,这和词这种文体的社会地位和起源性身份是有关的。词本来起源于歌姬舞女在酒宴之上辅佐官僚大人助兴的工具,并不能和朝堂之上论对的诗文相比,只是闲散的士大夫阶层娱乐、言志的歌曲,甚至有些词人以作词为鄙事,以至于不收入别集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王国维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最后一位巨子”[2],此时提出词有境界,显然有提供词体的审美地位的现实思考有关,换言之饱含着他自己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怀,这也是观堂先生为人为文的一大特点。
二、境界的判定标准和分类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显然牵扯到我们论述的佛家世界和我们的世俗世界的不同,在王国维看来,境界不仅仅是景物所独有,也包括人们的情感,所以境界的判定标准不在于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精神,主观精神也可以成为境界的一部分内容,而关键的因素在于真实性,能用真实的情感和写真实的景物,都可以成为有境界的表现,这里提出了文学作品真实性的问题。
真实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真景物”。景物之真在于“不隔”,这一王氏所特有的概念:不隔,则“语语都在目前”,辞章比较准确地描写和刻画出事物的特点。而“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二者隔的原因在于运用了谢灵运《登池上楼》和江淹《别赋》中的典故,谢江二人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词句,正是准确描摹和观察客观世界,用心加以经营的结果,但是后人继续循规蹈矩,把它作为典故来借用,就渐渐失去了典故的鲜活和感动人的文学力量,成为陈陈相因的堆砌,丧失了审美感染力,同时也是自己描写的景物完全等同于谢江二人的论说,这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违背了王国维的写景真实性原则。虽然运用典故,但是没有写出自己笔下景物的个性,使得读者在面对无限丰富的景物时只有典故所代表的一种审美情感,则更是缺乏审美创作力的表现,自然显得比较隔膜,为王观堂所不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谈到真情感,则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文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审美艺术,当然允许一定程度的夸张和虚构,而且适度的夸张和虚构正是文学作品审美想象力和感染力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虚构必须建立在艺术真实和情感真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文学的真实,但是我们说“海南雪花大如席”则明显不是客观真实存在的。而真实情感的第一要素则为发自内心,把文学作为“个性化了的人类之感情”[3],是真实内心的写照和流露。“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和李贽的“童心”说相得益彰,论述的正是词人为文的真性情。
正是为人和为文两者都是真实的,那么情、辞、景三者达到有机的融合和统一,景物因为描摹得细致真实而富于个性;情感因发自内心,有赤子之心而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情景交融,物我一体,成为有境界的好作品。
至于谈到有我之境界和无我之境界,则和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相联系。在两种不同的境界中,都是有审美主体的主动参与和情感投射的,只不过由于有我之境界,自我在其中比较明显,“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作者把自我的情感投射到客观的物象之上,使得意象饱含作者自身情感的隐喻意义,意象的客观性由于主体的情感而披上一层审美的面纱,显得宏壮。至于无我之境界,以物观物,主体隐匿于物体之后,以隐匿化的情感物再来观照物象,则是物和我融为一体,此时的物和我已经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情况,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恬淡超然之境界,由于以物观物,那么词体的境界必然缥缈含蓄。从王国维举例的诗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论述有我和无我的主客体关系之外,还包含风格学和为文为人的心态史的意义。
“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两者相互配合,成为为人和为文的统一标准。无论是我与世界的关系还是我与物象的关系,主客观作为一种通用标准成为为人和为文的对应。客观诗人需多阅读世界才能有所感发;主观之诗人则需保持赤子之心,才能不为世所羁绊,超脱于世界之上,产生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这种阅世的深浅和情感的主客显然产生了一种对应关系,换言之:客观之诗人由于阅历较深,对事物看法比较中正平和,更加富有俗世的经验,对于世界有一种洞察和穿透力,从而作品中更加优美旷达,切中时弊。而主观之诗人,如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于世界的了解和经验较少,也能够摆脱俗世浅见,产生基于其本心的思考和批判,由于没有俗世的经验,对于社会通常的禁忌和规则缺乏了解,也能打破常规,产生基于本性的终极性思考,对于人类产生异一种直觉式的思维,“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上升到极为高远的人类境界。
三、境界的文艺观和人生观
境界在王国维开篇就从人生角度用三阙词来对意境进行论述,换言之,境界在此处是指向人生的三重境界,在此我们不拟对具体内容展开探讨,而是“然蘧以此意解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里显然有解释学意义上的辞章解释问题。
其实不仅仅有此一处是创作性误读,如说南唐中主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此时他极力提高词体的地位,和《屈原》的离骚中香草美人之词放在同一层面来进行论述,但是在谈到张惠言的“深文罗织”时,又说“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我们不难看到在转折时代,词人本义和读者创造性误读之间两者复杂的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说中有审美的真实情感和对于词体的社会意义承担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协调的悖论关系,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人间词话》中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出现,这并非王国维不能为境界写下应有的定义,而是在易代之际,词话这种文体本身的艺术形式限制了王国维对于西方现代科学和系统意义上的定义的把握和理解,然而又并非仅仅止步于此,在文艺境界和人生境界之间的两个自我形象的徘徊纠结是造成概念含义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第一章对境界二字的借用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境界是一个复杂并且含混的概念,“境界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学的概念范畴或风格、特征,它实际上探讨的是文学本源的问题”[4]。至王国维借用时,西方的分析归纳和中国古代传统的评点式批评在作者这里并用不悖就有效地昭示出这一点,至于说到为什么觉得张惠言“深文罗织”则是兴的情感占了上风,把心中载道的一面压抑下去。
在作品欣赏过程中,创造性误读的出现在现代的解释学视野下不仅仅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作品创作年代和评论年代的时间距离,后人在阅读欣赏中不可避免进行二度甚至无数度自我的创作,把自己对于作品阅读之前的期待视野和自己人生的经验运用到其中,从而产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阅读效果。而在接受美学看来,作者在创作完成作品之后,便和作品脱离关系,文学批评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追寻作者原意“深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而是不断进行阐释的过程,尤其是经典作品就更是如此。
进一步需要追问的创作发生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是,即使作者宣称自己创作某部作品的原意是如何如何,且不说作者和时代以及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单单是如何忠实传达自己的“心中之竹”和“画中之竹”的关系就已经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了。
在《人间词话》中,作者不仅仅谈论文学作品的境界,更是把它拓展延伸至人生的境界,进行创作性误读,产生了关于人生三重境界的经典论述,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一转化的机制如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完成的?笔者认为文学境界和人生境界两者异质同构性是其转化的重要范式。
在王国维的解读中,不仅仅有人生三境界的论说,也有其他如“诗人对宇宙人生,需入乎其內,又须出乎其外”对于创作和人生两个问题的综合论述,类似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人间词话》中还有很多,这与作者极高的文学修养也有很大的关系,能够将两种问题进行通观的能力更是卓异,本来中国古代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知人论事”的传统,再次作者调动自己的理论资源对传统进行归纳总结,关于“淫词”“鄙词”和“游词”之间的区别就尤其见出这一点。作者虽然认为古代艳词“艳鄙之尤”,但是不为“艳词”“鄙词”的原因在于真实。换言之,认为作品内容是关于艳丽的,但是情感是真挚感人的,因此并不会因为它的题材而否定它的客观价值,这也是在通观的基础上对于题材和审美情感二者关系的精妙论述。题材的大小,善恶并不会影响作品的本身水平,“境界有优劣,不以是分优劣”关键是作品中在论述时所流露出来的审美情感态度如何,这才是文学评价中重要的元素之一。
在文学境界和人生境界的论说中,有一个“故知解词之人正不易得”的夫子自道,虽不无得意之色,但是也暗暗说明了解说词体的困难之处,甚至可以说是解说艺术作品的不易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对于自己的“蘧意”有所内省,也有所保留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文学境界和人生境界是两种不同质的事物,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在此我们看到一代大师的自省精神和怀疑精神,也可以想见西方现代科学精神在清末对于王观堂先生的积极影响,使之跳出了中国古代解词学的某些窠臼,而能有所创发。
注释:
[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钱建平:《<人间词话>“境界说”新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01期。
(李忠 河南郑州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