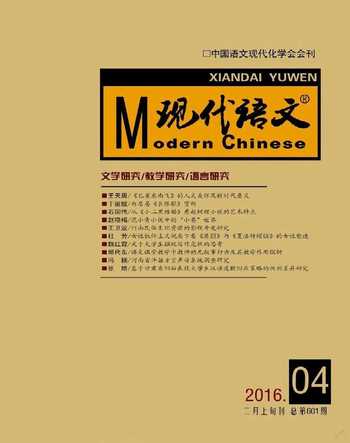浅析萨都剌词的特色
2016-05-30赵静
摘 要:萨都剌是元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词作虽不多,但特色鲜明。文章试图揭示萨词之特色:富于宗教意趣,词风兼容刚健清丽,善于锤词炼句、使事用典。萨都剌以其创作实绩,证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家的贡献,对其词作加以研究,也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添砖加瓦。
关键词:萨都剌 元词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萨都剌(1307?-1359年以后),字天锡,号直斋,族属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是回族人。因祖父以武功镇守西北,萨都剌生于代州(今属山西),即古之雁门,故自称雁门人。《雁门集》为萨的诗集。萨都剌在元代文坛影响很大,被誉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1]现存的萨诗有七百余首,而其存词却不多,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金元词》中,收萨都剌词15首,杨光辉从《诗渊》中辑得萨都剌佚词1首。[2]萨都剌这16首词,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宗教法曲、咏怀、赠答、游历词。萨词放诸总体艺术成就不高的元代词坛,颇具特色。笔者试就萨都剌词的特色略谈一二。
一、词作富于宗教意趣
元代蒙古族统治者采取包容优待的宗教政策,在开化多元的宗教氛围中,仕途不顺的萨都剌南北游宦,结识众多僧侣道士,参悟人生哲理。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萨耳濡目染,其诗作亦融儒、释、道于一炉,颇有玄理与禅趣。
萨都剌《酹江月·游钟山紫微赠谢道士,其地乃文宗驻》记录的乃是文宗图帖睦尔就藩金陵时“驻跸”紫薇观之事,作者云:
金陵王气,绕道人丹室,紫霞红雾。一夜神光雷电转,江左云龙飞去。翠辇金舆,绮窗朱户,总是神游处。至今花草,承恩犹带风雨。落魄野服黄冠,榻前赐号,染蔷薇香露。归卧蒲龛春睡暖,耳畔犹闻天语。万寿无疆,九重闲暇,应忆江东路。遥瞻凤阙,寸心江水东注。
花草“承恩”,道士受赐,皇恩之浩荡,足见道教在元代备受推崇。紫霞升腾,红雾缭绕,电闪雷鸣,气氛神幻,仿佛仙人呼之欲出;翠辇金舆、绮窗朱户,天上人间,已不知身在何处。作者运用的一系列意象,色彩绚烂,如“紫霞”“红雾”“翠辇”“金舆”“朱户”等物象,既光彩照人,亦显耀出逼人的神气。下阕勾勒出一幅佛堂春睡图,卧在暖暖的蒲龛,听着仙人的言语,俨然已入出尘之境。词人游访紫薇观,胸中既不忘儒家的君臣纲常,殷忧朝堂,同时也怀有道家“长生不老”“清静无为”与“返璞归真”等思想。
在《全金元词》所收的萨词15首中,游道观、仙山之作各有一首,《法曲献仙音》二首体现了道家追求的“长生”和“无欲”思想,而萨的其他词也多透着禅趣:如“沉火香消,梨云梦暖”,香火燃尽,好梦入眠,无声无息,安宁而祥和;“淡淡长空孤鸟没,落日招提铃语”,意境空灵幽远,清净淡雅,读罢心神恬淡,似有所悟;又有“几度暮鼓晨钟”“出岫无心,凌江有态,水面鱼吹絮”“荼蘼花落”,等等,其笔下的“云”“江”“鱼”“花”等物象已非简单的客观事物,而是自我心性的写照,“无心”的不是白云,凋落的亦非荼蘼,它们只是作者寓情的托物罢了。萨诗尚“神情寄与物”“万法归于心”,所生之作,极具禅意。
二、词风兼容刚健清丽
署名干文传的《雁门集序》言萨词:“其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门,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女便娟也。”[3]萨都剌将北方文学的雄劲刚健和南方文学的婉约柔媚相结合,而去北方文学之粗率,南方文学之绮靡,兼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评论萨都剌的诗“清而不佻,丽而不褥,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也”。[4]
胡应麟《诗教》认为:“天锡诵法青莲”。萨的词诸多借鉴李诗的意象,同时渗入了李白的俊逸与洒脱。如《登凤凰台怀古》:“天外三山,洲边一鹭”便化自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登金陵凤凰台》)。而李诗经词人丹青妙手,将天外山、洲边鹭的情态勾勒得生动传神。《水龙吟·赠友》中“出门万里,掀髯一笑,青山无数”句则颇有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意味。“万里”与“无数”极言意境之远阔,一“掀”一“笑”又尽显词人洒脱奔放之性情。
萨都剌长于吊古,多感慨苍莽之音,“词不多作,而长调有苏辛遗响”[5]《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是萨都剌以同调同韵效东坡的《赤壁怀古》而作,颇有苏词之豪致。纵观全词,无论是意象还是用典都效仿苏词,而怀古之余的深沉咏叹,亦深得苏轼怀古词的精髓。诗人以“蔽日旌旗,连云樯栌,白骨纷如雪”极现战争之恢宏场面,如天风海雨逼人;“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气象“大”而“远”,诗人登临远望,除见苍天,空无所有。东吴西楚,朝代兴替,置于广阔的天地间,竟只觉微如尘土。此句领起,造境开阔,拓千古之心胸。“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此时“无声胜有声”,胸中的无限滋味皆入无言的明月中了。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萨都剌的题画词则朴素自然,流丽清新,另有一番韵味。其词辞藻优美,清丽隽秀,色彩深浓浅淡各得其益,如画般令人赏心悦目。如《题清溪白云图》中“出岫无心,凌江有态,水面鱼吹絮”句,白云“无心”出洞,江波有其姿态,连鱼儿也吹动着漂浮的柳絮,极其富有生趣;“映水朱楼,踏歌画舫,寂寞知何处”中,又有“清溪”“朱楼”“画舫”等宁静雅致的意象,令人心旷神怡。动与静的结合,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闲适而和谐的图画,给人以平静愉悦的审美享受。
美学大师朱光潜曾说:“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6]萨都剌作为一个画家,以艺术的审美入景,在色彩与线条的设计上匠心独运,其作也就颇具诗情画意。
三、善于锤词炼句、使事用典
萨词好用典故,而无斧凿之缺,措辞造句,亦能别出心裁。如其《满江红·金陵怀古》中“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及“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分别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整首、《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句,“玉树歌残”也引自晚唐诗人许浑《金陵怀古》“玉树歌残王气终”句。但萨效仿前人,毫无生硬之感,反而铸就词风的大气包容:东晋王导、谢灵运二户盛极而衰,南朝陈后主所奏《玉树后庭花》乃奢靡之曲,又何尝不是亡国之音。“胭脂井坏寒螿泣”句亦有典故:隋兵攻打金陵,陈后主与妃子避入胭脂井,终被隋兵所擒。词人的情感在典故中积聚,至末句“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终喷薄而出。六代繁华落尽,如今只有山青水碧依旧,岂不怅惘!此句虽无玉砌雕砖,却能摧枯拉朽,极尽废兴之感,成为咏史之绝唱。词人过淮阴侯庙,以“鸟尽弓藏”这一成语来总结韩信的不幸。韩信呕心沥血辅佐刘邦成就帝业,却被刘邦以谋反之名处决。他临刑前发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而登姑苏台怀古,词人则以伍子胥遭谗与名匠干将被杀的悲剧入词,刻画出昏庸无道的君主形象。这两首词摄入君臣嫌隙的典故,表达对无道君王的痛斥,对蒙冤忠臣的痛惜。联想到自身屡遭贬谪,词人也不禁萌生了“百事不如归好”的遁隐念头。
《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也是萨都剌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诗人回想徐州历史的风云变幻,追忆西楚霸王,虽盖世无双,却难逃四面楚歌,不过江东的命运;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也只留下一片陵阙,而今却又“禾黍满关中”;唐朝关盼盼为夫守节的燕子楼也早已人去楼空……英雄帝王,抑或贞洁烈女,纵使生前轰轰烈烈,最终也只能化为尘土。想到人生漂浮不定、身不由己,词人心生感慨:“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但萨都剌并未在消极中沉沦,而是敞开胸怀,痛饮高歌,表现出豁达豪放的性情,与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元词,向来评价不高,甚至有“词衰于元”之说,而萨都剌以广阔的意境、清峻的風格、不落窠臼的表达方式,力矫元词的委靡之弊,为已显孱弱的元代词坛吹进了刚健清新的气息。萨都剌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家的非凡才华,对于萨词艺术特色的研究,也可以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构添砖加瓦。
拙作蒙刘嘉伟副教授指导,特致谢忱!
注释:
[1]萨都剌:《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页。本文所引词作均据于此,下不一一注明,以避繁冗。
[2]参见杨光辉:《萨都剌佚作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3]萨都剌:《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4]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85页。
[5]吴梅:《词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6]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8页。
(赵静 江苏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