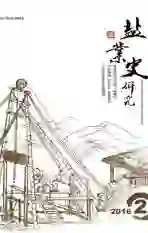清代民国时期川鄂盐运群体及其盐业贸易
2016-05-30杨亭
杨亭



摘 要:川盐运鄂即史称之“川盐济楚”,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川鄂盐运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过去对川鄂盐运的研究偏重于盐运路线的考证、辨析与梳理,以及盐运古道沿线的聚落与建筑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对川鄂盐运中的践行者即背夫,川盐的盐别,甚至盐业贸易等问题缺乏深入探讨,进而使得川鄂盐运的研究滞后于盐业生产与专卖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将上述之命题加以拓展研究。
关键词:川盐外运;川鄂盐道;背夫;盐业贸易;市集结构 中图分类号:K89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6)02—0043—11
一、问题的缘起
对盐运古道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研究的成果来看,明显滞后于私盐、盐商、盐业改革、盐业人物、食盐专卖、盐业生产与盐产地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盐运古道研究可供查阅的文献史料极少,虽有一些地方志的记载,却寥寥几语并且偏重于水路运输路线,故不能为研究者勾勒出陆路盐运所牵动的社会互动与民族关系以及商贸往来等全景图,同时,传统盐运活动作为特定年代的产物,随着时间的远离和空间的阻隔,被尘封于历史的年轮,加之盐运者大多早已作古,因此做口述史研究自然难度加大。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学术界仍然对川盐运销作了积极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川盐销楚的专门性研究上①。学者们分别考察了川盐济楚的历史背景、原因、效果及其影响等,他们认为川盐进入湖南、湖北市场,推动了近代两湖行盐制度的演变。罗益章的论文《川盐济楚运道概略》② 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却疏于对川盐外运路线的考证。除此之外,在盐运古道研究方面,有王肇磊等的《鄂西北私盐运道概略》③,文章认为私盐贩和鄂西北地区的人民共同开拓了庞杂的运盐通道,部分解决了当地人们的吃盐问题。赵逵的《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④ 以川盐古道沿线的聚落、民居及古镇的区域分布入手,探讨文化与地域等相互影响等问题,应该说,此书对理解建筑与城市的本质均有启发意义。
为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取川盐外运的川鄂道作为研究对象,揭示清代至民国时期作为盐运的践行者——背夫,盐运的主要运载物——花盐和巴盐,以及由盐粮交换体系反映的经济活动与商品往来等,成为了本文的研究重心所在。
二、背夫:川鄂盐运的践行者
背夫亦称“背子客”“力脚子”等,作为川鄂盐运的主要运载者,用“背篼、扁背、背夹、双叉夹等工具”①,身背100余斤的盐,蚁行于四川东部(今重庆东北部)至湖北的秭归、巴东、兴山、竹山、竹溪、房县以及恩施等县的崇山峡谷之间的青石板路。背夫一般10余人一队,在或高亢激昂的“哟嘿哟嘿”或舒缓清幽的“哟——嘿”声伴随下,附和着打杵声响彻在盐道上。由于“川省产盐地方,辽阔零星,俱系深山峻岭,即滨江通水道者,不过五六处,其他尽路行背负”②,又“井灶散处山野深谷,僻壤穷乡;运输兼有车装船载,人挑马驮;运道遍及大江小河,山道险路;销区分布内地市镇,边陲村寨”③,于是,在川东地区则出现了背夫这一特定群体。据《四川盐法志》记载:“凡盐行陆地,骡马驮运最便。人力则计岸多担荷,边岸有用背负者,一人率负百斤。而骡多者几与马力相埒。踯躅巉岩绝壁间,数十百步辄一憩息,夏月挥汗成雨,严冬身不挟纩,劳而忘寒,亦天下之至劳苦者也。”④ 由此可见背夫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还有清代的刘源在旅经川东时,亲眼目睹了贫苦百姓肩挑背扛负运盐的情景,于是写了《川东道上口占》三首诗,其中有“贫民生机一肩担,劳碌奔波苦亦堪;共说升平鹾禁免,大家同贩雪花盐”⑤。这些被称为“井盐诗”的诗句,直接反映了清嘉庆年间负运盐的背夫们为生计而忙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兴盛。
那么,背夫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道:“东经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矿、竹箭、木耳、石菌,其所宜包榖(谷)、荞豆、燕麦,而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棲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其种地之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傭(佣)工为生,此皆仰赖。”⑥ 由此可知,背夫有来自于“棚民”,由于生活之地土少石多,为了生计,于是成为“背子客”“力脚子”。除此之外,还有“川省自教匪平定以来,所有遣散回籍之乡勇并贼中自投来归之众,为数甚多,此等人不敢公然为匪,往往亦挑卖数十斤盐,聊为糊口之计。窃以重庆一府计之,商人不过数十户,而赖盐以生者,大约不下十余万人”⑦。又“川盐行楚,井灶捆载增至数万人,重庆肩贩,川河纤夫,又不下数万人”⑧。由此可知,背夫庞大群体的组成不仅有“棚民”,还有遣散回籍之乡勇以及自投之土匪,身份十分复杂,亦即“此辈皆无业游民”①,他们背负盐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活动范围极广。由于背夫生活在社会下层,成为被上层社会区分与排斥的对象,甚至是将其定位为“勤学兵,懒耕田,好吃懒做背锅巴盐”②,属于被社会所遗弃的对象,从而在传统社会难以立足且处于身份游离的境地。正如调查访谈对象所回答的:“有背盐后人大多也不愿意提起自己的祖辈背盐的历史,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背盐是很辛苦的事,没有办法的人才去背盐。”③
对背夫而言,背负沉重的盐翻越一山又一山、一坡又一坡,不仅是自身体力的消耗与透支,还会经常遭遇意想不到的灾难,云阳县档案馆藏的“云阳盐务监运处”之“硐村盐运站关于揹夫谭顺才跌岩失吉损失盐斤的呈文、令”档案④,作为对背夫背盐路途命悬于一线的绝佳明示。见下述列表所示:
附一:谈话录 卅四年四月七日 于本站
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哪里人氏?现住哪里?
答:我叫谭顺才,四十五岁,是云阳人,住卖地坡。
问:你今天揹盐在什么地方出事?其情形怎样?
答:我今天在盐栈揹官盐一包,行至喀蚂石因雨后路滑失足致人盐跌岩,其中我并无情弊,并有当地人亲眼看见。
问:你的话是实在的吗?
答:是实在的。
(问话人:张醴泉 答话人:谭顺才)
附二:揹夫谭顺才切结
具切结人谭顺才于三十四年四月七日在硐村盐栈揹官盐一包在喀蚂石因雨后路滑失足致人盐跌岩,如嗣后发现有盗卖盐斤情形及其他舞弊情事,甘愿受最严重处分中间不虚具切结是实。
具切结人:谭顺才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八日
附三:同行揹夫何光照等切结
具同行切结何光照等四月七日在盐栈揹官盐,有同行揹夫谭顺才揹官盐一包,在喀蚂石因雨后路滑失足致人盐跌岩,倘嗣后发现该夫有盗卖盐斤情形或舞弊情事,夫等甘愿受最严重处分中间不虚具切结是实。
具同行切结人:何光照 钱银州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八日
附四:查勘切结
为具勘结事查左开盐斤于运输途中发生损失,经查各节分陈于左,倘日后发觉勘报不实,或有共同舞弊情事,甘愿听凭依法惩处,特具勘结是实。(此处转述损失表略)
具勘结人、主管员:
硐村运输站主任 张醴泉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八日
不仅如此,背夫还会受到各方势力的侵害,下述之忠县档案馆藏的“忠县盐场公文”中的“忠县涂井场苦力刘开元呈文”① 即为明证。
事由:为认还不还、窦哄欺骗勒搕苦力,叩恳彻查严究由。情民一寒透骨下力课生,于国历十月二十一日与人背盐一百斤到黄金场售卖,其盐系在售盐处所买之官盐,当在中途卖去二十六斤,尚余七十四斤,背至高井地方,突遇盐场公署秘书刘文清验票,与盐斤不符,诬为私盐,以言语百般威胁,估民与伊给洋两億元,乃能将民释放,并退还盐斤,否则将民送法院治罪等语。民在伊势力之下只得向他人兑洋两億元,交刘秘书手,伊当将盐退还三十四斤下有四十斤及税票,刘秘书窦哄民回涂井交还,讵料回 井后,反将盐借词没收,一面乃哄民缓日发还,经催索数次,伊一味支展,一侯再侯,遥遥无期,认还不还,显系居心勒搕欺骗,窃民以一苦力现被伊搕洋两億,复要赔人之盐,情迫算何只得叩恳钧君作主,彻查究办严饬该刘秘书,又清退还搕洋,返还盐斤以恤苦力而塑法纪,则民生当衔环死当结草。谨呈川康盐场管理局局长陈。
忠县 井场苦力 刘开元 指印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虽说如此,背夫却凭其健硕的体魄、刚健的品性,在崇山峡壁间烙下了历史的印记,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内陆的东西部盐粮交换的实际践行者,也是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等民族交往与社会互动的推动者。在此意义上讲,背夫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特殊的群体,或者说是作为依附于盐业生产组建的社会组织,构建了盐业生产地与销售地及其与盐道周边族群的关系,所以说,背夫这一特殊群体不仅使人对盐粮等生活必需品基本需求的实现成为可能,并且满足了族群内部与外部之间通过集市完成经济交换功能的同时,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其他社会功能。
三、花盐和巴盐:川鄂盐运的运载物
盐在自然界主要以固态的岩盐或是液态的卤水形式而存在,因此想要提取食盐需按照开采岩盐和蒸煮卤水的技术处理。川鄂盐道中运输的花、巴盐,则属从卤水中获取,即获取卤水、在水桶中净化与过滤和柴炭煎煮,直至盐结晶,最终形成花、巴盐。熬制花盐既有柴灶又有炭灶两种方式,因之称柴灶煮成的盐为柴花、炭灶煮成的盐为炭花。譬如,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大宁盐场的记载:“由大宁河上沂十里,谭家墩乃盐厂营守备驻劄(扎)处,人烟稠密,山内柴厂自谭家墩至溪口一带,河边柴块层积如山,用以熬盐,又济之以煤,煤亦出附近山内,俱用船装载,由谭家墩越山碥名舌条山,均通水路二十里至两河。”① 由于盐场柴灶所需用的薪木数量巨大,并且随着对周边树木的砍伐殆尽,导致盐场柴薪价贵难得,正如嘉靖《云阳县志》所记载:“国初(明代初年)四山皆茂林,取之易致。……四山濯濯,未免取于数百里之外,用工难而价贵,得薪之难有如此……旧以巨薪煎咸卤,易以成功。近因薪贵附以茅草,脆弱无力,既不足以成烈焰,而卤水日淡又多费,沸之难。此所以尽一旬之力,所得不补所失。”② 而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从外地迁来水市口以卖柴薪为业的薪夫张荣廷,最先在汤溪河边发现煤炭开采后卖给盐场试烧,因火力胜过柴薪而大受欢迎……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逐渐兴盛”③。由此,盐场的燃料由以往的柴薪改为煤炭,盐产量得到了大幅增加,同时也缓解了对山林植被的大肆破坏。
又据《四川盐政史》记载的大宁场花盐盐别的柴花与炭花之比较即可见一斑,“民国前期,大宁场炭花:质细色白带灰,味平,行销引票各岸;柴花:质细匀,色味比炭花稍优,行销票岸。原盐成分:炭花含氯化钾85.43%,水分3.18%,杂物11.39%;柴花含氯化钾48.82%,水分8.7%,杂物42.48%”④。同时,通过大宁盐场制盐成本及场价报告表显示,柴花和炭花在平均月份的制盐成本分别为71873.27元和63528.48元;核定场价分别为90233.33元和76208.33元⑤,可以看出柴盐制作成本明显高于炭盐,随之核定场价也会偏高,所以各盐场逐渐以生产炭花为多,但由于柴花具有的优势是炭花不能及的,于是柴花与炭花一并外销楚岸。
除了上述的盐别之花盐以外,在川鄂盐运中还有一种盐别称之为锅巴盐,在民国时期川盐外运至湖北省属各县的档案中统称为花、巴盐,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绝少论析。据史料记载:“巴盐急火煎之,卤水结晶至底而不捞,经两昼夜而成。巴盐有如煎锅形,径约四尺,重约五百斤。”① 又“徐下子水煮二三日或四五日,视火力之大小,待盐凝如锅范成厚四五寸许,大径四尺,重可五百觔”②。以及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道:“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王隐《晋书·地道记》曰: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③ 很好地说明了在云阳盐场制作的锅巴盐的形状,还有制作锅巴盐的过程,即晋人王隐说的是用石头熬盐,但实际上是用粘土团熬制卤水,以此增加盐的浓度。我们认为,无论花盐还是锅巴盐,其制盐工艺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只是锅数、灶数多寡与过滤与否方面稍有不同,这一点在对盐场的实地调查时从盐工的口述中也得以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称为花盐与锅巴盐,一个重要的区别点在于:花盐是在盐场成批量生产,熬盐时需要加入石灰,亦盛行用淀粉亦或是豆浆等物,被称之为“植物蛋白凝结法”,熬制成盐后即从锅中舀出至过滤桶,待晾干运至盐仓封存包装,其品质“干净、粒细”。比较而言,锅巴盐则相对产量少,大多是在农家作坊中熬制,一般是以家族为单位,以共有的井出的卤水,作为生产条件,卤水在春冬季节因含盐量有浓淡之别,家族根据历算实行轮班制度。譬如在忠县的涂井盐卤之分配,即依历书之干支,以六十甲子分配为家族灶户取卤之日进行熬制。取一次卤水灌满一锅后即可开始熬制,不需要加入石灰等物,待两天两夜成盐后,再从锅中整体取出,像大锅形,不需要过滤,其品质“味重、较多杂质与水分”。
由于“锅巴盐呈块状,硬结而多杂质,但在当时却深受湘黔少数民族喜爱”④。有关锅巴盐的形制、重量等,我们在对背夫后辈的访谈中也得到了类似的回答,“我是从六七岁的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背盐,父亲背的是锅巴盐,大约有150斤,是块状的并且很硬,住老店子(客栈)时把锅巴盐放在火塘的灰里埋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到锅里滚一下,然后再埋回去,东家是不容易发现的”⑤。因此,背夫在盐运路途解决了吃盐问题。同时,锅巴盐深受湘黔少数民族喜爱,“外观俱呈灰色,均向黔滇诸者推销,盐味较重也,平均溴碘之量,均颇丰盛”⑥。不仅如此,根据“锅巴盐及花盐成份对比表”⑦ 的数据显示:锅巴盐的溴化钠量达到1.8的高值,碘化钠量达到0.93的高值,而与花盐相比,花盐的溴化钠量却是微量和部分痕迹,碘化钠量极少。还有锅巴盐的氯化钙达到15.12的最高值,氯化钡达到1.37最高值,而花盐的氯化钙和氯化钡分别是0.23和0.57。通过锅巴盐的特质和便于长途运输,及同花盐成份的比较后,我们找到了锅巴盐受到湘黔民众喜爱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锅巴盐的盐味重,便于长途运输,并且富含较多人体需要的其他化学成份,也符合聚居在丘陵山地民众生产生活的能量需求,故此得以大力推销之。
四、盐业贸易:川鄂盐运贸易体系的形成
川鄂盐运路线属于川盐外运中极为重要的一条陆路盐运大通道,它是连接中西部地区的陆路通道,始自忠县的涂井、 井场,渡长江,在石柱盐运码头西界沱云梯街上岸,由背夫背载锅巴盐翻楠木垭(或刺竹垭)经过青龙场(或鱼池坝),过石家、黄水、万胜(或枫木)、冷水运出川境至湖北塘、利川、咸丰、来凤等地销售①。还有始自巫溪大宁盐场靠人力背夫翻过大观山,到达湖北的房县和竹山所属地带,也由后坪或鸡心岭,通湖北竹山、竹溪,通往房县②。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促成了中西部地区的物资流动与经济交换,也形成了盐运古道沿线集市以及城镇的兴盛。
川鄂盐道的贸易主要以西部的盐和中部的粮食、布匹与农器等为主的物资交易与商业贸易的形式表现,并且是通过受雇于雇主的盐夫以盐交付给中部盐商,而后又从对方盐商处将雇主所需的交换物资背回交予雇主,以此实现物资的流动与商贸的往来。笔者认为,盐粮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平常的生活必需品交易,由于盐和粮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因此在川鄂盐道陆路沿线也就形成了相对密集和持久的贸易网络,甚至形成了盐场民众“饮食便给,不忧冻馁。不织不耕,恃盐以易衣食”③ 的生活景象。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川鄂盐道沿线“层层皆山,一坡方平又上一坡,……沿途山沟两傍(旁),坡下俱辟水田,田随山势之高下,如梯级过水塘坪,则山高地瘠,仅种杂粮”④。因此,盐道沿线的山民自然就会以当地出产的杂粮等物资同外来的大米尤其是盐等物资进行交换,譬如在《大宁县志》中记载道:“竹、房、兴、归,山内重冈叠巘,官盐运行不至,山民之肩挑背负,赴场买盐者,冬春之间,日常数千人。”⑤ 从而促成了农村经济活动的繁荣。据《川盐纪要》记载,忠县的涂井和 井盐场距离运署陆程600里,距离分所陆程1200里;云阳的云安盐场距离运署陆程900里,距离分所陆程1500里;巫溪大宁盐场距离运署陆程1300里,距离分所陆程1900里⑥。而在盐场所处的集镇与街道上,以及在盐运署与盐业分所路途之间自然会形成一些集市,譬如忠县的涂井和 井盐场分别就在旧场镇和金鸡场镇设集市进行贸易,即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社区”;同时,涂井和 井盐场之盐在外销湖北时,就在川鄂古道沿线的起点即石柱县的西沱古镇,中段即湖北的利川、恩施,终点即来凤、咸丰等地形成了集市乃至于有了城镇的兴起,即为施坚雅提出的“中心市场社区”。由此也就形成了从“基层市场社区”的场镇向“中心市场社区”的市镇纵向延伸的贸易网络,随之盐也因此从基层市场向中心市场汇聚,直接造成的是边缘地域场镇的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更高一级的市场进行交易。从物资流动的表层来看,实现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满足了各地民众的生活所需,但从物资流动的深层来看,却是完成了中央王权对边缘地域的经济控制与宏观调控,同时也是通过盐税实现富国强兵所采取的必要的政治与经济策略。另据《石砫厅志》记载:“忠、万交邻之西界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郡邑也。”① 说明了一个市场体系由于“内部道路体系长期不变的传统性而实质上没有现代化”②,但是盐运的陆路交通网络却使得传统的定期市场体系不断兴盛与繁荣。
随着楚岸在清初的肇始,乾隆元年(1736)由四川改隶湖北的建始县额销云阳水引93张,乾隆三年又湖北改土归流的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七州县照建始县例,同食川盐,共销水引34张、陆引1196张,分别由云安、大宁和彭水场配运③。同时,“川盐济楚”还使川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省属各县,具体见下表所示:
据川东区三十二年度食盐配领地点及配销县份每月及全年应配数量表⑤ 显示,云阳场署的盐仓容量为69000.00市担,各配领地点每月应配所辖各县担数是24700.00市担,所辖配销县分别是:恩施,人口数目327254,每月应配平均担数为15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为18000.00;利川,人口数目219608,每月应配平均担数为7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为8400.00;建始,人口数目231046,每月应配平均担数为20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为24000.00;鹤峰,人口数目71340,每月应配平均担数为3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为3600.00等等。大宁场署的盐仓容量为31700.00市担,各配领地点每月应配所辖各县担数是9100.00市担,所辖配销县分别是:竹溪,人口数目180703,每月应配平均担数15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18000.00;竹山,人口数目197012,每月应配平均担数15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18000.00;房县,人口数目222610,每月应配平均担数1800.00,全年共计应配担数21600.00等等。又据川康区食盐整售零售价格月报表(民国三十六年六月)⑥ 显示,大宁场据点销往竹山的柴花和炭花的整售价分别是145000元和120000元,零售价是160000元和140000元,领盐仓价是76520元和61520元,运输方式是肩挑,运道里程为395里。竹溪与竹山情况相同。销往房县的柴花和炭花的整售价分别是180000元和160000元,零售价是190000元和170000元,领盐仓价是76520元和61520元,运输方式是肩挑,运道里程为395里。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测川盐运销至湖北所属各县沿途,必然会刺激并催生集市数的增加与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会形成诸如西界沱之兴盛状态的城镇。
《巫溪县志》记载:“清末民国初,巫溪县仅有宁场、古路有集市贸易,物价偏贵。抗战时期,随着盐业的兴旺,曾出现宁场(盐)、桃园子(药)、猫儿滩(煤)、白鹿溪(土特产)等4个专业性市场,城厢、古路、上磺、凤凰、宁桥等5处综合性市场,城乡贸易相对繁荣。”① 由此可见,清代至民国初期,甚至是到抗战时期,川东的集市数呈明显增加之势,是由于各盐场制盐的兴旺、贸易的频繁、人口的增加以及市场的交易额所决定的。
针对盐场定期市开市的日期,在盐场志和府县志中的记事,几乎完全看不到,其间虽提及集市,但不记开市日期,这并不是说宁场、云安场、涂井和 井场没有定期市,我们只能推测大约是因为定期市都是每日开市的,故一般人都不予以特别注意,从而府县志中便不作明了的记载罢了。在《大宁县志》中云:“黎明时乡人咸集,以盐米桐油及鱼为最多。”② 这里所记的,正是每日开的集市,由此也可以认为,每日开的市,就是定期市最发达的形态。所以,府县志中缺乏定期市的记事,但不能说没有定期市的存在。那么,在这些定期市中买卖交易的货物有哪些呢?地方志上记载的较少,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兹举如下:唐代李贻孙的《夔州都督府记》载云安盐场:“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齐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③ 在《忠州直隶州志》中有金鸡场“市易盐米”等记载④,不仅如此,“鄂盐商来宁场贩盐时,顺路运来大批山货药材和各
种农副产品及土特产”①,通过府县志和盐场志文献可知,盐场集市以交易盐米为主,并且是较多见的,因为外商来大宁场、云安场、涂井和 井场主要是买盐,同时兜售并输入给当地不出产或是出产得很少亦或是缺乏的物品,而当地人则以拥有的地方产物盐,换取必备的生活用品。我们亦可从列举的盐场定期市交易种类表中获知,盐场的居民以盐来换取外来客商或是山民的物资,譬如盐场居民以盐换取外来客商的粮米、棉与布、农具,而同山民则是换取山货或者是药材等,因此在盐场就形成了外来客商和山民同盐场居民之间的商品贸易圈。
同样地,我们从田野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当问及涂井场在民国时期的贸易状况时,杨正瑞老人(91岁)回答道:“那时我还小,记得一般早上都会跟随母亲去涂井场镇赶集,就是拿锅巴盐或是菜同别人换米。”② 在大宁盐场问及胡承铭老人(79岁)时,他也回答道:“当时(民国时)横家街上每天都会有集市,河边塞满了小船,不断地从船上卸下货物又将盐搬上船运走,‘背子客在盐店前聚集。街上本地人做生意的很多,称为‘打雁儿,就是用盐及土特产同来自湖北、湖南等地的商人交换大米、海参与鱼肚等海产品以及铁器。”③ 另据《巫溪县志》记载有“清末县境内粮食遇灾歉需从外地输入”以及“民国31年(1942),单宁场粮食交易量就达到了2570市石”④,说明了粮食贸易在盐场的经济活动中占有较大比重。而盐粮交换的具体价格之比是如何的呢?我们以《云阳县盐业志》中记载的云盐与大米整售价格比较表⑤ 找到一些依据,譬如以1930年(民国十九年)为准,云盐每年的平均价是4.854元,大米的年平均价是5.452元;价格比差云盐与大米是0.598元;价格比差率为12.3%;食物交换量(斤)是一担云盐易米数为89.034斤,也就是说云阳盐场盐与米的交易是为每100斤盐可换取大米89.034斤。
除了以上探讨盐场定期市及盐米交易之外,理应论及山民贸易,但是由于史料记载寥寥几语,要想一探山民贸易之究竟,可谓是困难重重。譬如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就有“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曰荒场,当山货既集,如有嘓匪猝至,则场头恐其劫掠,敛钱相赠,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盗绳也”⑥,以及“再下坡行山沟数里,至龙雾坝为山内场集,自水塘坪至龙雾坝山坡高陡,大石嵯岈”⑦。除此之外,也提及山民的主要食物“山乡日食以包谷、红薯、洋芋为大宗,至荞面麦粉,因时更易”⑧,但是其间对山民集市的集期及其物品交易等只字未提,因此对山民贸易的探究未能如愿。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川鄂盐运的盐运主体和承载物以及由盐米交换形成的市场体系的细致分析,试图弄清楚清代至民国时期川盐外运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川鄂盐运中的盐米贸易及其运行规律,始终是处于国家调控之下的因传统性而生成的市场体系,它因此区别于因现代交通体系而商业化,且是渐入国家化的其他命题。同时,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专章另述川鄂盐运中的盐米贸易为一种文化载体即“小传统”在地方上的表现,也就是说,针对盐米贸易的市场体系的探究,理应将盐粮交换活动促使的各族群之间、外地盐商与当地人之间、山民与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等纳入其间考量之。
(责任编辑:邓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