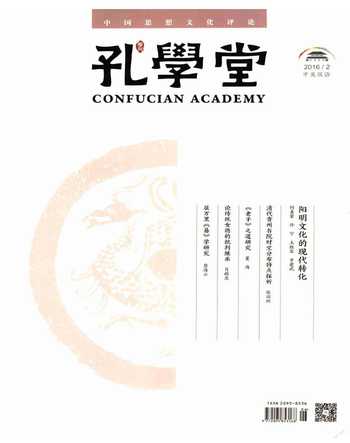从心学到心态学:阳明心学的当代转换
2016-05-30何善蒙李栅栅
何善蒙 李栅栅
摘要:传统的复兴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如何从中国传统中找到应对当下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已成为传统研究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文化复兴的角度来说,阳明学在今天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来说都是如此。本文立足于现代性转换的需要,从现代人的心态角度出发,试图从阳明心学中找到适合当代心态学需求的思想资源。如果可以实现从心学到心态学的有效转换,那么就意味着阳明心学所具有的当下的意义的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阳明心学对于今天,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纠正现实的作用。
关键词:心学 心态学 良知 知行合一 生活世界
作者何善蒙,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栅栅,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浙江 杭州 310028)。
研读经典,学习古圣先贤的为学大义和处世之道,是古今学者一贯秉承的治学宗旨。而为学的最终目的,便是达到儒家的“下学而上达”的境界,学习圣人之道以达天理、天道,用近代新儒家的说法,便是“内圣外王”。无论是“下学上达”还是“内圣外王”,都强调了为学对于处理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从古至今,学习和钻研儒学都与现实生活分不开,例如当代“国学生活化”“儒学复兴论”的提出,都是在强调回归经典,从经典文本中为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法。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国际地位日趋上升,国家经济迅猛增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突出,人民生活压力大,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在增加。这些不断爆发的社会现象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新特征的展开,个体应该如何恰当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尤其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换言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何应对不断发生变化的外界环境,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当今社会,每一个个体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焦躁、抑郁的情绪,抑郁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越来越频繁地被人们提及,由此,我们不得不开始关注心理健康问题。而面对这些心理方面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仍然是回归儒家的经典文本,从中寻找答案。
对于当代人的生活来说,社会心态的问题成为了诸多问题中非常重要且具根本性的。而如何解决它,对于社会来说是非常急切的;对于理论来说,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么,从传统思想出发,我们可以对心态的问题有怎样的思考呢?本文将以阳明心学作为切入,探讨心学对于当代心态学的启发意义。
一、心态学是心学的当代表达 [见英文版第6页,下同]
费孝通先生曾经探讨过类似的心态问题,他认为:
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
基于这样的学术思考,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心态论”,他对心态论的定义是:人的行为背后,决定行为的心理和意识状态,比普通所说的心理学的内容还要扩大一点,包括理性的价值判断和艺术欣赏,也叫人生态度。事实上,心态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概念,是关于人的精神领域的范畴,包括正面的心态和负面的心态,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在个体精神中的反映。将其放置在今天的社会现状中,也恰恰是我们亟需了解和解决的心态学问题。正如上文所举的社会问题和个体心理问题,如果我们从心态学的角度去分析,就是在庞大的关系网中,个体应该如何去恰当地应对和处理不同的关系,并保持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心态。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回归儒家经典,从儒家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去寻找一个契合的答案、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源,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心学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先秦孟子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此后北宋张载提出“大心”之说;南宋陆九渊倡导“简易功夫”,正式提出与朱熹“理学”相对的“心学”,成为宋明心学的开山鼻祖;至明代王阳明确立了“心”的道德本体地位——心即是理,即是良知。简言之,王阳明的心学是承接孟子的思想,沿着北宋五子之一张载的道路,继陆九渊之后,完成了对心学的集大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良知本体人人皆有,人人皆可上达天理,成为圣人。联系当代社会存在的心态学相关问题,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自我与外界以及自我与个体的关系,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个体自我本身,即在应对诸多的关系时,“自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才能保证在变化的世界之中表现得恰当和适宜。当考虑“自我”时,个体必须回归自身,反求诸已,从“自我”身上寻找一个能够处理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关键”,从心学的系统来说,就是“本心”,就是“良知”。
至此,从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心态理论引申而来的心态学,与王阳明的心学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如果在心学系统的理论基础上对心态学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说,心态学是指在个体的行为背后,决定这些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本心,它时刻指导着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要求,又完全内在于个体自身而不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强制和干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与心的关系时,反映着个体的精神状态。这个基于心学之上的心态学不同于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心态理论,在于它的立足点不再是外在于人的文化塑造力,而是内在于人的、完满自足的、人人具有的本心,这个本心就是心学系统的“良知”“本心”。从这个本心出发,或许能够对今天越来越普遍的心理疾病、心态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和思路,而这也正是通过对经典的回归和重新阐释,对当代社会所产生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二、心态学要以良知为基础 [7]
要在心学的基础上讨论当代社会心态问题以及心态学的本质,首先需要了解阳明心学系统是如何阐释的。“致良知”是整个阳明心学思想的根本旨趣,阳明最早提及良知,大概是在龍场悟道后不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阳明对于良知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自觉。在整个阳明心学中真正系统地、自觉地倡导良知,是在1519年左右开始的,那时阳明在江西忙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可能正是此事件,使得阳明对于良知有了直接的、深刻的领会。此后,良知作为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经常出现在阳明的作品中。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在于孟子,阳明对于心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孟子对于本心、四端之心的说法,而良知亦是由孟子最早提出。孟子给良知一个非常简洁的界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作为一种能力,所谓的良能是天生具有的,作为一种认知,良知也是天生所具有的。而阳明就是直接继承孟子的这种心学传统,并将“良知”的概念作为自己学说的根基,这样一来,良知学说就有了孟子学说的支撑,在理论上也取得了其发展的合理性。
在阳明对于良知的界定中,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从道德的本体落实到道德的行为,由此,知的意义可以直接和行为方式相连接,于是,在良知的意义上,知行是必然合一的。这里的知就是良知,就是道德本性,而行就是道德行为,这两者,显然是同一的。于是,在阳明心学中,良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么一个核心概念,阳明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讨论,在阳明的描述中,良知也具有了丰富的内涵特征。首先,就作为一个本体而言,良知是永远存在、普遍适用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其次,良知之所以可以是普遍适用,无间于古今、贤愚,是因为良知是自然会知的,这是从良知作为一种道德判断的意义上来说的,“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第三,因为良知本体是内在于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对于良知是有着非常明显和直接的把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良知是独知的,“所谓‘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第四,作为道德本性的良知,不同于一般经验意义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良知是无知无不知的,“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最后,因为良知作为本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所以,良知在当下亦是具足的、圆满的,无别于贤愚、无别于古今,“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从阳明对良知的内涵的理解,可知良知是人人具足、当下便知的。同时,良知作为一个道德本体,是与道德行为密不可分的,这样的良知对于心态学而言,也就意味着,在人人都具有的良知的指导下,个体的行为具有了判断是非的选择性,在庞杂的关系处理中,只有在良知的规范和指导下,这些行为才是符合“义”的,也就是恰当的、适宜的。并且,在这样的心态下,个体也不会萌生违反道义的、过度的私欲和要求,不会做出伤害他人、伤害自我心性的行为。那么无论是在什么时代,无论其经济多么繁荣,科技多么先进,人们都不会因为私欲得不到满足而痛苦,也不会因为与外界关系处理不当而懊恼,因为良知指导下的个体根本不会有私欲的产生,而处理关系亦总是符合良知本体的要求,符合道义的要求。
然而,良知本体虽然能够保证人们的行为总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但是良知本体本身却容易被遮蔽。虽然人人具足此良知,但有的人能够成为圣人,有的人却只能做一个愚昧的、甚至危害社会的人。因此,在阳明这里,良知本体的存在,虽然提供了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但是,因为没有确立起对于良知的信仰,所以总是为物欲所遮蔽,于是就没有办法在当下就实现这种圣人的可能性。而实现这种圣人可能性,就需要在心上做工夫,需要发明此本心。在阳明心学的系统中,本心即是良知,良知即是本心。所以,只有通过在心上做功夫,保持内心的澄明,才能保证良知不被遮蔽。《传习录》中记载了阳明弟子徐爱的一段话:
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徐爱作为阳明最早的弟子及妹婿,可以代表阳明的观点。阳明本人也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也就是说,要想使良知本体发挥其道德规范的作用,就要时刻保持内心的澄明,只有内心澄明,才能在应对任何事情时都能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心态。
因此,心态学必须以良知为基础,心态学既然是一门关于反映外在事物的内心状态的学问,那么它就是一门关于人本身的学问,其最核心的概念仍然是内在之本心。现代人由于心态问题所产生焦虑、躁狂、抑郁等问题,虽然与外界的环境有关,或者对环境的不适应,或者外在条件的缺乏,但最根本原因的仍是内在的本心。本心萌生过度的不正当的欲望,这种不符合道义的欲望往往很难得到满足,或者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过程中,迫于一些强加的压力和舆论,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种种这些,都会使人产生忧虑的心理。若人人将良知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基本出发点,时时刻刻以良知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就不会产生多余的私欲,也不会做出恶的行为,心态自然而然会平和而宁静。就像孔子评论颜回之乐,“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也就是说颜回找到了比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后来理学的传统中认为就是道,所以颜回的乐基于他对于道的体认和追求,圣人之道成为了颜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不管是富贵也好、贫贱也罢,对于颜回的内心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颜回的内心始终是以道为乐。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成为像颜回那样的亚圣,的确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普通人亦可以学习颜回这种安时处顺的心境。在今天的条件下,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将其作为人生唯一的奋斗目标,即使物质条件匮乏,但是只要调整好内心的状态,做出适当的选择,树立合理的目标,并常怀感恩之心,内心的焦虑和忧虑便会消失,这便是以良知为基础的心态学在今天的社会中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关怀。
三、心态学要以知行合一为基本内涵 [11]
心态学与阳明心学发生契合,并以良知为基础,也就必然要涉及阳明至始至终都在强调的知行合一。这在阳明的心学系统中,曾经许多次被提及,其针对的是当时的知行不合一、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实,而这个事实在阳明看来,明显与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相背离。因此,对于阳明来说,重要的是要救正世道人心。用什么来救正?必须得用儒家的道德教化来改变,重新在社会的意义上树立起对于良知的信仰,由此来拯救世道人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这个病就是将知与行分开、知行不统一。同時,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说,也是对当时朱子学的直接批判。朱熹讲知行,最为概括性、最经典表达就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比喻知行的关系就像眼睛和脚的关系,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地描述出了知行不能分开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割裂知、行的做法非但不应该,而且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在知行这里要区分先后的话,那么知在先,行在后,也就是说必须得有一定得知识累积,然后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去实践,由此也可得知朱子是将知看的比行更重要。然而,在王阳明的时代,朱子系统中以知为重的倾向导致知而不能行,知而不行的状况极其明显,显然朱子的知是知识性的知。本来在朱子的意义上对知行的论述没有问题,然而,在知先行后的意义上,尤其是在现实的意义上,知行必然被隔断。简单地说,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知而不能行,以正人心,息邪说。
那么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的呢?在《传习录》中,有一段弟子徐爱请问知行的记载: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
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非常明确地基于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实出发的,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就知行本体来说,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只是一个,知行本体为一,这是真正的圣人之学所在,是未有任何私欲隔断的知行本来状态。其次,既然知行本体是合一的,为什么古人会把知行分开来说呢?这是因为“补偏救弊”的需要。古人强调知的时候,是针对那种“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的“冥行妄作”,所以,需要用知来规范其行;古人强调行,是针对那种“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的“揣摸影响”,所以必得用行来改变这种空想的方式。最后,阳明对于知行本體的总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是阳明在知行作为两个概念的前提下,对于知行本体做的一种综合性的描述,知就是良知,就是道德观念。人的道德观念是人的行为的指导,人的行为则是其道德观念的实现。由此,道德观念(良知)和道德行为必然是一致的,将两者分开来说,只是为了从分析上来体现各自不同的特点,事实上,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是不可分割的,本来就是合一的,分说只是“补偏救弊”的需要。
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理念可以说是发人深省的,放置于今天的社会,仍是一剂救弊的良药。今天的人们,仿佛已经习惯以多副面孔示人,却唯独不敢做自己,追求的是父母师长希望自己去追求的东西,反而没有勇气去反躬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而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忙忙碌碌却浑浑噩噩,所以总是感觉迷茫没有方向,甚至产生悲观厌世的心理。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迷失了本根。这个本根就是阳明心学所说的“本心”“良知”,此“良知”本是人人具足的,没有圣凡之分,没有智愚之分。这个良知能够提供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并且在知行本体合一的前提下,能够将这个道德规范准则切切实实地生活之落实在洒扫应对进退之中,那么在纷繁的世界里,在复杂的关系,再强大的诱惑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所以知行合一的理念对当代心态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阳明说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原本就不是分开两个过程,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恶念,都已被赋予了道德行为意义上的恶,而行为上的恶举,也能反映到人的良知之上恶的遮蔽。而任何心态问题都只不过是一知一行上的不恰当和不时宜所导致的人心之疾,因此只要个体保持本心的澄明,不生妄念,并将良知扩充到事事物物上去,内心就是坦荡而明净的。其次,阳明说知行合一工夫,主要的侧重点在于说行,而不是说知。所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在阳明看来,如果是真正的知,那么就必须在行当中体现出来,离开了行,根本就谈不上真知,所以行才是最基础又最为重要的。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要有十足的行动力,空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树立一个志向,就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努力的过程也是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只要按照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事情,就不会感觉碌碌无为毫无目标,也不会因为没有努力而懊悔不已,至少努力奋斗的过程会让内心充实。
四、心态学要以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为目标 [13]
今天我们谈论心态学,讨论现代社会的心态问题,并从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传统中去汲取思想资源,就是立足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心学并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历史的纯粹理论,而是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指导人们行为和心灵的活的思想源泉。现实生活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社会关系、诱惑、惊喜、欢笑的场所,在其中,人的行为具有伦理性,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同时,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现实生活的目标是要在每一个阶段达成该阶段的愿望这样做是让个体感觉满意和快乐。总而言之,生活的最终目的是要追寻幸福,即心灵的快乐和满足。所以研究心态学,着眼点是生活世界,而其最终目标,亦是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在生活中所呈现的就是一幅活泼泼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画面。
从心学的角度来谈,阳明要呈现出的是一个活泼泼的、快乐的生活世界,而且要在本体上为其找到根据。在这个层面,阳明非常明确地提出乐是心之本体。由此,乐在本体的意义上得以确立。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世界所实现出来的种种方式,也必须是在乐的本体要求下展开。而关于乐的本体的探讨,最初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孔子,孔子常常谈乐,在《论语》开篇,就有对乐的表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从一个人的经验生活来看,这三层的描述,既有知识学习,又有人际交往,又有自我体认,大体上覆盖到了人的整个生活世界,这就意味着,对于人来说,生活 的本质特征应是快乐。而孔夫子则是用其经历践行了这一点,虽然他一生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发自于内心深处的那种快乐,是从来没有消失的,这其实就构成了孔子形象的最大意义。孔子对于其最为重视的学生颜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予了肯定,“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由此,在孔子和颜回那里,恰恰都是非常准确地传递出了儒家对于生活世界的这种快乐的精神的坚持,这种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家最为重要的传统。所以到了阳明那里,这种快乐的传统仍然在整个心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阳明弟子陆澄曾经与老师讨论孔颜之乐,阳明有一段说明: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也就是说,乐是心之本体,在此意义上乐也就是良知,但此本体与经验世界是分不开的,它虽然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七情之乐,但是,它又必然是存于其中的。
在确定心之本体之乐后,阳明对乐之功夫也作了一番说明,“九川卧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对曰:‘功夫甚难。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在這里,“常快活”最为直接的意思就是要时刻保持一种快活的心态,用它去面对生活经验中的种种,也就是说如果“常快活”是一种功夫的话,它首先也是治心的功夫。治心的功夫的一个重要的方式,用阳明的话来说就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对于君子来说,就应该安于他所处的位置,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应该有非分之想。这是基于对自身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自己的现状出发,而不是不安于现状,常常有外在的、非分的想法。当下的状况,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常快活”的根据,也是决定我们所有行为的出发点,我们所能够作的正确的方式,就是针对这种事实而来。如果我们在贫贱的时候想着是富贵会怎样,在患难的时候想着安逸会怎样,便无法获得一种恰当地应对我们所处之境的方法。由此可以说,阳明的常快活的意思是,个体必当从自我的当下处境出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去埋怨、批评我们的事实处境,在与所处之境达到一种内心契同的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自得于心,才有可能常快活。
因此,心态学从心学的思想资源中找到了可以切切实实落实于现实社会的思想基础,那就是要以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为目标,要以快乐的精神为保证,达到“常快活”的境地。生活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复杂而广大,如果一味的去追求不符合当前实际的愿望,而不去关照自己内心的真正追求,便无法找到人生快乐的真谛。既然乐是心之本体,既是良知,而此心之本体是人人完满自足,那么每一个人不仅能够存养此心之本体,而且有义务将此本体推至生活世界,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要求。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以快乐的心态面对生活,时刻遵循本心,并落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怀,小至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用实际的行动去践行内心真实的追求,做到知行的真正统一,内心一定是澄明自足的。只有内心澄明,才不会生出过度的欲望,也不会产生嫉妒、焦虑、抑郁、躁狂等心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心态学是王阳明的心学之当代转换,对当代人群普遍的心态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