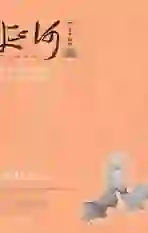龚学敏:所有的写作必然是诗学的实践
2016-05-30王琪
王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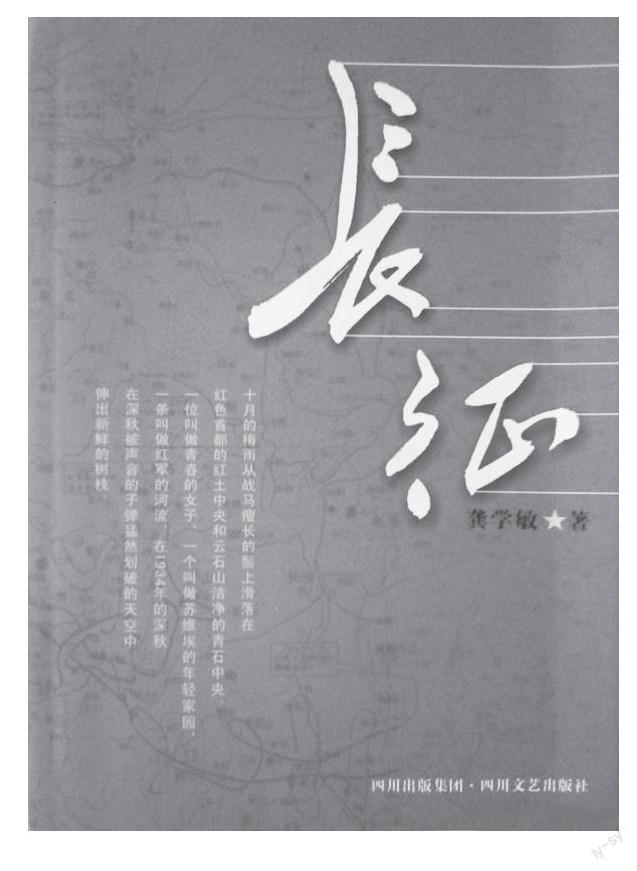


名家档案
龚学敏,1965年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1987年开始发表诗作。已出版诗集《幻影》、《雪山之上的雪》、《长征》、《九寨蓝》、《紫禁城》、《钢的城》。《星星》诗刊主编。
办好中国诗人公认的优秀诗刊
王 琪:龚老师您好!我们算得上是同行了,只不过《星星》诗刊是一本纯诗歌刊物,《延河》是一本综合性文学刊物。而《星星》诗刊诞生于1957年1月1日,绝对是新中国诗歌史上创刊时间最早的诗歌刊物,一直为繁荣和推进中国新诗做着不懈的努力。您是《星星》诗刊的元老级作者和编辑,在《星星》诗刊即将年愈花甲之际,您对这本刊物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龚学敏:您好!《星星》诗刊是中国当代诗坛创刊时间最早的专业诗歌刊物,今年已经创刊整整六十年。创刊以来,《星星》诗刊一直保持前沿、开放的姿态,以推介中国新诗最新成果、展现诗歌文本演变、发现和扶持青年诗人为己任,六十年来,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诗坛的流变和繁荣,特别是几代诗歌新人的崛起。现在,《星星》诗刊从六十年前的月刊已经发展成现在的集《星星·诗歌原创》、《星星·诗歌理论》、《星星·散文诗》、《星星·诗词》于一体的“中国诗坛航空母舰”。有句话说:“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六十年来,每一位《星星》人和每一位《星星》的作者、读者都像珍爱青春和爱情一样,珍爱着《星星》。这既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星星》人的压力。对于现在的《星星》人,我们除了珍爱,又多了一份对《星星》的敬畏。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对诗歌的敬畏,另一个是对《星星》优良传统的敬畏。这种敬畏,让我们倍感责任,不敢有丝毫懈怠。比如昨天,一位优秀的大学生诗人在他们学校的图书馆看到了1957年第一期的《星星》诗刊,欣喜之余,马上用微信拍了照片发给了我。这种传递,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星星》的力量。
王 琪:每个编辑都有衡量作品的一个眼光和“标尺”。面对《星星》诗刊的大量来稿,您心目中的好诗歌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喜欢发哪类稿件?
龚学敏:不错,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对诗歌的判断,都有个人的偏好。但是,如果他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编辑,他衡量作品必定有他自己独特的眼光和内在的标尺,有他对文学和诗歌的敬畏之心,有他对生命的理解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浮躁的世界,他对诗歌的理解必定是基于文学之大道和诗歌创作基本特质和规律的,这是底线,文学的和诗歌的底线。目前,有种说法很流行,即现在的诗歌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是的,诗无达诂。从根本上说,诗歌确实没有恒定的标准与众口一致的正确答案,但,每一个用心写诗的人,对诗歌的理解,诗歌技艺和基本之道的把握,跟用心编诗的人,他的眼光和标准想来是不会有太大的差池的。
《星星》选稿一直坚持三审制,个人的喜好必须服从于《星星》的这一优良传统。当然,《星星》之所以成为中国诗人公认的优秀诗歌刊物,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包容。在诗歌艺术范畴内的包容前提下,我们推出的诗歌作品力求符合与“呼应”《星星》封面上的:当代性,权威性,经典性。
王 琪:有人说,编辑事业充满着风险与考验。我对这句话理解为:编辑工作要敢于审视作者作品,也要乐于接受读者的需求与挑剔,但要架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辑真的好难做。
龚学敏:编辑是一种职业,每一种职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和考验。读者表达他的需求,或者挑剔,这是正常不过的,估计每一位编辑在工作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甚至会受到读者的误解和责备。我觉得,诗人和编者是一种相辅相成和相互成就的关系。能够很好与作者和读者沟通,并且架起畅通、信任之桥的编辑绝对是好编辑。要成为好编辑,不仅要具备娴熟的业务能力,还需具有对诗歌潮流、诗歌发展大势与精微之道的有效把握能力。要一心一意地有为诗人服务、对读者负责的理念和具体行动。需要说明的是,《星星》诗刊的编辑收入都不高,但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这不是标榜,是我们《星星》人对诗歌的虔诚与敬畏。
永远关注诗歌本身、
文学本身
王 琪:的确如此,所以《星星》诗刊编辑的辛苦劳动,值得社会尊重。那么,对于在传统纸媒遭受新媒体强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一本创办多年的文学刊物如何生存,是个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要摆脱困境、寻找出路,是否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和力量才能独辟蹊径?《星星》诗刊在这方面先抵一步,做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龚学敏:面对未来,谁都不敢说自己做好了任何的准备,尤其对于当下众说纷纭的诗坛和诗歌创作,很多时候的预言和判断往往无效甚至成为笑柄。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传统纸媒也好,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也罢,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传播的手段而已。今后,还会有为我们不知的、更新的传播方式出现。而现在,包括《星星》诗刊在内的所有文学刊物,永远关注的应该是诗歌本身、文学本身,只有发现好的作品,扶持好的诗人才是办刊根本。诗歌如此,文学如此,许多比文学、诗歌还要严肃的话题也同样如此,内心的、有效的坚守才是解决这个世上各种疑惑的王道。
王 琪:据统计,中国目前有7亿人在玩微信,这一庞大的群体,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可能是建筑工,也可能是保姆,可能是中学生,也可能是货运司机,等等。请您简单分析一下,期间是否还潜藏着大批的诗歌爱好者?
龚学敏:肯定,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让他去追求诗意。
王 琪:诗歌是为时代发声的。想就关于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请您谈谈,诗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必须与时代同步,甚至要有所超前,对吗?
龚学敏: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诗人、诗评家谈过,我要回答的未必有新意。我个人认为,有一点需要在诗歌创作中引起重视,比如,我们敬仰的伟大诗人屈原,作为个体生命的他,没法脱离他置身的那个时代,但他的人格精神和诗篇是超越时空的。当我们今天读到很多过于世俗化的诗歌作品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思考,这些诗人的境界是不是应该比世俗高一点?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高于生活的,伟大的作品都是要超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
写诗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
王 琪:在我所知道您出版的几部诗集中,比如《幻影》《长征》《九寨蓝》《雪山之上的雪》《紫禁城》《钢的城》等等,有好几部是以长诗结集出版的。其中2015年出版的《钢的城》是以攀枝花市为主题创作的1800行长诗组成,众多诗评家认为,这是您诗歌创作走进生活的一次突破,也是中国大工业诗歌创作的一次嬗变。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会想到要为一座城市歌颂和赞美?
龚学敏:写作有时候就是机缘巧合。2014年初,因工作需要我去攀枝花市,和当地的朋友们一起聊起了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命运是这个时代发展最好的一个例证或者说注脚,它今天所有的美好绝对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实践。我自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正是这座城市的命运打动了我。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钢铁的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挑战,我呢,又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于是,马上决定了给这座共和国唯一一座以花朵命名的城市写一首长诗,而这首长诗又是源于钢铁,与“诗意”相差甚远,但这种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是一首我的创作中用时比较少,写得比较快和顺手的一件作品。对自己的创作是不是有突破,我还不觉得,别人怎么看,也不重要,我认可的一点是,我做到了,把冰冷的钢铁写出了诗意,这个就够了。今年初,我又去了攀枝花,和当地的诗人朋友们自然而然地又聊到了《钢的城》,我说,这首诗在攀枝花这个地方绝对比我的生命存活的时间长,因为,很多年后的攀枝花诗人要对他置身的这座城市写这么长的诗歌时,他很有可能把这首诗找出来翻一翻。我曾经给我许多在小地方生活、工作的朋友聊到,做一名小镇的名流,安心地写一个小地方,这样作品的纵深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内容和惊奇,这样的文人越多,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才会有更好的“渠道”和“目的地”。
王 琪:看得出,您是善于写长诗的实力派诗人,而长诗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创作水平。如之前您写过的长征、紫禁城、九寨沟等,由此可见您表现出很强的长诗创作功底。对吗?
龚学敏: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有他自身的偏好,甚至是怪癖。我写东西,喜欢写别人不愿意写的题材,或者少有涉足的领域。我没有什么写诗的功底,更谈不上长诗创作的功底,我写一个题材时,喜欢长时间地泡在与它有关的氛围中,慢慢琢磨,有时候为一首小诗可能需要调动很多的资源,包括阅读书籍,听有关的音乐,甚至与之有关的绘画、舞蹈等其它艺术门类。
王 琪:您认为自己目前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可否称得上您的代表作呢?
龚学敏:我迄今为止,还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更谈不上最满意。这一点,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我讲的不是实话,但我确实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很多时候都会羡慕那些有代表作的诗人,这既是对自己写作本身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肯定,像我这样没有代表作的诗人,也是一种缺陷。对于过去出版的几本诗集,我是一旦印出来,拿到手上就后悔,最后的结局是羞于示人。去年,我把我自己博客上过去贴出来的很多诗都加密了,我想等有了时间,还要认真修改后再拿出来,有一部分甚至会重新写,因为有些东西我认为值得我重新写。写诗这么多年,一直认为还没有写出自己最满意的诗,有时候会觉得它已经离自己很近了,像是就在前面等着自己一样。写诗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写诗天赋的人。包括现在的写作,我自己认为已经是很慢的了。
诗人要适当保持
一种神秘
王 琪:一个人的诗学观念和艺术追求,和他所生活的场域、个人经历、审美情趣无不有关,请问您的诗学方向是什么?
龚学敏:一个人的诗学观念和艺术追求,肯定和他所生活的场域、个人经历、审美情趣有关。我出生在一个汉藏文化交融的高原小镇上,一直到16岁才第一次出门到300多公里外的师范专科学校读书,三年后又回到我读书的小镇上唯一的中学教书,到《星星》诗刊工作前,我一直在高原上不停地变动着职业。高原上的生活经历肯定会影响我的诗歌,甚至左右我的写作。说到诗学上的方向,我从来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清晰表达的“未知”,就目前对我自己而言,汉语和现代性,这两个关键词是我一直的思考。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探测”,一旦明白无误了,也许写作就失去了意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所有的写作必然是你诗学的实践。
王 琪: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您的诗歌作品代表了您的个人品质与精神价值?
龚学敏:是否代表了我的个人品质这一点不好说,精神价值是肯定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诗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我们现在评论有些诗歌,有些诗人,或者诗歌现象时,如果能够跳出诗歌本身看有些问题就清晰多了,也用不着废那么多的口舌了。
王 琪:记得梁平老师在一篇评述中提到,您是一位被遮蔽的诗人。认同这个观点吗?当今中国诗坛,不为人知的优秀诗人很多,他们不讨好、不媚俗,甚至很少主动向外投稿,却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立场,始终让文本说话,这样的诗人值得敬重。龚老师,请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高见。
龚学敏: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用浮躁可以归纳很多人的时代。作为一个编辑,一个几十年一直对诗歌抱着敬畏之心的写作者,我从内心深处一直向真诚的,向不讨好、不媚俗,坚持和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立场,让文本说话的诗人致敬。
王 琪:读您的诗,我有一个显著的感受,就是在叙写或抒情中特别唯美,印象最深刻的是写“九寨蓝”的那些章节,活灵活现,仿佛让我们置身那方神奇而瑰丽的山水天地间,这种独特的语境,显现出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神性与力量,体现在文本上也显得您非常从容和自信。请问这是您积累多年创作实践的结果,还是有感而发、一蹴而就呢?
龚学敏:一般来讲,每一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多年创作实践积累的结果,对一首诗而言,大多是一蹴而就。你提到的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神性与力量,这是我喜欢的一种表达,真正的诗人应该拥有这种力量,同时,也能够用这种力量来寻求、探索人类那么多的“未知”和“秘境”。什么都知道的人是不适合作诗人的,诗人告诉我们的答案本身,更多的时候,就是要保持一种神秘。
诗歌仍是我最大的兴趣
王 琪:您是怎么处理诗歌和生活的关系?或者说,诗歌是您的最大兴趣吗?您做过教师、警察、工会主席、报社总编等工作,我以为,您最后选择了诗刊的职业编辑,就是的。
龚学敏:现在的这个世界,诱惑、吸引我们的事物真是太多太多了,我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觉得,诗歌应该说是我最大的兴趣了。我开始工作的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最初是长达七年的中学数学教师,那时候的生活似乎还显得很平静和单调,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慢慢喜欢上了诗歌写作,开始尝试着写一些东西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态度”。当时的九寨沟,坐客车到成都要用掉三天的时间,遇上道路塌方,一个月收不到信件也是正常不过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外界离我很远,包括已经成为传说的那个伟大的诗歌时代,那么多优秀诗人在写什么,在说什么,在干什么,与高原上开始写诗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我至今认为,这个没有外界影响的最初写作,是我迄今为止还能对诗歌的神秘持有强烈好奇心的重要原因。之后当警察,去政府部门,甚至于当接待办主任、宣传部长、总工会主席、报社的总编辑等等,有时候,让人感觉到,人生真像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只是拼命地不让自己掉下来而已。可是,箭总归要掉下来的。去年,我回九寨沟参加一个来自北京、上海等四面八方的作家、诗人的文学活动,在县里有很多领导在场的座谈会上,我说自己这辈子就想着在《星星》诗刊一直工作到退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在内心涌出一阵幸福感,是的,这是一种人生莫过于如此的幸福感。当年,在我做出这个选择时,不少的亲戚、朋友、领导、同事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他们的不解。不过,现在他们大多慢慢都理解我的这种选择。
王 琪:成都是一个非常幽雅、闲适的城市,除了闻名遐迩的美食美景美女,以成都诗群为核心的四川诗歌,新时期以来表现得异常活跃,那么成都可否视作一座令诗人们向往的诗歌之城?
龚学敏:成都确实是一座令诗人们向往的诗歌之城。要成为一座真正的诗歌之城,需要很多的要素,比如,诗歌的历史与传承,优秀的诗人,关于这座城市优秀的诗歌文本,经常性的、有影响力的诗歌活动,不同美学追求的诗歌群体等等,当然还需要一本有影响,并且能够包容的诗歌刊物。关于成都可否视作一座令诗人们向往的诗歌之城,在肯定的情况下,我真的希望有人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这种研究不仅对成都这座城市有益,对四川诗歌,甚至中国诗歌、中国文学也都是有益的。
用自信心对待自己的诗歌作品
王 琪:时值丙申初春,又是一年复始,新上任《星星》诗刊主编不久,有什么新的打算?新的创作计划也有吧?
龚学敏:《星星》诗刊已经走过风风雨雨的六十年了。六十年来,《星星》诗刊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诗歌爱好者、诗人们的喜欢,是因为一代代《星星》人始终坚持诗歌刊物应有的责任和担当而造就的,这种责任与担当已经成为《星星》精神,并将一直传承下去。
至于我自己的个人创作,目前正在写一首长诗。我在成都的住址离金沙遗址不远,经常散步便走过去了。这是一个3000年前商末周初的成都人活动的遗址,这个时期的四川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是非常灿烂的,也是非常神秘的,具有想象力与精神价值的,有意思的是,现存的这一些仅仅是零散的历史的切片,几乎没有清晰的来龙去脉。我想这种题材的诗歌写作才会最大限度地调动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因为我一直认为想象力才是诗人的真正的天赋。当然,我离诗人这个称谓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如此,我对这首已经写就了一部分的长诗依然充满期待。我认为真正的诗歌写作者,应该用这种自信心对待自己还未完成的作品。
王 琪:地处西北的陕西与四川仅秦岭之隔,但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积淀等方面差异甚大,最后,想请您谈谈,由于类似某些因素的存在,对一个诗人的成长与诗学的建构起多大的作用?
龚学敏: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汉语覆盖着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历史积淀,所以说,我们的诗歌应该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可惜,现在的诗歌大多千人一面,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有着较强辨析度的诗人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诗人了。趋同和媚俗一样,不仅伤害了诗歌,也影响了诗人关注这个世界的态度。
王 琪:今天,受我们《延河》主编阎安老师之托,我和您有了这次愉快的交流和对话。我代表他和众多《延河》读者在此向您致谢!
龚学敏:不客气,有机会咱们再聊!
一如和龚学敏老师的初次偶遇,他总带着温和的性情,不疾不徐的说话语气,与我款款交谈。间或扬起手臂,又缓缓放下。他不一定高谈阔论,但低声细语时,总能语惊四座。言之凿凿之外,关于诗学方面的交流和办刊经验,龚老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积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理念,那就是对待汉诗写作的认真态度,如何为做一名称职的诗刊编辑尽心尽责。
访谈中,龚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赞同,那就是:向真诚的,向不讨好、不媚俗,坚持和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立场,让文本说话的诗人致敬。而在国内很多诗人和编辑同行的心目中,龚学敏老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呢?
责任编辑:阎 安 马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