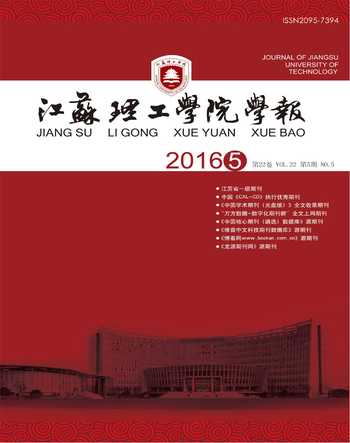英汉情诗“一”之隐喻认知
2016-05-30周子伦欧裕美
周子伦 欧裕美
摘 要:爱情诗都利用数字和事物的相似性,通过隐喻投射来理解抽象的情景和事物。由于人类的认知和思维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数字作为隐喻手段的使用也有异同性,“一”的隐喻具有相同的寓意,在诗词中的虚指和概数的隐喻用法则不完全一致,缘于英汉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中,经历不同的生活和历史进程,有着不同的社会宗教文化的哲学渊源,就必然存在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英汉情诗;爱情;一;隐喻;认知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6)05-0013-05
亚里士多德《诗学》和《修辞学》中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名言:“……尤其重要的是善于使用隐喻字……”。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比显而兴
隐……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是人类认知、思维、经历、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人类思维具有共性,英汉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迥然,拥有不同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哲学渊源。在英汉语言中,数词的运用也深受各自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的影响,语义范畴进一步扩展,并向多个认知域投射,沉淀了特殊的隐喻和转喻文化内涵,既代表其本身的数值,也承载丰富的隐喻意义。学界对数字是否具有数量概念外的外延和寓意,鲜见详尽的论述。国内对数字具有比喻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涉及英汉数词翻译问题,但较少论及对其隐喻作用,更多的论文只是对比英汉数词的文化内涵,语言学专著也没有对数词隐喻进行系统的、专门的论述。日本学者绪方隆文《作为比喻的基数词》一文认为:基数词是比喻的表达方式之一,它的形成过程与比喻相同,也是在同一化和焦点推移的两个过程中形成的。依据比喻的含义,数词或基数词的比喻,也是将两种原本不同的对象物视为相同的物体(同一化),并朝着引人注目的方向置换(焦点推移)的表达方式。在各种词语组合中的数词或基数词的比喻,正是在这两个过程中生成,从而起到隐喻的作用并赋予隐喻的意义。古籍《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也。”爱情诗词一直是人类永恒的咏歌主题,前蜀和后蜀时期的《花间集》尽是咏歌男情女爱,或冶游欢会,或离别惆怅,或相思苦楚,或孤寂情怀,或遗弃的怨恨。《花间集》中的词以及近现代著名英美爱情诗中的数词隐喻映射有同质性和异质性,虚实皆指,为爱情诗词平添一缕缕浓郁的缱绻情愫。
一、合二为一的隱喻
吕叔湘指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1]2-3一(one) 是最小的自然数,在数量域里可以由“小”而表示数量“少”,转喻为“单一”“唯一”。在人类文化中,“一”别赋予了万物之始的意义:“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说文解字》)。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与“道”相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一”寓意生命起源,是数字之始,也是万物之始,据此可以引申为“相同”。汉民族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哲学思想,引领人们中意事物的成双成对,“两全其美”“双喜临门”,即是如此,由“二”“两”“双”构成的词语多含褒义。《花问集序》曰:“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锦丽;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可见文士与歌伎,才情相融,假以声色,使词得以风行,“男子作闺音”(to write with a female pen)是花间词的一大特色,以女性口吻诉说爱情、别离,言语之间有女子的温婉,又有文士的雅趣,特别是数词一和二(两,双,对)的“合二为一”“两人一心”的爱情隐喻比比皆是。如“社前双燕回”“一双娇燕语雕梁”“金雁一双飞”“还似两人心意”“草初齐,花又落,燕双双”。双飞鸟喻指情侣,或借双飞的燕子、大雁、金鹧鸪、彩蝶、黄莺等动物,这是《花间集》中最常见的喻体。而要衬托两人缱绻相思,则有“终日两相思”“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二年终日两相思”等不一而足。如温庭筠《菩萨蛮》中的“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刻画女子新著绣衣,又黯然神伤,一袭新绣的绫罗短衣上的那对金鹧鸪,寓意有情人两心相悦,反衬情郎缘何还不归和自身的孤寂。词中不着一“思”字,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一缕缕的愁情,一脉脉思肠。还有“钗上蝶双舞。心事竟谁知”的“蝶双舞”即衬托闺中女孤枕度日的寂寞和抑郁以及对情郎的款款相思之情。
人类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来说,各种认知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认知心理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通。[2]5可见人类思维是具有共性的,中西文化在“爱是成双”这一点上有许多相似的隐喻表达式,中西方文化中“一”代表万物的本原,在爱情生活中比喻恩爱情侣,两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中西,表示两人合二为一的结婚内涵,汉语用“合卺、结发”等字眼,英文则可用two become one表示而合二为一,那比翼双飞的禽类昆虫正是人类恩爱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如莎士比亚《凤凰与斑鸠》诗句:So they lov'd, as love in twain. Had the essence but in one; Two distincts, division none: Number there in love was slain. (他们彼此相爱,本质乃是一体:分明是二,又浑然为一,数已为爱所摧)。[3]152-153 合二为一的隐喻思维是人类的共性,谁又能在莎士比亚诗中的one和two画上一条鸿沟?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one是万物的本原,如英语one的是 unity or, in technical contexts, monad,is a number, a numeral, and the name of the glyph representing that number. It represents a single entity, the unit of counting or measurement。英文中也以The Great one(伟大的一,太一)指代圣经中的上帝耶和华,数字one被等同为“创世主上帝”。如英语习语the Holy one、There one above,这是one从数字向宗教的投射。《圣经·创世纪》提到:Therefore a man leaves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and clings to his wife, and they become one flesh.在爱情诗歌中亦是如此,如T.Campbell《自由与爱情》(Freedom and Love)中的When two mutual hearts are sighing for the knot there's,no untying(当这两颗心为结合而叹息,这爱早已难分难解);G.G Byron的《想当年我们俩分手》(When We Two Parted)中的When we two parted silence and tears(当我俩分手,泪水默默地流);P. B. Shelley《爱的哲学》(Loves Philosophy)中的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in one spirit meet and mingle, why not I with thine?(一切按神圣的法度,交汇融合成一整体,我为何不能与你合二为一)特别是雪莱用隐喻来折射人类对爱真实的真谛的诠释,揭示世间万物皆成双这一神圣自然法则,把爱的真谛诠释得淋漓尽致。全诗没有出现“爱”字,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把隐喻性用到极致。另外,表示亲昵的动词“混合、接吻、拥抱”(mingle、mix、kiss、clasp)尽管没有出现数字,诗人从语言学角度创造出“成双”(pair)的隐喻,从另一角度看让读者联想到成双合一(Love is pairing)这一意象。无论是“混合”还是“接吻、拥抱”都属于两个实体间的融合;A.E Housman《当我们一路走过田野》(Along the Field as We Came by )中的A country lover and his lass, two lovers looking to be wed.(是一位乡下情哥和他的情侣,两个情侣打算配对成双);John Donne《别离辞:莫悲伤》(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中的Our two souls therefore, which are one(于是,我俩的灵魂浑然一体)等,其中one和two都表示爱恋双方合二为一的隐喻,其中two并非纯粹数字,而是隐喻两个心爱的恋人合二为一的爱情结果,这种一和二(one and two)是确切的数字,也是一种爱情隐喻,是中西爱情隐喻的同质性的体现。
多恩运用圆规的两条腿喻作two souls,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依恋关系,是对爱情忠贞和完美的隐喻,两只脚合二为一(圆圈象征着美满和谐)归于宁静安详。由于圆规的双腿是互动的,其实就是一体的(Our two souls, which are one),圆心腿的坚贞,另一条腿才能画出一个完美的爱情之圆,比喻一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灵魂之恋。圆规承载了灵魂的忠诚和爱情的完美鲜活的形象,圆规的两腿是两个分别的个体,缠绵的圆心脚则象征着紧密结合的“已渗透了彼此的心灵”两颗灵魂。这种心心相印,永不分离的灵魂并不因恋人的身体而分开,一方不得不离开时,确信一方的灵魂是紧紧伴随另一方的,一方归家另外一颗灵魂才能放下牵挂,最后诗行的隐喻是,Such wilt thou be to me, who must like the other foot obliquely run(你就是我的另一半,如同那另一条腿,侧身转圈),寓意两人如同一体。多恩在《翌日》(Good Morrow)中将自己和恋人比做构成整个世界的两个半球,构成的这个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美满(Where can we find two better hemispheres),没有严寒,只有温暖,用数字比喻他们的爱情合二为一(If our two loves be one, or thou and I)。罗伯特·勃朗宁《深夜幽会》(Meeting at Night)中的Then the two hearts beating each to each,衬托出两人幽会时芳心可可,剧烈跳动的声音盖过屋内别人的惊喜声的情形,渲染了夜会情人那如痴如醉的万种柔情,Philip Sidney 的The Bargain 中的My true love hath my heart,and I have his,By just exchange,one for the other given(我的摯爱拥有我的心,我有他的心,我们两人公平合理,彼此以心换心),one for the other即隐喻两人心心相印,合二为一的恩爱情愫。
二、虚指
(一)比喻瞬间或短暂之“一”
新华字典“一”词条:(1)部分联成整体:统一,整齐划一;(2) 纯;专:专一,一心一意;(3) 相同:一样。从语法角度看,《花间集》中的“一”可和量词、名词、动词连用,并因组合的差异相应包含不同的隐喻意义。
“一”比喻开端及发生的瞬间,“一”在汉语中时间表示很短或动作短暂的隐喻。如“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少年郎,容易别,一去音书断绝”中之“一夜”“ 一霎”“一去”的“一” 皆为虚指。词人通过对自然景观“夜雨”的细腻描述表示瞬间或短暂,女子由于情郎“一去”, 用一个“一”字传神地将女性种种相思爱恋之情书写殆尽,真切毕现,表达出来女子孤独寂寞的内心情感,写出她们无尽的悲愁与伤感,或因眷念铭心而梦绕魂牵。英诗的one / a也有短瞬含义,如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中也有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让我们暂时离别),诗人信誓旦旦暂时作别情人,许诺那怕千沟万壑阻隔,也要归来欢聚。a即是瞬间隐喻。
(二)“一”+量词隐喻“孤单”
在“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的特定场景中,“一曲离歌肠寸断”的悲怆场面;有在“迢递去程千里,惆怅异乡云水”的临别之际,女子“满酌一杯劝和泪,须愧,珍重意,莫辞醉”(韦庄《上行杯》)的饯行场面;“伤心一片如珪月”写出“伤心”之感,又把这一份伤心比喻为闲锁宫阙的珪月,情景交融;“洞房不闭白云深,当时丹灶,一粒化黄金”指丹砂化为一粒黄金,词人在芊绵温丽之中,略带失意、怅惘之情;“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中的“一带”象一条带子,比喻有情人虽近在咫尺,一带之遥却违于礼法不能厮守,突出深闺女子凄凉孤寂的心情;“红纱一点灯”,夜阑人静之际,那红纱中的一盏孤灯,红影摇曳,朦胧隐约,伴着那相思女子度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何其凄凉,那一点灯烘托了环境气氛,是一颗在苦恋中燃烧的心,虽备受煎熬却始终执着如一,永不熄灭;“景阳楼畔千条路,一面新妆待晓风”比喻宫内楼边的条条道路上,柳枝干丝万缕,一抹青色,迎风飘舞,好像美丽的宫女们新妆一样清丽,迎接着晨风的吹拂,开阖有致。[4]12 “一”作为数词出现的最原始最基本用法,既表示具体的数量,也作为一种隐喻手段表示虚指。
(三)“一”+名词隐喻“全、满”
“一”不仅实指数量义,还表示“全、满”,是虚指的意义。“饮散黄昏人草草,醉容无语立门前,马嘶尘烘一街烟”,黄昏时街市一瞬,人们散去,醉客无语倚门,马鸣奔驰,一阵尘烟,如蒙太奇一般,鲜明展现在眼前,展示词人伫立在滚滚红尘之中,默默地凝视着伊人,突现出一见倾心的特有感受;“一庭浓艳倚东风,香融,透帘栊”为更好展现词的主旨,词人特意选择从室内向室外的叙事视角来窥探,从帘内向外望出,袅袅东风中一庭红杏,枝叶相交,互为映衬,重重密密,香气四溢;“一梦杳无期”中,词人以神话衬托出梦后再也没有相会之期,以神女相思之苦比喻闺楼女子的孤寂,恰似楚王一梦与之相遇后,就此人神永隔,所以说是“杳无期”,只留下永久的惆怅。此类是数词“一”出现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源自上古,即数词与所修饰的名词间没有后世所说的量词,数词数的本义被弱化了,转喻成为副词,表示“满”,“全”。
(四)“一”+动词隐喻“一旦”
数词可对动作的数量或数位进行称说。此种形式为偏正短语,数词充当动作数量或数位的状语,动词为中心语。如:“少年郎,容易别,一去音书断绝”追叙闺中少女与少年郎分别时依恋的情状,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衬托少女之相思之怨;“玉郎一去负佳期”写少妇的愁容,千里路遥,书信难过,空闺独守;“一梦云兼雨”写在荷叶繁茂、波浪泛着色彩的地方,美人和情郎偷偷约会,尽情欢爱,如梦如幻,以及心中满是对情郎深深的爱意。“一”比喻短促,一刻千金的情景;“江边一望楚天长”中的“一望”二字,颇能传神,表现主人公顷刻间由喜悦变为忧愁的神态,描写美好景物之后,立刻转入凄苦境界,词人站立在江边,感受着美好的秋景;“一望巫山雨”看似写巫山佳景,但结末也隐含着佳人之怨。南宋叶梦得评此词为“细心微诣,直造蓬莱顶上”,其境界缥缈,情意深邃。可见数词可以单独对动作的量进行称说,也可和量词结合后对动作的量进行称数。数词和动词直接结合,数词处前,动词置后,“一”既可作为动词的状语,也可作为一种隐喻手段表示一旦、一俟。
(五)a / one比喻“不确定”
a / one泛指人或前面提到的事物,比喻不确定,相当于a certain,如乔治·威瑟 《我爱过一位美丽的姑娘》(I Loved a Lass, a Fair One),诗人没有具体说出他爱过的姑娘的信息,而用大量篇幅描述这位他所钟爱的姑娘如同《圣经》中的示巴女王(She was indeed a rare one. Another Sheba Queen),是超群绝伦的世间美人,其中a和 one 喻指诗人心中的美人。One指代前面提到的人或事,如多恩《翌日》Let us possess one world, each hath one, and is one中的one就指代world,数词转喻成名词。a/one艺术性的隐喻用法一如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艺术是思想的结晶。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体现了最大量的思想”。
(六)一(one,a)隐喻“同一性”
“一”表示“相同”的意思,“one”也有这样的意义。如“一片春愁谁与共”表明仙女的孤凄,“一样”的春愁无人与共,语言含蓄,情在词中;“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这一次欢会可能是情侣的最后一次,此生可能是相隔天涯,更可能是形同陌路,但不管怎样,他们是无法忘记对方,此生再辛苦,他们的爱总有一次值得永远珍藏;Robert Browning 的Life in Love(恩爱一生)中的a修饰love,比喻爱是一体的,一致的,同一的。
三、结语
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说:隐喻构建我们的感知、思维及行为方式。[5]3-4数字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记录历史不可或缺的文字系统。数词“一”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获得十分丰富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人们利用数字和事物的相似性,通过隐喻投射来理解抽象的东西。英汉爱情诗词中的数字“一”是表层符号,深层隐喻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同样会受到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的影响,所以数词“一”虚指意义的获得,受文化背景的制约,由数字“一”组成的数词语义场具有数量概念和符号之外的涵义。英汉语言“一”的隐喻具有相同的寓意,而虚指和概数的隐喻用法则不完全一致,两者异同兼有。相同之处是人类思维方式同一性的体现,不同之处则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奉若神明的西方神学宗教文化的差异之反映。数词“一”的运用除基于隐喻需要,也体现汉语诗歌对平衡、对仗及音律美的语用要求。宋朝姜夔认为“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正是反映中英爱情诗词常通过含蓄手法,让读者通过自身的想象和联想,体察作品深隐的寓意及其无穷的语言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中国人学英语·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
[2]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1999(1):3-15.
[3] 王佐良.莎士比亚绪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52-153.
[4] 李冰若. 花间集评注[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
[5]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4.
Recognition on Metaphor On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ove Poems
Abstract: The use of metaphor one ha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ove poems. Due to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cognitive and thinking model of human being, Chinese and English have “one” as the same metaphors but sometimes not all metaphors are in conformity with each other due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life, history and different social philosophical origin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Key words: love poem; love; one; metaphor;cognition
責任编辑 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