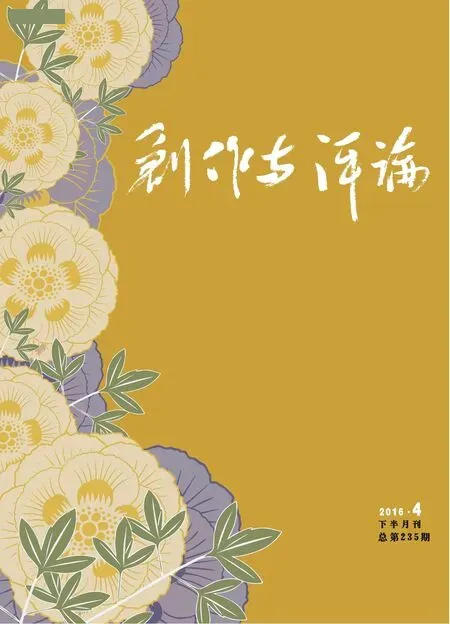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
2016-05-28刘永春叶炜
○刘永春 叶炜
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
○刘永春叶炜
主持人语:
本篇对话由作家叶炜和批评家刘永春合作完成。叶炜以写作长篇小说见长,尤其是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出版后得到广泛的关注。从目前的状况来看,70后作家显然更偏重也更擅长写作中短篇小说,并且有不少作家的作品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作家逊色。相比之下,有厚度、广度与深度的长篇并不是特别多——国外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叶炜的这次写作实践,可以引发的话题是非常多的。叶炜与刘永春的这次对谈,主要是以这部作品为基点,涉及70后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乡土写作的困境与前景、什么是好的文学等问题。对谈中提出的不少观点也值得注意,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这决定了我们始终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精神免不了要不时地出现胶着和矛盾。”“我一直在努力实践一种‘大格局’的写作,从自身的‘小宇宙’出发,不断抵达‘大宇宙’的奥妙和深邃。”
李德南刘涛
一、“以毕生书写向乡土中国致敬”
刘永春:叶炜兄好!你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大视野的刻画,尤其是对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与命运变迁做了非常动人的重构。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们来说,厚重沉痛的乡土情感是我们的人生底色,是我们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情感处境。那么,你在动笔之初是如何构思如此浩繁的大规模书写的?
叶炜:的确,乡土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较为显著的成长底色,它因此也成为了我们较为深刻的人生记忆。虽然在城市工作多年,但我们的身上仍然有着较为浓重的“土”味儿。对于乡土中国,对于苏北鲁南,对于生养我们的村庄,我们始终心怀感恩。无论是历史课本,还是老人们的口口相传,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的这一百年是不平凡的,中国的农村在这一百年历经了上天入地的变化。但我很好奇:百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农民到底经历了什么?中国这一百年的精神底色有无改变?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是处于剧烈变动还是所谓的“超稳定”状态?我想到生我养我的村庄去寻找答案。

叶炜
真名刘业伟,文学博士。1977年出生于山东枣庄。200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等,在期刊发表各类文字200余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江苏师范大学作家工作坊主持人,美国爱荷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于是,我从最容易着手也是最为熟悉的《富矿》开始,寻找乡土文明不断式微的根本原因,试图给出自己的回答。构思写作《富矿》,是带着感伤情绪的,字里行间免不了有些许愤激的情绪和先验的设置。《富矿》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发现一味去哀歌和凭吊是不能找到答案的。当下的新乡土写作一定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书写,这就要求作家一定要善于“去蔽”。于是,我又构思了更接近当下农村生活的《后土》,想以苏北鲁南的一个小小的麻庄的基层政权生态,窥探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史。与《富矿》比,《后土》更加“温情”一点。而在构思刚刚完成的《福地》时,则把这种“温情”上升到对人性的观照,把视角从《后土》的乡村治理扩大到国家政治,把乡村伦理道德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之中,想以此“还原”我心目中的乡土中国。
刘永春:相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其他年龄段作家,70后作家是较为沉默的一个群体,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但部分70后作家已经展现出了扎实厚重的精神容量、轻盈自如的文本形态和自省内敛的主体特征。经由《乡土中国三部曲》,你的叙事能力和精神向度已经得到充分展示,兄如何概括自己作为70后作家所具有的写作初衷,自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又受到哪些因素的触发呢?
叶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这决定了我们始终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之中,精神免不了要不时地出现胶着和矛盾。在这种状态中,我最想探求的就是自己的精神来路,以此解答人生的困惑,寻求思想的文学表达。我无意代表任何群体,也不为任何人代言,我只想代表我自己。虽说在文学不断式微的当下,抱团取暖不失为一种策略,但这种“抱团”在某种程度上彰显的往往是自身的“无力”。或许一个人的寻找免不了注定会“百年孤独”,但恰恰是这种“孤独”才最有力量。我一直倡导有力量的文学和有思想的学术,惟有有力量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
回首我的创作之路,多半是出于自身的兴趣所在,兴趣的激发是我长久写作的力量之源。从小学开始,“我要写作”一直是我的人生理想。为此,在报考大学时,我对我的老师说:只要能读中文系,什么学校无所谓!大学本科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硕士阶段也是汉语言文学,到了博士阶段,我干脆选择了国内唯一的创意写作专业,成为国内第一个创意写作方向的文学博士。我始终认为,能够接受系统的文学训练是这一代作家的幸运,有了文学学科专业的锻造,不但可以提升我们的知识素养,更能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扩大创作的视野。在大学阶段,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和思想类著作,这让我很早就确立了文学的启蒙意识和哲学追求。我一直在努力实践一种“大格局”的写作,从自身的“小宇宙”出发,不断抵达“大宇宙”的奥妙和深邃。
刘永春:据我所知,如众多70后、80后作家一样,你也是从青春校园文学起步的,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什么因素引领你转向了乡村书写呢?
叶炜:我的写作一开始主要集中在青春题材,只有很少的乡土写作。尽管大学时代我发表在文学期刊的第一篇作品是农村题材的《民间传说》,最后一篇作品是《母亲的天堂》,但大量的作品还是集中于青春校园,比如“大学三部曲”《大学.com.狼》《大学. com.羊》和《中毒》等。大学毕业以后,我进入高校工作,按照常理应该继续书写青春校园。但我在写作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对于文学创作来讲,大学校园所在的都市尽管十分“有料”,但并不是当代中国的底色,尤其不是我自己的精神底色。我在乡村长大,童年的经验是无法割舍的,也是不应该舍弃的。而且,在我最初的写作中,最满意的也不是校园题材,而是不多的乡村书写。我应该听从内心的召唤,回到我的村庄,去书写我的父老乡亲。土地里面有真正关乎中国的故事,我的任务是如何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把它们讲出来。归根结底一句话,当下中国的底色是乡土,探求中国避不开乡土书写。这是我的内心选择,我要以毕生的书写向乡土中国致敬!
二、“以叙事创新向现实正面强攻”
刘永春:在我看来,《乡土中国三部曲》包含的《福地》《富矿》和《后土》组成了一个视角交错、时空融合、方法各异的文化多面体。其中,《福地》侧重辛亥以来风云诡谲的中国现代史,尤其是艰苦卓绝的抗战。以万仁义所代表的“仁义”精神与万家几兄妹为象征的现代家族革替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而小说努力弘扬的是传统文化中优良的精神土壤,而这片土壤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风化直至流失殆尽。这种文化转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现代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多灾多难,一个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日益虚无与人性状态的不断恶化。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姿态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反叛传统、批判历史而确立其合法性的,但其后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精神资源的“返回”却从未停止。你在《福地》中很好地处理了对乡土中国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反思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特点也同样集中表现在万仁义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身上。那么,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既保守又先进、既为己更为人、既持家教子又护佑乡邻的乡绅形象?这个人物身上闪烁着令人困惑又令人钦佩的光辉,与以往的意识形态书写中的乡绅完全不同,他反而是乡土中国最具“乡土精神”的一个代表,这种书写对以往的乡土叙事是极大的颠覆,你在构思时进行哪些方面的尝试,你对万仁义这个形象又会如何评价呢?
叶炜:塑造万仁义这个不同于既往文学史的乡绅地主形象,源于我的真实生活经验。我生活的村庄里有一个韩姓地主,尽管我和他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但因为村庄不大,见到他的机会很多。我记得报名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上课正是在这个韩姓地主的大院。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并没有那么坏,反而有一点点温和。在我的家乡,有一个讲故事的传统,而在这些被不断讲述的故事中,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韩姓地主的事情。在耳濡目染中,一个乡绅地主形象逐渐立体起来。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既保守又先进、既为己更为人、既持家教子又护佑乡邻的乡绅形象。像这样的人物在鲁南大地广泛存在。
我试图写出地主的两面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观察地主有一个阶级的视角,就是地主是一个恶的代言人,很多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写的。其实地主(也就是乡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存在,他的身上有两面性,有两个角色,一方面有他的社会管理的角色,乡绅在乡村的风俗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管理的时候有他暴力的一面;另外一方面他又有保护乡村的作用,是守护者的角色,为什么有些乡绅都是名人,就是他保护乡村的能力发挥得非常充分。
有些人或许认为,这是一部为开明地主正名的小说。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历史的叙述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披沙拣金的工作,而文学,尤其是小说,却不能忽略那些个体。或许这些个体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老万这一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在苏北鲁南的抱犊崮山区,像老万这样的开明仕绅并不少见。所以,在历史遗漏之处,正是文学出发之地。这倒不是说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文学完全可以提供给读者另一种真实。这样的真实有别于冰冷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是有温度的感性存在。历史常常喜欢关注整体和大人物,而小说则常常在个体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兴奋点。
人是复杂的,而像乡绅地主这样的人物更复杂,对他们进行对错和道德等方面的评价没有那么简单。我自认为这个形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个能够立起来的人物,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
刘永春:小说中还有一个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人物,就是绣香。她早早就死去了,却在小说中无处不在,既充当了某种预言者,也充当了万仁义很多行为的引领者,时时提醒着万仁义,成全着其“仁心义举”。万家的其他女人,不管妻妾还是女儿,绝大部分都是时代和命运的牺牲品,肩上承担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历次苦难。与她们相比,绣香在死后反而具有了省察一切的超能力,因而其命运中的悲剧色彩最淡。这个人物形象虽然不构成小说故事情节的主要动力,却是深化小说主题的绝佳途径。这种人物形象的设置方式及其叙事功能的充分利用,展现了你不俗的叙事能力。你在设置绣香这个人物形象时,是否已经意识到了她可能带来的叙事便利和对小说主题展开带来的开阔视野呢?
叶炜:的确有这方面的考虑。
鬼魂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蒲松龄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聊斋志异》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这个叙事传统在当代作家这里没有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自从现实主义写作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以后,乱力鬼神之类的东西已经被文学逐渐抛弃。殊不知,鬼神叙事正可以弥补文学的单调,能够为现实主义写作注入灵动色素。其实在《富矿》和《后土》中,已经出现了这种叙事,但多是经由“梦”这一载体来阐释。比如在《富矿》中,麻姑多次与二姥爷的对话,《后土》中刘青松和土地爷的对话,都是通过做梦这一心理学方式来完成的。与此不同,《福地》的鬼魂叙事不但更加密集,而且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福地》中的鬼魂不需要再经由“梦”的媒介,而是直接由鬼魂出来说话。在第一章中鬼魂就出场了。为何要在小说一开始就进行鬼魂叙事?在我看来,这一叙事很重要。一方面是情节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老槐树叙事的补充。每当老万遇到难事,绣香总要出来劝慰或者支招,在重大困难面前,甚至会直接现身施以援手。鬼魂叙事在小说中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力图构建一个混沌的文学气氛。
此外,我之所以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采用鬼魂叙事,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我正在努力实践的超现实主义写作需要。
刘永春:如果说《福地》主要刻画现代中国农民在历史与命运中的浮沉悲剧,那么,我觉得《富矿》则侧重书写当代农民在欲望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自我毁灭的人性悲剧。当然,这种悲剧仍然与单纯重视经济开发而忽视文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前者是人被历史压迫,后者则是历史通过欲望潜入人性造成自我异化。从闭塞的乡村到现代矿区的转变,使得麻庄人亲眼见证了现代化的神奇力量,也使得他们对矿上的城镇化生活趋之若鹜。传统的乡土道德轰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就是盲目遵从内心欲望而导致的利己主义。城市文明带着自己的病菌侵入乡村,改变人的精神结构与人性结构,这其实是现代乡土书写常见的方式,但很少有作家会利用矿区作为叙事场所和推进方式,这种构思与你的人生经历有关吗?在你的心目中,麻庄所代表的传统乡村出路何在呢?
叶炜:苏北鲁南有很多煤矿,苏北重镇徐州和鲁南明珠枣庄,都是因煤而兴、因煤而富、因煤而变的城市。在我的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接触到煤矿和矿工。我的一个姨夫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煤矿工人,我从小就听他讲许多关于矿工的故事。来到徐州以后,又多次到矿区考察。这里曾经是经济上的高地,也是人人称道的能源富矿。当地下的黑金被过度开采,这里逐渐从一度繁华的能源大户沦落为亟需改造的经济洼地,由煤城明珠成为老工业基地。就像曹雪芹笔下的那座大观园,繁花落尽之后,绚烂终究归于平淡。巨大的经济落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然而却让这里成为文学的“富矿”。
在我的心目中,中国的传统美丽乡村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的底色一定是田园的,而不是城市化的,甚至也不是城镇化的,它是中国独有的村落存在;其次,生活在这里的人身上保留着中国典型的传统美德,更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再次,村庄的民风是淳朴的,这里的人身上闪耀着善良的光辉,而少有都市的污浊;最后,乡村自治功能能够得以高度实现,乡贤名士的风范得到极力张扬;等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乡村改造,重点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不是人居环境的城市化,在这方面,反而要尽量保存传统的东西。
刘永春:在整个三部曲中,最打动我的是《富矿》的后半部,尤其是作为官婆转世的麻姑再一变而成为“大洋马”,这种巨大的、撕裂性的转变所蕴含的巨大悲剧性让我久久难以释怀。在我看来,这个人物形象是20世纪文学中难得一见的乡村女性,她的悲剧命运在周围女性同样的悲剧命运衬托下,沉重得让人窒息。是的,“窒息”就是我在读到《富矿》后半部时的直观感受,而且的确让我长久地沉浸其中,欲哭无泪。与《福地》不同,《富矿》主要由麻姑这样一个女性而不是万仁义那样的男性来承担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为什么?你觉得麻姑这样的悲剧女性在哪些方面、以哪些途径与当代乡土中国的命运相契合呢?
叶炜:我认为中国所谓的现代化存在着一个不断“粗鄙化”的问题,包括发展的盲目性、造城的暴力性、文化的欺骗性、经济的泡沫化。这样的“粗鄙化”在乡村改造中处处可见,这造成了乡村不可承受的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我觉得,文学在表现这些时,不能回避,应该正面强攻。在这方面,女性比男性更能彰显矛盾的对抗性。所以,我选择了麻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麻姑的自我选择。麻姑身上有着中国妇女的某些美德:勤劳,单纯,向往美好,等等。但也有不少缺点:对物质化追求的向往,对欲望化生存的转变等。这一点与当代中国的命运是契合的。当代中国乡村经受了城镇化的挤压之后,焦虑感、矛盾性不断凸显。这些在女性身上有着更为集中的表现:一方面,留守在村庄的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了与传统妇女美德相违背的歧途;另一方面,从女性打工者的城市遭遇反观她们与乡村的关系,其紧张程度已经非同一般。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当代乡土中国的症候所在。
刘永春:除了被麻姑等人物形象所负载的巨大历史悲剧打动以外,我还觉得《富矿》比《福地》对中国社会的精神反思和文化批判更为深入、更为尖锐,也更为有效。麻庄矿与麻庄村构成鲜明的两极,一边是梦幻般的现代城镇生活场景,带着颓废的肉欲气息,另一边则是逐渐被抽空的乡土田园。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敌视。许多人在两种场景中来来往往,男男女女都被裹挟进“现代化”这个巨大的漩涡中,最终那些美好的生活和人性都不复存在,直到下一场大洪水与末日一起来临。在那场大洪水之前,我注意到小说中美好的人物与人性都被毁灭了,而大多数人遵从自己的欲望卑微地苟活着。这是城镇带给乡土的必然命运,还是人类历史车轮碾压下的暂时黑暗?这种人性的坍塌是我们为社会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吗?你鲜明地用了“轮回”一词,我理解为它代表了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可以这样理解吗?
叶炜:在写作《富矿》的时候,我有意把人物的命运推向了一种极致,正如你所说,美好的人物与人性都被毁灭了,没有毁灭的都在遵从自己的欲望卑微地苟活着。表面上来看,这是城镇带给乡土的一种必然命运,但这种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化“粗鄙化”发展的后果,是现代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代价。但我宁可把它理解为暂时性的黑暗。
在《富矿》中频繁出现的“轮回”一词,可以看作是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事实上,《富矿》的结构也是一种“轮回”式的结构:从零到零。《后土》《福地》同样如此:《后土》采用的是二十四节气,《福地》是天干地支。这都是循环的结构。我有意在彰显“轮回”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可以说,这也是我的哲学观。
三、“以温情思考与生活努力和解”
刘永春:《富矿》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现在,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制造城镇的运动中,楼房越盖越高,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矿工们努力工作然后到娱乐场所尽情挥霍,而附近村民为他们提供着挥霍的资源。”城镇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入侵当然是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可是你的小说中也深刻描写了乡土社会本身对城镇文明欲拒还迎的复杂姿态。在此背景下,出卖肉体、获得金钱,在城市人紫秀的眼里“是无烟工业,是绿色生产,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后的自主选择,是劳动光荣身体致富”,而在麻姑眼里则是“用身体糊口活命”,“矿区越发展,对于那些没有钱的穷人越是刺激,他们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会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来。”两个人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系统,前者是城镇话语,后者是乡土话语。两种话语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无法截然地判定谁对谁错。《福地》《富矿》与《后土》同样充满着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探析与思索,或者也可以说,《乡土中国三部曲》是在城乡互动的总体背景中思考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命运的。当然,主要的叙事场所仍然是乡村,而非城市。麻庄,就是乡土中国的缩影。由此,麻庄的历史变迁理所当然也能折射出乡土中国的文化悲剧。
我的阅读感受是,这种悲剧色彩到了《后土》就有所减弱,虽然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力度和对复杂人性的思考深度丝毫没有减少,但矛盾冲突明显变弱了,甚至有了些中和的趋势,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尤其是小说对前任的村支书王远既有深入的揭露,也有温情的理解,这与传统的乡村恶霸形象截然不同,反而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在你看来,这是否来源于三部曲反思道德失范、呼唤精神重建的主题呢?同时,这样的结局安排对刘青松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重要,他身上呈现出来的乡土智慧和宽恕之道与万仁义遥相呼应,二人都宽厚待人、以乡邻的命运为己任,堪称传统美德的化身。我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精神脊梁,兼具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现代社会的宽广视野。可以这样理解吗?
叶炜: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从《富矿》到《后土》,我在努力试图与生活达成一种“和解”。现实是残酷的,但生活依然在向前。当我们无法与生活决绝对抗时,只能选择和解。随着阅世的深入,我对当代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有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问题当然要暴露,答案也要不停地去追寻。但在追寻答案的时候,我们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应该有所缓解,以便能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
在现实生活中,王远这样的村干部广泛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主流”。我认为通过反思他们,可以反思现在的的乡村基层政权的生态,也有利于深化反思道德失范、呼唤精神重建的主题。
刘青松和万仁义是我所钟爱的人物,如你所说,他们兼具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现代社会的宽广视野,不但是《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精神脊梁,更是乡土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刘永春:在悲剧色彩有所弱化的同时,《后土》的叙事结构和人物设置也与前两部不同。《福地》以万仁义和绣香一男一女、一生一死、一明一暗、虚实结合的手法结构起整部小说;《富矿》以麻姑(大洋马)为叙事单线,勾连起六小、蒋飞通、胡列等男性与笨妮等女性、麻庄村与麻庄矿两个文明场域,从而刻画了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欲望膨胀与人性畸变。《后土》虽然以刘青松为主要叙事视角,却集中展示曹东风、刘青松与王远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心理纠葛。如果说前两部因其叙事结构而更具深度的话,《后土》则因其立方体一般的叙事结构而更具广度,更能呈现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在艺术上虽不具备前两部同样的悲剧色彩和人性深度,但也能够别辟蹊径地从政治角度展示乡土社会的当代命运,同样也有其成功之处。《福地》与《富矿》更具传奇性和戏剧性,而《后土》回归到生活本真,更具日常性和写实性,是“生活流”,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其实水面之下却也有着各样的人性漩涡。小说不紧不慢地处理着当今乡土社会的种种矛盾,将笔致指向乡土社会的底层结构和日常状态。这种变化是有意为之吗?如果将《后土》中温情的社会改造与《福地》呼唤的文化重建、《富矿》呼唤的道德回归相结合,是否可以看做是你对乡土中国未来出路问题的最终答案呢?
叶炜:你敏锐地捕捉到了三部曲的内在韵律。从《福地》与《富矿》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凸显,到《后土》对日常乡村生活本真的发掘,其间的变化明显。这种变化既是我的有意选择也是无意为之。“有意选择”是指我在体悟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变化:绚烂总是归于平淡。“无意为之”是指我在写作之初确实是我控制着文本,但在写作开始之后,文本慢慢有了自己的“选择”,人物的命运有了自己的脉络,既是可控的,又是不可控的——它们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内在逻辑。
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创作中,《后土》着眼点偏重于政权改良和社会改造,《福地》着重于观照乡村伦理和传统文化,《富矿》侧重人性轮回和道德回归,三者相结合,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看作是我对乡土中国未来出路问题的答案。至少,这些都是我自己对乡土中国的思考。
刘永春:《乡土中国三部曲》摇曳多姿,仿佛奔流的大河,不断生出令人叹服的美丽浪花,风格丰富多彩、叙事角度多变、主题立体充实。这在近年来的70后作家创作中并不多见。总的来看,三部小说都属于乡土书写中的现实主义流脉,具有尖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厚实沉重的文化含量与独具特色的叙事形式。可以说,《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现实主义特征十分明显。但是,还有另外一面,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那就是三部长篇中都有一些超验性的人物、神祇或者现象存在。这些叙事要素与明朗、尖锐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既然不同,它们带来的是某种神秘感、宿命感与无助感。它们构成了一个与主要情节相互映射的镜面世界,有时候是平面反射,有时候是曲面反射,十分有趣。比如几部小说都写到乡村中的土地神信仰、看似疯癫实则清醒的男女疯子、可以俯瞰世界的死者或者树灵,诸如此类的超验性要素在小说中承担了怎样的叙事功能和艺术功能呢?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与情节要传达怎样的主题呢?这种叙事手法更多受到中国的志怪志异传统影响呢,还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叶炜: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如此复杂,乡土中国的历史又是如此吊诡,以至于探寻现代中国的现实,不得不回到古老的中国。在我看来,这样的时间跨度和题材书写非常适合一种超现实主义写作。《乡土中国三部曲》中所使用的老槐树视角以及时或闪现鬼魂叙事和土地神以及男女疯子等,让小说有了超越现实的灵动幻象,既让所书写的故事既附着于现实存在,又充满了历史的想象。整个小说可以说是一次超现实主义的写作实验——既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又有魔幻主义的营构。
《乡土中国三部曲》描绘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有现实的书写,更有历史的回望,有民风民俗的展示,更有乡村精义的探求,其书写对象是很广阔的,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视角。比如,在《福地》中,老槐树不但知晓麻庄所发生的一切,能够和麻庄那些死去的魂灵对话,也可以和麻庄的老鼠等动物交流,更可以穿越历史,和天地人鬼神沟通。所有这些,都是其他叙述视角所不能承担的。对我来讲,这也是打破当代文学中的叙事成规的有益尝试。从效果来看,这些让小说文本更加灵动,叙事更加丰富,艺术更加摇曳。
我从小所接受的故事传统是乡土大地万物有灵,长大后我接受的教育则告诉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人类对未知世界应该有自己的敬畏感。中国是一个缺少宗教意识形态的国家,作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寻求真理真相,探求和构筑中国的信仰系统。这也是我在《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中所隐含的主题之一。
如前所述,这种叙事手法受到了中国的志怪志异传统的影响,当然也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可以说本土和外来的两个影响都有。但从我的阅读视野和知识结构来看,本土的影响是根本的,外来的启示是次要的。
刘永春:麻庄,是三部曲共同的叙事场域,我注意到它既是文学化的虚构也是现实文化地理的真实呈现,尤其在《福地》中,麻庄有着明显的地理坐标。三部曲始终将麻庄放置在“苏北鲁南”的位置上,多次对这块地域的地域特征、文化内涵做出阐释。例如,“这里是苏鲁大平原,齐鲁大地南大门,苏豫皖衔接带,为孔孟老子等圣贤之地,既上承曲邹孔孟之礼,又下纳丰沛汉王之风,为一代帝王之乡;既北蓄泰岱之豪放,又南收江淮之灵秀;既西取微湖之广阔,又东收沂蒙之厚重;既有‘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的豪放,又有‘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的悲壮……”可不可以认为,麻庄、苏北鲁南,既是你的生命故乡,也是精神故乡呢?
叶炜:是这样的,你的解读非常准确。《后土》在《作家》发表时,附了我的一个创作谈,我在创作谈里写到村庄是我出生的“血地”。那里,已经成为了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换句话说,麻庄和麻庄所在的苏北鲁南既是我的生命故乡,也是精神故乡。我深深地爱着那个村庄,爱着那片广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我将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对它们顶礼膜拜和深刻反思。我要在持续不断的“精神还乡”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来路,建立我自己的精神王国和生命信仰。
刘永春:《乡土中国三部曲》展现了你良好的写作状态和美好的创作前景。尤其是其中的反思精神、求索姿态和辩证思维,令人十分敬佩。你的乡土写作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同龄人和忠实读者,非常期待你的下一部大作问世。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