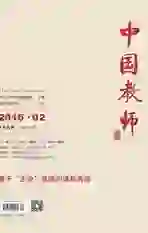无之玄、有之玄和“第三玄”
2016-05-14陈建翔
陈建翔
一
《道德经》的第一章是全书核心,讲了十几个重要概念、重要思想,总归于一个字:“玄”。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说,“道”有两个最基本的秘密:“无”和“有”,它们“同谓之玄”,这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法门。那么,“玄”是什么?
玄,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应该是中性偏贬义的。我们能够从“玄”字联想到“故弄玄虚”“玄学”“玄幻”“玄妙”等词语,其意大抵与不切实际、虚幻缥缈、胡思乱想有关。“玄”字的意思能“堕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令人嗟叹!一部文字的流变史,差不多是浓缩的文化演变史。“玄”字的语义堕落,其实是文化的堕落和智慧的蒙蔽。在老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玄”应该是寓意很美、很好、很深刻的一个字眼,代表着深奥、幽远、永恒,像谜一样地引人入胜。据南怀瑾考证,玄“等于一个环节接连一个环节,前因后果,互为因缘,永远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1]。玄深奥到不可测知。如果勉强对应为现代人的词汇,我倾向于将其翻译成“奥秘”。
老子说“道”包含“此两者”“玄之又玄”,那等于是说,道之玄不止一个,应该有两个;一个玄里面又套了另一个玄。对此,范应元说:“玄之又玄,则犹云深之又深,远之又远。”[2]庄子则用“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3]来解释老子。
那么,这个“玄之又玄”、这个秘密套秘密具体是指什么?应当如何理解?对此,历代在《道德经》研究方面深孚众望的大家,理解不尽相同。王弼、陆希声说,是“始”与“母”,河上公说是“有欲”和“无欲”,范应元说是“常无”与“常有”。我赞同范应元的说法,以为“此两者”“玄之又玄”,指的是“无”和“有”。我把它们分别称作“无之玄”(关于无的奥秘)和“有之玄”(关于有的奥秘)。
无之玄“玄”在哪里?老子讲它是“天地之始”。那天地之始又是什么情况?那就是混沌无状。其实,老子用来形容“道”的一些描述,都可以用来形容“无”即“天地之始”,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①。又如,“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②。我们的视觉、听觉、本体感觉,都不起作用了。邵若愚说:“不可以视听求,不可以思议知,不可以语言及。”[4]无之玄的奥秘,一句话:无知,或不可知的无限存在。
有之玄“玄”在哪里?老子讲,它是“万物之母”。万物之母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使万物生育繁衍,生生不息,“道”是万物生长总的子宫、总的源头。无论万物怎样繁复、杂乱,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那就是道。万生于一,万源于一。我们不能留恋、迷失于万物而不识其母,不能留恋、迷失于“万”而不识其“一”。实际上,道与理的关系是道一理万,我们不能留恋、迷失于理之万而不识道之一。有之玄的奥秘,一句话:一生万的生长并作(其中两个重要的中介是“一生二”和“二生三”)。
老子还用了一对概念来说明“无”和“有”,那就是“妙”和“徼”。什么是“妙”?王弼和范应元倾向于是“微妙”(“妙者,微之极也”“妙,微妙也”。)[5]现代一些学者也解释为是“微妙”。这当然不算错,但过于刻板,没有讲出“妙”的妙处。我理解的“妙”的妙处是:无形而无限。什么是“徼”?徼的本意是边界。现代有些人引申为“端倪”,这是脱离原意了。我的理解是有形而有限。“徼”是跟“妙”相对来说的,一个没有边界(无形无限),一个有边界(有形有限)。
对于玄之又玄的状态,老子喜欢用“恍惚”来描述。“妙”和“徼”是分别说明无、有的,“恍惚”则是整体性地说明无、有的。“恍惚”是什么意思?即若暗若明、若有若无。饶有意味的是,老子既用恍惚来描述无之玄,如“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③。又用“恍惚”来描述有之玄,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④。
说到这里,顺便评点一下我国台湾地区叶曼老师对老子“有之玄”的误解。她在讲课中数次提到《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说“老子对道的描述,还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还是不究竟的,因为里面还有物、有精、有信”。我想,这是大大地冤枉了老子,而且冤枉得没有道理。难道《道德经》的其他部分,叶老师都视而不见吗?叶老师讲佛、讲道,大部分是很慈悲、很精彩的,但对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一章的解读,实在令人困惑。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讲“道”是无形无相、空无一物、不可致诘的,总归是个“无”,这里所谓的“有”(有物、有精、有信),讲的是“可道”,就是道表现出来的现象界,是无有叠加态。这就如同佛陀讲般若自性,必须对着“色”来讲“空”,色是万有,没有色,空就是断灭空。同样的道理,可道固然非常道,但没有可道,如何讲常道?怎能摘出一个“有”来,讲那是老子对“道”的全部理解,然后说“不究竟”?不应该。
老子讲无,也是恍惚;讲有,也是恍惚。实际上,恍惚描述的是无有叠加的情形。无有叠加态,换成佛学术语,接近“一合相”。无有叠加态已经是可道,非常道;一合相也是方便法门,并非本体,但我们现在说的是现象界,是由相还体、以假修真。
庄子深懂老子。庄子的“芒乎芴乎”,与老子的表达堪有一比:“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6]芒乎芴乎(芴乎芒乎),与惚兮恍兮(恍兮惚兮),有异曲同工之妙。
玄之又玄,一个混沌无状的“无”的奥秘,套了另一个生生不息的“有”的奥秘,这是老子给我们描述出的一个美轮美奂、不可思议的宇宙景态。老子把它看作宇宙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总规律、总法门(众妙之门)。
二
但是,“此两者”还是“二”呀,从“二”到万物,似乎中间还缺了一个环节—“三”?“三生万物”嘛。
老子说了“二”(“此两者”),我们就只会学着说“二”,就要一直“二”下去?孔夫子说了,不会举一反三的学生,就不想教他了。学习《道德经》,首先固然需要跟着老子亦步亦趋,但不会举一反三,不敢举一反三,恐怕也不行。老子举一了(道),甚至都举二了(无、有,“此两者”),我们应该可以“反三”了。
“三”是什么?是一、二之间的关系。无之玄,有之玄,二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是“三”要面对的问题。
“三”在哪里?举一反三,“三”恰巧在“反”里。
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讲“道”的来历时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第四十章又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这是无有叠加态的运行状态和基本规律。
学习和研究《道德经》,不能死守循序渐进、线性逻辑和抠字眼的办法,而要用融会贯通的办法。第一章是一个总纲,是出发地,要反复不断地从这里出发,跳到各章,再回来,再出发,再跳。跳来跳去,就可融会贯通。讲无之玄、有之玄之后讲“反”,就要跳到第二十章和第四十章。
“反”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平衡点,也不是固定的居中状态,而是自由的往返流动,是一种大趋势所呈现的律动。如何往返运动?如何流动(律动)?老子说,向矛盾事物的对立面往返流动,向“弱”的方面(更为虚空、处下的方面)往返流动。
“反”,一字千钧!有这一字,整个大自然就活了,呈现出相拥而舞、活灵活现、丰姿绰约的韵律感。老子的《道德经》,其实质就是一套讲宇宙万物流动往返必然趋势的“反论”。在第十六章中,老子又提出“复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是一种在繁杂万物中看到循环往复规律的观念。“复”与“反”相近,强调周期性,“复论”是“反论”的延伸。
我以为,对老子的“反”的解读最为熨帖、到位、传神的,莫过于庄子的“游”(“神游”“天游”“逍遥游”“游刃有余”“游心于物之初”等)。一个“游”,生动地传达出遍布大自然的自由的流动、往返。这就是灵性,宇宙与人的灵性的舞蹈。
“反”是无有叠加态的运行状态和基本规律,但这个“反”不是完全没有前提的,而是有前提的;不是完全没有掌控的,而是有终极掌控的。“反”需要一个前提—“和”,也有一个终极的源头和掌控者—“御”。和、反、御,是隐含在玄之又玄的两个叠套奥秘中的第三奥秘。
关于“和”,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负阴而抱阳,是无有叠加态的另一种更为形象化的说法(据此,我们似乎也可把无有叠加态称作“阴阳叠加态”)。“负”就是背着,“抱”就是抱着。后面背一个,前面抱一个,多形象啊!自然万物,和合相拥、对立统一的状态栩栩如生。“冲”是运动、振荡、变化,“和”是叠加事物在运动、振荡、变化中形成的相互依存与融合的状态。
关于“御”,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中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整章就是对“无”做描述。“古之道”是什么?就是“无”。“无”比“有”要古老、深远、玄妙得多,所以很清楚,在无有叠加态的矛盾运动中,“无”是御者,要以无套有、以无御有,而不是倒过来。这是“无”“有”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规律。也就是说,“无”“有”之间的“反”,不是矛盾双方绝对均等的机械钟摆,而是存在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决定性、掌控性力量。老子把这个终极意义上的决定性、掌控性力量叫作“御”(具体地说,这个能够做终极掌控的“御者”,就是“无”)。应当说,近人在研究、讨论老子思想时,对“和”、对“反”比较注意了,说得比较多,但对“御”的认识是很不够的。没有“御”,无有叠加态就没有终极方向,没有魂。
到此,对于无有叠加态的矛盾运动,老子一共讲了三个字:和、反、御,串起来就是:和中有反,反中有御。这就是玄之又玄的无有叠套结构的内在运行规律,我把这个内在运行规律称之为“第三玄”。“第三玄”是“无之玄”与“有之玄”的相互关系,隐含于作为宇宙最基本矛盾关系的两玄之中,存在于由两玄作为细胞和基质构筑的其他一切形态的矛盾关系之中。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第三玄”即和、反、御运行规律的注脚:在芸芸万物生长并作的“和”里,老子看到有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存在—“复”(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反”)。“复”的循环周期运动,终归何处?终归其根;何为归根?归根曰静;何为静?静就是前面讲的虚极,也就是无。无,便是根本意义上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那个御者,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归结之处。老子说, 归于虚极,归于无,这就是复命,复命以致永恒(“常”)。
三
老子没有明确地提出“第三玄”的概念,但这个思想蕴含在他对“道”的全部论述中。“第三玄”是按照大自然的本性自由流动的,是和中有反、反中有御,化解一切单方面的执着,改变对立双方的僵硬立场。“第三玄”基于矛盾,但它是对矛盾对立关系的消解,是对矛盾双方和谐共存统一体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玄”是存在的桥,而不是四处挖沟的挖掘机,它使世界圆融贯通,往返无碍。
我们通常只有僵硬的两方:善和恶、美和丑、好和坏、上和下、活着和死亡……我们通常会执着、偏爱两方中的一方,强烈排斥、压制另一方。我们以为排斥、压制了矛盾对立双方的另一方,所执着、所偏爱的一方就能够更加强大。殊不知,这样的结果,只能使所执着、所偏爱的一方失去灵性,存在就僵化成尸体,变成标本。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恋尸癖爱好者,就是入殓师崇拜者。
二元对抗,极端化地厚此薄彼,造成画地为牢,失去自由空间。我们被各种二元对抗的概念所困。我们通常只有一条道可走,一直走到黑;我们没有“反”,没有“游”,没有“第三玄”。世界对于我们,变得日益狭隘、局促、困顿、刻板,寸步难行。
这恰是老子所忧。老子总是很担心相辅相成的对立面被破坏。他在《道德经》第二章中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用了这么多成对的概念来讲对立面不离不弃、相拥而舞的道理,然后在这个道理的基础上提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接着,他在第三章中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就是告诫人们不要人为地制造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以免造成片面、畸形、病态的发展。
老子是“第三玄”的。“第三玄”是在无和有、善和恶、美和丑、好和坏、上和下、活着和死亡等之间存在的,超越二元对抗,在二元之间自由地往返流动,所以说它是存在的桥。老子的“第三玄”将世界圆融贯通。这个世界,就复活了灵性,都活了。
我有时乐于把第三玄理解为“C哲学”,或曰“第三方”(观点)。所谓“C哲学”,即看待任何事物,不执着A,也不执着它的对立面B,而是在A和B之间往返流动,即“反”。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相拥而舞”。譬如,以量子理论来说,“C哲学”既不执着粒子本位,也不执着波本位,而是粒子与波叠加,是粒子与波之间的往返变化。反(C)不是实体,只是关系,是运动的节奏和韵律。
说“第三玄”是“第三方”(观点),这是进一步强调它对二分、二元思维的溶解作用。凡是有对立、对峙、对抗、分裂的地方,都可以用第三方来溶解。第三方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不是裁判,而是溶解剂。它溶解对立双方的执着。当对立双方的执着被溶解后,自己也随之溶解,因为它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只是回到整体。“第三方”是二元化世界的怀疑者、解构者和解放者,当然,也是捣乱者。它在结构深重的二元世界中不是怎么受欢迎的。二元世界愤愤地对它说:“你捣什么乱!你又不想争什么,你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到的东西、好不容易确定的东西打个稀碎,然后一走了之?!你天性就是来破坏的!”
“第三方”的本质是溶解剂,复原“道”原初的、整体的样子,所以,它其实是回到“一”,回到原点。
参考文献:
[1]南怀瑾. 老子他说[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4.
[2][4][5]老子著. 河上公, 王弼, 范应元注释. 名家集注道德经(册一)[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11:8、10、5.
[3][6]安继民, 高秀昌注释. 庄子[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53、233.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