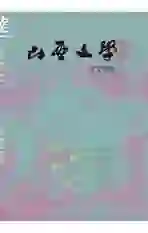在城市之光书店上课
2016-05-14祝大同
久居山西,和文学纠缠了大半辈子。退休以后,2012年夏,有机会到河南郑州一家民办大学教书。
2013年春季开学,教大三年级一个与影视文学有关的课程,搞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想对孩子们的影视文学基础有一点儿了解。孩子们多来自省城以外的地区,在中小城市或乡镇完成中小学教育,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这些孩子对于应试科目以外的知识几近于苍白。依我的标准,该看的没看过,该读的没读过。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多读一点儿书,开卷有益,无论将来干什么,多读书总没有害处。可是光在手机上读那些“盗墓笔记”、“大兵小将们的心灵鸡汤”怕是不行,总得读一点儿经典。那一年初来乍到,有一点儿生猛,还有一点儿热情,总有一点儿老天真。于是就想把班里的学生带进书店上堂课,对着书架,介绍一些近乎青年必读书样子的图书,具体明确,立竿见影。
于是就想到了城市之光书店。
多年习惯,喝一盏淡茶,翻几页闲书,书店就成了常常盘桓的地方。尤其是独立书店,如我们山西的尔雅,日久情深,以至于跟尔雅主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时,刚好有一本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书店之美》,副题“20家文化地标书店的精神向度”,介绍了全国20家民营书店,没有我们山西太原的尔雅,然而河南郑州的城市之光名列其中。
一到郑州,安顿下来,便去城市之光朝觐。
走进城市之光,便知道田原的《书店之美》20家文化地标之所以选入了城市之光,放弃了尔雅的道理。尔雅书店的店主人跟我说过,尔雅是全国单位面积营业额最高的书店,尔雅真的就是一座一心一意卖书的书店。然而,城市之光则不同。进门,迎面是收银台,两壁装饰着电影海报,一边的架子上是文艺调的明信片和笔记本,空间尽管窄仄,却罩在浓浓的艺术沙龙的韵味里。
顺着黑白两色的楼梯走上去,记得在楼梯的转角处推荐的是麦克尤恩,而麦克尤恩的处女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是我那一阵子非常喜欢的。上到二层便是平面陈列的推荐图书,第一眼看到藏蓝精装的《保罗·策兰诗选》。保罗·策兰是我景仰的诗人,我还清楚记得北岛《保罗·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的结尾一节,1970年晚春策兰投河而死,“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之中,……”让我惊讶的是,《保罗·策兰诗选》居然夸张地摆着一大摞,一二十本不止。我有些狐疑是店家的固执,还是河南郑州居然就有那么多人购买保罗·策兰,真的有吗?后来,我才知道,店家以为《保罗·策兰诗选》特异地小众,不会有再版的机会,所以多备一些,以期提供给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未来的读者。东西南北,四围是书,量并不大,应该册册都是经过主人精选的经典。冒昧地说,有一点儿小号万圣书园的意思,透着一股子高冷的范儿。东面有一处凹进墙面的小舞台,周末的晚上会有民谣歌者浅吟或细语。几年以后,我在这里欣赏过一场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利奥·福的小戏剧《开放夫妻》。书城的中央留有一片池座,布置了桌椅沙发,还有一处吧台和土耳其壶煮的云南小粒咖啡。
身陷其中,我会有一点点迷茫,远远看着店主人开哥和郑姐,哥儿清癯,姐儿娇小,哥儿姐儿衣着举止举手投足透着倜傥放逸的洒脱,在一个金钱与权力喧嚣的时代,在这里竟然嗅不到一丝一缕呛人的烟火气。那天,空气中影影绰绰地弥漫了莱昂纳多·科恩若有若无的吟唱,便隐约可以捉摸了城市之光的精神向度,让我这个客居异乡的旅人恍惚间有了归家的感觉。
去了城市之光,找到了店主人开哥,说明了我的企图。开哥毫不含糊明确地表扬了我,赞同我的想法,对于这件事情甚至似乎有一点儿期待了很久的神情。开哥的鼓励,让我平添了许多信心。我知道学校不可能给出任何费用,上午的课,书店还要提早开门,给书店添许多麻烦,开哥不但不嫌麻烦,而且推荐由郑姐介绍外国文学图书部分。郑姐欣然允诺。
于是,2013年3月11至15日,星期一到星期五,三个下午,两个上午,每次3个小时,在城市之光书店二层,我从楼梯入口处平面陈列的图书讲起,到南面临窗的几排书架,影视戏剧,哲学历史,中国文学,蜻蜓点水,一掠而过。郑姐则介绍整面西侧书架上的外国文学。郑姐那年春天理了短短的头发,如少年一般,那几日常穿一件洗尽铅华的博柏利经典格子衬衫,潇洒睿智。我猜想郑姐虽然出身山东大学中文系,但在外国文学上面多有用心,尤其是现当代的欧美文学,对近些年来中国出版界译介外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如数家珍。而且郑姐应该有极好的西学学养,讲到一些西方文学的经典著作会给同学比较不同版本译笔的优劣。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对不住郑姐,到了后两天,这种愧疚甚至变成有些惶惶然的忐忑。这五天,无论对于郑姐还是城市之光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回馈。虽然一连三个钟头苦口婆心介绍了那些对于我和郑姐以为都是值得一读的经典,但是能够从书架带走一册两册的同学其实寥寥无几。私下,我和同学们说,我们无来由地给城市之光带去许多麻烦,无以回报,希望同学用手机拍几张照片发发微博,也算给书店做一点儿推广,响应的同学也并不如我希望得多。至于,在这些孩子们中间可以有多少内心的回应,我就更不敢去揣度了。但是,郑姐依旧充满热情,从法国的尤瑟纳尔开始,英国的麦克尤恩,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德国的聚斯金德,最后转到南侧书架,日本的川端康成,甚至还有那些年轻的芥川奖获奖作家,如我也喜欢的青山七惠。每次结束以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同学围上去和郑姐交流,我看到郑姐似乎也在享受这种交流,让我惶惶然的心稍稍能有些平复。
《观念的水位》的作者刘瑜说过:“我有时候经常会在想,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曾经成功的说服过一个人吗?我觉得好像都没有。我的意思说什么?就是很多时候你看似你说服的人,其实他本来就是同意你的,或者是那种本来就没有什么观点,他可能本来就在一个灰色地带里面,你那么一转就过来了。”刘瑜的这种经验让我沮丧,却也让我鼓舞。我们或许真的不能说服一个人,或者真的不能改变一个人,但是肯定还有尚在懵懂之中,或者如刘瑜所说尚在灰色地带里面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指引,给他们那么一转。
离开自己虽然简陋却也还舒适山西太原的家,到河南郑州这所民办三本的学校里教书,住筒子楼,用公共厕所,还常常有人便后不冲,除了自己一些或明或暗不明不白的理由,渴望遭遇可教的孺子,救一人胜造七级浮屠,大概是我内心最大的期待。我想这也是开哥和郑姐逆流而上撑着这间城市之光书店的心情吧。
我在豆瓣上读到了城市之光书店十年前写下来的文字:
如同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一样,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流浪,寻找爱情,寻找梦想,生活中却充满了浮躁、不安和紧张,这些情绪如同梦魇与每一个城市人紧紧相随。在一个阴郁的下午,放下心情,喝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这世界的纷扰仿佛也变得遥远了。书店,是城市的一个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提供阅读、聆听与交流,在精神层面它承载着与另一个世界的出口。作为垮掉的一代的发源地的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代表着自由、平等、先锋的生活理念,我们的城市之光书店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梦想。与城市之光的相遇,就好像与一种生活方式的相遇。
十年,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长成一个打酱油的少年。十年,不算太长,也不能算太短,可是这十年对中国书业却是风云激变的十年。城市之光不忘初衷,在晦暗不明的夜晚为我们守着一盏灯,煮一杯清咖啡,备一册寄放魂灵的书,守着一个信念,守着一个梦想,谢谢城市之光,谢谢。
祝大同,1951年生,江苏句容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深蓝色的日子》《偶尔,会绝望》等。